- 12
- +1600
荒草地:村里的“快乐酒徒”,变老了|镜相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 | 抱布
编辑 | 柳逸
(澎湃新闻·镜相工作室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夕阳照在一片田垄上,是鸡蛋黄的一抹。鸡蛋黄投射在我家门口那块菜园子地上,园子里种满各式冬季蔬菜。在园的另一边,则是长满半人高蒿草的荒草地,在寒风中特有一种荒凉意味。两块地的交接处,野草的枝干伸到了我菜园子里来,有许多被母亲折枝除掉了。于是草与菜各自生长,遥相呼应,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片风景。
荒草地与我家的菜园子中间,原有一堵石灰石堆成的矮墙,作为两块地的区隔界限。农民对土地所属权的观念非常强烈,一旦确定了是自家的地,就做些明显的区隔,以免日后不清不楚而起争议。
界限这边是我家的地,界限外那边是邻家的地。

荒草地(作者供图)
二十年前,这两块地是反着长的。因家庭生活兵荒马乱,没人打理,我家的地常荒着,长满草橛子。石灰墙外邻居家的那块地却是充满生机的,一年里总是地尽其用,在春天种上了黄豆,在夏天里收豆翻地,在秋天种上了红薯。
打理那地的,是邻居家的一个女人时婶,她常常一边浇地或除草,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
后来不知是哪一家在石灰墙边插种上了一溜“臭花”苗,此花因散发难以名状之气味而得名。其实“臭花”有个雅名,叫五色梅,这种植物很贱霸,极快地就长成了一道天然植物篱笆,把那石灰墙形成的界限进一步加强了。
五色梅一年四季都开花,花瓣不止一种颜色,呈细喇叭状,被我们这些孩子一瓣瓣揪下来,头尾相接做成一条手链。
时婶常常一边浇地除草,一边和对面的我家祖母拉着家常。等到祖母走了,她便时常地问着我的话。虽然我才十三四岁,但是已经能少年老成地应和大人的话。
这样过了三五年,渐渐地,在五色梅篱笆的两块地之间就很少发生对话了。
因为时婶害病走了,那块春天种黄豆、秋天植红薯的地从此无人打理。时婶的三个女儿早早辍学出城打工去了,这一家里就剩下她的丈夫,一个五十开外的大叔,大家都叫他乌力。
我们的邻居乌力是个神奇的人,他长得高大强壮,爱喝酒,愿意结交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当乌力坐在客厅里与父亲喝酒的时候,总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信息。“只是出不去,要有文化出得去,城里遍地是黄金,只消低头拣。”有时他把这些话用一种略夸张而自黑的方式说出来,常惹得我们大笑。
也就是说,乌力是一个乐观而具幽默感的酒徒。这样的人,在村人眼中多少是不正经的,比如他描述自己和时婶新婚时的情形:“那还用说的,我可是从头发顶亲到了脚趾头!”惹得众人大笑。
男人如此地在外面稀罕自己的女人,在村里虽称不上惊世骇俗,也是极其少见。然而乌力从不像个安分守己的农民那样活着。
他不仅言谈上大胆,行动上也特立独行。时婶嫁给乌力后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生完第三个时,追结扎的公家人来到了乌力的家,让夫妇两人到镇上去做结扎手术。根据当时的政策,如果不配合就要受到惩罚,比如被搬去家里的家具等用品。乌力当时的家里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他还是毅然地做了决定,让时婶到镇上去结扎。
人们也有劝的,“再躲躲,说不定下一个就是了呢。”“那点家私值多少钱呢?”可乌力并不那么认为。女儿怎么了?也一样养。夫妻二人随后到镇上去做了结扎。等到他们回来,人们不再说什么,可是肚子里还在嘀咕着。
乌力很爱自己的三个女儿,叫她们“阿崽”。这是一种对孩子宠溺的称谓,相当于都市中“宝贝”的称呼。这三个女儿很快长大,个个都出落得婷婷袅袅。尤其是大女儿大美,身子纤细,面容甜美,声音清韵。只可惜只读完小学,便跟着村里打工的队伍到特区去了。去后不久,便开始给家里寄钱回来。到了后来,大美成了乌力的骄傲,每次酒后总要在别人面前夸耀一番。
我父亲的行动常常是落寞而散漫的,因此不知道是乌力寻着了父亲,还是父亲寻着了乌力,总之两个人混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有点多。
乌力与父亲每喝酒,必定要做点好吃的。他的厨艺无疑是出色的,炒菜的架势如同他的性格本身,挥挥洒洒。他尤其喜欢炒猪大肠下酒,大肠先用盐腌起来,再用手抓一遍,翻过来,反复地冲洗。等锅里的油烧得滚烫,乌力把洗净切好的大肠一扬手撒进锅中,一顿翻炒,再淋上生粉水,撒入胡椒粉,香味一出来就起锅。“活要干净,火候要到,配料要足,别人炒的猪大肠我从来不沾!”
有时到了半夜,父亲依然没有回家。我睡得半迷糊,被卧室外间白色的灯光刺醒,同时听到父亲与乌力两人大声说话的声音。父亲与乌力一边斟着酒,一边剥蛋吃。见我过来,乌力递给我一个蛋。剥开一看,里面的蛋黄还有些流溢,深黄一坨,没有熟透,我犹豫着不敢下嘴。“蛋要八分熟才好吃,营养高。”乌力的话是极其渲染性的,我终于戒除了不敢吃的心理,一边听乌力讲着许多轶事。
原来大美在城里打工的工厂车间里表现不错,很快就做上了主管,工资升了不少。乌力还有意无意透露出开小轿车的厂长儿子追大美的讯息。父亲是古板的,他听着乌力说这些,并不发议论。我是有极大兴趣地张耳听,不时还要问几句。父亲便呵斥:“还不快去睡!”

第二天,我看见时婶一个人在对面的地里锄草,耕种。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乌力已经不愿意出来种地了。“种地穷一世。”他说。
乌力家在村里先富了起来,最鲜明的标志,就是盖起了一栋两层高的白色瓷砖楼房。房子封顶的那一天,我放学经过,见几乎全村的劳力都聚在了乌力家,筛沙子的筛沙子,活水泥的活水泥,担砖头的担砖头,一个个满头大汗地为乌力家的新房子出力。乌力在一旁端茶递水,脸黑而红着,一边又聊到了大美。盖房的钱自然是她寄回的。
新房子建起来以后,乌力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跟着大美出城打工了。崭新的房子里只剩乌力与时婶两人居住。
乌力家新房子的外墙贴满白色瓷片,在一片灰扑扑的农村房子中,格外引人瞩目。从村外回来的人,远远地在村口望一眼,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栋白房子。乌力与时婶住在一楼,进门左手边第一间房子,他们还在房间里装上了电话机。
我们家没有装电话机,彼时外出打工的母亲常把电话打到乌力家。每有电话来,时婶便扯开嗓子朝我家叫喊。我听到喊声,匆匆跑去,进门的那一刻却有些犹豫,好像一个乡下人进入一个新房子是一个突兀的存在。我径直走到乌力和时婶的卧室里,听完电话就飞快地跑了出去。
他们家二楼在我看来更是一个梦幻,那地板铺着锃亮的瓷砖,墙壁刷得雪白,贴满各色明星海报。每间房的门口,都挂着一幕珠帘,珠子轻轻摇曳,如同大美姐妹三人般烂漫。二楼平时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才得以到那宫殿般的地方坐坐。大美从桌上宝气的水果托盘里抓起一把白鸽糖果递过来,气若吐兰地问我:“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我便感到被关注的紧张与荣耀。
乌力家的新年热热闹闹的。打工的青年们来串门,坐在二楼的红沙发上,观看着CD机里传唱出各类新年贺岁歌,一片喜乐洋洋。有时候播放最新出的港产武打片子,那是和过去的战争片大不相同的解构狂欢美学,尤其令年轻人着迷。
某一年的春节,乌力家异常热闹。我隐隐约约听得时婶给大美姐介绍了一个邻镇的青年,定了年初四那天相看。左邻右舍都在议论着这个事儿,不知是哪位有福的后生。
然而到了初四那天傍晚,乌力醉醺醺地来到我家。
他在厅里与父亲闲聊,一边诉说着刚刚与时婶大吵一架的情形。乌力剥开一粒花生,抛物线一样送进嘴,眼却盯着我家开着的电视机屏幕道:“这女人真正是头发长,见识短,它老母个×,她说那男的愿意上门哇!”
“那不正好么?”父亲斟了茶回应他。
乌力把花生粒在嘴里咬得“咯嘣”响,然后抿一口茶,道:“没用的!美崽出去这几年刚有点出息,你说这又弄回来。没用的。”
“时姐也是为以后打算,总得老了有个依靠。”父亲劝解道。
“不用靠,靠啥靠得住!我看得很淡,老了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就是了。”
想不到“两腿一伸”先走的那个不是乌力,却是时婶。
正在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时婶却被诊断出得了尿毒症。那时得尿毒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人来说就相当判了死刑。
时婶走时,女儿们一个哭得两眼红肿如桃。乌力却静默地,没怎么哭,也不跟人说话。电话机旁的那张属于他和时婶的床铺被剥去了帐幔和被单,显得凌乱不堪。那一切都随着旧人化作了一缕白烟。乌力怔怔地望着这一切,仿佛一个久睡的人没有醒转过来。大美红着眼睛,走到二楼抱来了一床新的被褥,帮乌力把床铺重新整理了一番。
大美第一次发现,强壮高大的父亲矮了许多,坐在床边就像一堵小山。
时婶走后的第七天,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三个女儿都要离家,再不走就要丢了城里的工作。大美因为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便多请了两天假留下来陪着乌力。乌力却对她说:“做你的事去,不用管我。”“阿爸跟我到城里去住一段吧”
就这样,乌力跟着大美来到了城里,为了陪父亲,大美特地从厂里的宿舍搬了出来,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
在乌力日后的叙述中,那次进城变成一次“进城奇遇记”。他描述大美带着他游览世界之窗、逛地王大厦时的情形,那世界的奇观以微缩的形式来到眼前带给他的惊诧,那站在近百层的高楼大厦下感到的目眩神晕。乌力没有描述的是另一面。他看着大美每天早早出去,很晚才回来。这时的大美早已从以前上班的玩具厂离职,和曾经开着轿车追求的富家公子也似乎没有了什么联系。据说是对方的家庭不满她的学历。这时的大美在一家香港人开的贸易公司里上班,只有排到调休时,才有时间带乌力到处去转转。
在城里待了半年后,乌力终于因为无法忍受城市的枯燥无味,再次回到了村里。从那以后,他开始一个人住在这栋白色的房子里度日。
他偶尔还找父亲喝酒,喝多了,开始说着另一套话:“阿美真是实心眼,让她回老家来找个人家,竟不肯。”那时的大美应该已快到三十岁,在村里人看来是老姑娘了。时婶走了以后,两个小女儿反而很快地谈了恋爱,早早地走入了婚姻。只有大美还迟迟没有动静。乌力有点闹不清这个大女儿的想法。
去了城里半年的乌力,似乎从失去时婶的打击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再次变回过去那个乐观的酒徒,但似乎又与从前的他不一样。当他把花生剥开,抛物线一样扔进嘴里的时候,目光常常盯着前面的电视屏幕。屏幕上有时候正放着古装剧,更多的时候是一些美食节目,甚至是动画片。当看到节目上的厨师在烹煮一道宫爆鸡丁时,他便对人说,今晚特码出“蛇”,蛇吃鸡嘛。这类节目在那几年的收视率奇高,观众们如乌力一样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想象能力,从平常无奇的现象中发现某种隐秘的关联。一道家常菜可能隐藏着某个特码,在动画片里猫追老鼠的游戏也能被解读一番。

乌力留在房间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在过去那间他和妻子居住的有电话机的一楼卧室里,做了一道暗色窗帘,拉上以后常常分不清白天黑夜。乌力有时候坐在屏幕前直到深夜,第二天醒来已是正午,在梦与醒之间寻到厨房里弄点吃的,找一点酒,很快又缩进了那房间里。
我偶尔从他家经过,能听见里面传出“沙沙”响的电视声。
极少数的日子里,他像个穴居动物一样走出那间大,迷蒙着双眼在村里晃一晃。有时候晃到我们家,与父亲聊完再次猜错的特码,便是骂着娘。最后,他聊到了自己的失眠。
父亲劝他把重新把那些屋前屋后的田地种起来,荒着可惜了。
但乌力否定了这建议。
“人生短短几十年,还要像阿时一样做到死么?不值当啊。”顿了顿,又说:“我反正也是断子绝孙的命,做那么多来干什么?不值当。有吃吃,有喝喝!”说完端起手中的酒杯饮尽了那酒,呵呵一笑。
后来,乌力从外头带回一个比他年轻些的女人,据说是个寡妇。他恢复了一点过去的挥洒,从不见天日般的卧室里出来的时候多了,每天一大早骑着摩托出去镇街上买菜。有时还和别人说到那女人如何稀罕着他。
大美姐妹自然很快知道了乌力带女人回家的事,意见一致地表达了反对。因为她们每月打到父亲账上的钱用得很快,从而感到了可惊的压力。在大美的追问下,乌力才透露那女人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每个星期去学校的时候要给的伙食费正是乌力这里掏的。
有两个月,女儿们没有再打钱过来。
乌力和那寡妇便常常锁在卧室里,电视机的声音重新沙沙响了起来。有时候,乌力看中的特码和女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两人还会吵几句。有一次我从窗下过,听到一两声我不该听到的声响,红着脸快快走了开去。
寡妇到后来还是走了。在那之后,乌力又不间断地带回过一些女人,都像露水夫妻一样,过一段日子就断了往来。根据乌力酒醉后的描述,他和那些不知从哪儿来的女人们不是抱睡在一起,就是爬起来看电视猜特码。他出来活动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高谈阔论,但身体比以前肥胖多了,谈到激动处,脸色涨红,像只庞大的发情动物。
自从乌力开始带女人回家,父亲和他的交往就少了,大美姐妹也极少回家。过了两年,大美回到家乡,和一个离异带着孩子的男人结了婚。
十多年过去,乌力再也带不动女人了。他依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屋后的耕地长满了野草,甚至种了几棵大的桉树。桉树生长速度很疯狂,不几年便遮天蔽地,到了秋冬,摇一地的碎叶和种子。有时候到某个地方去,不得不穿过那几地时,便沾满一身草橛子。一个冬天的夜里,乌力醉醺醺地回来,桉树刮起了一阵风,把不知什么东西撞得咚咚响。乌力在屋角小解时不禁打了个寒噤。“阿时,你回就回,可不要吓我。”他后来声称,确信自己在那一刻见到了死去多年的妻子。

村里的屋子和猫(作者供图)
春节我回到村里,在路上碰见了乌力,几乎快认不出这个当年谈笑风生的老酒鬼了。他的身子明显地矮缩了下去,像一堆泥裹在灰扑扑的大衣里。也许是长期不见光的缘故,眉毛和头发竟也有些花白。尽管如此,他还能踩着电动摩托出去买菜。
他已经不住一楼那间卧室了,连电视机都淘汰了,搬进了过去女儿居住的二楼。大美回家探亲时,给乌力买了一部华为手机,他很快就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号,取名快意人生,头像是一张戴着墨镜、脖颈处挂着粗黄金项链的男人。快意人生常常给父亲的微信分享各种各样的视频,我有时候帮父亲清理手机信息,无意中点开那些视频,马上便传来一阵煽情的音乐和少妇舞蹈,还有一些是劝世良言类的视频。
快意人生在村里的大群也异常地活跃,村里大部分的人已经住进了城里,但在这个虚拟的微信群中,大家似乎又重新找回了乡音和过去的亲昵。哪家娶亲建房有好事了,便在群里发个电子喜帖。每当这时候,快意人生便热络地同人攀谈起来。他有时也会把那些视频发到群里。母亲节那天,群里有人发了两个视频,妇女们晒儿女的礼物。村里人过节也与时俱进了。乌力也来凑热闹,他自拍了一个视频传上去,在那个视频里,人们看见一个光着半个身子的老汉,将镜头从自己那张大脸开始推移,将整个屋内移了一圈,最后落在墙上的一张静穆的遗照上——一“你们是不知,今日是母亲节咩?”
群里没有任何回应,都认为他发错了信息。
乌力有些疯疯癫癫起来。他有时带着貌似欢乐的情绪,甚至有几分醉意,在群里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人生嘛,最重要是快乐。祝大家人生幸福。”有时又突然怨怼一番。
一次,群里有个年轻人不会说话,接了一句“有国家养真好”,暗指乌力领低保的事。乌力马上反击一通:“你们呢?哪一个不是国家养的吗?”
他说开了头,滔滔不绝起来。“噢哟,讲起来我惭愧呢,没生得儿子呢。你们呢,养得大把阿仔,赚得大把钱,好像认为低保没啥意思呢。你知不知,我日日打针呢......”
因为患了通风,乌力的双腿走路一瘸一瘸的,经常进出医院,自称和医生护士都已经混得熟了。打几天针,舒服一些,他出来继续喝酒。那天他再次坐上我家酒桌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是大美那一如既往的担忧和嘱咐。乌力哄着电话那边说:“好咯,阿崽。喝不多,喝不多。”
一天,村干部把生态林的补偿方案发到了微信群,引来了一波议论。部分早期出城的村人不太满意现有的分配补偿方案。
乌力听了,开始大发牢骚:“祖国的山河是你家的么?可不要乱讲!说到土地,村里谁有我清?村口大塘都被整去了,你们如今过意得去么?生产队分田哪一家又没分到?年轻人有几个知?如今你们有了钱就看不起乌力。补偿款开会怎就没有通知我?我不是这个村的不成?我以上说的可不是什么好话,大家好自为之。祝大家平安,每一家平安。”
乌力七十多岁,他现在说话常常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自居了。
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树不知什么时候被雷打了枝头,枯萎下去。因为这块地多年没有耕种,父亲曾试图说下这块地,借过来一起种上青菜。这个提议却遭到了乌力弟弟的强烈反对,甚至跑来大闹了一通。人人都知道,现在农村的土地又开始值钱了。近两年,村里的土地进行了新一轮的确权,并在确权后给每家发了新的田证。乌力家的那些地自然也在确权之内。
春节时,乌力的三个女儿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回到村里来看望她们的父亲。荒草地上的一棵桉树不知什么时候被雷打了枝头,枯萎下去。大美带着六岁的儿子回来村里,央人把荒草地上枯萎的桉树锯断,视野一下开阔许多。几只蜜蜂在草丛中钻来钻去,在人间的某一个春天里,乌力却老了许多。大美回城前还说,要把这些地翻整出来,做孩子周末研学体验的实验田。
乌力柱着一根拐,坐在屋门口,眯起眼望着女儿汽车离去时扬起的一阵烟雾。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人物乌力、大美均为化名。)

镜相栏目此前发布【铭刻“小地方”长期主题征稿】,本篇独家作品为此次征稿的优秀作品,征稿持续进行中,欢迎各位优秀非虚构写作者的加入,征稿详情见海报或【点击此处】跳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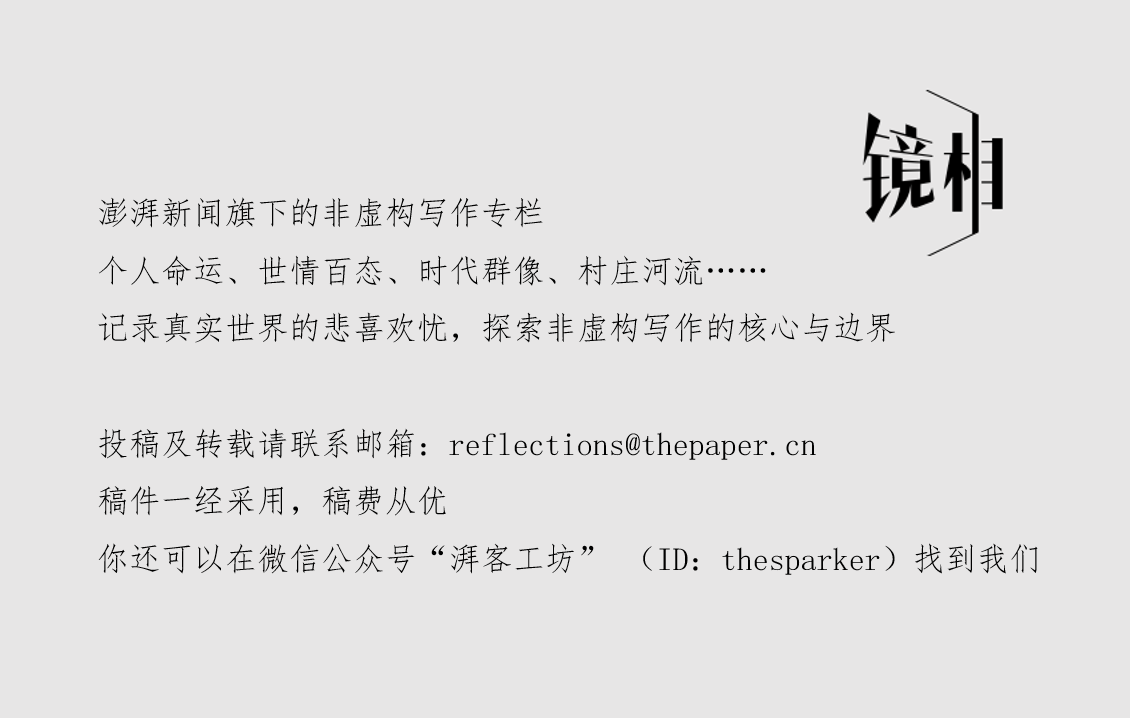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 解读|王毅三天密集会见日方官员
- 国足多人伤停低调备战澳大利亚

- 商络电子:公司为小米眼镜间接供应被动器件和射频器件等产品
- 最高可贷5000万元,金融助企稳岗扩岗力度加大

- 人体红细胞中,携带氧气的主要物质
- 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氧气和什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