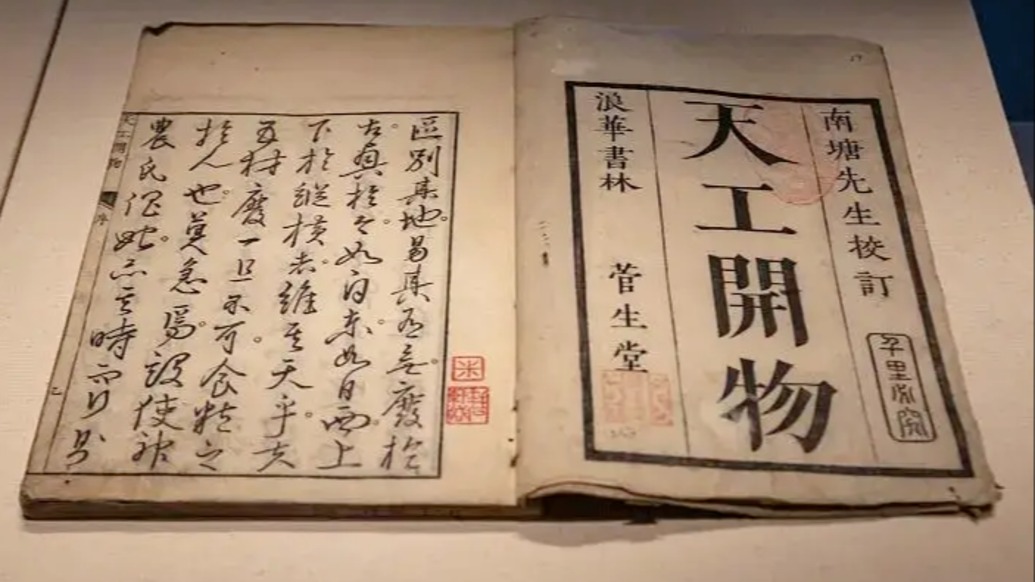- +152
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④︱圆桌:跑田野,要有思想上的问题和架构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圆桌交流
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对话
学员:我目前是研究生二年级,在构思论文架构。通过研习营的学习,对研究观念有所冲击,之前对于论文的构思是对于一个人物身份的定位,但是并不清楚如何判断。但是,听过冯老师关于社团及参与其中的人的活动的演讲;贺老师对近代工人身份建构的演讲后,意识到解读历史材料时,应该敢于质疑和挖掘文字记录没有告诉我们的东西。这是对于自己的冲击。对于张乐天老师关于书信研究的演讲也非常有感触,人的多样性的体现,而不是以好坏的二元对立标准来评价人物。
科大卫:你能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对于开展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类的名词来描述人,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但其实都是同一个人,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人有时会伪装成好人,有时又扮成坏人不是很正常的事么?
学员:我在参加研习营之前虽然阅读了很多综述,还是不知道历史人类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参加研习营之后仍然无法确切的明白历史人类学的旨趣。通过几天的会议学习,头脑中仍然缠绕着很多疑问和概念。
科大卫:我相信你的疑惑在于对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和概念有所期待,但是历史人类学恰恰是最反对下定义的。我如果给历史人类学下了定义,就会被萧老师指正不是一个人类学者。我认为历史人类学等名词不过是标签,是被人拿来用的。你不应该去追究这个名词的定义,更好的做法是在研习营的几天时间里,思考学者们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名词,并观察使用这个名词的学者们在做什么事情,怎么做。到这一步,就不是由老师来告诉你们历史人类学是什么意思,而是你们通过观察告诉老师们,历史人类学是在做什么。
萧凤霞:历史学家做田野调查,很可能与大家认为的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同。但实际上,历史学家进行田野调查是有历史根源的,比如法国的年鉴学派,欧洲的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也给我们很多启发。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假的”历史学者,他(科老师)是一个“假的”人类学者,但是两个假,加起来就是很真的(学问)。因此,“真的”在哪里,这完全是一种阐释(interpretation)。另外,做田野不是记录下来人们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人们怎么说的。
学员: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天跑田野的时候,看到了外滩是很现代化,很高档的,没有不卫生或者人群杂乱的区域;但是到了城隍庙的市场,则是非常混杂的,出售的商品也不是很高档,与我家乡所在的小城市的市场非常相像。我认为这种市场是一个从明清到现代过度的一种市场形态,我不知道这些小市场的最终归宿是不是像外滩那样形态的市场?
科大卫:我希望学员可以找一些上海外滩的老照片来看。现在看到的外滩地点是十九世纪(形成的),但形态景观不是十九世纪的。如果看到老照片会发现当时外滩的建筑物都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没有那么宏伟,当时的建筑技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到某一个时候,很多大城市,大银行开始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上海也跟上了那个潮流。城隍庙是十九世纪的建筑风格,但是外滩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建筑风格,要比较的话,应该要看看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外滩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
萧凤霞:我们总是以为城市有一个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但是,发展这个概念本身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发展?(城市中)发展了什么?农民也好,城中村也好,我们自己看外滩也好,看到什么是所谓的发展?我们是如何对待这个概念的?(How do we engage with that concept)很多时候,那些概念都是我们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就如张乐天老师提到的,我们看到把城市与农村放在一起,就觉得农村更乱、更落后,这些都是过往一些直线型的思维方式。可是,当我们用历史学和人类学去理解,便可以对原有的直线型思维方式进行挑战,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因此当你观察事物,不要把他们二元对立起来,即便是外滩、石库门、田子坊这些今天看到的景象,都是不同年代、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创造出来的。如此看待问题的话,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野则会变得丰富,看到的“人”也会变得丰满起来。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
学员:正如老师所说,跟访谈对象聊天,最重要的不是他讲的内容,而是他如何表达,以及他没有表达的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以一个“上帝视角”去听和看访谈对象?如何去发现访谈对象“未言说”的内容?
科大卫:其实访谈对象已经表达了,只是你没有接收到。
张乐天:在田子坊的访谈说明,对访谈对象的了解不能仅局限于访谈,还需要接触他的生活。
学员:我的困惑在于如果想要了解某段历史,但是当时人已经故去,没有办法做访谈的时候,要怎么办?
科大卫:我想回应你提到如何访谈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我最初在香港新界做田野,从当时的访谈中了解到明朝的情况。我认为,访谈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术。我们大部分人很喜欢讲话,但不懂听人家讲话。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训练当中,我们没有特别懂得听别人讲话。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两天田野考察的访谈只是一个例子。试想一下,当你跟别人谈话,他又不认识你,他真的会跟你讲很多话吗?我想不会的。当你需要与他人访谈的时候,他也在观察你,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因此你需要让他跟你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去培养出来的,这也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因此,访谈是一门需要学习和训练的技术。
学员:我在这两天捕抓到一些细节,我就是到处拍沿街的水龙头和吊扇,因为我想通过一些细节去思考上海民众的生活状态,比如说他们用的水龙头跟我们用的很不一样,他们用的比较多是旧式的水龙头。再比如书信,就像张老师所说对于史料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通过族谱、书信和墓地来整合我的材料。因为我一直很相信科老师的一句话,所有材料都不是完全真的,都需要去不停的整合。
科大卫:我没有说所有资料都不完全是真的,我说所有资料都不是真的。但是你要知道张乐天老师的收藏,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们非常感谢他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去收藏这批资料,里面真的有很多宝贝是可以挖掘的。
学员:我谈两点启发。第一,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贯通的。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到田子坊的故事,就可以看到基层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以及文化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对于访谈的理解。之前我向程美宝老师请教,她提到一定要进入访谈对象的世界,要跟他们做朋友,要去理解他们生活的世界。我几天也一直在不停的反思,虽然跟我的访谈对象相处了一年多,但是一直跟他们有一个很强的隔阂感和距离感,所以我会以后慢慢去摸索如何更好的访谈。
学员:我想讲这几天印象最深的两点,我是读文学的,虽然也在关注历史,但我最大问题就是我无法进入历史场景去理解。即便以前老师不断解说,让我把历史放回历史场景,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一次听到贺喜老师和张乐天老师的讲座之后,我就发现,我们解读文本,想通过这些文本来理解当时人的生活,但是其实这些文本上的那些词,我并不理解,甚至会用我自己的经验和概念去套用,但这与文本上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张老师提到的那些民间书信让我触动特别大。
科大卫:你需要开始认得文本。当他们讲故事的时候,是用某种文本来讲故事,你需要认得文本是哪个时代的,然后文本之外,再看看有什么故事,这是我们要做的事。你开始能了解到文本的变化就非常好了。
萧凤霞:讲到文本,我年轻的时候编过的两本文学的书。当我1970年代刚去农村,充满革命的热情,看到外国的都视为是西方的东西。当我来到农村,老农民问了我一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他问:我们只是农民,你为什么对我们有兴趣?这是一个从田野观察到的标签。同时,我把目光投向从1930年代到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看看他们怎么去看农民。从文学的角度,字里行间也能触摸这段历史。
圆桌总结
科大卫: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名词。
历史人类学,只是一个名词。干什么事呢?我们说:不能就是读书,要去跑田野。为什么跑田野?第一天的时候,贺喜老师说了四个理由。第一,起码知道当地的地理环境是怎么样子的。第二,你需要对这个地方有感情。第三,需要去见地方上的人,去学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感情,看他们做的事。第四点才是你们这几天你们都以为你们要干的事情——找资料。当地还有很多资料,有文献的,也有实物的,这必然是我们要找的,但并不是你的头一个目的。只有把这几个东西拼起来,才能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去跑田野。
去跟人家谈话,去跑地方,需要有个思想上的架构。我是历史学者,我的架构很多时候是个历史的架构。历史是讲故事的学科,故事有头有尾的,历史学者的功夫就是说清楚这个从头到尾故事怎样演变。我们昨天不是去了龙华寺?张伟然替我们讲这个地方原来是怎样的,河道在哪里,也因此龙华塔有了灯塔的作用。他也说,城里面还有其他佛寺。我昨天晚上回去真的翻了地方志,发现以前真的曾有很多个寺在这个河边。从宋元一直到明初,江南很多地方都是佛寺的世界啊,它们是最明显的建筑物。至于寺庙那个前面那条街,一年开两次那个香市,赚到的钱怎么分配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只有留个疑问。还有,到了明代 ,倭寇来了,你想想,当地怎样搞防卫。小小上海县城的地方官,到哪个时候,才会有一点动力,在地方与政府之间,我们就能看到社会出来了。还有一点,清末有个军工厂,你有没想到辛亥那一年,那些地方会是怎么样?在有人要起义的时候,有多少人要去这些地方抢那些军火?这肯定是很紧张的地方,整个历史好像就在你的面前。

然后,我们去了老城。老城有很多好地方,但其中城隍庙,对我最有启发。我们走到豫园,冯筱才老师跟我说:“每天定那个粮米价钱那批人就在里面。”我是一页一页地翻过《北华捷报》三遍的人,它是上海的报纸。《北华捷报》是有米价报道的,当时的米价是如何确定的?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豫园)。它这是商人的总部,是金融中心,是当时股票的中心,但是旁边就是城隍庙。可以想象,这里面的人每年要怎样去城隍庙去拜,城隍庙是政府制定的制度,地方官也要去这里拜祭,你马上可以联想到情况是怎样的!就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上海老城社会重要的一角。
再走下去就到了民国时候,我们在田野中看到“大上海计划”的痕迹。很幸运的是听了刘刚教授的演讲,对我启发很大:他讲了一点,和萧凤霞老师讲的也有密切关系。他给我们看了一张一张的房屋登记图,里面是有号码的。我有个同事(张瑞威教授)是研究土地登记的历史,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基本上1800年以前全世界都没有绘出这些登记图的三角测量技术。后来英国人介绍到印度,再介绍到香港、上海;日本人也把它用到台湾。三角测量的地图与我们明清时代的鱼鳞图册不同。鱼鳞图册是不能准确告诉您一块地是在哪里的。到了有这种新的地图,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注明每一块地的地点与边界。把这块地编上号码,城市里的每一个单位才开始有产权。刘刚老师把上海和青岛作比较,上海一直保留了原来的产权,但是,德国人在青岛把土地都收购了,政府再分出来,没有原来居民产权的问题。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产权问题时,也想像德国人一样搞这一套,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界或老城搞。所以,大上海计划只可以在离开热闹的城市中心很远的地方实现。我以前都看过大上海计划建筑物的照片,感觉过它们是那么宏伟的,但是,透过金大陆老师多次和我们讲的情况,我现在知道, 那时候这些建筑建成的时候,周围都是荒地。昨天下午也走过了田子坊 ,可以看到一直到今天不同的时代如何面对新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产权”的问题那么重要,有不同的产权,就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就有不同的人在博弈。跑了这两天的田野就知道,可以看见,原来开发商对一个城市的历史有多么大的影响。政府当然更愿意去和开发商谈判,和一群人相比,和一个人谈判更容易。但政府要冒很大的风险:开发商的眼光是很短的,他要赚钱的,两年把房子卖完就跑了,接下来环境的问题、用电的问题、交通的问题,都是需要政府来处理的。现在政府要面对这些事也不好处理。
我们也不要只是停在上海,程美宝老师也谈到了广州的情况,尤其是声音对城市的影响。我们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