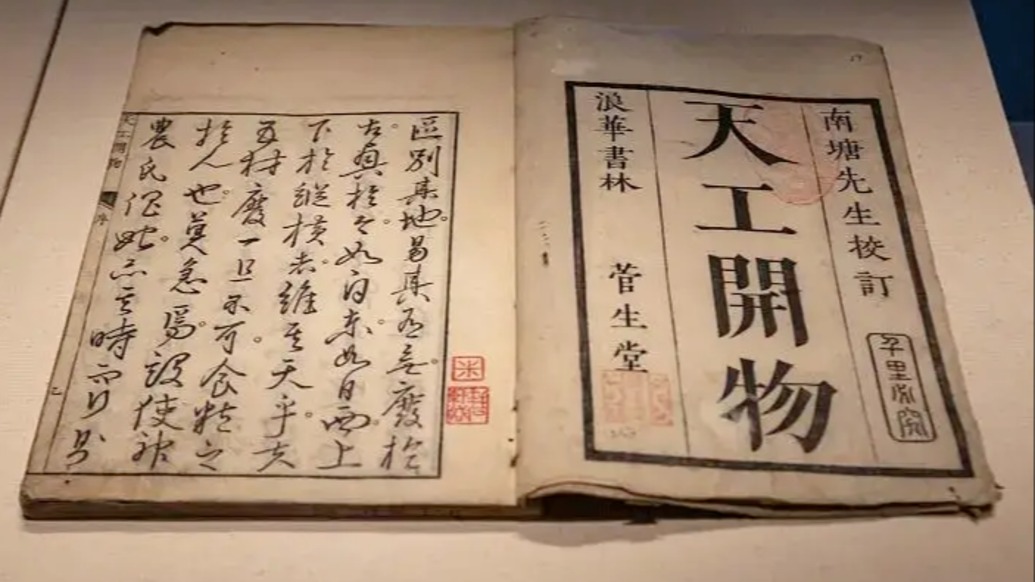- +1
城市的历史人类学①︱王笛 冯筱才 贺喜:城市与城市人
7月14-19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在上海开营。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深入乡村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工作,并在田野与文献的基础之上探讨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的演变与及地方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等研究课题。本届研习营将历史人类学的旨趣与关怀带入城市,开始探索如何在城市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正如在开展乡村研究时所强调的那样,透过田野考察,希望能把制度史的问题,紧扣到具体的地点与人群;而以田野的眼光去读文献,则期待能恢复深埋于文献中的现场情景。在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领先于世界;然而。从清末民初起,因为交通的演变,工业化的影响,现代建筑业的兴起等理由,全世界的城市化程度大大迈进,中国社会也如是。所以,在时间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需要往下推。有鉴于此,首届“城市的历史人类学”研习营邀请了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贺喜、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乐天、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上海师范大学钟翀、同济大学刘刚等诸位教授为学员举办讲座,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分享了自己对于城市史研究的看法与思考。此外,研习营还特邀复旦大学史地所张伟然、上海社科院金大陆、马军、牟振宇、林超超等学者带队,在上海城市进行了田野考察。
王笛: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种取向
王笛教授根据自己研究成都茶馆的经历和体会,回顾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并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和中国当代城市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罗威廉(William Rowe)的城市史研究
中国的城市历来是西方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影响重大的当属罗威廉(William Rowe)。罗威廉相继出版了两本关于汉口的专题研究——《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王笛认为这两部书堪称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城市里程碑式的著作,西方学者第一次对一个中国城市进行如此详细地分析。在西方人的传统认识中,中华帝国是一个控制严密,高度集权的社会,故而中国从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城市。这一观点在西方大为流行,著名学者如黑格尔、亚当斯密,乃至马克思等都有类似的观点,其中以韦伯(Max Weber)在《论城市》(The City)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而罗威廉的研究恰恰反驳了这一固有认识。罗威廉笔下的汉口,是一个有着独特发展优势的商业城市,所谓的中央集权的严密控制并未完全笼罩汉口,政府不仅不限制贸易的发展,而且鼓励长途贩运。
罗威廉对汉口商业与社会的研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以个案研究来试图推翻宏观认识是否合理。有学者认为汉口只是一个特例,难以改变过去对中国城市的整体认识。王笛教授在讲座中谈到,他对于成都的研究也为罗威廉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后来西方一些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也同样说明,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仍然是拥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与活力。王笛教授认为,韦伯研究中国城市的模式实际上继承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一贯认识,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的中国学术界,那时候中国学者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也普遍认为晚期中华帝国是停滞的社会。王笛教授结合自己早年研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指出中国城市的发展没有走向西方式的发展模式,但这并非是停滞,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最后,他说,罗威廉关于汉口商业社会的研究,其最大意义就是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城市。
四年之后,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第二部研究著作出版,这本书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最大争议在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王笛教授认为,事实上,罗威廉所使用的公共领域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罗使用的是中国传统语境中“公”的概念。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一些西方中国学研究者,如冉枚烁(Mary Rankin)、全大伟(David Strand)等人也都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概念。而且冉枚烁在使用这一概念之时,哈贝马斯的有关专著尚未被翻译引入英文世界。在王笛教授看来,这一场看似热闹的学术论战,似乎更像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行为。
西方对社会主义城市的研究
罗威廉的汉口研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城市的认识。然而以罗威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城市研究尚显薄弱。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王笛教授根据研究者群体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城市政治和社会的相关问题。代表人物有薛理泰(John Wilson Lewis)、怀默霆(Marin King Whyte)和白威廉(William L.Parish)等。其中怀默霆(Marin King Whyte)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5卷中关于共和国的城市生活部分,仍然是迄今为止对1949年以后城市研究最全面的著作。这一类的研究主要的问题是过于宏观,缺少个案,同时研究材料大多为二手材料。
第二种是基于实证的、档案资料的分析。这一类研究几乎都是历史学者做的,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和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主编的《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一书,收录的文章研究接管城市、文化政策、资本家接受改造等城市相关的方方面面,关注新政权的建立对于普通人工作生活和思想形态的影响。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的建国史系列具有代表性。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城市生活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不少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参与的,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此类研究较多关注当代议题,如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和农民工等,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城市的研究。
回顾学术界对共和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王笛教授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分别是:建国到改革开放国家主导和高度控制的时期,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国家控制下降城市活力开始迸发的时期,21世纪以后中国城市伴随着商业革命和公共生活的变化而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图景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国时期的城市研究仍有巨大的研究潜力。
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
王笛教授认为目前对于共和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文化生活方面关注很少,研究的时间段也大都局限在20世纪50年代,档案资料逐步发掘,但是已经有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此在最新有关1949年后成都茶馆的研究中,王笛教授试图为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这本书中,我们已经跟随王笛教授的文字领略了成都茶馆的历史魅力,而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茶馆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常人的印象中,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会加速传统因素的衰落。但是王笛教授发现,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有五六百家,到了2000年竟然增加到4000多家,此后到现在已经发展到9000多家——茶馆并未随着成都的现代化而消亡,反而越来越繁荣。王笛教授最后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思考。
首先是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遭遇了大变革,传统文化也遭受了西方的冲击,作为体现和承载文化的中国城市,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当中哪些因素变化了,哪些因素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这也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其次,革命和政治运动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共和国时期各种政治运动塑造和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茶馆作为街坊交流和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试图施加影响和竭力占据的公共空间。对于国家层面的革命、政治与社会百姓之间的关系,茶馆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微观视角。
最后,从社会最底层考察社会生活的演变。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往往能够感知城市变化最敏感的脉搏。王笛教授在讲座中讲起自己研究茶馆的趣事,提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茶客与茶馆附近的算命先生互动交流,从而获得了最鲜活和真实的底层感受,对于之后自下而上地研究城市发展和社会演变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冯筱才:谁的城市?
晚清以来,商税对田税的补充,及科举的废除,使佛山镇的权力中心再次转移:通过选举,商人与宗族领袖进入本地议会,对本地官员和传统功名出身的士绅形成了冲击,这是一场全国性政治结构转型的开始——延续科大卫教授意犹未尽的佛山故事,冯筱才教授讲述了进入民国后,另一批在这次政治结构转型中获得更多合法性基础的“新贵”——社团故事。

何谓社团?为什么要从社团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研究城市,当然首先要研究是谁生活在其中?各种城市景观变化的背后,居民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如果我们翻阅民国时期的史料,譬如报纸,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可能就是,我们满眼所见都是铺天盖地的社团活动,相反个人生活记录相对比较缺乏。即使我们去查找当时人的日记,有时每日寥寥文字更多的是将个人与社团联系在一起的记录。
当个人的意图、活动被包裹在史料所展现的“社团”之下,那么,研究者该如何来解读这些“现代”的声明?是谁在控制这些社团?社团活动对城市和个人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影响?
冯教授指出,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类型并不相同,例如行政驻地、工商业中心、或移民安全岛等,但相似的结果是人(包括他们带来的物、钱、信息)向城市的集聚,从而出现了显著的从传统“城乡一体化”到近代以来“城乡分离”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冯教授说,在“民主”的政治理想下,人们自由结社,社团代表成员,背后是一整套从西方移植的话语和逻辑;但同时,这位议员可能也是宗族(或不被新政承认的政治团体)成员,尽管名义上他代表的是一个选区、一个被新政承认的社团,这就为我们了解一个近代城市的权力结构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不止一套话语和逻辑的存在下,我们不得不分辨文字材料背后他们的真实动机。
晚清的议会新政一直延续到民国,进而发展出了党派政治,一时间,政治社团在全国各地各级议会中涌现。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其他领域团体的结社热情也十分高涨,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团体成立:有承包地方财税的商会、行会,维护地方军事与治安的商团,经营公共事业的善堂,主办文教事务的教育会等等。这些功能集聚体的背后,是学者们所观察到的近代以来我们国家的行政从“小国家”到“大国家”的转变,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同团体、而非零散的个人打交道;面对政治分裂格局下各自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及其强势派系,“结社”也成为各地人们应对变局的一种方式。
冯教授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些熟稔政治话语、并主动利用社团合法性日益稳固的环境以成立社团来获益的人。在对社团资质毫无监察的背景下,这些社团的实际活动与他们的名义并不相符,一旦深入了解真正组织、运行“社团”的“人”,以及他们的人际网络和结社目的,就会发现社团“名”与“实”之间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其中不乏类似“皮包公司”的社团,只见于电报末尾的署名电请,而不见有任何实际活动的迹象。
讲座中,冯教授讲了苏州社团图章管理和北京人力车公会的“段子”:民国初年曾经有几个社团图章都由一个“坐办”管理,因此他经常可代表全苏州几个重要社团发通电,大量社团的实际情形可见一斑;而看似由下层劳动阶级组成的北京人力车公会,背后则隐然存在研究系政客的力量。
这两个生动的例子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之后互动环节中,不少学员举出自己关心的社团,想请冯教授来判断“真假”,但冯教授指出,每一个看似轻松的观察结果背后,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不遗余力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每一个个案都需要福尔摩斯式地寻找线索、绘制人物生平和成员关系网,不可以以一概全。例如在对上海总商会和“五卅”运动的研究中,冯教授介绍道,正是在与虞洽卿后人的访谈中,了解到其与段祺瑞亲属的密切世交关系,印证了自己对虞洽卿和段祺瑞私谊的猜想,从而从政治互惠的角度探讨上海总商会资助“五卅”罢工的动机更加令人信服。
民国时期不少城市中的“社团”,自身未必有恒定的政治理想,其活动也未必是服务于为其声称代表的“群众”。但是在近代剧烈变化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政治竞争,还是经济资源开发,或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造成清末民初社团繁荣的现象,但背后存在的操控性不可忽视,由此人们对近代中国城市中的许多活动与现象,也可能要谨慎判断。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团、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民初以来结社政策在此时有了新的异动:社团登记制度使国家更容易对社团进行直接管理;庞大的军费开支下社团承担起筹款的公共责任;打击封建迷信使得传统社团文化权力被转移乃至式微。
从民国初年到南京时期,城市社会权力网络一次次被重塑——从民初社团“繁荣”时代中普通人被各种团体代表,到国民党政府负责对社团进行合法性审核、乃至操纵,城市究竟成了谁的“地盘”?通过一系列问题,冯教授再次将我们的关怀引向传统中国社会向城市的转型:城市是什么?是否商人“自治”权利得而复失,城市重新回归传统的统治中心?这一次,似乎不像佛山那样有宗族的影子,但所谓“四大家族”、“孔宋豪门”这些词汇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血缘宗族语言。传统意义上的社团,自愿性色彩似乎更加浓厚,但晚清民初之后走向了另一面,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助于我们透过报纸、档案等史料上的社团之“名”,去了解真正掌握近代城市权力结构、驱动城市往什么方向发展的是哪些人的“实”。城市史研究,如果不是通过大量田野调研及穿透纸面的深入史料分析,把握作为历史实际行动者的“人”的表现或观念,而是仅依据史料中一些虚虚实实的“社团”活动来简单判断“群体意识”或人们的行为及观念,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误解了城市历史的主体,历史研究的重建工作也很难真正实现。
在这次讲演中,冯教授不仅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更是强调了对史料怀疑的严谨态度和求证的灵活技巧,并启发学员在学术史中进行综合的对话和思考,使大家得到了治学方向、方法、态度等多方面的收获,对何为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看待史料、研究城市有了明快直观的印象和了解。
贺喜:工作的改变与工人阶级的兴起
谁是普通人
晚清以来,中西之间的文化碰撞使一些新的词汇得以引进及传播。比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提出要挽救当时的危局需要“保国家”、“保圣教”及“保华种”,这里就有国家、宗教以及人种等新的词汇。贺喜教授指出,我们需要很敏锐地注意到,与这些新词汇相联系的是全新的政治理论与意识架构。这些词汇的使用可以说是“普通人”形象的塑造、演变与接受的过程。
贺教授通过《老残游记》《文明小史》《阿Q正传》三篇小说来分析不同时期的作者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述时人及其人际关系。在《老残游记》中,家庭构成、财富功名以及出身官职是描述人物时的常用因素。小说通过老残的经历,反映清末的社会关系集中在官民之间。《文明小史》虽然和《老残游记》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是聚焦于那个时代人们所追求之西洋“文明”究竟为何意。如果说《老残游记》聚焦于官肥民瘦,《文明小史》则凸显出外强中虚,失落的乡间子弟在上海见世面,遭遇了满口新词汇的假洋人。这是不是“文明”呢?在第三本小说《阿Q正传》中,鲁迅笔下的阿Q是在变革前不被承认,革命后又不准革命的人。虽然与身份相关的新词汇已经被引入和普及,鲁迅在描述阿Q的时候,仍是无法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叙述困境?因此,三本小说显示了当时的人对于自我认知的困惑与焦虑,亦提示了我们如何再去回顾那个时代的思路。

谁是工人
对工、工人、工作以及工人阶级的讨论,是贺教授讨论近代普通人身份建构问题的一个例子。与“工”相关的定义在明清时期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工”是士农工商四民中之一种,这联系到王朝的赋役征收。其次,工与技艺传承以及该行业对于技艺认定联系在一起。比如,木工往往以崇拜鲁班先师的方式来显示身份的源流。做工的时候,鲁班真尺不仅是丈量工具,也涉及从事木工所要应对的世界观问题。再次,并非做工的人都可以有平等的工的身份。比如在山西的一块由乐户所立的碑刻中乐户特别要强调他们也拥有“工”的身份,从而合理化边缘人群立碑祭神的行为。在明清时期,苦力在地方社会也往往是不被承认的人。
当清末机器工业开始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李伯元所著的《广东机器工人奋斗史》中,他笔下的机器工人大概可以算作是第一代接触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在习得技术之后,目标是回乡开厂招工,从而成为管理工厂的老板。而所谓“劳资关系”体现在同乡的关系之中。至于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罢工”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明清时期一直都有机工叫歇的记录。
那么,清末民初有没有出现新的现象?
1920年代邓中夏的长辛店日记,体现了第一代接受清末新学的大学生对“工”的看法。他以新式词汇以及词汇后的政治理论描述观感,定义人群。清末出现的新词如“团结”也被频繁用来形容工人生活。新的媒体塑造的形象也影响着工人的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大路》,将此前不被承认身份的流民和苦力塑造成“开路的先锋”。科技影响下工作的变化与工人的定义的转变密切相关。机器的运用不仅限定了人的工作地点、方式,机器还取代了工人的技艺。由此,传统工匠需要达到的特定技艺的门槛被打破。一战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及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已经倡导“人人皆可以成为劳工”。
贺喜教授指出,这套词汇把我们对“工”的定义改变后,我们已经成了脱离这套新的词汇不能表达的人。

- 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 起草组负责人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 政府工作报告深读|八大政策要点

- 中金公司:银行有望保持高分红的特征
- 欧盟将召开特别峰会讨论防务及乌克兰问题,泽连斯基将参会

- 成语,形容冰雪漫天盖地
- 冰上的一项集体运动项目,也叫冰上曲棍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