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 +135
王安忆:驻校紫金港
编者按:2019年9月9日,浙江大学举办“小说的构成:王安忆的浙大文学课”启动暨浙江大学“驻校作家”聘任仪式,在此仪式上, 王安忆女士受聘为浙江大学“驻校作家”,并作了八讲报告,梳理后集结为《王安忆的浙大文学课》。此文王安忆所写为序言《驻校紫金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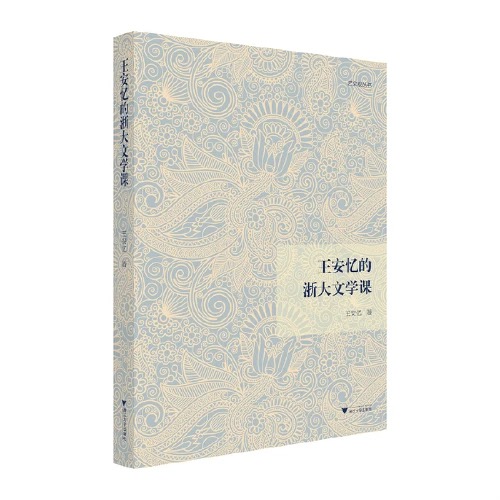
二〇一九年秋,应浙江大学中文系驻校计划邀约,前往杭州。高铁下站,翟业军、陈力君二位教授来接,驱车往紫金港校区,一路大道通衢,未有半点山光水色。后来查看地图,发现市区无限扩容,浩渺的西湖陷在其中,仿佛补片,变得极小,不由感慨发展的迅猛。紫金港是浙大合并之后的用地,面积广阔,楼宇宏伟,尚有许多地方未开发,前途不可限量。和所有的新校区相像,规划设计呈现一崭齐的样式,循序渐进的历史沿革隐匿到了幕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底下,涌动着学生的自行车队、运输物资的厢型车,还有工程车辆,就像二、三线城市的中心地带,好在,人和车不断向支路分流,那里有着湖泊和绿树,气氛便舒缓下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雨中月下看湖的浪漫情调云散了,但不意间很快得到补偿。这一日,去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日正是我到校的时间,赫赫的路标一字不落看进眼睛,以为识得方向,启程时候却迷糊了。经过一片水域,有天鹅和看天鹅的小孩,还有玩耍空竹的大人,草木扶疏中开着细小的长蕊的花朵,脚下遂成青石小径,不知道通往何处。正犹疑,迎面转出一个推车的男人,向他寻路,回答不是业内人,所以不清楚学校建构,擦肩过去又立定,问从哪里来,投亲还是访友,倘有亲友,就请他带去要去的地方。杭州人喜欢攀谈,有一回跑到西湖喝茶,邻桌的人怕我们吃亏,历数多种经济的搭配,然后又是“从哪里来”——同样的入径,去向则有不同,问在上海住哪个区,哪条马路?总之,言过几巡,生变成熟。回到紫金港,告别邂逅,听自行车轮在石路上“克朗克朗”响一阵,静下来,忽见路旁有石牌刻文,题头“南华园”三字,原本浙中民居特色村落遗存,为某人私产,二〇〇二年浙大迁移,聚土建校,属地政府买下赠送,保留几幢旧屋,再开辟庭院楼阁,作会议接待用,平时无人,虚席以待,茶水服务。自后,上课之余,几乎天天造访,凭栏依窗,看荷叶从青到绿,从绿到黑,莲子也枯瘦下来,异乡的人就该回家了。

王安忆
接下聘任,即考虑课程设计。初步拟定一门,专述小说的构成。这题目可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作以来,就萦绕不去,曾假设为小说的“物质部分”;或用排除法,“故事不是什么”;继而陈述式,“故事是什么”,将小说限定为“故事”,也花费不少笔墨。这一时期的文章——自许“文学评论”,多发表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创办、程德培主编的《文学角》。《文学角》是一份短命的刊物,但在新时期文学中,对当时的青年我们,起到推助,至今还在释放效应。文章集结,一九九一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由李庆西责编成书,题名《故事和讲故事》,是我首次以理论登场。和浙江杭州的关系,可上溯曾祖辈,母亲的籍贯向来填的是杭州,此时结下的则是文缘。书依序出版面世,事情并没有落定,反倒一发不可收拾。“物质部分”呈现出有限,不能尽全解释小说何以为小说,折回头再向“精神部分”取路。一九九四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安排,受聘客座,那一学期的课程集稿出版,书名即为《心灵世界》。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课堂,而不是讲座,课堂和讲座的区别在于,前者为系列,后者仅一锤子买卖。作为系列,一方面有“量”的要求,“量”又来自“质”,就是讲题的内涵,有没有充裕的资源足够分配于每一课时;另方面却也可宽限时间,舒缓节奏,从容展开。我想,这次课程是极好的培训,在四十岁的年龄里,既年轻有力气,实践和阅读且又积累了认识。整理讲稿也是训练的项目之一,缜密思想逻辑的同时,保持口语表达的明快。
正式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上课逐渐常态化,不再吝惜思想,也疏于记录,往往是受约稿的催逼方才成文,总起来有两辑,每辑三篇:一是入职现当代时期,嵌进张新颖本科教程中的三堂,二是研究生“方法论”中的三堂,添上其他零星讲稿,汇合成《小说课堂》一书。自从二〇一〇年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主讲小说写作实践,课堂模式为导修和讨论,通常叫做“Work-Shop”和“Seminar”,一切都在临场发生,很难完整成文。后来,到二〇一六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驻校,举办系列讲座,我专辟一章,描述了这个课程。香港城大总共为六讲,面向社会,听众就不止本校学生,因此设计比较广泛,并不拘于某个母题,相互之间也没有密切的关联。前二讲更接近写作生活的个人体验,接下来的三讲涉及叙事的形态,似乎又回去小说的“物质部分”,第六讲从《红楼梦魇》看张爱玲的人生观,且又脱跳到“心灵世界”。显然,小说的“物质”很难独立于“精神”而存在,不得不在其间盘互往返。这一回,浙大的课程,是从“物质”出发,最后还是在张爱玲一节上归宿“精神”。为什么总是张爱玲,总是有她,又总是被她引到沟里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专门分析。在我却是简单的,选择的文本里,她是惟一的中国现代作家。她和我最近,说起来是前辈,时间上其实有大部的交集,只是被空间割据了,放大了看,则有着共同的背景,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无法保持客观,冷不防就滑了脚,落入感性,扑面而来“心灵世界”。小说这样的写实性的产物,器和道仿佛水乳交融,前者有后者的内囊,后者有前者的外相,如何分离它?挑战在这里,劳动在这里,劳而无功也在这里。最后一讲张爱玲,多少有些缓解之前持续的紧张度,刀刃上走了七讲,眼看收官之际,真感到疲累,不免放自己一马,抽身退步上岸,进到小说的本体论。

王安忆
为应对预期的关隘,选定细读和分析的多是人们熟稔的经典,算是以易克难的策略吧。对照一九九四年复旦课程的书目:《巴黎圣母院》《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独》,这一回的《傲慢与偏见》《贝姨》《安娜·卡列尼娜》《ABC谋杀案》,无论是题材的历史感、思想的哲学性、社会生活的宏伟度,还是解读的勇气,都收缩了尺寸,回归世俗,合乎大众的品味。创见的野心安静下来,趋于平常。《追忆逝水年华》和《坎特伯雷故事》,企图比较大,涉及起源,前一则是叙事活动的物理,后一则带有小说的经学的意思。对我而言,学识和经验都称得上冒险,事实上,讲座一开始,就翻了船。
《追忆逝水年华》,我只在第一卷第一部的八万字上手。全文二百万字,归纳统筹需要超级的工作量,我的立论且远不足以覆盖全局,单这八万字,都够我受的了。准备的过程就不怎么顺利,既要将叙事剥离时间载体,又要用叙事佐证载体的时间性质,他证和自证,两下里纠缠不清。后来,人文学院的楼含松院长为这堂混乱不堪的讲课总结:“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说得真是太形象了,我不断地掉下坑里,爬上来,再掉下去,直至彻底陷进去为止。其时,在案头上,还寄希望现场有不期而遇的契机,困境迎刃而解,我这人的运气向来不错。但倒运的一天终于来了,很不幸,事情比最坏的打算还要坏。浙大中文系在正式开课之前举行欢迎和受聘的仪式,因此第一讲就安排在五百人的礼堂。说实在,机灵的人一定会临时换个常识性的题目,谈谈个人经历、文学现状,总之,泛泛而论,类似读者见面会,而我极少参加读者见面会,性子又轴,要命的是,关于时间的题目如同魔咒,将我控住了。打开备课本,按原计划开头,几乎就在同时,讲课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忽然间失去讲述的欲望,了无兴致,只想着马上结束,匆匆略去过程,直接到达结论,借楼院长的“挖坑说”,我还没有挖下坑,直接跳了下去。浙大的课程便在这挫败中拉开帷幕。
第一讲结束,回上海过了中秋,再来浙大,就有点从头来过的意思。第二讲上,补充了前一讲,后半时间开头第三讲,拖进第四讲……如此头尾衔接,顺延至第五讲方才整顿课时,循序进行,计划也过去一半。这是一次颠三倒四的课程,回忆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在复旦上讲台,不由佩服那时候的鲁勇,勿管逻辑错接,文不对题,材料匮缺,那么多的“水词”,那么
多的来回重复,我又不善谐谑,缺乏急智,只能实打实地硬上,竟然毫不影响情绪,劲头不减,终于坚持到最后,按陈思和的话,“功德圆满”。现在却不行了,体力也许是个原因,职业性的消耗是个原因,但又不全是,似乎是,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即便要说的话也不那么容易出口了。想的越多,说的反而越少,经验越多,也越生怯了。我不敢冲口出来一个结论,一个定律,而是需要更多的取证,更多的实例,等实例搜集到眼前,却又觉得无以对应,就要怀疑立论,结果是互相取消。有时候,在前辈或同行那里看到相仿的说法,一方面觉得安心,另方面则是失落,好像自己白忙了一番,现成的路上又走了一遍。接着慢慢想开了,殊途同归,但到底路径不同,经历不同,方法也有不同,增添了心得,至少对自己而言,有些许思辨的价值。总之,不再是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以气势压人,而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每一课下来,心情多是遗憾和不满,遗漏了准备,丢弃要点,又受气氛左右,出虚浮之辞,换取肤浅的效果。所以,讲稿的整理对我尤为要紧。
虽然有详细的备案,但事实上,几乎从头来起。其中有三讲,“贵族”“理趣”“美国纪实小说”,由我们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硕二〇一九级同学整理录音,看记录稿,当堂的粗疏和散漫令人汗颜,好在勾勒了轮廓,保留了基础,转换书面终究方便许多。这一级同学入校正逢疫情,我拙于线上交道,就错过了面对面的课堂,在纸面邂逅,可谓以文会友,别有一番意味。顺便解释,整理的时间不完全按照讲课的顺序,实际的讲课也和大纲略有差池,“理趣”和“贵族”调换了先后,正式书稿的依序还是根据现场排列,所以,时间标示就不一致了。
浙大前后两月,多在紫金港度过,参观了地标性建筑求是大讲堂,古城楼的款,最惊人的是通体青铜材质,固若金汤。四边尚未建设,平野之上,可远眺西溪湿地。考古艺术博物馆则是现代风,直线和直角结构,虽为初始新建,没有全开,却也有几样值得记的。镇馆之宝颜真卿碑,碑体无存,只有表皮,想来中国无数壁画石刻,就是这样被洋人切剥,流失出去;数幅郎世宁“乾隆镇准噶尔得胜”铜版画,工整细致,中国界画的布局,细部则是写实主义,一个个小人头,眉眼表情无不亦动亦静,栩栩如生,几近勃鲁盖尔之趣;再有日人所捐浮世绘,西安借展俑人;等等。校区延伸出一条“堕落街”,和所有大学同样,补充学校伙食的匮缺,在复旦五角场,叫作“黑暗料理”,有点昼伏夜出的气氛。“堕落街”不分昼夜,到饭点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有一款大盘鸡木桶饭,量特别足,仿佛看得见少年人的生长荷尔蒙。在甚嚣尘上的中心外围,星布了新落成和施工中的楼盘,并校的迁移还在进行中。西湖在遥远的地方,几乎被忘记了,母亲家败落的旧址——三十年前,承杭州文学朋友帮助,我走进去过,如今也模糊了方位,和后现代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杭州向周边极速扩张,辖制下的“县”变为“区”,“镇”为“街道”,“村”为“居委”。江南绵密蜿蜒的田地和小径被水泥覆盖,硬化,取直,成北方式的朝天大路,于是风也粗犷起来。
在我第一讲的开端,也是整个课程的开端,引用了艺术史家巫鸿教授关于中国玉器造型的解释,空间性的艺术可以将隐匿的性质外化为显学,语言艺术却是从隐匿到隐匿。当我整理讲稿的时候,又读到巫鸿教授另一本书《物·画·影》,以镜子的起源带入“镜像”的概念。书中写到法国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面向拱窗等高等宽的镜子,将室外花园的景物映照其中。
《扬州画舫录》卷十二,记“绿杨湾门内建事厅”中有一堂,壁画山水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于是,一真一幻,山重水复。小说也是镜像,起于复制,终于转换。这一过程在文字真不容易描绘,真和幻都在虚拟中,文字本就是个天大的虚拟。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同伴采访作曲家王酩先生,当时他正值壮年,不想已成故人。他向我们述说写作的经验,有一回,主题出来了,在第二乐句便圆满完成,如何突进第三句,也就是“起承转合”的“转”,苦思冥想不得,忽有一日,福至心灵,破壁而出。或可以归结“灵感”,事实上呢,是有现实打底,那就是调性关系提供了工具,开辟新天地。这个叫作“调性”的自然法则,在我们也没有明显的约定,文字依着不可见的轨迹进化。小说的材质就是这样,解析小说的材质也是这样,以不可见诠释不可见,我极力使两者分离,费尽口舌而不详一二。整理讲稿就像重蹈覆辙,再一次体验挫败。说到这里,不禁想起课程的开讲,就是一个隐喻——楼院长说的,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即便是“坑”,不也是物质性的?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上海

- 三十年手足情深
- 两会|委员建议引进AI加强审核
- 四位省级政府一把手将“去代转正”

-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 深康佳A:拟购买宏晶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8%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股票明起复牌

- 第一架望远镜是由谁发明的?
- 明朝的主要法令条例,由朱元璋制定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