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46
邢树青,与中国曲剧的漫长告别丨镜相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丨杨海滨
编辑丨柳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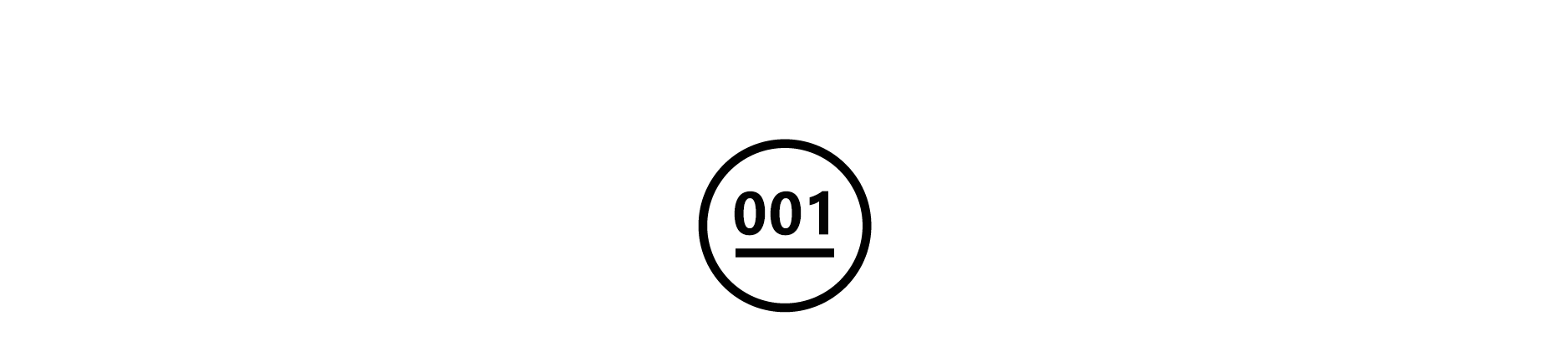
风雪中的绝唱
激烈的锣鼓胡琴猛地奏响,红绒大幕缓缓启动,在这处搭在丘陵折皱中的简陋舞台前,几盏射灯刹那间照亮黑暗中空旷的舞台。邢树青身着旦角戏衣,从舞台左侧,随着逐渐宽厚的序曲,款款移步至舞台中央,以娥娜之姿亮相,凝成一个经典造型。
要是以往在豫陕鄂一带这样亮相,台下早已一片喝彩,而眼下的寂静让她无所适从。她眯眼俯瞰,只见雪花淡淡地飘着,空旷的麦场上,仅坐着几个穿棉袄的老年农民。她知道曲剧正被时代的洪流冲击得淹淹一息,可这寂寞还是让她出乎意料,一时愣在台中。旁边乐队急骤的锣鼓声让她回过神,她瞟了眼愈发肆意的雪花,内心叹道:“要下暴雪了。”一转身,兰花指在空中一捻,开腔唱出第一句唱词,竟然带了哭腔……
这是1988年冬的某天,繁荣了百年的中国曲剧,正被兴起的狂歌劲舞取代,呈现出日薄西山的颓势,南阳淅川曲剧团也在这大背景下,面临解散的厄运。正在这时,身为剧团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邢树青,意外收到数百公里外的三门峡地区的南洋村人的邀请。准确地说,是南洋村八家从山西倒运煤炭的老板的邀请,为庆祝家中老人生日,他们出资八百元人民币,指名道姓要她率团来演出。她思忖再三,决定为全团六十余人的口粮,放低身段应约前往。
到达南洋村时,天气还好好的,到傍晚演员化好妆后,天气骤变阴沉,飘起鹅毛雪花,再加上北风吹拂,八户老人都缩着脖子回了家,为数不多的观众也陆续离去,最后只剩下一位老人孤零零地坐在舞台前的麦场上。
“我为他楼台一别肠望断,我为他无心对镜来梳妆,我为他茶不思来饭不想,我为他抛头露面背井离乡……” 当她唱完著名的传统古戏《泪洒相思地》时,早已泪流满面,她知道,自己的哭泣早不是女主角王怜娟的爱情,而是对眼下曲剧现状的悲戚。
这时,台下那位老人蹒跚走到台前,朝她挥手,说:“雪下得太大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要走了,你不要唱了……”
就在老人说话时,一位中年男子从暗中闪出,高声说:“邢团长呢?”管后勤的老李随即把邢树青挡在身后,带着讨好的表情说:“在这呢,王老板。”王老板说:“合同上写着这场戏不能少于三小时,你们才演一小时,不能散!”老李的笑脸在灯光下显得发青,唯唯诺诺地说:“王老板您看,下这么大的雪,也没观众了,再演纯浪费时间。”王老板坚定地说:“没观众也得按合同规定,少于这个时间,我不付钱。”说罢走回舞台前,在雪中看他们。
邢树青对大家说:“各位理解一下,我们一定把这场戏唱完。”于是灯光再次聚焦在舞台中央,锣鼓家伙再次响起,演员面对空旷的黑夜、浓密的大雪,以及被大雪覆盖的白色山冈,唱完了这出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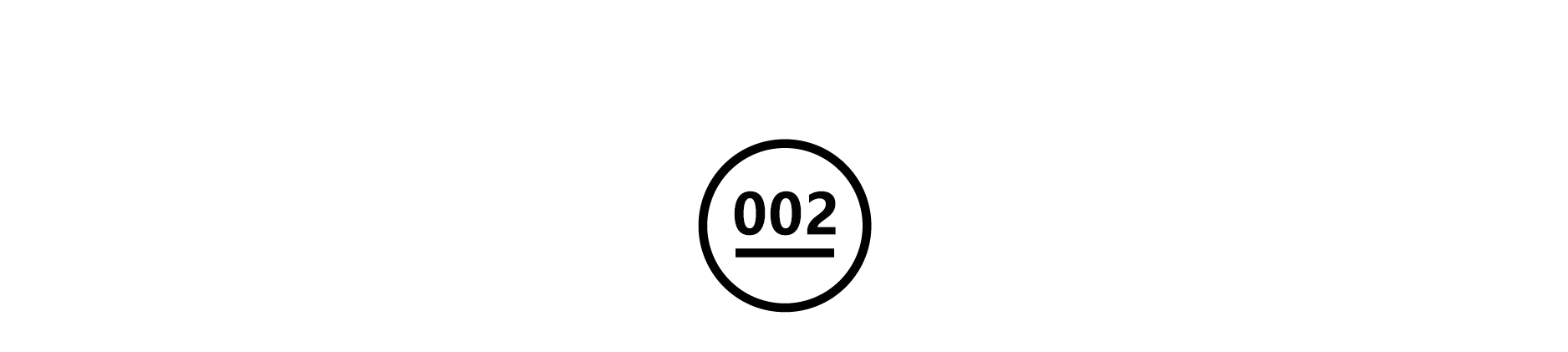
命中注定“曲剧人”
1937年春天,邢树青出生在南阳淅川之西的西坪小镇,这地方是河南曲剧诞生的中心地带。七岁以前的记忆,尽是模糊的森林和古老幽长的石板街,第一次能清晰记忆的事是1944年夏天的某个傍晚,当红色晚霞逝去后,她站在西坪镇那个用石头砌成的坚固戏台前,第一次看到花花绿绿的美丽衣裳和曲剧脸谱,并幻想自己就是台上的一个人物。
命运从那时就隐喻着,她一生将在甩动的水袖和光彩照人的脸谱中度过,只不过那时她只有七岁,意识并不清晰。直到八年后的1952年,那时新中国已成立,她以淅川县实验曲剧团第一代演员的身份、十五岁少女青春的身段,站到了她第一次看戏的那个舞台上,重新演绎了数年前的那场古装戏全本。她的戏剧人生从此正式开始。

年轻时的邢树青,作者供图
七岁那年,她第一次看完那场曲剧后,便被在西坪镇卖麸子酒的父亲送到镇上的私塾,读了一年《三字经》《百家姓》,后又学习了一年的《九十洲绣像烈女传》,第三年她被转送到西坪完小,读由丰子岂作品配图的国文小学课本。这年淅川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她也在1951年小学毕业,参加商洛师专招生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
就在这关键点,她的生活却出现变动。母亲早在她年幼时去世,父亲在1950年因私藏大烟,被政府逮捕进了监狱,之后她便跟奶奶生活,可奶奶也在初春猝然病逝,她瞬间成了孤儿。走投无路时,她忽想起父亲年轻时在荆紫关结拜的兄弟杨有庆,他家离商洛更近,或许能帮助自己实现上师专的愿望,于是她走了两天山路,来到杨大伯家。大伯听到这些变化几乎哭着对她说:“我这一家四口人,从来没吃饱过,还把最小的闺女送了人,大伯没能力供你上学。”但杨大伯还是挽留她,让她和他们一起生活:“只要我有吃食,就有你一份。”她留了下来,某天她正在院里劈柴时,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悠扬的唱戏声,便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腔走到简陋的剧场。
这时的剧团完全是私人的野戏班,凭收门票生存。她没钱买票,就站在入口处听戏,到半场后才大胆求守门人放自己进去,守门人不许,她就站着继续听到散场。第二天她又早早站在入场处,守门人终于在后半场经不住她再三的恳求,放她入场。到了第三天,守门人还没等她央求就挥手让她进去。
当她第七天再来看戏时,守门人对她说:“我们戏班现在招人,你这葵花脸柳条身,天生是个唱戏的料,来报考吧。”邢树青说:“大叔您说我能唱戏?”守门人说:“让班主考考看嘛。”邢树青说:“那您帮我报个名,只要有饭吃就行。”
翌日,当邢树青再来剧场时,守门人说:“我已给班主说过,你现在就去见她。”“现在?我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怎么见人?”邢树青忐忑地看着脚上隐约露出脚趾的布鞋,说:“我不想见团长。”守门人说:“是哩,唱戏人必需讲究形象,但班主不会嫌你衣服不好,只要嗓子好就行。”
那天她唱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几首歌,班主说:“嗓音的条件不错,明天来报到吧。”
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大伯时,却遭到反对,他说:“就是因为你父亲不在,我才不同意,好好的姑娘家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唱戏。”邢树青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叠烂的录取通知书,说:“我不能去上学,也不能让您养活我一辈子,去学戏就是个活路。”
到达县城后的某天,她看到两位身穿中山装的干部,正式挂牌成立“淅川实验曲剧团”,在豫鄂陕交界处成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管理的曲剧团。一个月后,从淅川各地来的小学员们陆续到位,从南阳来的老师开始给他们排戏。她也在排演第一出古装戏时被挑选为女主,并在导演讲述梗概时恍然大悟,原来七岁那年在西坪镇看的那场留在记忆中的戏,正是眼下排演的《二堂认夫》。从七岁时朦胧的第一次看,到十五岁跃上舞台的第一次演,连她自己都惊讶她和曲剧不可思议的缘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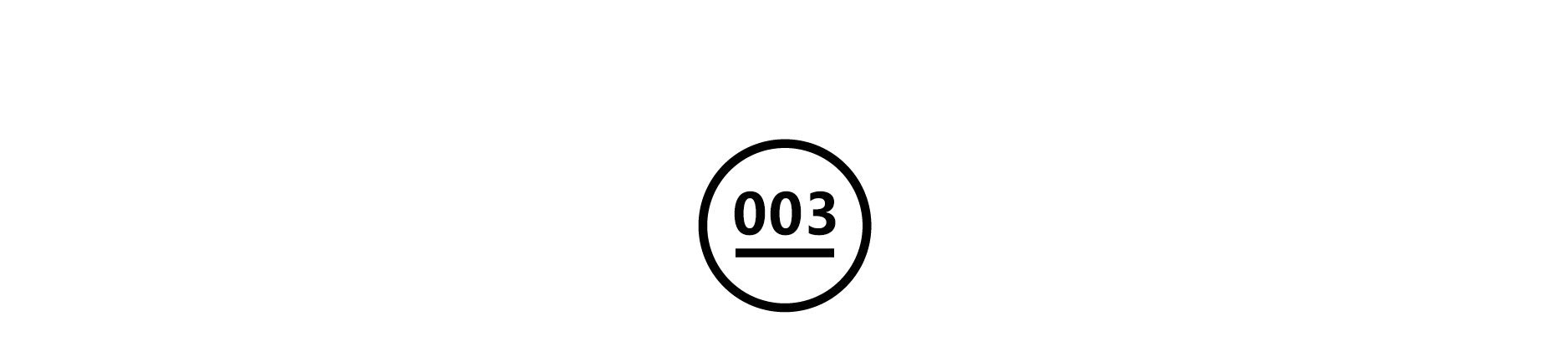
高光:那个叫“二十万”的女演员
从1954年开始,邢树青随着淅川曲剧团开始在内乡、西峡、邓县一带巡演《阎家滩》《王宝钗》《天河配》《泪洒相思地》等大戏,她俏丽的嗓音和清秀的扮相,初露锋芒便斩获名声。之后她又随团到山东德州、河北邯郸、邢台一带商演,受到外省戏迷的如潮好评,年底回到淅川休整一段时间后,又马不停蹄地去陕西商南、商洛、丹凤和湖北老河口、襄樊各地继续演出。
1955年春,她在湖北老河口演出《阎家滩》,每场戏票都提前售罄,这天的演出马上就要开演了,可剧院外仍围着许多人在买票,戏迷见买不到票,便开始骚动起来,恰好有个观众的母亲突发急病住院,他拿出那张票喊了声“退票谁要?”,还没等话音落地,早有数人围来争抢。其中一人问,卖多少钱?卖票人说,你看值多少钱?其时正规票价是五元(老币值,兑换为新币约为五分)。买票者说:“看邢树青的戏,也不给你讲价钱了,二十万成交(兑换为新币约为二十元)。”卖票者说:“我这是便宜你。”后来几场演出,黑票价格已经高达二十万,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老河口的观众在无意中冠给邢树青“二十万”的绰号。这个票价后来也传到陕西、河南一带,成为一个标准。

舞台上的邢树青,作者供图
邢树青在1955年首次当选淅川县人民代表,并出席县人代会,连她都不相信,一个深山的小女子,竟然可以代表人民坐在大礼堂商议国事。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她的人大代表之职一直任到1994年退休。同时也以“三名”(即名导、名编、名演)中的“名演”身份,参加了南阳市第一届高级知识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南阳地区著名的戏曲人。
这年河南省戏剧学院在郑州成立,在河南这样的戏剧大省,这无疑是一声惊雷。第一届学习班,面向全省各县剧团的骨干们,省戏院直接给各地区剧团发红头文件,其中就包括淅川县曲剧团,且指名道姓要邢树青参加学习。而此时,她正随剧团在内乡商演,因她的名声早已在外,成了全团经济收入的支柱。团长便指派一名新演员代替她去郑州,没想到第三天那位演员从郑州返回,对团长说:“学院要邢树青本人去,别人不能替。”几天后,学院没见邢树青来报到,时任第一任校长的杨季梅——河南省著名的戏剧教育家,直接把长途电话打到了淅川县宣传部部长处,部长不敢怠慢,当即派车赶到内乡演出地,等她把台上的戏唱完后,立即送去郑州。
邢树青像饥渴的禾苗,在学校被老师们精细地修剪着唱腔中的不足。老师教会她一系列功底,短短半年,她的唱腔像添了润滑剂,进入了更加触神的境界。
195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第一个来访的苏联乌克兰歌舞团,省文化厅对此十分重视,特意准备了一场联欢晚会。其中,戏剧部分,决定上演由河南省戏剧学院改编、洛阳曲剧团原创的《赶脚》中的一折。袁文娜导演为确保戏的质量,让洛阳曲剧团的年轻学员主演A角,B角由郑州曲剧团的学员担任,接待外国贵客,怕有闪失,袁导竟把最年轻的邢树青设置为备用中的备用——C角。
郑州的夜晚是美丽的,演员们在一天的排练后,融入夜色游玩散步去了,邢树青却独自在学院蓝球场的一盏发黄路灯下,揣摩白天袁导指教的动作和唱腔。圆润明亮的唱腔,惊动了仍在二楼办公室的校长杨季梅,她从楼上走到她跟前,问:“为什么白天不练晚上练。”她说:“我从山区来,基本功差,怕别人笑话不敢练,可我又想学会这出戏,想着把它带回淅川。”杨校长说:“你是C角,从明天开始和A、B角一道练,不能因为基础差白天就不敢练。”第二天晚上,杨校长又见她仍在灯光球场独自练功,再问:“你白天没跟导演排练?”邢树青说:“白天也练了,晚上再练练记得更牢。”
袁导为精益求精,反复更改细节,这惹毛了年轻气盛的A角,她说:“我们的原作已非常好,不需要再改,再改就不是我们的戏了,我也不排了。”这让杨校长和袁导大为惊讶,当即换B角上场,意外的是,B角唱腔不准,经常跑调,不能胜任涉外演出。杨校长马上想到那个在很多个晚上独自在蓝球场练功的邢树青,说:“既然AB角都有问题,那就让C角上!”
那场表演成了邢树青的高光时刻,乌克兰演员迪纳摩看了她的《赶脚》后,当晚便通过翻译找到杨季梅,说:“我要追求邢树青,把她带回乌克兰。”杨校长对翻译说:“邢树青是个戏剧演员,要天天练功吊嗓,现在没时间谈恋爱,等她成年再说这事。”小伙虽吃了闭门羹,但并不灰心,第二天,他手捧鲜花来到排练厅大门口找邢树青,却被袁导挡在门外,同时,别的老师把邢树青带到市中心的“河南人民剧院”排练,回避小伙的穷追猛打。

1956年河南省文化厅招待乌克兰歌舞团的节目单,作者供图
数天后,在乌克兰歌舞团离开郑州的前一天下午,她才和同学们回到学院,袁导递给她一身漂亮的连衣裙,让她换上,参加欢送苏联朋友的晚宴。
晚宴上,迪纳摩端着红酒杯,从人群中走到邢树青面前,喋喋不休地嘟哝着她听不懂的外国话。袁导对她说:“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说谢谢。”这个外国小伙可劲对她说着什么,说到最后竟然流了泪,这让邢树青迷惑不解。直到翌日上午,在郑州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火车开始启动后,她看到迪纳摩抱着一束玫瑰花从车厢跳下,朝她飞跑而来,袁导眼疾手快,把邢树青拉到身后,可还是没来得及拦住塞进邢树青怀中的那捧玫瑰花束。邢树青抱着那束花,莫名其妙地看着火车在风中远去……
1959年年底,她接到省文化厅的通知,要她随从各剧团抽来的角儿,还有南阳曲剧团的精英们,以曲剧之名,在第二年6月进京,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获知这消息的沿途百姓,早早地在北上的公路上堵着演员们,非要他们演出一场才放行。就这样一路走走演演,直到八月中旬,大家才赶到郑州。在郑州戏院休整的数天,大家白天学习政治,晚上继续演出经典剧目《阎家滩》。由于是进京汇报演出,所有演员必须通过详细的政审才可放行。
就在大伙通过政审关时,她却接到电话,领导要她留下等政审结果,再决定是否进京,也许是因为姑姑是地主成分,影响到了她。她只能无奈地看着大伙兴高采烈地上火车,一时,她眼里噙满泪水。因为焦虑,嘴唇也当即起了一排水泡,晚上说话时,声音像哭声一样嘶哑。数天后,当淅川宣传部发来政审确认通知时,她早早就背上远行的小包,买了张火车站票前往北京,一夜站下来,腿肿得像馒头,下了车连路都不会走了,硬在进京前夕归了队。
10月11日和15日夜里,她两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演出曲剧《阎家滩》。老舍、赵树理在领导人离场后,专门和演员们座谈。老舍夸赞了大家的表演,甚至还专门夸奖了邢树青。据邢树青传记作者记载,老舍先生赞她“吟咏之间,吐纳玉珠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她也知道自己的艺术离老舍先生说的还相距甚远,但那赞誉成了她一生自我鼓励的最佳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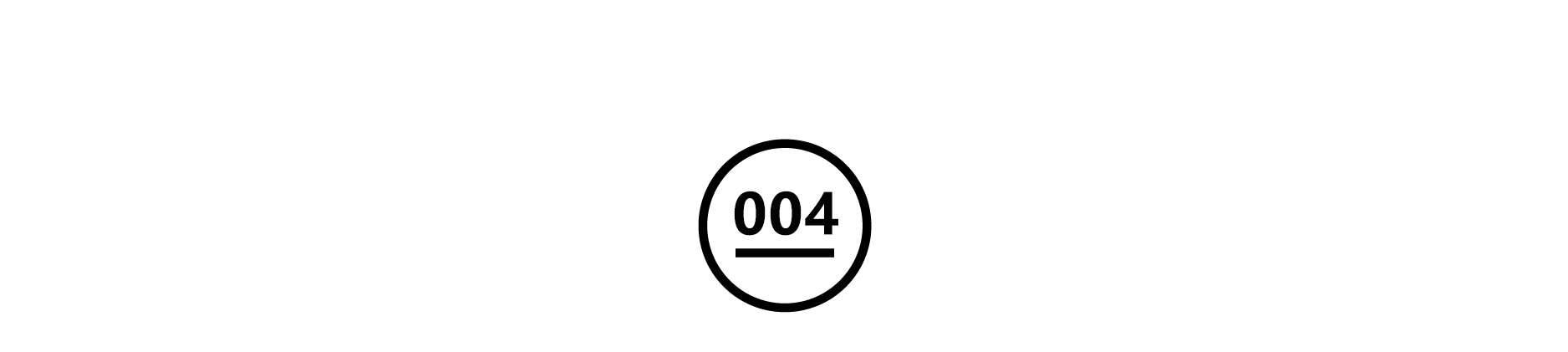
归来:从样板戏到《王宝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淅川亦不例外,邢树青被淅川曲剧团革委会要求隔离审查,接受群众的批斗。同时期剧团的其他骨干演员或被打倒,或被下放。
随着形势的发展,剧团需用曲剧宣传政治方针,这就需要演员,可剧团已没人能支撑场面,县革委会主任找到了她。就这样,白天她和走资派、黑五类站在一起,接受群众批斗,晚上在舞台上以主角的身份演出样板戏《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和《龙江颂》,且常年累月在全县各个乡镇循环演出,直至1977年得到平反。

20世纪六十年代淅川曲剧团,作者供图
次年,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允许剧团公开上演古装戏,可传统戏剧剧本在过去十年早已荡然无存,就在导演急得跺脚时,她悄无声息回到山区老家的老屋,拿出藏着数十个传统剧本的小木箱,献出《泪洒相思地》《阎家滩》等剧本,导演向她鞠躬致谢。
1982年,邢树青在商洛演出时,特地去了趟戏剧人物王宝钏当年居住过的寒窑体验生活,在那,她偶然结识了正在考查的西安五四剧院的艺术总监王河青先生,当他听说眼前这人就是轰动豫鄂陕的著名曲剧演员,号称“二十万”的邢树青时,便力邀她率剧团去西安五四剧院演出。
这个五四剧院,可是古都西安艺术门槛最高的殿堂,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级艺术团的表演。邢树青率领淅川县曲剧团进了五四剧院,且一演就是《王宝钏》五本连演。什么是五本连演?就是这一出戏,从头到尾要连续演五天才可演完,像电视连续剧,五本连演连续演了二个月,观众仍络绎不绝,尤其河南乡亲,更是奔走相告,一时轰动西安。
《西安晚报》的记者在题为“深山里的百灵”的一篇通讯稿里写道:邢树青在塑造人物时,很少运用幅度较大的程式动作,而是以自己的唱腔艺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一腔一板,如泣如诉,唱得剧场一片呜咽。

《西安晚报》报道邢树青演出盛况,作者供图
五四剧场第一回邀请一个县级剧团,就如此声势浩大,把同在这个舞台演出的歌舞《丝路花雨》衬得冷清。最后一场演出的中场休息时间,西安观众王守义率数十位戏迷上台,赠给邢树青一面绣着金黄字的“春归红楼”大锦旗。这事传到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陶海清的耳朵里,他当即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对王河青说:“你要留住邢树青,不能让她回淅川,我带着最好的录音师明天就到西安录音。”
当时西安最好的录音棚在陕西电视台,而《丝路花雨》组正在那里录制,由于邢树青的演出任务紧迫,陶海清调动了在西安的所有关系,找台长、局长讲了各种理由,硬把前者挤到了后面,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月。这个老牌唱片公司,能放下架子,为一个深山里的艺术家录音,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邢树青曲剧磁带的封面,作者供图
1992年,正值这张唱片发行十周年,河南洛阳的黄河音像出版社对它进行了重新包装,即沿用邢树青的唱腔,但用年轻的洛阳曲剧演员王豫华的表演来对口型,重新演绎了当年邢树青版的王宝钏,发行数万盘磁带。此时正是录音机流行的时代,邢树青的曲剧唱腔如此风靡了淅川的大街小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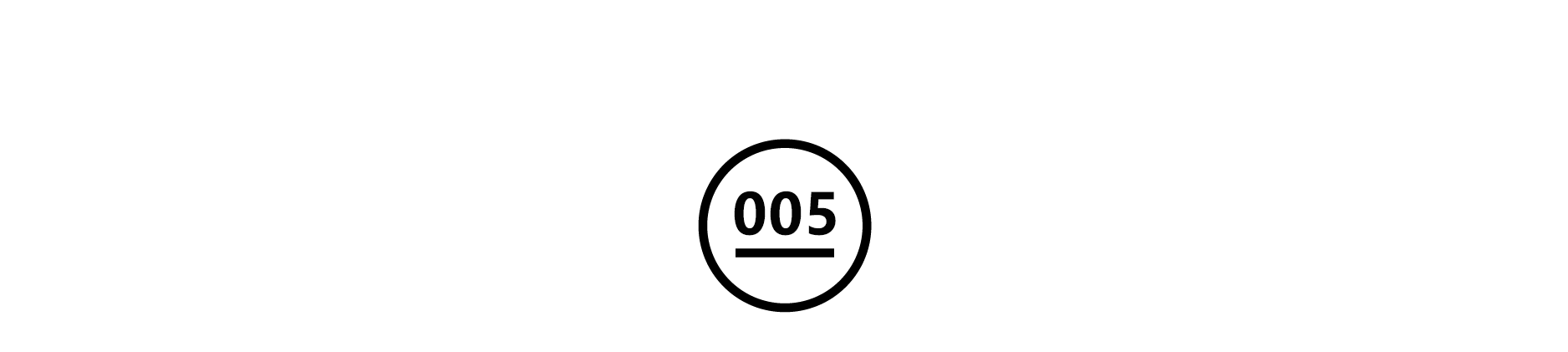
漫长的告别
在那之后,曲剧便走向了寂寞,直到2009年,慢慢没落的曲剧又像干涸的大河,在经历漫长的旱季后,终于迎来雨季的润泽,人们在那些闹腾的歌舞中重新想念起曲剧的蕴味,戏迷们开始怀念起她的唱腔。县文化局也想趁机振兴曲剧,借此时机为“河南县级剧团里唯一一位一级演员邢树青”举办一场“邢树青从艺56周年暨告别舞台表演会”。
从那张保存着的光盘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真是场不可思议的曲剧盛会。从她坐进化妆间开始,就有戏迷隔窗围观,问哪个是邢树青,她说我就是,戏迷说你都恁老了?是啊,岁月让她变老,可她的戏迷也在变老,而曲剧在沧桑中一直年轻着,并在诞生百年后的今天愈发散发出魅力。

邢树青在告别演出中唱《红梅赞》
当开演时间到来,她从化妆间走出,数名徒弟在前开道,后面跟着两名强壮保安左右护驾,像香港大歌星一样接受戏迷的欢呼,在那条百米长的通道上,戏迷上来迎接、送花。有个姑娘奋力拨开人群迎上她,说我代表中风的妈妈来献花。当邢树青知道她妈就是在“文革”年间找她茬、贴她大字报的同事时,立刻想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话。这场告别演唱,竟让她意外捡回了一段失去的友情。
70岁的邢树青站在舞台上,唱起了高亢的《红梅赞》,韵味一如既往,如同当地纯厚的麸子酒,四处飘香,台下人也如喝醉一般跟着唱,一首曲剧竟唱出万人大合唱的波涛汹涌气势,她浑身颤栗,热泪盈眶,觉得自己早化成飘荡在广场上空的一个音符,恍惚间仿佛回到六七十年代曲剧最兴盛的时刻。
她唱了三小时,每逢要结束时,观众仍高呼“再唱一曲”,她就再唱,一曲接一曲。“再来一曲”的呼声如穿城而过的丹江河水,她气喘吁吁,看着台下情绪高涨的戏迷。最后的最后,她第五次谢幕,与舞台,与戏迷告别。
岁月让一代表演艺术家老去,并隐于深红的幕布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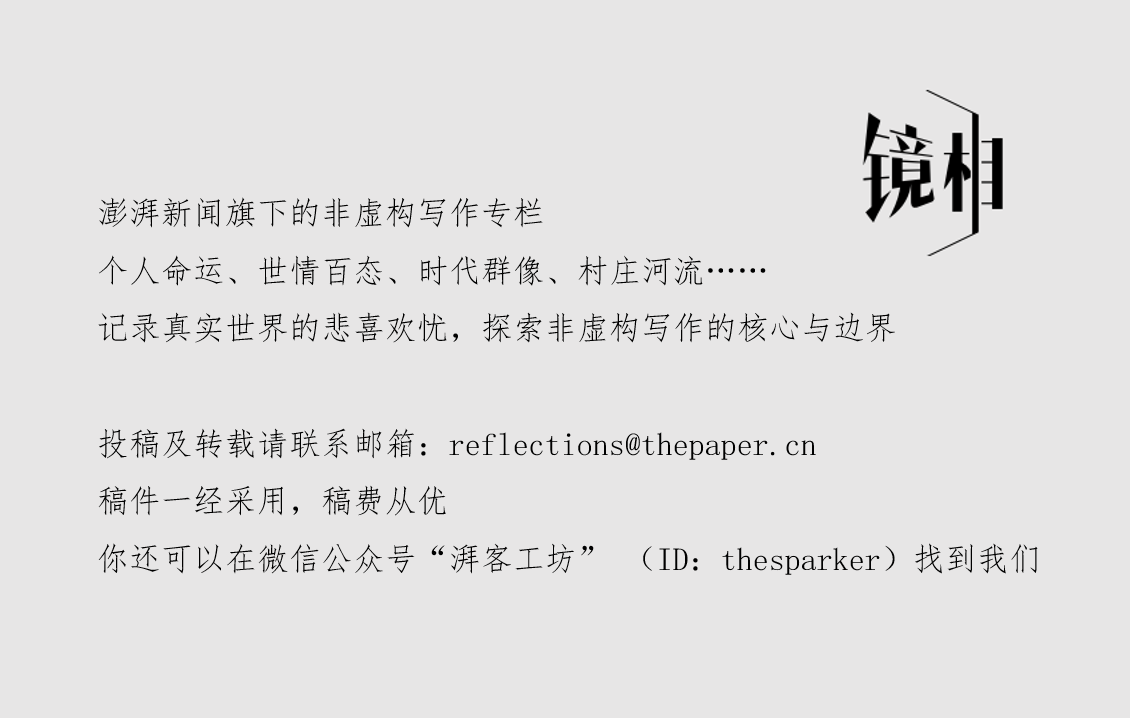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 解读|王毅三天密集会见日方官员
- 国足多人伤停低调备战澳大利亚

-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跌0.18%
- 沪指尾盘翻红

- 人体红细胞中,携带氧气的主要物质
- 光合作用的产物是氧气和什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