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1390
出走的母亲,写出了自己的《秋园》|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丨沈后
编辑丨吴筱慧
去年夏天,我在豆瓣“永恒的女性故事”小组刷到一个女孩发帖推荐母亲的自传。
在帖子里,她用165个字概括了母亲的人生,其中涵盖诸多元素:家暴、先婚后爱、单身育儿、中年被骗、老年独居……我瞬间入了坑,一口气追平了更新进度。
在这部名为《谷底不黑》的自传中,我看到了一度困于家务的女孩对独立的渴望,也看到了独立后努力打拼的女人在婚姻和育儿中的挣扎。相比于那些虚构的大女主叙事,这个真实故事并不畅快。女主角屡屡践行女性主义却不自知,始终无法实现100%的出走,而且有着固守传统的一面。但我认为,这恰是现实中许许多多正在觉醒的女性的处境。
《谷底不黑》完结的次月,我前往山东日照,拜访了它的女主角——60岁的晓虹。她的小城独居生活确实闲适,但也没有读到的那么美好,对于失去的巨额财产,以及她认为一并失去了的“证明自己的机会”,她仍有深深的不甘。
我也和晓虹的女儿瞳瞳聊了几次。借着这次写作,她终于了解了母亲成为母亲前的经历,也得知了有她参与的这27年里,母亲对多少重大事件做过“善意”的隐瞒。由此,她开始重新看待母亲的种种“错误”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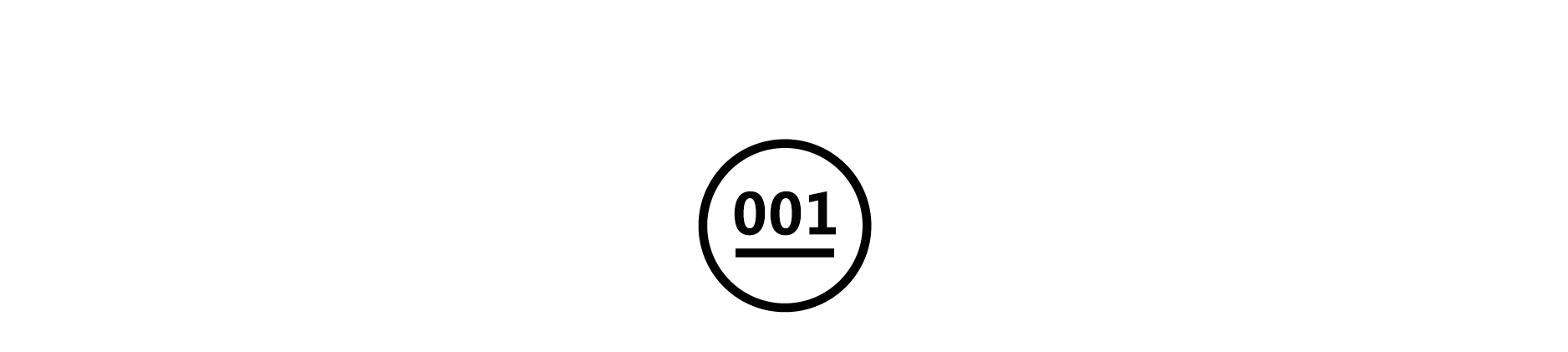
“您干嘛不自己写呢?”
瞳瞳听母亲念叨过很多次,如果把她的人生写出来,都能拍个电影了。
在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之前,瞳瞳并没有把母亲的话当真。她不知道,母亲在四十几岁时,曾一度以为这个愿望就要被实现了。当时她们的一位邻居在某知名导演手下工作,打算以晓虹为原型创作剧本。可惜,剧本最终没有完成。
后来瞳瞳步入社会,结交的人多了,愈发意识到母亲的人生并不平凡。当母亲再度提起自己的愿望,她便提议:“您干嘛不自己写呢?”
晓虹总是推脱:自己哪有那种文笔?上学时,她一直是理科好、文科差,数理化单科最低也有七八十,但语英政加起来都不过百。她读书很慢,必须朗读或默念,甚至用手指逐字指着,才勉强读进去。高考落榜后的40年间,她几乎再没读过书。
她想,自己这样的人写自传,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瞳瞳不这么认为。有次,她和朋友提起此事,朋友向她推荐了《秋园》。《秋园》的作者杨本芬奶奶也是五十几岁才开始写作,过去也是个普通人,从未做过文字工作。朋友对瞳瞳说:“你回去读读,让你妈妈也读读,(就会知道)她可以的。”
2023年1月,瞳瞳找母亲过年,把这本书带了过去。她问母亲:“她行,您怎么就不行?”接着,她给母亲念了这本书的前几页。“您看看,是不是语言挺质朴的?有很华丽的写作技巧吗?也没有吧。”
晓虹仍很犹豫。瞳瞳没有放弃,她坚信母亲是想写的,受过很多委屈的人,会有强烈的倾诉欲。
瞳瞳给母亲“打了三个多小时的鸡血”。最终触动晓虹的是《秋园》自序里的一句话:“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她想,自己未来也会面对这种境况。人死了,骨头也变成灰了,但写的东西会留下来,读的人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出现过。
于是,女儿返工后的某个上午,晓虹坐在客厅的餐桌旁,在手机的备忘录里一点点打出自传的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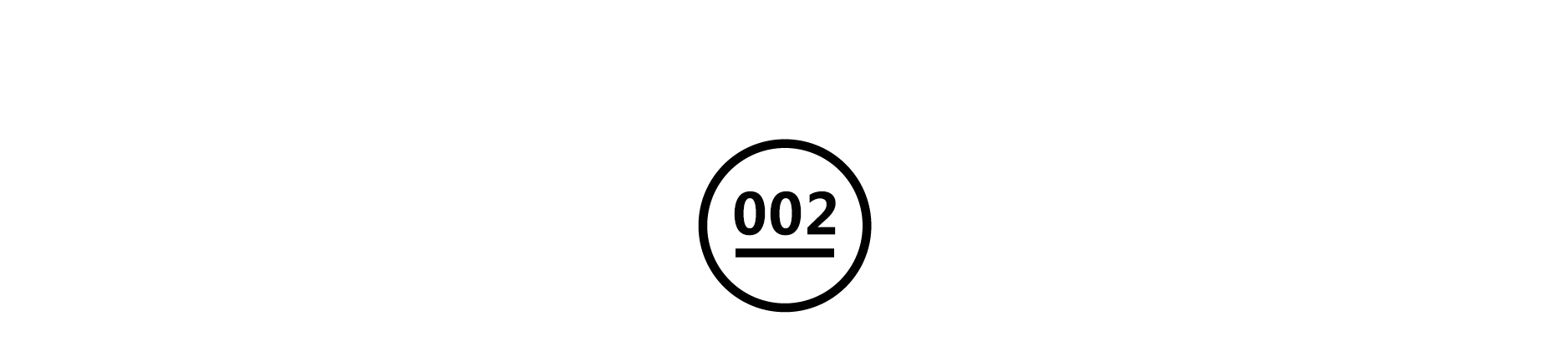
不受欢迎的孩子
“中国困难时期即将结束的60年代初期,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听起来像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但我好像不是这个家庭欢迎的孩子,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得到过父母的表扬,虽然家里的很多家务事都是我来做的……有段时间我觉得不挨打、挨骂,天都黑不了……”
故事从晓虹5岁讲起,那年她离开山东老家,去北京和父亲同住了8个月。那是她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相处,他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师,每半年探亲一次,因此晓虹对他印象不深,还闹出过“把爸爸认成叔叔”的笑话。
晓虹一到北京,父亲就什么都不干了,打水打饭、扫地拖地、甚至倒尿盆,都是她。当时的她还是个小不点,打水时,提着提手,暖壶会拖地,握着侧面的把手,开水又会洒出来。不过,她很快适应了父亲安排的角色。
那8个月是她被劳作困住的起点。从那之后,她承担了家里的大多数活:7岁,在寒冬里洗衣服,手冻得没知觉,却被父亲反复要求返工;8岁,开始负责全家的饭菜,第一次剁韭菜馅,因为剁得太碎被母亲痛骂;11岁,午饭时把襁褓中的弟弟带出去哄,回来发现父母没给她留一口菜;17岁,全家从校内搬到校外,“搬运工”只有她和父亲,她的脚趾被木箱砸中,鲜血直流……
相比之下,妹妹成年前只做过有限的家务,弟弟则像个“小皇帝”。家里订的牛奶都是他和父亲的,每天早上有人掐着时间帮他把饼干泡在牛奶里,他起床磨蹭了,还要呵斥:“奶都让饼干吃了,我吃什么?”
除了身体的劳累,晓虹还要面对心理的失衡。挨最多打的是她,得最少表扬的也是她。弟弟因为性别被偏爱,妹妹因为成绩被偏爱,而她几乎感受不到爱。
她很早就觉察到自己的优先级排在后面:妹妹出生前,她是和母亲睡的,有了妹妹,她就得和姥姥睡了。姥姥抽烟,床头还挂了幅暗色调的大胡子外国人的画像,她又呛又怕,只好把自己一直蒙在被子里。妹妹六七个月大时,长辈觉得无法再兼顾两个孩子,就把两岁半的晓虹送进了两周回一次家的全托。
这似乎为她后来的行为模式埋下了伏笔。学生时代,为了讨好父母,做家务时,她常常比要求的做得更多。家务挤占了学习时间,本就一般的成绩不见起色,距离父母的肯定也更远了。付出了这么多,挨打时更觉委屈,“咬牙切齿地看着,眼睛含着泪,就不哭出声来”,父亲看她不服气,便下手更狠。
她走入了死循环。
高中时,晓虹有了离开这个家的想法。“只要自己可以出去挣钱了”,就有希望。
1980年高考,她落榜了,意料之中的结果。她干了两个月临时工,之后凭借自己的理科积累,考上了高校的实验员岗位,得到了一份操作离心机的工作。
那份工作的工资是每月32块。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父亲就要求她给家里交钱:“如果结婚不用家里出钱,就每个月交15块钱的伙食费;如果结婚由家里操办,就交30块钱,包括过年做衣服也由家里管。”她揣摩父亲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交30块”,为了不惹他生气,她选择了每月只留两块钱。
不过,这钱只交了一年。一次,她和弟弟闹别扭,弟弟学着父亲的口吻怼她:“看不惯就别看,不愿在这个家就滚。”她问父母,弟弟有权利让她滚吗?父亲说,有。她心一横,找个借口申请了宿舍。
几个月后宿舍批下来,本来气已消了,但弟弟又对她说了同样的话。于是,20岁的一个深夜,晓虹哭着离开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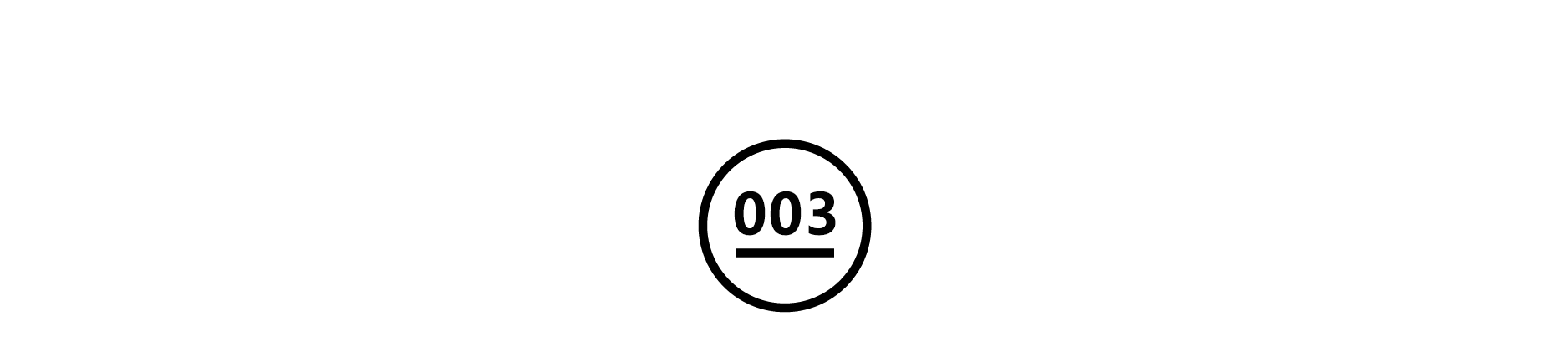
只能通过结婚离开
22岁那年,晓虹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公派留学日本的研究生,犹豫着要不要和对方接触。
那两年,她虽然住在宿舍,但实验室的领导认识父亲,专门敲打过她要“经常回家看看”。为了保住工作,她只好偶尔回去。家里只有姥姥欢迎她,其他人都不冷不热,有时连饭都不留她吃。她想,如果和这位研究生合得来,去了日本,就离家更远了。
身在异国的两人通过书信交往了几个月。男人在第一封信里就谈起他的计划——在半年后的假期回国和晓虹结婚。
找个知识分子成家,当时的晓虹是满意的。从小生长在高校,身边都是有学问的人,自己却学业平平,总被父母贬低,因此对这种“学习好的人”,她不自觉地戴上了崇拜的滤镜。“如果他不挑剔我,我有什么挑剔他的呢?所以如果不成,那肯定是他不满意我,他只要没问题,我就不会有问题。”
然而,当两人终于见面,情况却和她的设想相反:男人似乎很喜欢她,对她没有任何不满,她对男人的印象却不太好。他长得和照片有不小的差距,吃东西时还总发出吧唧嘴和牙齿碰撞的声音,最重要的是,见面第一晚,他不经同意就在路上对她拥抱亲吻,哪怕她说“给我点时间适应一下”,他还是用力搂着她走。
后来晓虹才明白,这不是适不适应的问题,她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但在当时,没人支持她对这种异样多作思考。最要好的同事笑她老古董:“可能你们没有时间谈恋爱,只能加快进程,人家是奔着结婚去的,又不是耍流氓,人家没错。”
最终迫使她接受这段婚姻的是父亲。面对她“不想结婚”的告白,父亲的反应是:“这事弄得满城风雨……人言可畏啊,以后你还结不结婚了?”那时正在重映60年代的老电影《李双双》,主角夫妻先婚后爱,父亲对她说,你也可以。
就这样,在见面的第4天,晓虹和这位准博士领了结婚证。
她用朋友借的几百块飞到日本,一边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一边努力地学日语、打工。80年代的日本正处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她打工一周的收入就够还朋友钱了。很快,她便像第一次离家那样,再度实现了经济独立。
但对丈夫的抵触情绪始终都在。她愈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真的不能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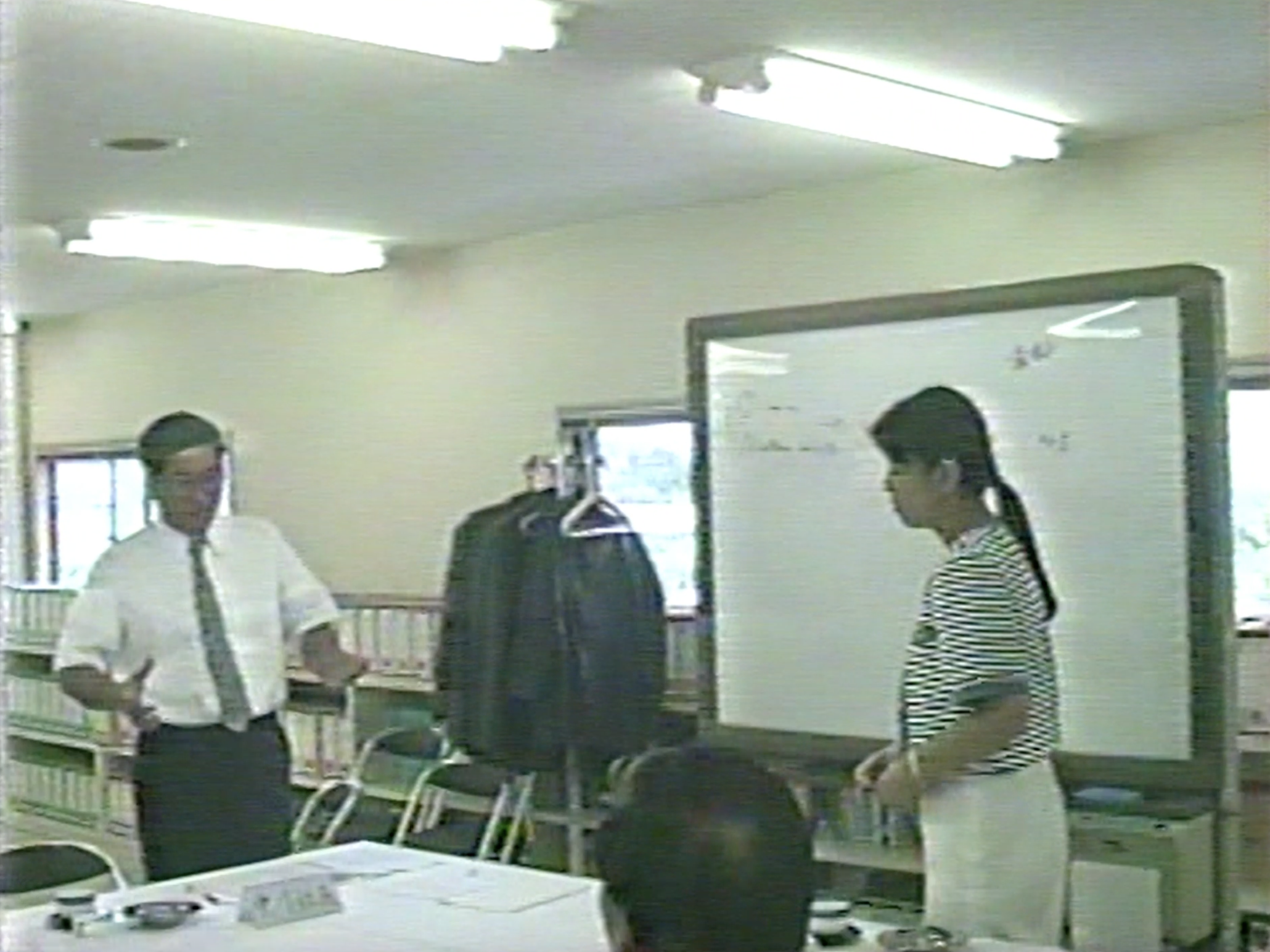
在日本时,晓虹为一次学术交流做翻译
次年她回国探亲,默默决定不再返回日本,和丈夫分开生活。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学业,她准备等他博士毕业再提离婚。
又是父亲改变了她的决定。当时她正在给丈夫写信,说自己会暂时留在国内,父亲在另一个房间说了几句,她没听清,被父亲冲过来狠狠打了一巴掌,连人带椅翻倒在地。这一巴掌,使她把写到一半的信撕掉,重新写了一封,说自己会很快买机票回去。
为了离开这个家,她又回到了和丈夫的家。
我问她:“当时有没有想过第三种选择呢?”她反问我:“哪有?哪有第三种选择?”
那个年代,她能想到的离开家的方式,一是工作,二是结婚。她之前的工作就在全家待了数十年的高校里,那时很多人的工作都是干一辈子的,她无法通过工作离开家,只能通过结婚离开。
此前,早有朋友劝她通过生育来调节夫妻关系,到时会放很多精力在孩子身上,就没时间和丈夫吵了。她总觉得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再做考虑。婚后第3年,“给自己的后盾”似乎足够厚了,她和丈夫开始试孕,好消息却迟迟不来。
半年后,丈夫查出不育。晓虹很喜欢孩子,这个消息令她备受打击,“但也给了我一个理由不跟他凑合了”。
她后来得知,前夫再婚后有了孩子,他并非完全不能生育,只是概率很低。我感慨道,如果当时知道是这种情况,她会怎样选择呢?她想了想,可能会再凑合几年,但最终还是会分开吧。

结束第一段婚姻的晓虹,和朋友合租在4.5贴榻榻米(约7.3平米)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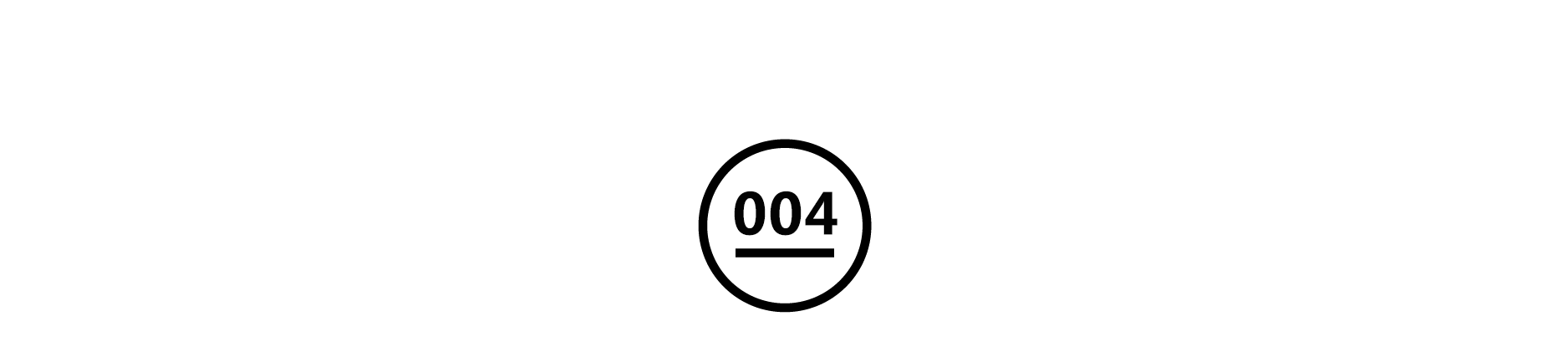
“他肯定打不死我”
1993年初秋,晓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当时她回国办事,在北京开往山东的火车上,与同车厢的男乘客一见钟情。男人比她小7岁,长相酷似日本当红演员加势大周。两人很快确认关系,在认识的第5个月结了婚。
婚后,男人变得陌生起来。原本温和的人,常常莫名地发火、摔门而出。和晓虹去到日本,只工作了不到一个月就躺平了,晓虹提出教他日语,他也不学。
他们很快有了孩子。晓虹生产那天,原本他是在产房里陪产的,后来因为晓虹情况不好,需要急救,护士就请他出去。晓虹死里逃生后,却发现他不在医院。第二天晓虹问他:“你就不想知道我是死是活吗?”等来的是一句漫不经心的“你死不了”。多年后她才得知,他说那晚回家了是谎话,真相是,他在游戏厅玩了一夜。
晓虹最不能接受的是他的暴力行为,女人、孩子他都打。在她的自传里,仅儿子男男出生的第一年,就有至少4段这样的记录——
“出生第10天夜里,男男醒了……我赶快去外屋冲奶粉,还没冲好,突然哭声就没了。我跑过去,看到他歪坐在孩子旁边,一只大手捂住了孩子……趴在孩子耳边大声喊着:‘哭,我让你哭’。我跑过去一脚把他踹到一边,大声说:‘你有本事摔死他!’他居然真的双手把孩子举过来头……”
“一天早上,正准备给孩子洗澡,刚把男男脱光放进澡盆,他推开与厨房之间的门,一股寒风扑进来。我喊他快关门,他没听见一样穿鞋,推开大门就要出去……‘关上门啊混蛋!’他穿着鞋跑回来,不知是用脚还是手给了我后背一下,我被他推得往前趴过去,男男被扔到水里,水一下就没过了脸……”
“某天我在做饭,让他给孩子换尿布,孩子不会老老实实配合,总是翻身,把他惹烦了,一大巴掌打在孩子屁股上………”
“我在里屋抱着孩子喂奶,因为什么事跟他吵架……他跑进来时我正抱着孩子,怕他伤着孩子,就赶快站起来,背对着他,把孩子护在怀里。他拿起皮带,握着皮带尾朝我狠狠抽来,皮带绕过我的腿,皮带扣抽到了左大腿后面,飞了出去………”
见面后,我问晓虹:“他打人的时候,你会有恐惧吗?”她的回答令我有些意外:“我就是怕他打着孩子,我倒不怕,他肯定打不死我。”
她说,如果他打得太狠,自己一定会还手。虽然她也知道,还手过去,一把就被抓住,“根本打不了他”,但从她的语气里,我听不到一丝怯意。
她向我坦承,如果不是父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声称要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激起了她的反抗心,她不会那么快就结婚。如果婚前相处得更久,男人把更多的样子暴露出来,她或许就不会和他更进一步了。
要不要离婚?这次的抉择比上次更难。他们已经有了孩子,她还是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而且这个男人是她自己选的,如果还是过不下去,父母肯定要看她笑话。最重要的是,这是她“打心底里喜欢过的人”,那些美好的记忆会把她从愤怒和失望往回拉。
长久的犹豫中,她再度怀孕。
这是个计划外的孩子,她“不想在摇摆不定的婚姻中再让另一个孩子跟着受罪”。甚至就在刚刚得知她怀孕后,丈夫又因为琐事引发的口角给了她一拳。
她尝试了药物流产,没有成功。或许这个孩子还是想来,她这样想着。这个被留下来的孩子就是后来鼓励她写作的女儿瞳瞳。

晓虹为刚刚满月的瞳瞳洗澡
二孩出生后,丈夫没有任何长进,依旧是工作不干、家务不做,孩子不看,“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我怎么会有(离婚)这种想法’的表现”。
但最终先把离婚说出口的并不是晓虹。这两个字是丈夫施暴后的口头禅,晓虹深知他不久就会把它收回,然后道歉、承诺、讨好。他吃准了二婚的晓虹不敢再离。
然而,那次晓虹终于下了决心。她想通了,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更不好,每次丈夫当着男男的面发飙,男男都会使劲搂着她的脖子,腿也紧紧夹着她的身体,她能感觉到男男的恐惧。男男已经有了创伤,趁着瞳瞳还小,不如尽早和这个施暴者分开。
她很快带着两个孩子搬了出去,开始了单身母亲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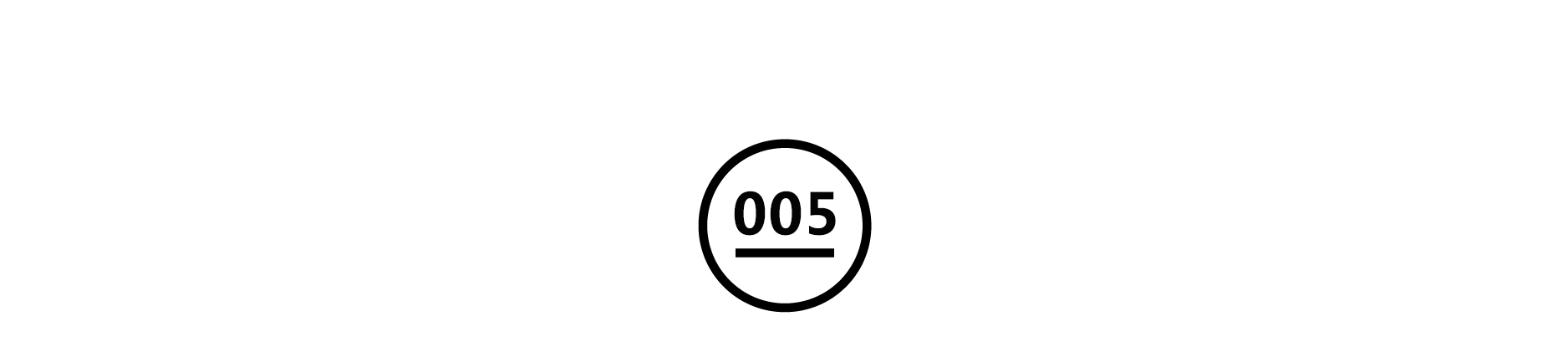
好母亲,坏母亲
1997年末,晓虹推着男男、抱着瞳瞳,独自拿着72公斤的行李回了国。当时的她并不担心自己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在日本生活了11年,挣钱是她最有把握、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她先后做过近十种工作。前几年挣的是辛苦钱,在拉面馆做面点、在西餐厅洗碗、在服装厂踩缝纫机、在商场和电车站门口卖糖炒栗子、在办公楼当保洁、在居酒屋跑堂……后来脱离了体力劳动,入职软件公司,从零开始掌握了电脑制图。
第二段婚姻开始前,她琢磨出向日本介绍研修生的生意。婚后几年,生意走上正轨,每月能按人头拿到不菲的管理费。离婚时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手下的研修生有23个,高峰时的月收入折合成人民币有七万多块。
回国后,她立刻请了住家保姆,又买了套新房,是178平的复式。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比周围的同龄人要好。

2000年,两个孩子在晓虹买的大房子过的第一个春节
不过,经济实力是一回事,给予孩子的陪伴是另一回事。
为了把劳务输出的生意继续下去,晓虹每年至少有两三个月不在北京,要去外省过目别人推荐的研修生,还要去日本办手续。她不在时,保姆分身乏术,临时找亲戚帮忙也非长久之计。因此,男男升小学那年,晓虹便为他选择了寄宿学校,同时,4岁的瞳瞳也被转入寄宿幼儿园“提前适应”。
我和瞳瞳聊过,童年的她是否缺少母亲的陪伴?她说,只能在周末见到母亲,对她而言“是很痛苦的”,每到周日晚上她都会哭,“觉得特别孤单、特别悲哀”。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晓虹。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个可能得问瞳瞳”。
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地去成为一个好母亲:
在日本时,她每周末都和孩子们通话,直到他们不想说了才挂断,每次几乎都有一个多小时。去趟日本,话费就得花掉几千。
在北京时,周末总被她安排上有趣的行程,去吃孩子们爱吃的炸鸡汉堡,或者带着帐篷和手提冰箱去郊区露营,延庆、昌平、顺义、平谷,都留下过他们一家三口的足迹。
男男时不时邀请同学到家里,每次算上家长有十几号人,她会做日式咖喱饭和御好烧来招待,大家都很喜欢。久而久之,“能去男男家玩”成了家长激励子女完成课业的筹码。
每年圣诞前,她会和孩子们一起装饰圣诞树,挂上彩球、缠上彩灯、用棉花作积雪。然后关上灯,让他们在圣诞树前许愿,说出自己想要的礼物。在一旁偷听完,她悄悄买好礼物,等到平安夜放入孩子们的圣诞袜。

晓虹录下了孩子们对着圣诞树许愿的画面
在自传里,她回忆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刻:“孩子们第二天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激动地查看圣诞袜。看他们被我‘骗’到的兴奋样子,我觉得好笑又幸福。他们总是好奇圣诞老人是怎么进来的,我说圣诞老人会穿墙,他们于是想不睡觉,等着看圣诞老人,我说不入睡圣诞老人就不会来……”
这份美好没能持续。渐渐地,在孩子们面前保持从容开始变得困难。
成为单身母亲的第6年,晓虹第一次发现男男偷家里的钱。惩罚从警告升级为痛打,后来还请派出所的民警帮忙教育,他仍屡教不改。
上初中后,他沉迷篮球,上课不听讲、放学不回家,成绩直线下滑。中考前给他请了住家老师,他却假装学校还没放假,每天掐着上下学的点去打球,把老师晾在家。
高一时,因为在球场得罪了学校的混混,他一个多月没去上学,也没参加期末考试,被学校劝退。好不容易有学校接收,他又偷偷翻墙出校,买了很多啤酒请同学喝,背了处分。偷不到现金,他就盗刷晓虹的信用卡,取了8000块,全买了耐克鞋。
另一边,晓虹的生意也出了问题。
2005年,她服务的日本工厂砍掉了一半的研修生名额,她的收入随之腰斩。3年后全球金融危机,日本深受波及,为了提高本国人的就业率,将中国的研修生名额从300万缩减到30万以下,她经手的研修生通通被拒,生意就此断了。
当时她和孩子们已搬进更大的房子——一栋252平的联排别墅,每月要还一大笔房贷,孩子们在私立学校的开销也不小。强烈的危机感下,她急着寻找其他挣钱的渠道,却一次次陷入骗局:被假古董商骗了40万;被表弟拉去给违规的彩票店投了80万;被朋友带进网络传销,损失了20多万;别墅也被人拿去抵押贷款,承诺的高额利息却没履行……
她的精神一步步到了崩溃边缘。那个笑容多过冷脸的母亲不见了,当两个孩子“不听话”时,她的愤怒很容易被引爆,动手的频率越来越高。
瞳瞳记得,从初中起,她不再觉得晓虹是个好母亲。家里常年气氛阴郁,母亲和哥哥上演过“很可怕的场面”,母亲也总向她“撒邪火”,最狠的一次,打得她从脖子到大腿全都是伤。相比于状况频出的哥哥,她并没有做过什么“值得被那样对待的事”,母亲能用的理由,几乎就只有她的屋子比较乱。
上一代粗暴的育儿风格被晓虹继承,而她多年后才有所察觉。“我小时候是这么挨打长大的,到了孩子让我生气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孩子们终有长大的一天。男男高中毕业后去了日本,不论申请学校还是打工,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依然没有改掉他的贪婪,晓虹填不完的窟窿,他就找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填。
瞳瞳再度对母亲改观是在成人礼时,母亲在学校统一要求下写的信,竟让她泪流满面。信的内容她已记忆模糊,但整封信满溢的、毫不掩饰的母爱,她如今回想起来,仍有暖意在身体里升腾。对母亲的恐惧和抵触,在她流露出这一丝的柔软后,瞬间消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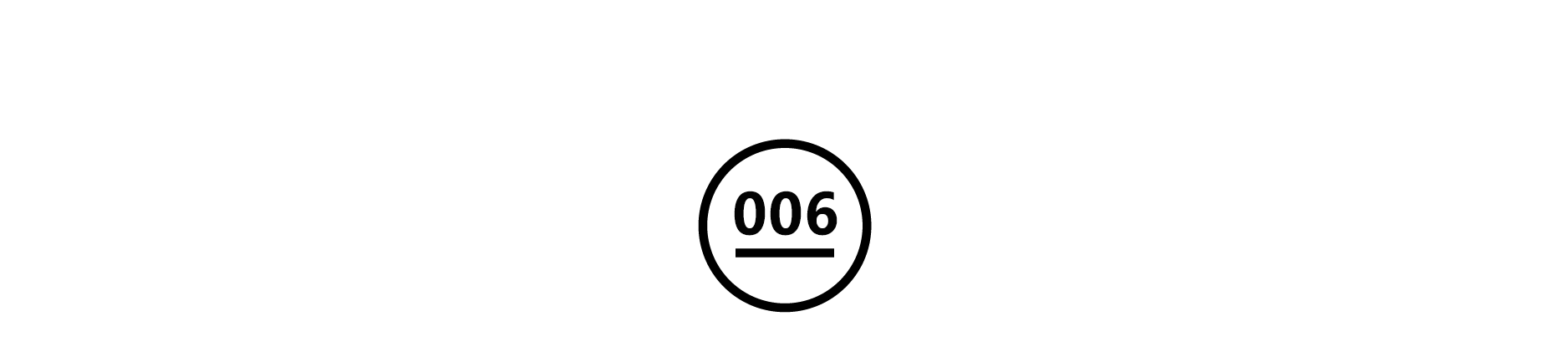
重新认识母亲
晓虹写的每个章节,瞳瞳都是第一位读者。晓虹告诉我,如果没有女儿的鼓励,她是坚持不下来的。她原以为自己能“写个几千上万字就不错了”,没想到最终写了近21万字。
女儿曾经给她发过一张图片,两个年轻女孩窝在沙发里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她们都在读您的自传,希望连载给她们”,读者沉浸的神态给了她最直观的鼓舞。

晓虹和瞳瞳的聊天截图
此前,瞳瞳对于母亲还是女孩时的人生不太能感同身受。她从三四岁起就听母亲唠叨姥姥姥爷的暴力和偏心,二十几年,一再面对激动的倾吐,她似乎免疫了。
“但文字是平静的。” 这次她终于能沉浸到母亲的讲述中,去体会母亲半个世纪前的生活。在母亲的自传里,她第一次得知了舅舅儿时的种种行径。她很少听母亲讲舅舅的坏话,没有这些,她无法“真正get到”母亲当年的感受。
对于母亲的第一段婚姻,过去她仅有的信息来源是两三年前偶然翻到的一份材料,那是母亲第一次离婚时呈给法院的。其中令她印象最深的,一是那个男人曾想强行和母亲发生关系,二是母亲刚到日本时不会说日语,也没有经济来源,当时她看到同胞见面会的海报,激动地拿给丈夫看,想请他陪自己去参加,结果被随意敷衍过去,没有去成。
“我当时看了特别心碎。”回忆至此,瞳瞳哽咽了,这是我们几次谈话里她唯一的哭泣。她说,从小看到的母亲都是“风风火火的女强人”,而母亲写下那份材料时,比她看到它时还小几岁,她想象出一个低姿态的女孩的模样,内心备受冲击。同时,她也给母亲的第一任丈夫定了性——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对母亲没有爱。
但在自传里,母亲写到他时,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怨气,对他的某些缺点也着墨不多。相比于那种恶狠狠的形象,他更像个书呆子,有些传统,有些邋遢。而且他是喜欢母亲的,母亲提出离婚时,他一直在挽留。
过去,母亲口中的父亲和她眼中的父亲也判若两人。她听得最多的,就是父亲不管孩子,甚至对哥哥下过狠手。
有记忆以来,她和父亲见面的次数两只手数得过来:小学时,心理上依赖母亲的她,即便见到的父亲看上去很温柔,仍默认他如母亲所说“是个混蛋”;初中时再见父亲,“既没有很抵触,也没有很喜欢”;高考后被邀请到父亲的城市,开始感受到他出于亏欠而努力想让自己开心,加上他的一些正义之举,对他有了些好感,也怀疑母亲谈及他时是否夸大其词。
通过母亲的自传,她认为有了相对客观的视角去看待父母的关系。除了早已熟悉的对孩子不负责任的父亲,她也看到了被爷爷奶奶捧在手心的父亲,和母亲刚刚相恋时的父亲,以及到日本后被母亲养着、自暴自弃的父亲。“他们那会是无解的,我爸要想成熟,必须失去我妈。”
离婚后,瞳瞳的父亲明白无人依靠,开始努力学日语、打工。后来他入赘到一位日本女性家,认真工作,参与育儿,也不再家暴。晓虹对此并不愤恨,她同意瞳瞳的观点,和自己在一起,这个男人是不会改变的。但她不后悔:“不后悔和他离婚,同样地,也不后悔和他结婚。”
刚回国那几年,很多朋友给晓虹介绍对象。她对再次组建家庭没什么兴趣,但盛情难却,就去见了几个人。后来她和朋友说开了:“人家不是丧偶的就是离婚的,他有他的孩子,我有我的孩子,那不是两个人过在一起,是两个家庭组成在一起。”她觉得肯定会围绕孩子产生很多矛盾,自己不擅长处理这些,就断了再婚的念想。
她说不准对爱情本身还是否有向往。很多时候,她不想再去喜欢一个人:“我这人是付出型的,如果真的喜欢,我一定会付出很多。付出太多,就会受委屈。”她不怕付出,但不希望再受委屈。
有时她又怀疑,要是真遇到了那个人,会不会又推翻这些想法?“可能也会想跟他在一起,无论结不结婚。”但这二十多年,她再没遇到过心动的人,再没体会过当年在火车上和看到瞳瞳的父亲时的那种悸动。
对于最黑暗的那段日子,瞳瞳也有了新的认知。
2015年,没有收入又屡屡被骗的晓虹忍痛卖掉别墅,填了各种窟窿后,剩下四百多万。那笔钱足够她后半辈子租房生活了,但她丝毫不能释怀,像接连输钱的赌徒一样,“老想找个机会捞回来”。
一个姓周的男人给她画了很多饼,北京、内蒙古、山东都有大生意可做。老周连哄带骗,把她的四百多万几乎全拿走了。受其牵连,她甚至因为涉嫌合同诈骗进过派出所,被释放后,当地的混混堵在派出所门口,她手机被抢、车胎被扎,想尽办法才脱身。

晓虹拎着从渔民那里买到的海鲜,沿着海边回出租屋
那几年,晓虹不止一次想过自尽。被抓那次,她一度担心自己的命就要交待在那了。但她从未和孩子们袒露这些。
因此,瞳瞳对此一概不知。六年级时,她第一次听母亲说家里的收入降低了很多,但初中3年,她并未感觉生活质量有明显下降。直到高中,她发现母亲会严厉地要求他们,不在房间就要把灯和地暖关上,稍有松懈就引来高声呵斥,她才对家里糟糕的经济状况有了实感。
家境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她读了母亲的自传才清楚。在老周集中出现的章节,她批注道:“妈妈是个骄傲的人,脆弱的心境不会说出来……那时我只知道要卖房子了,很难过,不知道妈妈压力大到不想活,更不知道这些可怕的事。希望天下父母都可以平等地跟孩子沟通,放下‘父母枷锁’,适当展示脆弱有利于父母和子女的相互理解!”
站在新一代独立女性的视角,母亲的很多决定都是瞳瞳做不出来的。她会直白地对母亲表达自己的看法:母亲为了摆脱姥爷而踏入婚姻,她说“等于对婚姻没有冷静思考”;母亲不想和第一任丈夫凑合,又怕离婚后会被指指点点,她说“他们说就说去呗,管他们呢?自己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亲戚借钱不还,母亲心里憋着气,又顾及脸面不想太强势地去要,她说“面子最不值钱了”……
很多时候,母亲也觉得当时的决定是错的。听了她的话,会回一句:“我当时要能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但瞳瞳也对母亲说,自己没有生长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她去走母亲的路,或许也会有相似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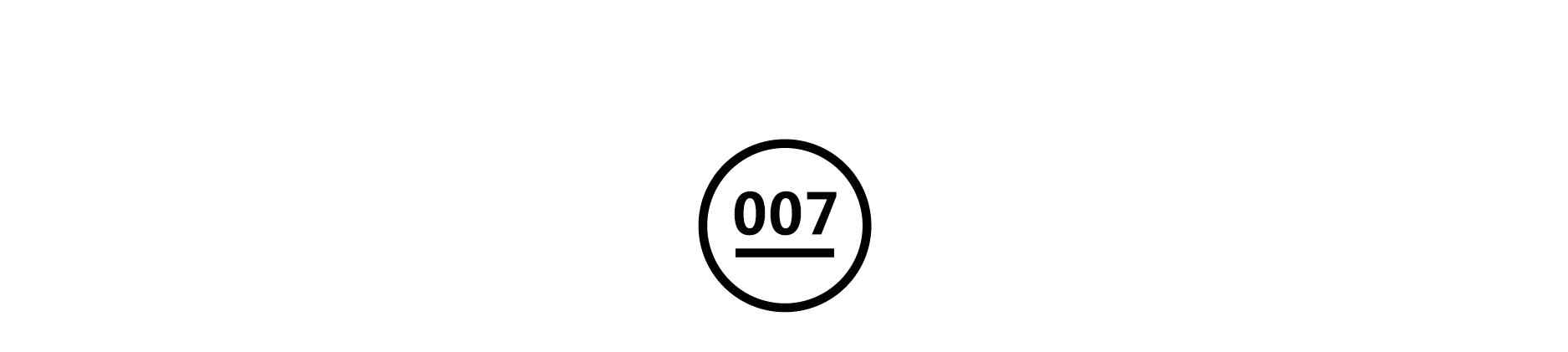
“把开水泼回去”
我曾向瞳瞳分享贯穿整个阅读过程的矛盾感,也是最为晓虹惋惜的点:
一方面,她敢于出走,而且行动力很强。比如,和弟弟吵架那次,她连夜搬出了家;向第一任丈夫提出离婚的第二天,她就拖着箱子去投奔东京的朋友;为了让自己在经济上更独立,面试软件公司时,从未摸过电脑的她,逼着自己用5分钟记下了键盘上所有字母的位置。
另一方面,她在出走后,并不总能在心理上与想远离的关系成功切割,尤其是在原生家庭方面。做实验员时,尽管是领导敲打她回家看看的,但她每次都会主动买上五六块钱的吃喝(那时她每月的伙食费还不到10块);第一次结婚前,她把两三年的积蓄拿给父亲买冰箱,导致婚后不得不借钱买机票;到了日本,大件的进口指标都留给了家人;后来做劳务输出,各种亲戚是最优先的,还让表弟“帮忙”搜罗了好几年候选人,把费用分去一部分。
为何母亲总是不能100%地出走?瞳瞳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觉得母亲一直渴望被认可,尤其是被姥爷认可,那种渴望甚至到了“钻牛角尖”的程度。
瞳瞳的猜想很准确。晓虹和我讲了更多自传没有提及的“断亲未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每次从日本回来,没换完的日元和用剩的人民币都归父亲。“他说,那个钱别带在身上,再丢了,留下吧,等你下次回来再花。下次回来,(他)还给我吗?肯定不给我了。”正当我默默为她打抱不平,她接着说:“其实我每次都多带,就是为了给他留下。我不还是为了让他高兴?这就是我傻的地方。”
将母亲的自传上传到豆瓣时,瞳瞳将标题定为《谷底不黑》。晓虹觉得这个标题蛮贴切的,自己的一生的确很坎坷,尤其是卖房后,别说谷底,都到地底下了,但她并不认为这些经历很灰暗,如果有重来的机会,她还想要跌宕的人生。
自传开始连载后,陆续有了成百上千的读者。晓虹特意注册了豆瓣账号,每次更新后的两三天,常常蹲在评论区。留言的大多是陌生人,有称赞她生命力蓬勃的,有共情她赚到钱时的开心的,有赞同她离开家暴丈夫的,也有心疼她掉入骗局的。她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正反馈,原来“我的这些经历对别人是有价值的”。
但她依然觉得,这辈子“没有哪个阶段符合我定义的成功、或者让我特别满意的”。她说自己始终是失败者。
这几年,晓虹独居在日照。起初她是为了老周口中的工程而来,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这座四线城市,绿化好,气候也舒服。她租了套70平米的二居室,10分钟就能走到海边,她每天都去散步。回到家,那只名叫栗子的暹罗猫一定在门口迎接她,就像她的另一个孩子。瞳瞳把自己的名字给了这只猫——她的英文名是Lizzy,读起来就像栗子。

晓虹与栗子
每月,晓虹能领到两千多块的退休金,已经工作的瞳瞳也会给她打钱。除去1250块房租,手里能有三千多块,足够维持生活了。
最终章发布前,晓虹断更了两个月。她一直对瞳瞳说,老周的生意是假的,但日照的工程是真的,她已经辗转联系上了“真正的”施工方,为自己谋了份差事。她相信,等了7年的工程就要开工,等自己拿到工程款,给自传“一个快乐的结尾”。

晓虹在日照的海边放风筝
瞳瞳不希望母亲一门心思等着这个很可能不存在的工程。她相信母亲还有很多可能性:母亲会说日语,可以偶尔给日本人当当地陪;母亲做饭好吃,可以接点上门做饭的活;母亲的手很巧,还在服装厂工作过,可以试试给宠物做衣服。挣钱不是目的,主要是给生活填充点新的色彩。可母亲总是说:“再说吧,我现在没那个心思。”
最终,在瞳瞳的劝说下,晓虹给自传收了尾。在结尾里,她写下了自己最理想的生活:“在一座漂亮的山里弄一块地,亲手砍木头盖房子,弄个大院子,在院子里种菜、种花......”就像李子柒那样,她这样向我概括。我鼓励她,现在就可以尝试这样的生活,但她觉得还不是时候。

晓虹与瞳瞳的近照,两人一同去看电影
这几年,她的朋友圈签名一直是:“面对别人泼的冷水,先接住,等烧开了,再泼回去。”她仍在期待“把开水泼回去”的那天。
她盼着让老周付出代价。她咨询过,如果起诉老周,律师费至少要20万,但老周已经无钱可赔,这20万注定是要打水漂的。老周如今正因另一桩诈骗案在监狱服刑,预计2025年春天出狱。她希望在那之前通过工程赚到大钱,起诉老周,延长他的刑期。可能的话,再给妹妹和两个孩子买几套房子。
(本文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实习编辑吴争对文本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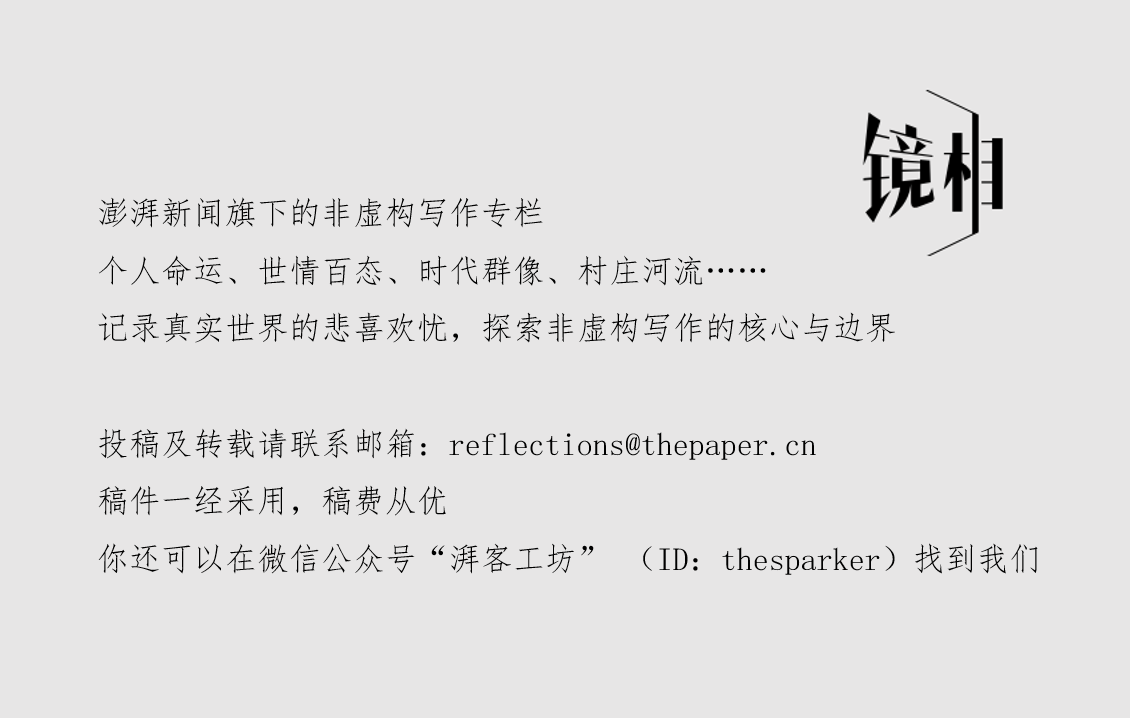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无缝衔接上帆时间
- 廊坊4.2级地震,京津冀有震感
- 一批房产类“自媒体”被禁言

- 机构:中国大陆云基础设施服务支出将在2025年增长15%
- 恒指早盘微涨0.25%,恒科指走强0.79%

- 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是
- 敦煌莫高窟的主要艺术形式是雕塑和

- 13假如AI欺骗了你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