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 +1647
藏族拳击少女:无法“热辣滚烫”的人生丨镜相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作者丨杨海滨
编辑丨柳逸

图源:电影《百元之恋》
昂亲拉毛在乱了方寸的脚步中,被对手一拳打破额头,汗水滑进破烂的肉里,和渗出的鲜血混成一串血水珠。但她还是努力提防朝她飞来的拳头,在血肉模糊的视线中,脑袋左侧再次被击中,整个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到场边的绳前。幸好没被击倒,她很快调整好步伐,回到台中继续跳跃着脚步,准备进行反击。
就在她的来回跳跃中,头上的汗珠继续如溪水般,流进不断渗出鲜血的伤口,混成一股血水流进眼眶。视野红彤彤,如无边无际燃烧着的森林。套着拳套的手无法擦掉血水,她只能不停地眨着眼,想看清并阻挡飞来的拳头,欲发起反攻。
但血水如瀑布,模糊了她的全部视线,对手立刻发现了她的破绽,又一次发起密集的进攻。她挨了一拳,踉跄着往后退,对手抬腿飞来狠狠一脚,结结实实踢在她的腰部,她倒在地上。
须臾后,裁判员举起她俩的手,宣布对手胜利。她没能体面地坚持完这个仪式,疼痛中,像爆了的气球瞬间瘫瘪。
医院的CT显示:她的两根肋骨被打断。
这一幕发生在2022年秋天,武汉洪山体育馆。她明白,这里成了她职业拳击生涯的最后一战。命运像在开玩笑,十七岁那年,也是在这个赛场,她第一次上场,被打得落花流水。
时针慢慢拨开八年的距离,她又重回原点。如奔驶的卡车猛然掉进深渊,她的梦想戛然而止,她不得不接受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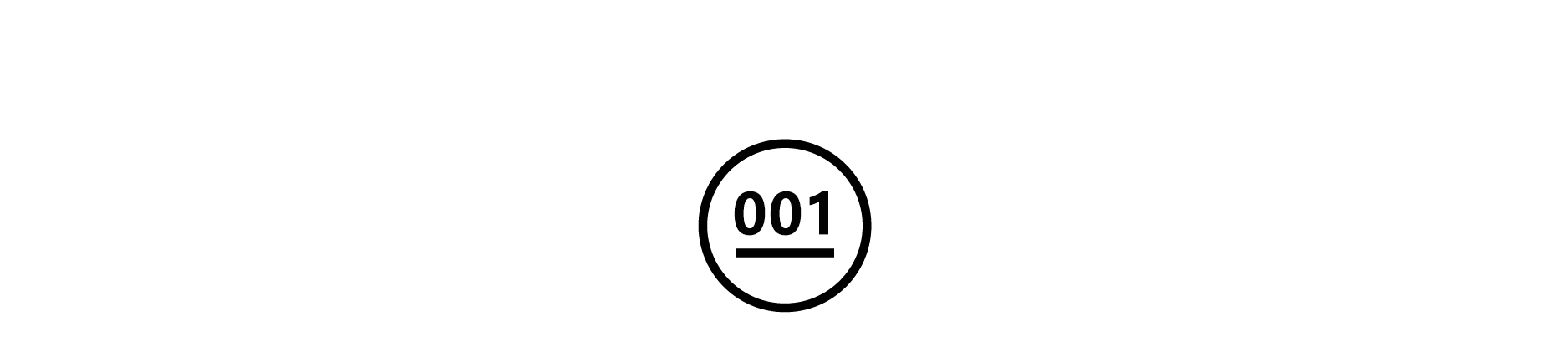
出高原记:“不是打架,是搏击!”
2014年夏,她第一次代表青海队来到武汉洪山体育馆参加拳击赛,第一次看到赛台四周黑鸦鸦坐满了人。聚光灯照在赛台中央,轮到她出场时,观众喧嚣如潮水的呼叫令她窒息,不由怯了几分。张翎教练拍着她的肩膀让她放松,第无数遍朝她吼:“你时刻记住我要胜利!我要击倒对手!我永远不会被打败!”
两年前在寒冷的青海省果洛高原,她在花石峡寄宿小学接触到搏击的第一天,张教练就灌输给她这样的理念,她也把它当成了箴言。她从慌乱的哆嗦中恢复了感觉,从容地走上赛场。但毕竟是第一次上阵,她敌不过对手的凶悍,在懵懂中败下阵来。

图源:电影《百元之恋》
她沮丧地回到多巴训练基地,张翎教练针对她的心理、体力和战术又训练了一年。每天流的汗够晚上她洗脸用,胳臂无数次地脱臼,手指打断过三次。又一年后,她在石家庄体育馆的女子赛中获全国第八名。
她想,我要拿全国第一,给父母和果洛藏人一个交代。2018年,她在郑州全国比赛中获第六名,渐入佳境的感觉让她洋洋得意。但体育竞赛从来就是高原上变幻无常的云,后来的比赛都没超越以前的成绩。
2022年肋骨断裂后,医生告诉她,以后再也不能从事搏击运动了,否则肋骨再被踢会影响内脏,有生命危险。她将电话打到张翎教练那,对像父亲一般的张教练哭泣。她就是在十六岁被他发掘出来的。
十岁那年,有天花石峡公社书记到冬给措纳湖检查牲畜成活率,看到她和大姐正在波光粼粼的湖岸上骑马,唱着阿妈教的高亢嘹亮的格萨尔歌曲放牛。书记上前问她:“你几岁了?上学了吗?”她说:“我十岁了,家里的牛羊太多,我要和姐姐一起放牧,阿爸不让我上学。”
书记扭头问她阿爸:“你应该把她送到花石峡小学上学。”阿爸说:“照顾牛羊比上学重要。”书记说:“再有钱也不等于有文化,尤其在咱们这样的偏远牧业点,适龄儿童一定要上学,政府免学费。”半年后书记再次来到冬给措纳湖下帐,见昂亲拉毛还是在骑马放牛,便在临走时硬把她带到花石峡寄宿小学。她成了超龄小学生。
上五年级的某天,她从电视里看到一档现场直播节目,俩女生在赛台上凶狠搏击,打得面颊鲜血淋淋的,她深受震憾。她在看那画面时脑里闪现出母亲坐在湖岸上唱着格萨尔史诗骑着骏马,在草原上与恶魔搏击的画面。这画面一下唤醒她心底的英雄主义,她想着要当格萨尔那样的女英雄,首先需要搏击的能力,这搏击正好能实现她的梦想,尽管她这时还没分清传说与现实的区别。
此后,她常到老师办公室要求看搏击节目。老师说这节目不是你想看就能看的,得等转播。她于是便在操场上自己模仿、练习起搏击动作。
有天放学,她像往常一样在寒冷的操场上,学着从电视节目里看到的搏击运动员的动作比划,恰被来支教的张翎看到。张翎好奇地走到她跟前,问:“这动作你是从哪学来的?”她说:“电视里。”
“你喜欢搏击?”
“他们打架打得太酷了。”
张老师纠正:“不是打架,是搏击!是体育竞技!”
她又说:“我想学打架,练一身本领回冬给措纳湖,像格萨尔一样保护我们的牧人和牛羊。我也想到内地去打架!我可以打败她们的。”她眼睛里充满了向往,将视线转向天空。张翎则再次纠正:“不是打架,是搏击运动。概念不要搞错了。”
这个纯真的藏族女孩给张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时刚从青海搏击队退役,被朋友邀来花石峡这所牧区小学支教,当体育老师。张翎觉得她是自己想在草原上物色的人选,就在每天放学后指导她学搏击动作,并让她坚持练习其中的几个动作十天,想考验一下她有无恒心。
她不知道这是考验,只想着老师愿意教,她就要好好练习。在这所地处海拔4500米、四季无夏的寄宿小学,无论是滴水成冰的早晨还是浓密的雪天,她都会在操场上训练。这种坚持和一般女孩的三分钟热度不同,让张翎看到了她所具备的成为搏击运动员的意志。在随后的训练中,他更是看到她的搏击天赋,预备把她带到多巴基地训练。
校长知道了张翎老师想把她带回多巴基地接受系统训练的想法后,告诫他:“带她成为专业运动员我很同意,但必须得到她父母的同意才能离开学校。”张老师像父亲一样把他的羽绒服给她穿上,让她坐在他借来的校长的破摩托车后座,到冬给措纳湖岸她家找她阿爸家访。
她阿爸说:“我们藏族人不喜欢打架,你为啥要带她去学打架?再说打架时有可能被对手打死。她不能去。”他见张老师满脸困惑,又说:“我家有一千头牦牛八百只羊,有的是钱,就是缺放牛的人,她要留下和她姐姐们一起放牛。”
站在一边的昂亲拉毛说:“我生下来就放了十年的牛,不想再放了,我要到西宁打比赛,实现我的理想。”她父亲用藏式特有的感叹词说:“啊嚓嚓!你一个依姆(藏语小姑娘)还有理想?难道吃手抓不比理想重要?”张翎又给坐在湖边一边看湖水一边纺牛毛绳的阿妈做思想工作。阿妈对他说:“我们藏族女孩没有每天去打架的。”然后又对她说:“以前我教你唱格萨尔,你也学得很好,我一直想送你去州上继续学习,就是不想让你去西宁学打架。”
新学期开学后,昂亲拉毛到果洛州首府大武民族中学上初一,可只上了一个月便回了花石峡,到镇政府大院找也是藏人的书记说:“请您替我转告我阿爸,我要跟张老师去多巴体育训练基地练搏击。”她看着书记有些意外的神情,强调说:“我就想离开草原到内地打比赛,拿全国冠军让你们自豪!”然后,她不辞而别,就这样来到了远在草原之外的多巴训练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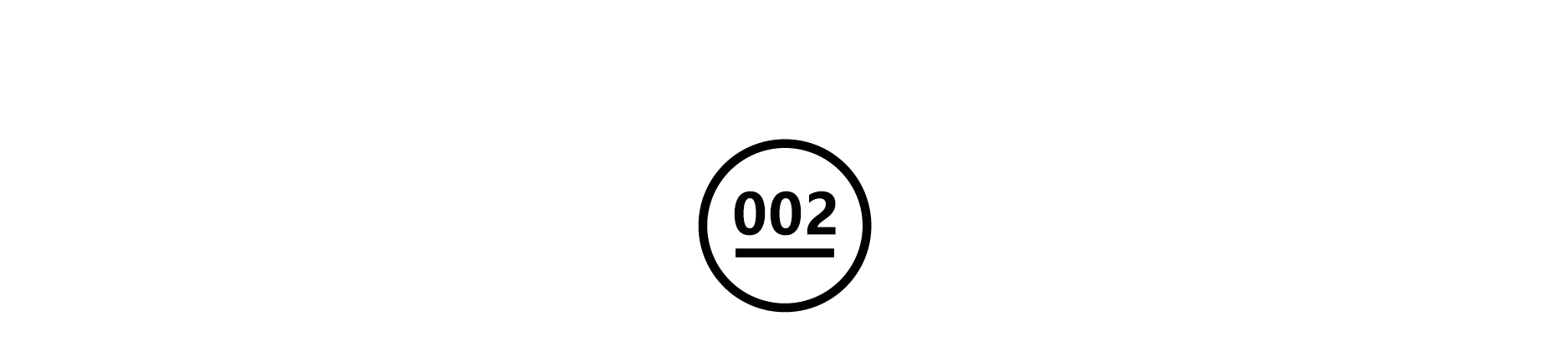
“热辣滚烫”,之后呢?
从武汉回到基地后,师兄林檎知道她伤势严重,有空就来陪她。林檎还告诉她,凡在全国性比赛进入前十的运动员,报考体育学院都有分数照顾,少数民族在文化考试上也有相应的照顾,还说:“你不是在2016和2018年全国女子赛两次拿第六,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复习文化课。我陪你一块复习去考试。”
第一次考试是他俩一起到北京考北京体育大学,这是林檎心仪的学校。她对考这样的好大学没信心,但还是去了,结果没被录取。接着她一人坐火车到郑州报考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还是因文化课没过线再次落选。
在职业运动员生涯即将终结,想上大学找出路也没实现的眼下,她迷惘得如同果洛高原上面对广袤山川没了方向感的白唇鹿。林檎看出她的困境,问她是不是想念果洛了。一提到果洛,她内心就飞扬起来。
也许藏族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天生就流淌在她的血液中。在十个人组成的女队里,就她一个藏族女孩。入队后,她每天黎明随队友在体育场,或沿着山脚下的乡村公路,跑三十公里,然后是长时间枯燥的体能训练。这训练能让人发疯,即使如此,在队友完成训练任务休息时,她又主动求张教练给她开小灶加码,直到浑身发抖、难以持续才停止。
张教练常找来多名男队员陪练,磨炼她的意志和抗击力,她自己也主动找到比她大两岁,打法也最凶猛,被她称为师兄的林檎,请他和自己对打。林檎是男队最好的拳击手,不想陪她练,她磨了他几天,说:“多巴镇上所有的饭店你随意点,我请你吃饭。”他斜视着她说:“你不知道队里规定不能在外吃饭吗?”第二天她把一把随身携带的精制藏刀——这是藏人的心爱之物——送给他,还在微信里转了一千元钱,希望他陪她对打。

图源:电影《百元之恋》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某次互击中,林檎如雪豹般敏捷的拳头铺天盖地朝她打来,让她在躲避不及中被打飞一颗牙齿,倒在地上痛哭。林檎和另一个队员抬着她就往卫生室跑。不久,林檎陪她到青海省人民医院安装了一颗假牙,俩人继续对打,她的成绩就这样慢慢上升起来。
一个月后,那时是高原的八月,昂亲拉毛的阿爸阿妈来多巴看她。他们按藏族人的习惯,晚上就在基地外、山坡下的杨树林中扎起帐篷。他们不习惯宾馆软塌塌的床,更习惯睡坚硬的大地。第二天她邀林檎一起去见她阿爸阿妈,她阿爸用藏语问她:“他是谁?”她说:“我男朋友。”他阿爸说:“他愿意跟你回冬给措纳湖放羊吗?”
林檎听不懂藏话,在昂亲拉毛的翻译后惊得目瞪口呆:“我是你男朋友?啥时候的事?”昂亲拉毛用撒娇的口吻说:“我求你当我男朋友行吗?我家有八百多只羊和一千头牦牛,价值一千多万,将来等你打不动了,我们一起回到冬给措纳湖边的草原上放羊,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蔚蓝湖水……”
在养伤的那段时间,昂亲拉毛每天躺在基地宿舍,晒着强烈的紫外线阳光,翻看手机里的短视频,无意中看到网红搏击博主王美丽和全国各地搏击爱好者相约在城市街道、农村地头、车站广场或蒙古草原对打、切磋的视频。几年前,王美丽随河北队来多巴训练时,曾同她一起吃住,早是闺蜜。有时她会被对方打得披头散发,更多的时候,她展现出一个现代女侠的豪爽。
昂亲拉毛想应该去找她一起做视频普及这项运动,也为退役后的生活探找出路。
她俩一起去了黄南藏区,由于这些地方海拔很高,即使像王美丽这样身体素质好的人,在泽库县多禾茂乡挑战一位藏族大力士时,不到一分钟也被对方打得屁滚尿流,还输给对方一千元钱。
王美丽不甘心这结局,翌日按约到另一村子,当她和一个年轻男子搏击时,被几位藏族老阿妈拦住,用藏语要她“滚蛋”,还骂道,“一个姑娘干什么不好非要打架,把孩子们都带坏了。”王美丽问她老阿妈说的是什么意思,她翻译了一遍后王美丽说:“看来藏区人民并不欢迎这项运动。”然后她困惑地又说:“我到内蒙古去打,牧人打不过我就送我一只骆驼!她们为什么担心搏击会把孩子带坏?”
王美丽离开西宁时对昂亲拉毛说:“希望你在青海能为我们的事业坚持下去。”此后,她叫林檎代替王美丽,在湟源县做了一期普及活动,因没有公司支持,更没专业拍摄团队,便搁置下来。
昂亲拉毛觉得,十岁不当牧女,去上寄宿小学,是她人生的一次破局,可那之后的困局仍一个跟着一个。眼下的困局是如何寻找出路。也许是人的本性,在身体和精神受伤的第一时间,她想到可以回到愿意包容自己的故乡,修身养性。可一想到老家,她又不知自己是以一个失败者还是成功者的身份回去,再说,当初要拿全国冠军让父母家人骄傲的豪言壮语还未兑现。
还是林檎发现了她踌躇的原因,建议她“既然我俩早晚要结婚,那你就先到我老家山东曹县,到我父母在县城里开的饭店当老板,等我退役后再一起经营饭店。”在回草原还是留在城市的彷徨中,她最终下了决心,听从了林檎的建议。
她来到山东曹县,在准公婆经营的一家中型鲁菜饭店里,以未来儿媳的身份负责管理。事实上饭店并不需要她管理,林檎只是想让她早点融入这个家庭,为今后的生活打基础,但随之而来的生活让她再次陷进困境。
以往她到内地打比赛都是十天半个月,甚至更短,属出差,然后就回青海,这次回内地却是长住,这对一个从小生长在高原上的藏族姑娘来说很不习惯。首先面临着夏天炎热的难关,即使房间全都安装空调,仍挡不住滚滚热浪,每天都像从河里捞出来一般,湿淋淋的。以面食为主的北方饮食习惯,更让她怀念起酥油糌粑、大块的牦牛肉、豆腐般坚硬的酸奶。即使准婆婆让厨师为她专门炖了肉菜,也索然无味,寝食难安。
到了年底,看到准公婆年终算账,一年辛辛苦苦也就挣了数万元,她又想起自己家千头牦牛和千只羊群的价值。而且,在草原上唱着格萨尔英雄业绩歌曲,就能把牛羊养大,这让她再次想起烙在骨里的冬给措纳湖畔的微风和白云。其实这想法早如兔子,在她怀里欲撞破眼下的困局,她忽然明白,原来故乡的冬给措纳湖一直都是她心灵所属之地,高高在上,呼唤着她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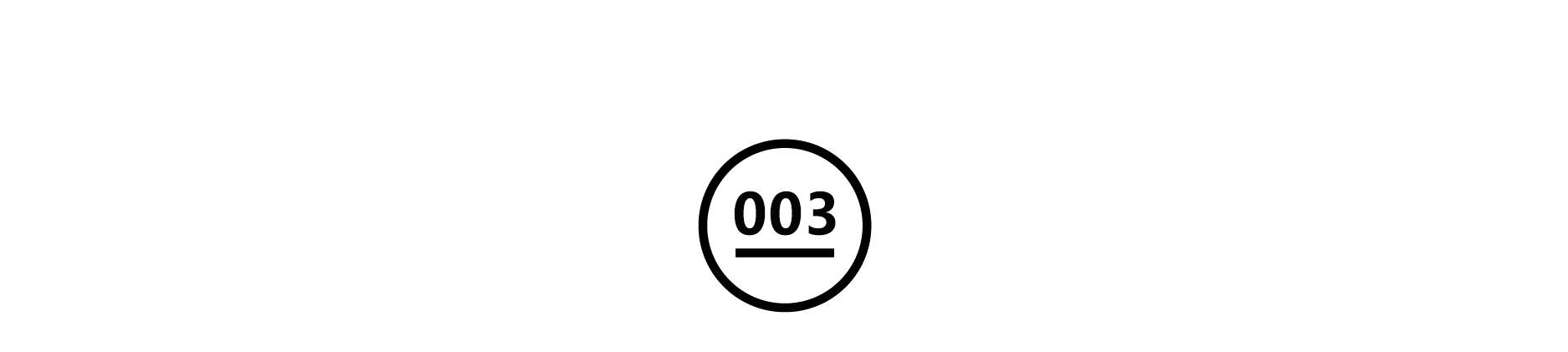
重返冬给措纳湖
昂亲拉毛从西宁坐班车回到花石峡。来接她的只有大姐一人,她问:“阿爸怎么没来?”大姐说:“去年中了风,半身不遂不能来接,阿妈的膝盖坏了,不能走路。”她这才知道,父母为了不耽误她训练,没把生病的事告诉她,这让她一时惭愧不已。
寒暄完,她让大姐载她到花石峡小学去看看,那是她人生第一个起点。她在校门口踮着脚朝里张望寻人,一个女生看见,从操场走过来问:“阿切(藏语姐姐)你找谁?”她笑着说:“找昂亲拉毛。”她这样说的时候就看见自己十岁那年的往事。
姐姐骑摩托车载她快速行驶在乡村公路上,那片挂在头顶的蔚蓝的天空之湖,盖住她的视线,她知道那是高原过于纯净的光线引起的视觉错觉——也是她在离别的八年中反复出现在梦中的湖。她大喊“停车!”,泪流满面地蹲在山坡上失声痛哭,像所有的牧人一样,反复吟诵起“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问候故乡。

冬给措纳湖,图源:视觉中国
阿爸已经卧床不起,母亲也行走不便,但还是当着三个都已成家的姐姐面说:“只有你还没成家,所以我就等你回来,给你一百只羊二百头牦牛,希望你不再离开草原,成个家安心在湖边放羊过日子。”就这样,她在瞬间成为拥有三百万财产的富婆。
随后几天,她长时间独坐在湖岸边看着湖水发呆,内心安静得出奇,这是以往没有过的。她仿佛一下从骚动中跌进十岁前的时光里,不时轻声吟唱起被她久久遗忘了的童年学会的格萨尔唱段。
有一天,她在住房后的草地上看到有辆生锈的摩托车,便问起阿爸是咋回事,阿爸惆怅地说:“我没中风前是玛多县‘野生动物救护员’,每周二周五骑摩托围湖巡视,发现受伤的动物和鸟就打电话报给花石峡‘野救队’的扎西进行救护。”他也是兰州社科院冰川研究所指定的阿尼玛卿雪山冰川测量员,每年夏至和立冬这两天,他就和三位邻居去测量冰川变化。中风后,他就不能再去了,那辆摩托车也就废了。
一个月后的周二和周五,在冬给措纳湖沿岸,人们会看到一个穿着藏服,用方格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眼前架着墨镜,手臂上套着鲜红袖标的女子,袖标上用黄色汉字印着“玛多县野生动物救护员”。她骑着摩托车如一只矫健的岩羊,在辽阔壮丽的山地上沿湖巡视,到零散的牧人家询问野生动物的活动情况,叮嘱他们遇到受伤的动物就立即给她打电话。
这个人就是昂亲拉毛,她自愿接了阿爸“野救队”的班。
冬给措纳湖地处玛多县西北的崇山峻岭中,百里无人烟,环湖一圈有百余公里,沿湖巡视一圈至少需要一至两天。所以在她每次巡视前,阿妈都会早早给她准备至少三天的糌粑、牦牛肉和一张狼皮褥。如巡视中能遇到牧人的帐篷,她就去借宿,虽然邻居间最近的距离也有数十公里以上,但彼此都认识,她会被他们热心款待。可到了冬天骑摩托车巡视时,因草原没有路,则需披荆斩棘,三天才能巡完,如在天黑前遇不到牧人的帐篷就得拿出狼皮褥,找个低洼处,如钻进洞中的旱獭,用藏袍裹住头脚睡一晚,第二天继续巡视。

冬给措纳湖,图源:视觉中国
某个周五,巡视到湖岸最西端时已是黄昏,她忽见一群天鹅被她惊飞,其中一只挣扎了一下就原地不动。她觉得蹊跷,下车就见它的翅膀断了。包扎好后,夜色已降临,如把它留下,它随时可能被动物吞噬。她当即给花石峡“野救队”的扎西打电话,相约双向到乡村公路某处移交,然后由扎西送往县上。
高原的夜晚如刷了墨一般漆黑,开着大灯的摩托车在辽阔的黑暗中,如挖隧道的挖掘机在蠕动。一个不留神,她的车身被数十公分的深沟颠翻,她整个身体被抛到空中又重重摔在地上,她摸着头上火辣辣的包呻吟许久,才忍痛爬起。她看了看那只装在袋里的天鹅,幸好没受二次伤害。可当她朝四周的黑暗打量时,看到远处数只绿莹莹的眼光正注视着她,她不顾一切,在哆嗦中扶起摩托车仓皇逃离,终在凌晨驶到那条乡村公路上,与扎西会了面。
2023年立夏这天,她和三位邻居叔叔去数十公里外的阿尼玛卿冰川测绘。他们骑摩托到了海拔已近五千,弧度陡得已不能再骑车的地点,弃车徒步走了数小时,才到冰舌与砂石交接处。当她爬上一块数米高的冰块进行测量时,脚下一滑,落了下来,旁边的叔叔眼疾手快去接她,被她身体的冲击力撞到数米下的沙滩上,一条腿当场摔断……
每个周日,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被她训练成习惯,和三个姐姐、姐夫拿着纤维袋,在湖岸上的草原里捡拾散落的空水瓶、塑料袋等垃圾,家里的那间房里堆满了数袋垃圾,她会让姐夫专门开车将它们送到镇上的垃圾站。
这样的生活如在湖水中升起又降落的太阳,循环往复,可时不时地,她的眼前还是会出现在搏击场上被人打得满脸鲜血的场景。她也不时从梦中惊醒,然后坐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本文据真实故事采写,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实习编辑吴争对本文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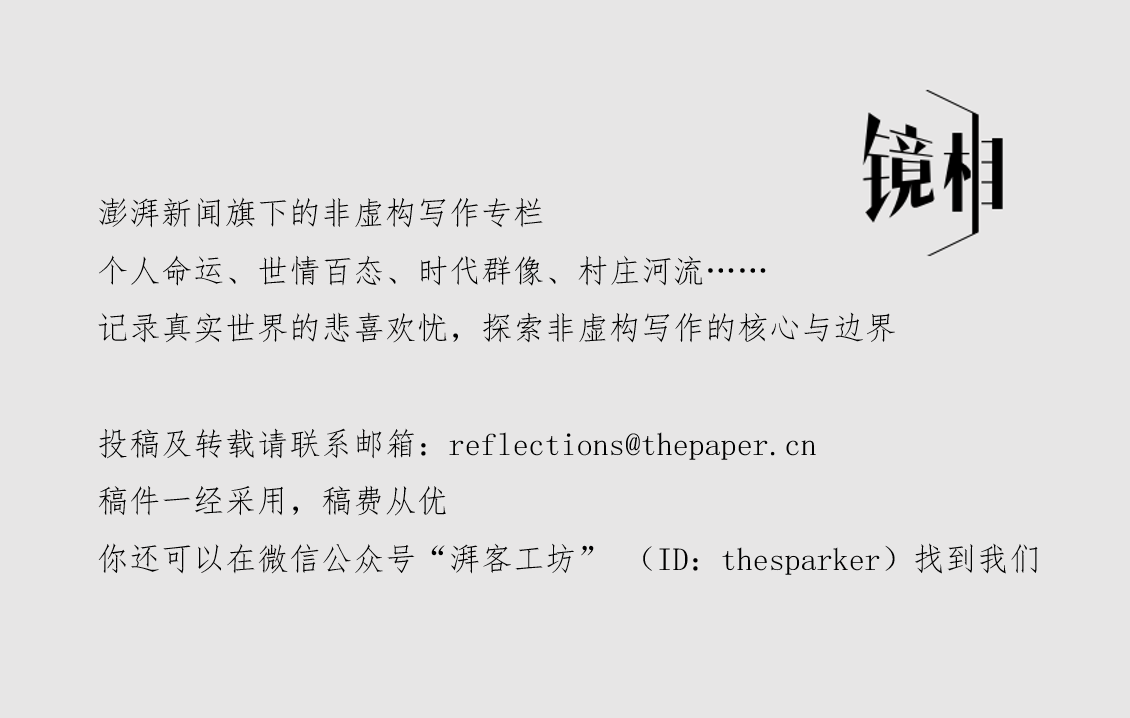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远亲不如近邻”
- 央行最新例会:择机降准降息
- 金正恩会见绍伊古重申对俄支持

- 胡塞武装称袭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美航母多艘护航军舰
- 经济日报: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

- 一位知名华裔男演员,主演电影《旺角黑夜》等,最近因为推出英语网课而爆火
- 《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的下一句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