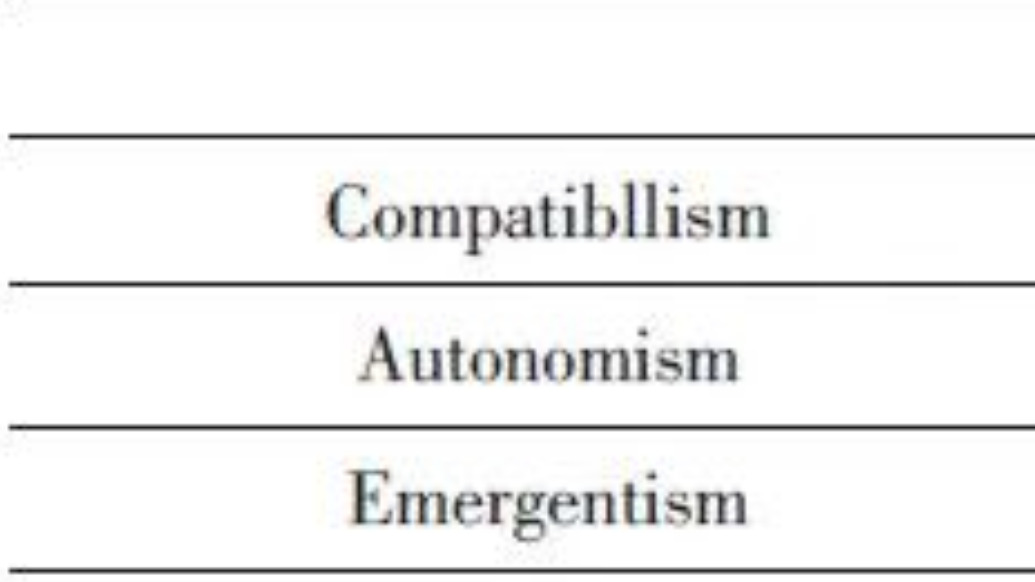- 15
- +1
谁是罗兰·巴特?一个喜欢在文本里捉弄倒腾的“捉狭鬼”
谁是罗兰·巴特?

作为现代思想的交会点,罗兰·巴特串联起列维-斯特劳斯、布朗肖、拉康、萨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整部法国20世纪思想史。他提出的零度写作、作者之死等概念风靡一时,其神话学、符号学等相关著作则为分析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提供了经典理论。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和文学批评家,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传奇。他的写作生涯贯穿了符号学、叙事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新的理论流派。他因独具一格、优雅睿智的批评写作风格而享有作家和文人的声誉,并以边缘和前卫的批评姿态获得了经典的地位。
汪民安教授在《谁是罗兰·巴特》一书中,生动地展现了罗兰·巴特的思想轨迹。罗兰·巴特是现代思想的交会点,作者将其思想放置在20世纪后半叶充满争论的法国思想图谱中,将他和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等人的思想进行对照,这既是对罗兰·巴特思想的总体呈现,也是在一个更宽泛的角度对当代法国理论的勾勒。此外,作者特别强调了罗兰·巴特对人文科学的巨大贡献和留给后世的丰富遗产。

《谁是罗兰·巴特》
作者: 汪民安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选读
罗兰·巴特1915年11月12日生于瑟堡一个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路易斯·巴特第二年在一次海战中阵亡。巴特在巴永讷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亲、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跟他的“终生孤独”的姑母(一个钢琴教师)学钢琴,他“生活在一种音乐空气中”。生于新教家庭,父亲早逝,同母亲相依为命,与音乐做伴,这可能奠定了巴特日后敏慧而阴柔的一面,他甚少写一些充满暴力的句子。相反,他的优雅、温和贯穿着他的所有文本(甚至在和皮卡尔的论战中,他也显得彬彬有礼、从容不迫),这种柔和风格,虽不能说成是阴性的,但无疑也不是充分阳性的。
1924年,巴特和母亲移居巴黎,只是在假期回巴永讷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巴特的母亲亨利特·毕格尔因为贫困,也出于一些无法说清的原因,不顾其资产阶级出身,学会了一门手艺,即书籍装订,挣得一些钱供巴特读书和生活。这段经历使巴特记忆犹新,他称他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潦倒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想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仍然不断意识到他们在物质上的败落。每学期开课前,巴特都感到一次小小的财政危机:没有合适的衣服,没钱买学习用具,没钱买课本。对此,他回忆道,他“所参与的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艺术,这门艺术永不变质地生存在每次钱的危机中心。他的家庭经历,不是苦难,而是拮据,即是说,交往的恐惧、度假问题、鞋子问题、课本问题,甚至饭食问题。这种能忍受的匮乏(如拮据总是这种匮乏一样)可解释自由补偿的哲学、快乐多元决定论的哲学、闲适(它是拮据恰如其分的反义词)哲学,他的成因无疑是钱而非性”。巴特将这段早期的拮据解释为他哲学的起源,正是这段日子埋下了他日后的享乐主义种子。

年轻时的罗兰·巴特
1934年,巴特中学毕业。考巴黎高师是当时有志青年的梦想,巴特也不例外。然而,他左肺出了问题,患上了肺结核,被送到比利牛斯山区治疗。不久,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巴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攻读法语和古典文学学位,并帮助建立一个古典戏剧团体,并且同这个团体一道去希腊旅行。1937年夏天,巴特去匈牙利讲课。这期间,由于肺病,巴特得以免除兵役,在“二战”的头两年里,他先在比亚济茨后在巴黎公立中学教文学。然而,1941年10月,其肺病复发,他不得不放弃在公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两年后,左肺在巴黎逐渐康复,而右肺又出了问题。这样,他只得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里,最后待在内森。在此期间,他一度打算做个精神病医生,为此,还进行了几个月的医学预备学习。直到“二战”结束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巴特才完全摆脱了肺病的纠缠。
这两次肺病对巴特影响很大。在疗养院里,他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并深深地喜爱上了米什莱和纪德,他读了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而且,正是在疗养院里,巴特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他写过两篇文章,即《论纪德和他的日记》以及论加缪的《局外人》的短文,后者正是《写作的零度》的雏形。
巴特因肺病得以免除兵役,且避开了战争,受战争的影响不大。苏珊·桑塔格声称,她没有在巴特的著述里发现“战争”一词,这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他们一般都对那段耻辱的历史难以释怀。以萨特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介入倾向,这在1968年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反,巴特正是在战后才逐步发展他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情趣。也许,战争并没有给巴特留下什么阴影,一个在战乱时代还沉浸在历史著述(米什莱)和美文(纪德)中的人,不是一个天生的局外人吗?正是在战后,也是在萨特的影响下,巴特开始转向现代文学,并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1947年,巴特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短论,这些短论明显地和萨特有关,它们既受萨特的影响,也针对萨特,这些短文后来就组成了《写作的零度》。

罗兰·巴特画作
巴特康复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先在图书馆做助手,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最后又去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教书。在亚历山大他碰上了符号学家A.J.格雷马斯,后者向他介绍了语言学知识,巴特此时开始熟悉索绪尔的著作。与此同时,巴特还继续为国内的《战斗报》等左翼报刊写稿。不久,巴特回国,在教育部的外事机构任职。1953年,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问世,这部著作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巴特带来了一些国内的名声。这部著作明显地对萨特表现出一种抵制情绪,它针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唱了一些反调,在战后介入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流中,巴特却露出了形式主义的尾巴。据说,在该书出版的前夜,巴特在巴黎街头散步,他预感到这部著作将产生的效果。然而,第二年出版的《米什莱自述》则反响平平。若干年后,巴特功成名就之际不无抱怨地说,《米什莱自述》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但无人喝彩,而《写作的零度》却长时间地被引用、谈论,尽管他早已对它失去兴趣了。
事实上,直到《神话学》问世,巴特才逐渐在巴黎知识界引人瞩目。这本书收集了巴特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写的大量社会神话随笔——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神话学》有明显的揭露功能,它旨在剥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粉饰性外套。这种去蔽方式影响甚广,它或许是巴特遗留给后世的几件最重要遗产之一。而且,“神话”作为一个巴特意义上的用语,被广泛流传着。1960年,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直到他去世。
有了固定的工作后,巴特开始潜心写作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都是巴特声名鹊起的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盛期的到来,巴特在巴黎知识界也如日中天,他成为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领袖人物。1963年,巴特发表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论拉辛》,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读拉辛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可载入史册的论战。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发文《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激烈攻击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他要“伤害”“刺穿”“进攻”“杀死”新批评,指责巴特等所做的批评是极端危险的。巴特写了《批评与真实》,对皮卡尔气急败坏的指责做了平静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应。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一场“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传记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争论,结果,这场争论以巴特的雄辩理性获胜而告终;同时,它也促进了新批评的发展,为法国批评界日后的冒险扫清了障碍,并将批评界的保守主义埋进了历史的尘土中。

罗兰·巴特画作
几乎是与此同时,巴特还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批评文集》。前者对符号学做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后者则在鼓励当时的先锋派罗伯格里耶和布莱希特,为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同时《批评文集》中还涉及了极多的话题,如结构主义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元语言问题、作者和作家问题以及文学现状问题等,这本书汇集了巴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代写作的诸多思考。此时,巴特的结构主义范型已大致确定,早期的神话学分析已被语言学模式取代了。正因为倡导结构主义,且对它进行了杰出的运用和解释,巴特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他和另外几个人有力地将这个运动推到了巅峰,他们分享了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的领袖人物位置:列维斯特劳斯负责人类学,拉康分管精神分析学,福柯则肩挑思想史和哲学,阿尔都塞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担子,无疑,文学的地盘就留给了巴特。正是这五个人扩展了结构主义的权势,结束了人道主义或存在主义的统治。
事实上,巴特并没有在结构主义的床上躺多久,他早早地爬起来了,并轻轻松松甩掉了结构主义的花环。1970年,他的两部新作改变了他的形象,这就是著名的《符号帝国》和《S/Z》。《符号帝国》是他于1967年访问日本的观察结果,在写作这本书时,他获得了极大的快乐。这本书一点也不带结构主义的色彩,巴特将日本分解成几十个符号,对每个符号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方式容易令人回想起《神话学》的方式;重要的是,巴特并没有按照结构主义原则将这些符号组织起来,从而观察它们的内在语法线索,相反,他仅把它们并置起来,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存在。《符号帝国》显然遗忘了结构主义的使命,《S/Z》离结构主义就更远了,或者说,它就是在和结构主义作对。这部著作是对巴尔扎克的一部不太著名的小说《萨拉金》进行的阅读实践,巴特在此正是以反结构主义之道行事,他将一个严谨规范的现实主义文本拆散了,并弄得七零八落,而且丝毫也没有统一它的打算。经过巴特的那只手——准确地说,是一只屠手——《萨拉金》已经面目全非了。

罗兰·巴特画作
1973年,他的另一部影响甚广的著作《文本的快感》出版,这是他的又一次转向,一次阅读和批评的形式主义向阅读伦理学的转向。在此,他充分地提高了阅读的地位,用阅读伦理学取代了阅读技术。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巴特此时都有充足的理由进入法兰西学院。巴特此时也面临着反对意见,他和传统的学院式研究大相径庭。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写过一些随笔;而且,他总是出人意料地变化,使人难以摸清他的思想体系,这也为他的思考和论断到底有无真实的价值和凭据埋下了疑问;另外,巴特似乎总是在处理一些小的主题,而不是学院内部留存下来的恒久而宏大的命题。总之,巴特身上的世俗气息压倒了学院气息。但是,关键时刻,福柯起了作用。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的友谊中断了十多年,彼此没有来往。主要因为两人在一起时,经常发生冲突。那时,他们尚未获取盛名,他们既相互欣赏,又相互竞争,结果不欢而散。当巴特想进入法兰西学院时,福柯已是那里的教授了。显然,就年龄、所获成就以及心理成熟度而言,两人重续友谊是当然的,也是必要的,况且,两人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巴特还曾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写过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并极其准确地道出了福柯这部著作的非凡价值。
福柯回击了那些对巴特的指责。他说:“我要补充一点,如人们所说,公众对他的兴趣可以被看作一种时尚,但是,我们可以使怎样的历史学家相信,一种时尚,一种激情,一种迷恋乃至夸张的说法不是反映特定时间内某种文化中的丰富内涵的存在?而这些声音,这些我们在大学以外听到的和正在听的声音,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是我们当今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难道不认为它们将会成为我们历史的一部分?”福柯对巴特的辩护最终使巴特入选。
稿件责编:何晶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图片来源:资料图

原标题:《谁是罗兰·巴特?一个喜欢在文本里捉弄倒腾的“捉狭鬼”》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美股持续暴跌,纳指跌入熊市
- 贸发会议警告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 反腐深入舞蹈领域:三人同日落马

- 浙江宁波:2025年计划供应住宅用地211.2公顷,同比减少35.55%
- 新疆吐鲁番雅尔湖石窟首次开放

- 被誉为“活化石”的中国特有树种是
- 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雨林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