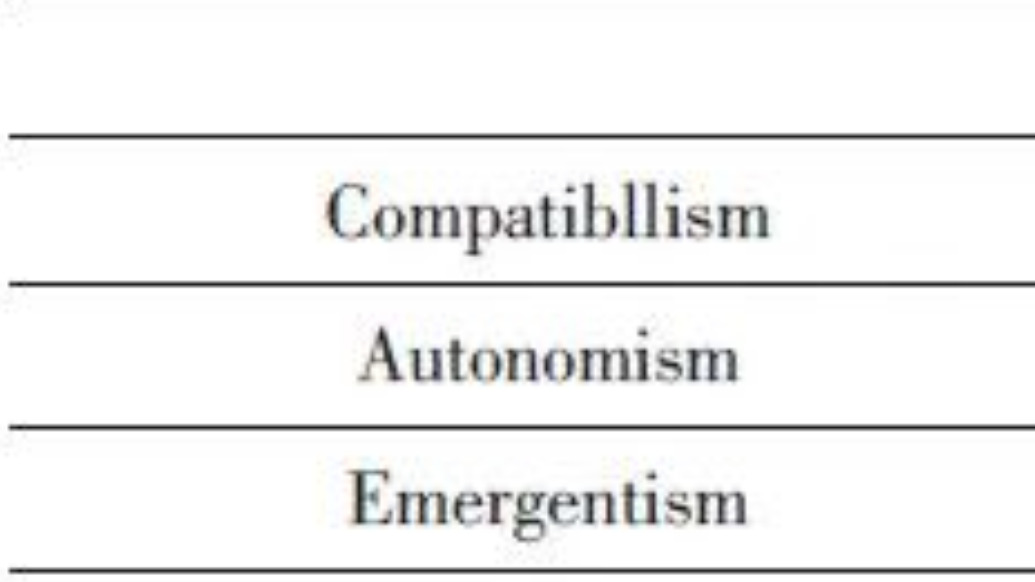- 25
- +11063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节选一)
编者按: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何去何从,仍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事关千万中国家庭乃至人类命运的重大现实决策议题。美国知名的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冯文(Vanessa L. Fong)于1997-2002年,在中国大连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多位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访谈,写成《唯一的希望》一书,探讨了独生子女在一个过去历代习惯大家庭模式的社会中成长的情形与体验,考察了何种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力量塑造其成长经历,并分析了独生子女身份对于青少年的主体性、体验、渴盼所带来的影响。以下为书中节选内容。

1999年,郭达去上成人教育学院,很失望地发现自己得和另外七个男孩共享一个小宿舍。过了几个星期,他离开了宿舍,回家住自己的房间。“我不能住那么挤的屋子!”他向父母抱怨。“我的一些室友总爱抽烟,让我觉得恶心!”
虽然他的父母担心他每天从家到学校乘坐往返两小时车程的公交车会浪费他的学习时间,但还是勉强同意让他回家住了。他们的许多亲戚听到这个消息时都感到震惊。他的堂姐赵丽丽说:“他应该是除了晚上睡觉时间别在宿舍里待。晚上人人都睡着了,没人吸烟。其他时候他去自习室学习。”她直到婚前一直和弟弟同住一屋。
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许多独生子女在上初中前都有自己的房间。他们的父母认为如果让孩子与闲暇时间更多的成人进行娱乐和社交活动的空间隔离开来,他们就能花更多的时间学习。虽然这项策略有效,但也引起了孩子对隐私的期待,而这对于在成长过程中和兄弟姐妹共用空间和物品的长辈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父母担心独生子女在长大成人后将无法适应更加拥挤的居住状况。大多数中国大学宿舍每间房间都有4-12名学生。办公室里也往往是有多名员工。已婚夫妇的家里很少有夫妻能各用一间私人书房。独生子女尽管怀有对第一世界中私人空间的期待,但仍然不得不应对第三世界的空间短缺。
潘娜的父母虽然是低收入的工厂工人,但是为了给潘娜提供好的生活条件不惜花钱。他们的公寓没有洗澡设施和热水。像孙薇的父母一样,潘娜的父母把烧开的水和冷的自来水倒在桶里,沾湿毛巾洗身上,但是每个周末都给女儿钱让她到外面澡堂洗澡。当我在1999年夏天开始辅导她的时候,她刚从小学毕业。当时她和父母在家里唯一的卧室里的一张破旧的床上睡觉,卧室里还有电视机和电话机。然而,当潘娜进入初中时,她的父母搬进客厅,也把电视机和电话机拿到了客厅。潘娜的父亲告诉我:“我们不希望她在我们看电视或者打电话聊天时分心,耽误学习。她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这样能争分夺秒地学习。”
潘娜的父母继续睡在他们破旧的床上,但为潘娜买了一张新床和新床铺。潘娜的母亲告诉她:“我们想让你睡得舒舒服服的,休息好了,就能精力充沛地听课。”
潘娜虽然很怀念能轻易看电视的日子,但也很高兴享有自己的房间。她把房间收拾得整洁干净,贴满了她所欣赏的电影明星的海报。
潘娜的外婆视力不好,骨质疏松症严重,不能自己做饭或购物。因此,她在四个孩子的家中轮流住,每个孩子每年花几个月时间照顾她。当住到潘娜的家中时,她和潘娜的母亲睡在客厅的床上,而潘娜的父亲睡在旁边的小床上。
有个星期六,我正在潘娜房间辅导她时,她外婆和母亲走了进来,外婆开始往她的床上躺。
“你在干嘛?”潘娜惊叫。
“你爸想看电视,但你外婆想睡觉,所以我让她睡在你的床上。”潘娜的母亲说。
“不要让她躺在我的床上!”潘娜喊。“她很脏,味道不好!”
“你怎么能这样说?”潘娜的外婆说。“我是你外婆!”
“忘恩负义的小坏蛋!”潘娜的母亲骂道。“你忘了小时候外婆是怎么照顾你的?你那么干净,还不是因为我们花钱让你出去洗澡!你外婆不出去洗澡,因为她想帮我们省钱,让我们给你买好吃的和漂亮的衣服。我们为了给你省下上学的钱,都不像你一样勤洗澡,你还敢抱怨外婆脏?”
“那好,你可以睡在我的床上。”潘娜告诉她外婆。“但不要脱掉你的衣服,也别用我的被子!”
潘娜的外婆在她床上躺了约一个小时,但后来说觉得听我辅导潘娜的声音比听电视的声音更难以入睡,就回到了客厅。
“我没有不孝。”潘娜内疚地说。“我当然很感激我的外婆。但我刚洗了我的被子,她身上也真的很难闻。你也闻到了,对吧?”我不安地点点头,继续讲解英语语法规则。
潘娜的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已经把我的女儿宠坏了,她不在乎别人。所有的独生子女都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什么都要最好的,从来不为别人着想。”

许多父母为了能让孩子拥有第一世界的饮食条件,将自己的饮食仅限于第三世界的水准。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大多数家庭都不阔绰。最穷的家庭都不能保障所有家庭成员一日三餐。即使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美味优质的食品。除了最有钱的父母之外,其他父母的饮食花销都低于子女。
1999年荀金的母亲从工厂下岗,她告诉女儿再也不能给她上学期间买零食的钱了。“你要是不给我钱、我在课间休息时买不了零食,我就会饿,不能集中精力上课!”女儿回答。
“给她吧!” 荀金的父亲说。“要是这钱能帮助她考上大学,就不算什么。”荀金继续有零花钱买零食,而她的父母在平日为了节省钱而免去了午餐。
这些青少年对食物的态度与父母的态度大相径庭,在食量上很少达到父母要求的程度。多数父母对食物持有第三世界的态度。经历过“大跃进”之后的饥荒(1959-1961)的父母将瘦体型与身体孱弱划上等号,觉得自己有责任让孩子尽可能地多吃。然而,青少年对食物有着第一世界的态度。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青少年们(包括最贫穷的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挨过饿,所以他们不像父母那样珍惜食物。不同于他们的父母,他们接受了一个以苗条为美的全球化的审美文化模式。尤其是女孩更害怕肥胖而限制食物摄入。有些学生拒绝吃自己不喜欢的食物。他们不会为丢弃食物感到不安。因为紧张的学习时间安排让他们的闲暇时间所剩无几,所以他们对时间的珍视超过了对就餐机会的重视。他们经常吃少量快餐,以节约时间用于休闲、学习、睡觉和社交。此外他们也吃各式零食,这些零食比他们父母做的饭菜贵得多。父母对孩子们过分挑剔的饮食习惯感到震惊。然而他们也在纵容这些习惯,因为要想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期待食量充足,唯一的途径就是用美味昂贵的食物调动他们的食欲。
一些低收入的父母告诉我,他们经常让孩子先吃饭,然后吃剩下的饭菜,而且他们通常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只吃剩饭或者有时索性不吃饭,因为不舍得浪费时间和金钱来为自己准备饭菜。当他们和孩子一起吃饭时,他们自己挑着吃不好的,让孩子吃好的,比如没煮破的饺子、最新鲜的蔬菜、肉最多的猪排。孩子们认为自己吃最好的东西是理所当然。当客人送给了父母昂贵的食品时,父母只略微尝尝,主要都留给孩子吃。他们告诉我,他们中午到饭店吃碗面会觉得后悔花钱,但不惜经常给孩子买昂贵的糖果、饼干和饮料,用来奖励他们考取了好成绩、让孩子能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地上课集中注意力听讲、或者在孩子情绪低落时鼓起他们的干劲。孩子考了高分,他们带孩子去昂贵的快餐店(如麦当劳或肯德基)吃饭,以资奖励,但自己舍不得在那儿吃。他们把在家里做好的便宜食物带到快餐店吃。技工学校学生陈旭东的母亲经常生病,她在1999年失业期间经常为了省钱不吃饭。她说:“我要是早点死了也好,这样就会给我儿子减轻负担。”
学生可以用金属饭盒带饭,在午餐前用学校大蒸笼热饭。这些饭盒里通常都装着前一晚晚餐的剩饭。有些学生因为饭的味道不新鲜不想吃。如果父母还是让他们带了剩饭,这些学生就把饭扔了,之后告诉他们的父母因为挨饿不能专心听课。虽然父母对这种策略有意见,但他们通常会向子女的要求妥协,让他们吃更好的午餐,因为他们不希望小孩的学习能力降低。他们担心便宜的餐馆和街摊的饭不卫生,就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去更干净更昂贵的餐厅吃饭。
“你们看见我们的学生扔到垃圾堆的食物了吗?”宋爱民在1999年向教师办公室的同事们哀叹道。“他们扔的比吃的还多!我们这些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永远不会那么浪费。这些学生不知道他们正在扔掉父母的血汗钱啊。父母太惯他们了,等他们长大了一定会难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过穷日子。”
“我要是因为浪费时间倒垃圾,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我有两个妹妹和三个弟弟,我12岁的时候就像给他们当妈一样。”大学生李萌的母亲在1999年告诉我。“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缝纫、洗衣服经常都是我做。再看看我的女儿。她已经18岁了,这些活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干!”
在工业化使得教育成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之前,全世界大多数儿童都是家庭劳动的全力参与者。在教育并不带来财富的社会中,儿童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劳作而非教育上具有合理性。只有精英让他们的孩子把时间花在接受教育上而不急于工作。然而,工业化后,第一世界的儿童成为教育的消费者而不是劳动的生产者。到20世纪中期,第一世界的儿童在家庭劳动中贡献甚小,以至于大多数对北美和欧洲家庭劳动分工的研究都很少讨论这个话题。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儿童继续充当家庭劳动力资源。
《红灯记》是“文革”期间(1966-1976)的几大“样板戏”之一,其中的一段唱词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将儿童作为家庭劳动者的文化模型。此剧的故事场景设定于中日战争(1937-1945年)期间,在一开始,一名出身贫穷不识字的共产党员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自豪地用歌声表达对他领养的17岁女儿李铁梅的赞美,铁梅的亲生父母也是贫穷的工人,为革命牺牲了。
好闺女!
提篮小卖拾煤渣,
担水劈柴也靠她。
里里外外一把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有时独生子女父母们在提到自己年轻时的生活时会引用这段歌词。它意在赞颂李铁梅和像她一样的贫苦家庭的孩子在小小年纪便很早熟地担当家庭劳务,在共和国成立前的精英家庭里饱受宠溺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们很少能有这种可贵的品质。李铁梅的养父和养父的母亲和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一些孩子的祖父母一样,都不识字。
许多父母告诉我,当他们十几岁时在收音机上收听《红灯记》时,对李铁梅的生活很容易感同身受。他们告诉我他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做家务、在地里干农活、或照顾他们的弟弟妹妹。在少数情况下,父母们会允许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专注于学业而不用做家务。其余的孩子不能以学校作业为由推卸家务。人们靠初中文凭就能找到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既不受重视也难以获得。“文革”前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从事精英工作,但当时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并不拼命地要求每个孩子得到精英的工作。当家里有活儿要做的时候,父母会让女儿和不太有才能的儿子停下学习去做。即使那些被父母鼓励要好好学习的孩子也不会觉得家务劳动和学习有太大冲突。因为大多数学生都花了部分时间做家务,学习的竞争并不那么激烈,不需要每个学生都争分夺秒地学习,以免落后。
然而,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青少年是在一个把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的体系下长大的,没有父母能够担负起忽视孩子教育的责任。在一个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学业成就获得精英地位的体系中,即使是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会“早当家”。在我的问卷调查中,我发现被调查学生的家务劳动倾向与家长的教育水平、消费模式或职业状况并无多大关联。像富裕的父母一样,低收入家长也想让孩子们有尽多的机会获得学业成功。学生的时间弥足珍贵,不能浪费在琐事上。大多数父母会在学生放学回家时就做好晚饭,黎明前起床准备早餐,让孩子们可以一起床就吃到早饭,孩子们花几分钟时间快速吃完早饭便赶去学校。
当孩子们有闲暇时,女孩往往会被家长逼着做家务,而男孩更有可能放松休闲。然而,当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孩子们没有了空闲时间时,性别与家务负担之间便几乎没有相关性。因此职业中专女生做的家务劳动明显比男同学多,初中的女生比男同学略多做家务,高中的女生与男生的家务劳动量大致相同。
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学生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享有不做耗时过多的家务劳动的自由。对于第一世界的人来说,这种权利感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很多代人当中儿童的家务责任已经轻松了许多。但是,我在大连城区认识的父母在自己的童年时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家务,所以觉得这个问题更为棘手。虽然他们给自己的孩子不做家务活动的自由,但他们并没有觉得孩子天生有权利如此。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节约学习时间的手段。因此,虽然学习的重要性超过了家务,家务的重要性也该大过休闲。当他们的孩子在不学习的时候拒绝做家务,父母就会觉得苦恼。
王松上高中的时候,父母很少要求他做家务。他的父亲告诉我,有时他会把水果和饮料送到孩子学习的地方,节省儿子去冰箱拿东西的走路时间。他的母亲告诉我,她每天早晨在儿子起床前把牙膏挤在儿子牙刷上,这样可以让他多出几秒钟的宝贵时间来准备上学。在1999年他高考失利后的那个夏天,他的母亲试图让他帮忙做家务。
“关了电视机来帮我做晚饭!”王松和我在客厅一起看电视剧时,他母亲说。
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错过这个节目。“不要说话了!”他告诉母亲。“我听不到电视声音了!”
“你不觉得对不起妈妈吗?我为了能送你出国,每天工作挣钱,晚上赶回来做饭。你要是在向冯老师学英语,我就不叫你帮忙了。但现在你只是在看电视!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这个节目对我很重要!”王松坚持说。
“我的儿子太懒了。”他的母亲对我哀叹。“我已经把他宠坏了,他认为我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
1999年,卢晶在读初中的最后一年,她的母亲邀请我到她家做家教。当卢晶尝试帮忙做晚餐的时候,母亲把她推开了。“每一分钟都要花在学习上。”她的母亲告诉她。“不要浪费时间进厨房。”
“你为什么不教我做饭?”卢晶抗议。“我成家以后该怎么办?”
“你要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就可以买饭吃,再雇个佣人,根本不用做饭!”她母亲回答说。
但后来卢晶没考上高中,她母亲的态度改变了。“我妈说,既然你现在上中专,有了好多时间,你该学学要想当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需要做什么了。”卢晶告诉我。
起初卢晶想学习如何做饭。不过没过多久她就厌倦了,尽可能逃避做饭。
“你难道不想学做饭,为自己将来成家做准备?”我在2000年拜访她家时,她母亲问她。
“想啊,但我已经学会了!”卢晶说。“我不需要每天做饭!”她说。
大连城区的大多数学校没钱雇清洁工来完成全部房间的打扫。所以他们要求学生轮流做清洁工作。老师们对我抱怨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独生子女在做这些活儿时的意愿和能力差远了。“当我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毫无怨言地帮忙搞好学校卫生,有些同学甚至抢着干活,来展示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一位名叫任俊的中年女高中老师在1999年告诉我。“但是现在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从不让他们干活,所以他们很懒,到了学校也希望自己能像在家里一样被宠着!”
独生子女也承认自己一涉及到干活儿就比较懒,但也坚持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比如,在1998年的一天,当一个高中班里轮到徐雪莹去倒教室垃圾时,她向同学们抱怨说:“我要是因为浪费时间倒垃圾,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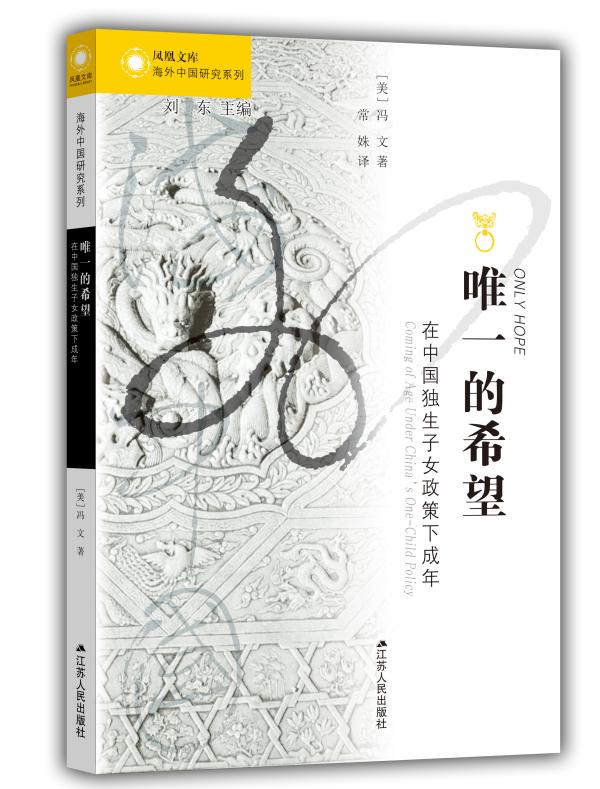
(节选自《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注释从略,冯文著,常姝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美股持续暴跌,纳指跌入熊市
- 贸发会议警告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
- 反腐深入舞蹈领域:三人同日落马

- 报告显示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正快速发展
- 2025年清明档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 被誉为“活化石”的中国特有树种是
- 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南美洲亚马逊盆地的雨林是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