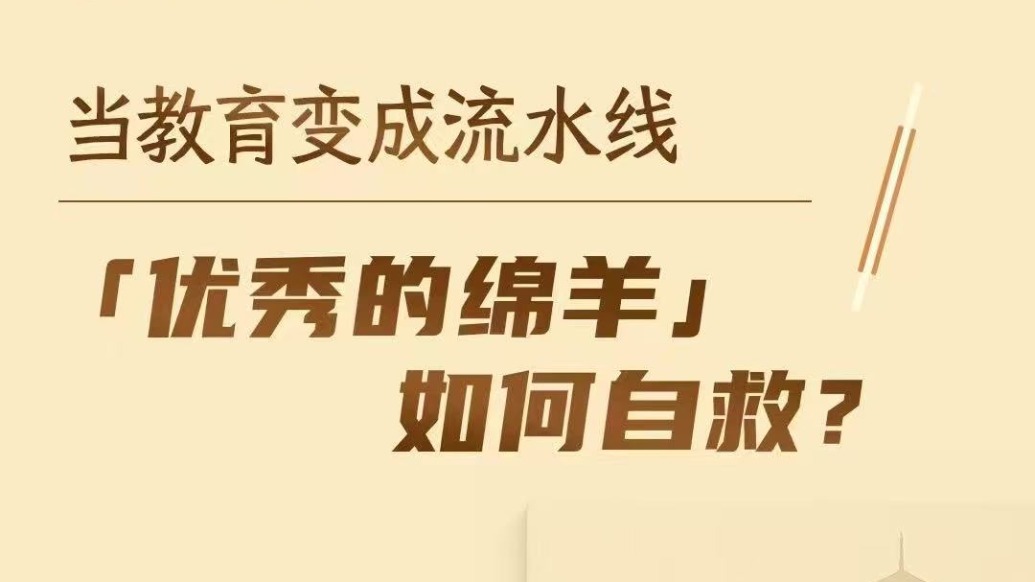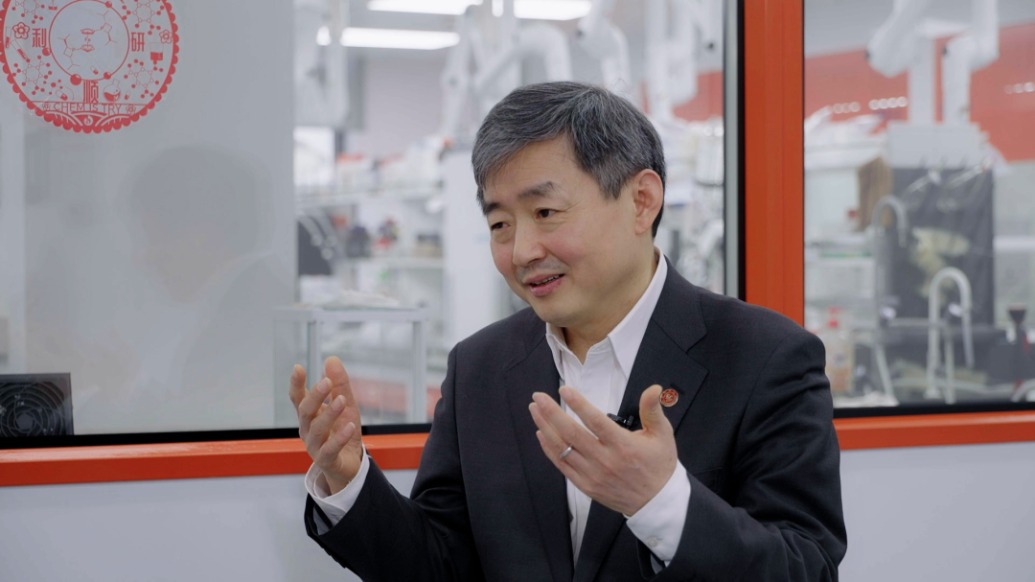- 9
- +1
一个中国老师和30位国际学生在博茨瓦纳
原创 苏菲 三明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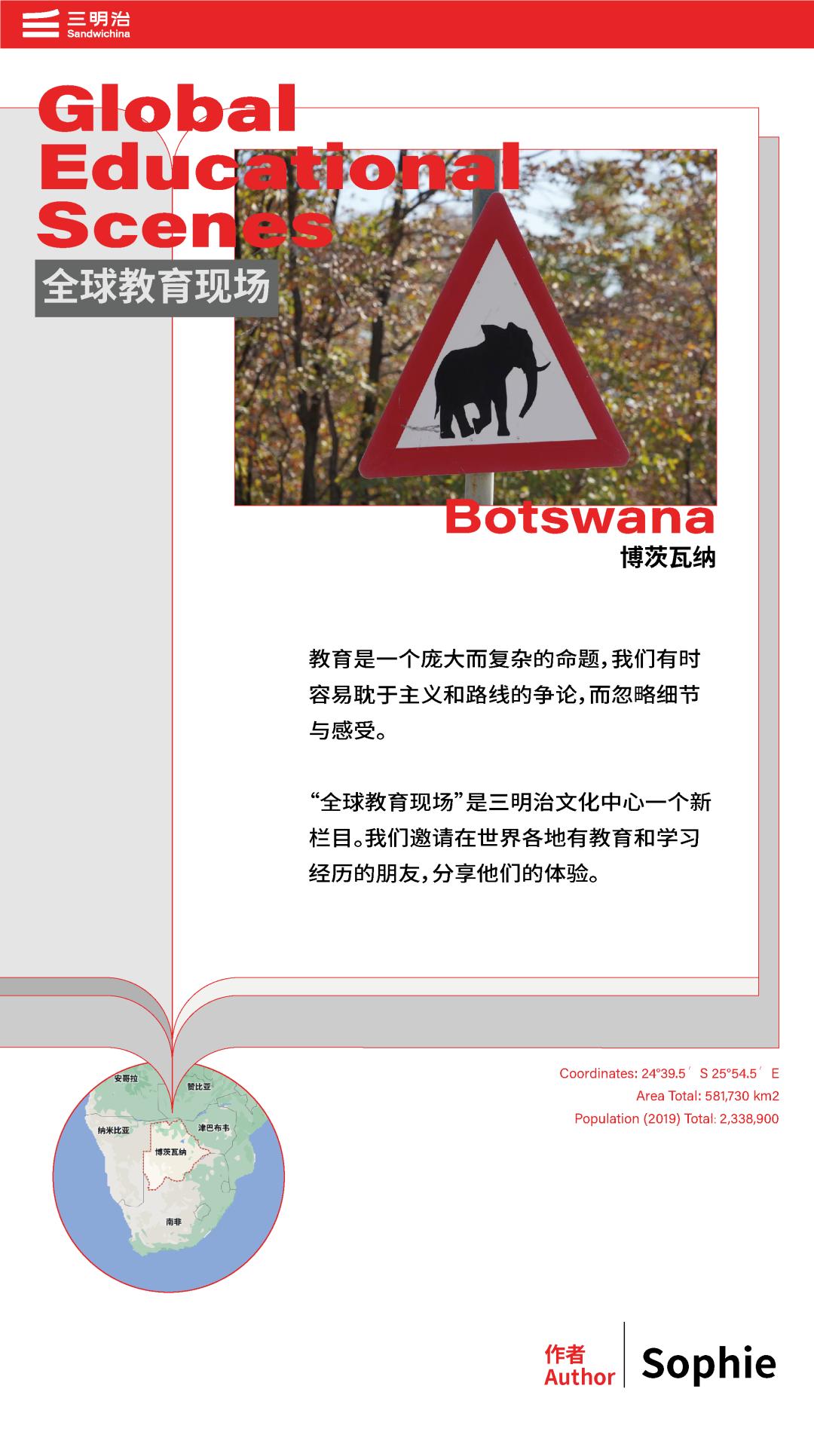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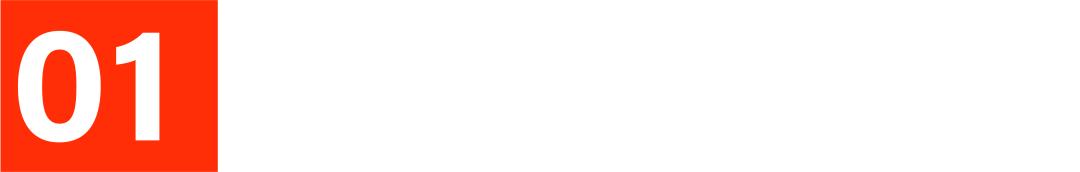
如果你见过博兹瓦纳的天空,那么你大抵也会想变成一只动物。这里常是云朵的王国,数不清的云朵以每秒零点零一次的速度慵懒地呼吸着。而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在天空的注视下尽情奔跑,扎实的的土地将你拱起,又时常变幻为河水与沙漠。这里,大地和天空享有同一个尽头。
一个同样是13万头大象和240万人类共享的尽头。
他们要如何相处呢?此刻不只我一个人正想着这个问题,还有THINK Global School (TGS)的30名学生。他们很快讨论起在学期前线上预习时了解到的知识。2019年,博茨瓦纳长达五年的“战利狩猎”(trophy hunting)禁令再次被重新废除。每年限量的狩猎证价格可高达5万美金,但猎奇者们仍络绎不绝地涌入境内。总统莫克格威茨·马西西对此给出了正向的经济价值解释:部分盈利将有效分配给对应的部落。而狩猎者不能带走的野生动物的肉则刚好可以成为村民饱腹的下一餐。
与很多其他的非洲国家不同,博茨瓦纳境内少有为限制野生动物而作出的地面交通区分,而这给村庄农田带来了不少损失。尽管也有大象无边界(Elephant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非盈利组织希望帮助农民不受大象侵扰,当我们带领TGS的学生去采访当地农户时,还是看到了现实的无奈。
游走在不同的视角间,初来乍到的我充分感受着新鲜的好奇和些许的困惑。我问起了本地人Benson的看法,他是TGS在哈博罗内(Gaborone)的专车司机。

Benson笑着问,“你想听真话吗?”
我微微地愣了愣,”嗯,那是当然了,你知道的,我心态很开放。“
”野生动物的肉简直是人间美味。“ Benson的语气变得腼腆起来。
这次我不再打算掩盖自己的吃惊,“你说什么?!”
“苏菲,你瞧,捕猎动物在商业化之前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但又绝非外界所以为的那样。这片土地上,我们的祖祖辈辈已经与动物相处了如此之久,不会贪婪地赶紧杀绝,那不可持续。”
“这倒是让我想起到了那些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原住民。”
“对,你说的是萨恩人(Saan)。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他们的捕猎对象也是有经验和选择的。说实话,那些天天嚷嚷着要动物保护的白人外来者,可能永远不会理解。”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合法化狩猎也许可以减少危害性更大的偷猎行为(poaching)。”
随着Benson越聊越起劲,他开始讲起疫情前曾经在日本求学的生活,给我看他和前女友在一起时的照片。他描述着回到家乡做旅游业时认识到千奇百怪的人,比如他和美国黑人相处之间微妙的张力与反差。他在我面前练习着他仅知道的一些中文词汇,畅想着未来可以去到中国做合伙生意。Benson说着说着,让我一时间感觉到世界也许真的就是那么小。
这种感觉,从我加入TGS的第一天,就有了。30名学生和11名老师,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和意料之外的谁说上知心话。
Benson的观点在后来我们去到马翁(Maun)市附近的Tuli野生动物保护区时,得到了一些当地向导的呼应。也许是久经风沙日晒,也许是见过太多不平静的命运,这些向导黝黑的皮肤和安定的眼神中充满着某种深沉的能量。我说是深沉的,因为这深沉会让我们这些外来者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并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尊重。

驻扎在草原上露营,失去了信号和城市中熟悉又繁复的一切,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了赤裸裸却尽显神秘的大自然。每天向导们开着越野车,带领我们辨识地上动物的脚印和空中鸟儿的类型,来收集一手数据并判断它们的踪迹。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接连看到嬉水的象群,惊慌的羚羊,警觉的斑马,悠闲的疣猪。但大部分时候,即使在飞扬的尘土中疲惫颠簸一整天,也不过是看到了一只在树下睡觉,同样孤独的鬣狗。学生们很快明白了无边无际的大自然中真实的随机性,这里不是人类社会建造出的动物园,没有既定的时间或是排练好的表演。在学习观察和等待臣服中,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夜晚降临时,就围坐在大本营的篝火边,而这一向腼腆的向导们也终于说起了他们自己的故事。
向导Adam是家中十个孩子的老六。回忆起童年,全是和哥哥姐姐们一起捕猎的场景。他最爱吃的是河马肉。
“河马肉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来自墨西哥10年级的新生Y小心翼翼地问起来。
“河马吃起来就是...河马的味道。“Adam一本正经的回答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也许是Adam描述的一切过于陌生,也许是Adam说起一切时显得那么云淡风轻,学生们继续发问,”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从小和野生动物一起长大,对它们非常有感情。现在能作为一个向导,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家庭,同时又能为外来人介绍这里的一切,并继续和动物相处,我很安心。“
学生们看上去若有所思,仿佛正试图在自己的世界和当地人的语境中找到一个中间点。这对于他们完成这次博茨瓦纳学期”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PBL项目制课(project-based learning)至关重要:不论是从环境生态还是人文艺术的角度,不论是呈现数据支撑下的科学故事,还是口头表演(oral storytelling)虚构的写作故事,总是需要先捕捉和理解当地有关人和动物的真实要素。
这样的要素对于TGS新学年的新生们而言,还包括过渡仪式ROP(Rites of Passage)中为期两天两夜的野外生存。
我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大家会经历和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了。

说起博茨瓦纳天空的云朵,其实它们也有害羞的时候。就像此刻,从哈博罗内在驱车开往马翁市的路上,天空干净得很彻底,像一片没有风浪因而十分静秘的海。

马翁市位于博茨瓦纳北部著名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附近,是许多野生动物的季节性迁徙之地,也是古老原住民萨恩捕猎人的聚集地。永恒的时间里,动物王国的规律少有变化,但人类社会经由历史不断的变迁已然十分不同。
随着草原上动物的故事逐渐立体起来,回到市区后TGS的学生们开始深入关于人的故事。来自英国的老师J和我一起带领着学生分析起贝茜.海德的小说。贝茜在南非长大,混血的出身和破碎的家庭让她从小就历经了南非种族隔离历史上几乎是最糟糕的一面。成年的贝茜在一场短暂的婚姻后决心带着儿子移居到博茨瓦纳,先后成为了老师,农民,和作家,最终经历和记录了这个国家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后的变化。
在《珍宝收藏者》(The Collector of Treasures) 一文中,女主人公Dikiledi因为谋杀丈夫入狱,并遇见了一帮同样罪行的女狱友。在父权伦理和乡村习俗的双重凝视下,属于无数个Dikiledi的命运已经被写好,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在命运展开的短暂一生中,在坚强的抗争与和忍耐中,小心翼翼地收集着每一次来之不易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如同一个珍宝收藏者。
这样的集体部落文化,冲刷着一个又一个人生,到今天剩下的是什么?非洲的祖鲁语(Zulu)中的Unbuntu,强调着我因我们而存在 (I am because we are),而当地的茨瓦纳语(Setswana)中也有表达同样概念的词语:Botho。在马翁市当地的一个社区理事集会点(kgotla),TGS的学生们看到了围坐等待着当地酋长倾听矛盾,仲裁争纷的村民们。以八大酋长部落联盟为历史基础与现代国会制度相结合的博兹瓦纳,已经算是当代非洲少有的一直维持国内相对和平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的两个月里,我们见到了因为同为单身母亲而团结在一起办农场的女性们,见到了懂得传统编织手艺而得以去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女性们,还有此刻围坐在kgotla前,裹着头巾,身着低至脚踝的裙子等待着表达和聆听的女性们。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我在博兹瓦纳待了两个月,肯定会立马期待我讲出什么惊险离奇的故事。但事实上,不管是人的故事,动物的故事,抑或是人与动物的故事,最终都被这些TGS学生们写尽了。学期末的对外公共成果展(showcase)上,生态科学的学生们展示着他们所制作的宣扬动物保护的网站,反映当地环境现状的科学论文,以及解释合法狩猎的概念拼接图(zine)。虚构写作的学生们则投入了口说故事(oral storytelling)的现场表演。
来自新西兰的R,创作了“斑马在哪儿的”的冒险故事,希望可以教育小朋友听长辈的话懂得在野外保护自己;来自莱索托的M,虚构了一个钻石失踪的悬疑案件,力图展现博茨瓦纳不同阶层在经济腾飞后的社会张力;来自印度的A,撰写了一则以当地医疗巫术为背景的话剧;来自加拿大的D,讲述了一场意外的森林大火中兄妹情的故事:
“Naledi在充满灰尘的道路上踱步,沙子扑上脚的时候,带来了一阵阵凉爽的感觉。她望向深蓝色的河,闪闪发光的阳光正在河面上舞动着,而此刻她一头厚厚的编发也开始随风荡漾。顶着头上装着新鲜水果的篮子,她走向母亲的小店准备开启一天的工作。云朵在天际中慵懒地徘徊,露出一个微笑。灵魂的深处她能感觉到,今天将会是不同寻常的一天。”
学生们的探索和收获让我倍感欣慰。期间我也曾略有伤感:作为老师自己却没能积攒创造出什么真正的故事。不过后来,生活还是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我想我最终收获了一种全新的自己关于自己的叙述方式。故事,总会找到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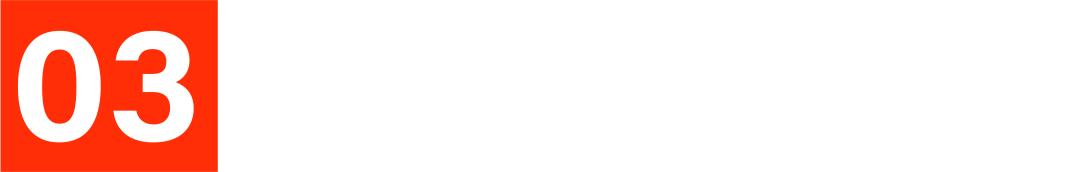
看着Tuli区寒冷荒野之上的星空,让我有一种在海里潜水的感觉。随着入水越来越深,被凝望着的星星似乎就格外迷人。然而银河像是水母一般,在我可以触及的距离之外极为缓慢地徘徊。
篝火已经把我的脚烤得暖呼呼。这真的是漫长的一天。我回想起今早,天还没亮,当地向导Patrick就驱车带领我们离开大本营,前往更远的沙漠草原。属于TGS新生们的过渡仪式就要正式开启了:所有学习演练过的野外知识技能,此刻将接受最真实严酷的考验。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勘寻找合适的露营点,收集着树枝,徒手搭建树下的庇护所,利用大象的粪便生火,然后烧水煮饭。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越升越高,尽情燃烧着它目光所及的大地上所有的一切。我们头脑的耐心如同身体里的水分一样,在无情的凝视下快速地蒸发。
“我们晚上真的会睡在这里吗?我是说万一大象来了怎么办,还有狮子,我们前几天晚上可都听见过狮子的嚎叫。” 来自孟加拉国的女孩R靠在树旁,用脚一遍遍踢着地上的沙。

”那别想那么多了,赶快干活儿吧。“ 来自西班牙瘦小苍白的男孩M头也不抬地继续铲着土,想要造一个新的火坑,同时指挥着来自加拿大的男孩D再去找更长的树枝。
我轻轻地拍了拍R的背,鼓励着她。如同我最终需要鼓励都在某一时刻曾害怕和质疑的大家,”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对这次挑战的实际和心理准备程度都非常不同,但我想要提醒的是,当你们选择了TGS的那一刻,你们也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教育,一种面对真实社会文化场景的教育。这意味学习的内容在每一个我们要去的国家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但现在,你们所面对的,就是博茨瓦纳的生存挑战。这样过渡仪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真正觉悟的勇士,更好地迎接TGS带来的教育挑战。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但是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方式是合作,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同伴。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们一起,ubuntu!“
向导Patrick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如同往常脸上没有明显的情绪,剩下的半天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帮着忙,就像来自天空的太阳,只是单纯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他那样的平静,因为等到太阳落日之时,我疲惫的灵魂真想跟着漫天的紫色一起消融了。面对兴冲冲前来交接“夜班”的老师,我像一个冰冷的兽医那样总结着白天发生了什么,分析学生的心理状态,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我自己呢,我明明知道这一切的意义,却在坚强乐观的外表下,翻滚着愤怒、失望、烦躁,难过、漠然等不同的情绪。我如同一个往天空扔着杂耍球的小丑,看不清发生着什么,只是重复着惯性动作。而就在意识到这种比喻的可能性的这一刻,我突然感到了自己的脆弱,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你还好吗?“ 我收回因为凝望着星空太久而变得有些寒冷的目光,随即被一个大大的拥抱裹住了脸。来自美国的女老师A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你今天回来之后就看上去有点闷闷的。“
“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只动物,也许我的情绪就不会像这里昼夜的温差一样,摆来摆去。“ 说实话,TGS这份工作的挑战性总是在不经意间袭来,或生理或心理,让人毫无防备。也许是有关于不同类型的孤独,频繁快节奏的旅行,也许是关于什么才是家,我的人生究竟需要多少的冒险,以及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听完我的倾诉后,A也讲起了她曾经做荒野治疗(wilderness therapy)培训时的体悟,人的身心如何互为因果。她讲起自己恋爱的苦恼,信仰的转换,思维的盲区。她总结道,“因此你可以像看电影一样,认为人生所有的事情是发生作用于你。你也可以认为是你自己要为所有发生的事情负责,因此你创造了,吸引了它们。你要选择你落在这个坐标轴的哪里”。
“你是落在哪儿?”
“我呀?我每天醒来,都觉得生活的一切是魔法!”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什么?“
生活...是魔法吗?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在1909年发明过渡仪式这一词的时候,定义了分离,边缘,聚合这三个阶段。当年的他会料想到就此20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分离,边缘,聚合吗?如今为TGS新生设计一年一度过渡仪式的我们,每一个学期都在经历新的分离,边缘,聚合,其中又充满了更多分离,边缘,聚合的时刻,可关于这些时刻属于我们的过渡仪式在哪里?
盯着眼前的篝火,蓝紫色和橘红色的跃动中,我和A沉默着。沉默良久,我们再次抬起头看向星空,而就在几乎是短于零点零一秒的瞬间,一阵强烈的白光从天空狠狠地飞速划过。
”啊!”我看回向A,大声尖叫着,“快许愿,快许愿!”
我完全不敢相信刚刚发生了什么。强烈的幸福和震撼冲刷着我的身体和头脑。“即使在最难过的时候,我也可以看见流星啊”,这个想法莫名深深地安慰到了我。生活中不经意间的小惊喜,往往足以成为掩盖一切不堪重负,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这些惊喜,也许有着一千个名字,一百种样子。它们是A每每感受到的魔法,是Dikiledi小心收集的珍宝。
我倚靠着A的肩膀,静静地看火苗中如何跳出点点星火。我感到了寒冷和温暖之间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任由自己再次潜入思绪的汪洋大海:我要是一只动物就好了。做一只猎豹吧,自信又坚定地在广阔的大地上奔跑,去冒险去体验去遇见。或者大象也好,因为它们总是母系群居,一定不会感到孤独。不过长颈鹿也不错,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野外长颈鹿的时刻,就在上周。它们和别的动物不同,那安宁又充满神性的眼睛会与我长久地对视。其实,不管是什么动物,它们似乎总知道自己是谁。它们应该永远不会有像我这样突如其来的狼狈时刻吧。动物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何表现,而人却需要意义,存在于故事中的意义。可对于人类而言,没有刻在DNA的叙事内容,也不存在完美的叙事方式。当旧的故事不能带来意义和幸福,是不是就得给自己讲一个新的故事了。这样倒也是个办法,这就当是我给自己的过渡仪式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我的思绪被开心的歌声拉出了海面。火堆那头,我的视线重新清晰起来,厨房的伙计还有向导们正缓缓走来。
“L and O生日快乐!” 向导们端来了蛋糕,学生们很快围了上来,拍起手大声欢呼着,用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一遍又遍地唱着生日快乐歌。
歌声中,L和O面对面心满意足地许完了愿望,开始拿起刀切蛋糕,但蛋糕太硬,怎么切也切不动。校长提醒她们小心点,却没有着急插手。最后L和O使了浑身力气,似乎也只切到了蛋糕的中间。面面相觑的大家望向厨房的伙计,不料他们笑而不语,随即接过了刀,将蛋糕猛地翻了过来。
沉默只用了一秒,所有人突然开始放声大笑,L和O一时间笑得捂起肚子蹲落在地上。
我跟着人群向前挤,顿时大惊失色:“我的天,那是大象的干粪便?!”
“我的上帝!” A和我一样在震惊中同时感到好笑:是啊,荒芜的沙漠草原上,哪里来的新鲜蛋糕呢?黑暗的夜晚中,被巧克力酱和奶油包裹着的大象粪便简直是个天才般的主意了。
“18岁真好啊,“ 我和A看着这帮笑嘻嘻的孩子,他们正捧着大象粪做出各种鬼脸自拍。我18岁的时候,可想不到10年后的此时此刻,我会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看着这些孩子。
”A,其实你不觉得,这大象粪便蛋糕恰好也是一种很强的隐喻吗?如同冥冥之中是在告诉这些孩子,甚至我们,人长大之后,就意味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遇见什么shit (糟心事儿),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laugh about it (一笑而过)。”

原标题:《一个中国老师和30位国际学生在博茨瓦纳| 全球教育现场·苏菲专栏》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今年以来最大地震
- 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地震应急响应
- 曼谷进入紧急状态,高楼倒塌致3死

- 广发基金2024年实现净利近20亿元,同比增长2.56%
- 易方达基金2024年实现净利39亿元,同比增长15.33%

- 北斗七星属于哪个星座
- 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是澳大利亚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