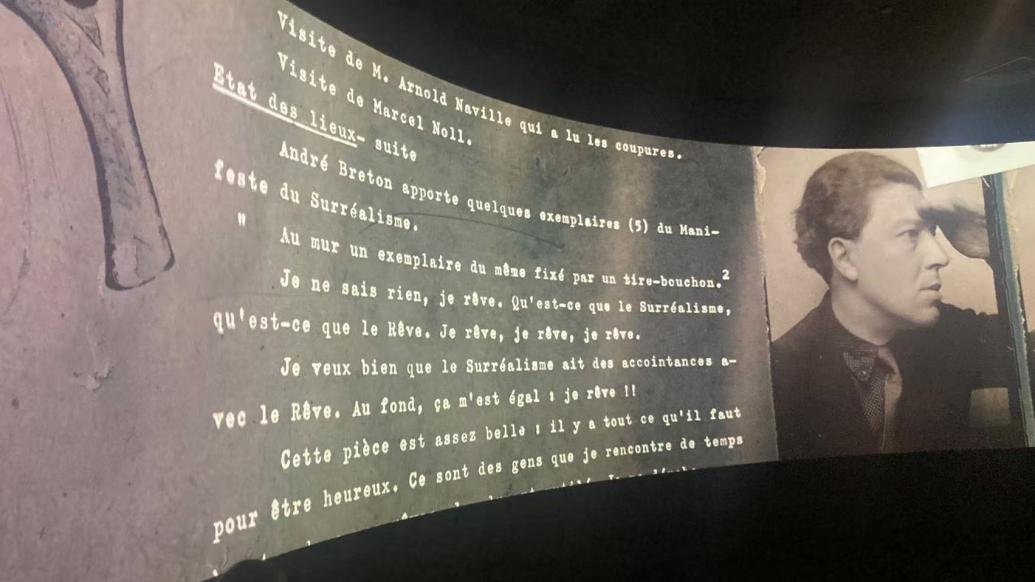- 3
- +124
海外族群冲突 | 如何统治帝国?
【编者按】
政治的内容不仅是规定谁在何时得到什么,它还指导一群人怎么与另一群人相处。而国家的统一并非当然之事,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分裂往往也不仅是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兴风作浪的结果。如何理解那些在制度上、行动中失败或成功的海外族群政治案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特别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族群政治研究小组研究员郑非为我们撰文讲述“海外族群冲突”。

萨拉托加大捷是世界史上著名的战役,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十三州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如何统治帝国?
一个大帝国如何统治一个自成一体、人口众多的边地?
这是1760、70年代的英国人普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烦恼的源头是日渐生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
英美分歧的由来是一个大题目,此处无暇赘述,只能说,当代史学家一般认为,英国对北美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与政治压迫。当时的人们也承认这点,比方说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埃德蒙·伦道夫也承认:“(美国革命)没有直接的压迫因由,不是基于仓促的感情之上……(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分歧的焦点似乎都出在“无代表不纳税”这个话语上。美方坚持认为,英国对美征税于法无据。对英方来说,事关英国宪政传统,这个质疑其实颇难辩白,只能支支吾吾。假如说“无代表不纳税”的话,那么为什么大英帝国不爽快接受这个意见,让殖民地往英国国会派出代表呢?
事实上有一大批人在英美危机甫发时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不列颠驻美洲的官僚们对此最热心。比方说马萨诸塞总督伯纳德在1765年11月在一封信中提议,“北美人认为他们不服从是有理有据的,因为他们在国会中未得代表。这种情况就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以其之道还施彼身,来强迫他们服从。让他们的话当真,让他们现在派出代表。北美大陆派三十人,西印度群岛派十五人,应该就足够了。既然在这个议会中殖民地得到了真正的代表,那么就对美洲政府事务兜揽到底。发布议会法令建立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政府体系,根据他们自己的原则,北美人将不得不顺从之。让大不列颠和美洲之间的关系一锤定音。从此美洲政府的权利,以及它们对大不列颠的服从,将一劳永逸的摆脱疑虑和争论。”
这个提议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殖民地都遭到了冷遇。
在伦敦一方,冷淡的态度来自于多种理由。有些理由自私,有些琐碎,有些出于愚昧无知,而有些则确实是由于制度限制。比方说,当时的议员是不领薪水的,所有人都必须自掏腰包。伦敦米贵居之不易,(据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估计)外地议员一年的花销至少在一千英镑(这笔钱不是小数目,狄更斯小说《孤星血泪》里面说,15英镑就能在外地开个铁匠铺子,可见其价值。如果按照购买力来说,1765年的1000英镑相当于2010年的10万7千镑,如果按平均收入水准来说,这1000英镑相当于2010年的157万镑),未必有那么多殖民地居民能花的起这个钱。殖民地政府每年总的行政经费(根据亚当斯密的计算,扣除马里兰和北卡罗纳)大概是64700英镑(且各殖民地有别,新泽西也只有1200镑)。如果每个殖民地派四个代表,就要总共花销52000英镑,所以殖民地政府愿不愿意花这钱很难说。如果是由帝国政府给薪水的话,就很难只给殖民地议员发,不对不列颠议员一视同仁(光下院议员就有558人)。况且,给议员给付薪水有违英国的传统政治观念,在此观念中,议员应该是有身家能“独立”的人,这样才能保证政治永远不会“堕落”成平民政治。如果是国王用自己的行政经费来发,那就更不行了,这直接违背1707年《任职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议员得到国王任命或从国王那里领取薪俸后,就失去了议员资格。”制定此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王在议会中安插培植亲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议会作为制衡王权的政治存在。
谈完钱再谈人。伯纳德建议的数目是30人,但美国革命领袖之一约翰·亚当斯要求根据人口比例来派代表,因此北美代表应该达到250人左右。下议院已经人满为患。美洲代表来的话,人少了不起作用,人多的话,有人就担心国会会臃肿不堪、喧嚣混杂、运转不灵与管理不便,国事必受影响,甚或有政治动乱的危险。再说,美洲派代表,爱尔兰、魁北克、西印度群岛诸殖民地以及东印度公司派不派?怎么平衡?
还有一个问题,不列颠美洲路途遥远,而不列颠的议会代表是每年一选,等到美洲代表选举完毕前往不列颠赴任,议会议事早已进行良久,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这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反对理由,因为无论是钱、代表人数还是选举制度,即使没有一致意见,还是可以坐下来谈谈,而谈判本身就是有好处的。
平等的问题
伦敦最主要的反对理由恐怕有两个。一是害怕美洲代表在国会中组成一个稳固的政治利益集团,同政府的反对派合作,或者与不列颠的工商阶层结合,来危害地主的利益(地主乡绅仍然是国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阶级考虑作祟。二同母国与殖民地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有关。在一个世纪之内(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十倍(从20万到200万),不列颠人口相对增速要缓慢的多(400万到700万),此人所共知。从幅员和资源含量上来看,美洲社会成长的空间也要大的太多。如果允许北美正式成为帝国顶层政治结构一部分的话,那么一步步发生由不列颠向北美的权势转移是相当可能的。
也许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考虑,历届英国首相才摇摇头拒绝了这个建议。据说国会里面找不出十个人赞同这个提议。
尽管不列颠不甚热心,但殖民地自己恐怕也并不欢迎这个口号落到实处。也正是在1765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决议说,派代表前往不列颠国会是不切实际的(Impracticable)。殖民地所有政治派别,无论是效忠主义者(Loyalists)还是激进派(Whigs),尽管在对母国的政治态度上各持一词,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
首要的理由当然是地理距离。根据北美政治生活的传统,地方选民通过发给其代表指令来保证议员的投票符合地方利益,英美之间横隔大洋,使议员有不了解民情的危险。但这个理由其实说不过去,因为长期以来,各殖民地都在伦敦派驻代理人,以游说议会,保护地方利益。之前怎么没有人抱怨这个问题呢?
瑞德(John Phillip Reid)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殖民地居民对地理距离的担心其实不是由技术因素而是由政治因素促发的。那就是当时殖民地的观察者认为英国国会非常腐败,充斥着宫廷的附庸关系与大臣的暗中贿赂。这样在监督不便的情况下,代表本身能不能抵制住诱惑,行事公正,就很让人担心。
但最根本的障碍在于,即使殖民地向不列颠派出代表,他们都只会构成国会中的少数。马萨诸塞议会解释道:“我们不想要国会代表,原因在于我们不认为殖民地将得到平等和充分的代表。如果不平等,那就根本没有效果。”宾夕法尼亚一份报纸刊登读者来信,说:“在国会有代表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除非不列颠和殖民地的利益一致,那么在国会有代表才有意义。在这个(设想中的)国会里,绝大多数人,家在不列颠,利益也在于斯,事务又是通过多数票决来决定的,如果我们期望美洲的利益(同他们的利益相反)能够得到考虑,那会是很荒谬的,荒谬程度如同期望从一个在争端中自任法官的人手上获得公正差不多。”而不列颠议会可以借助此合法程序对美洲任意立法,北美人只得哑口无言。
所以你看,抛开表面上的代表权问题,实际上双方所争执的,是帝国的边缘地带与中心究竟应该持有何种政治关系。
对殖民地来说,到底怎样代表才是“平等”和“充分”呢?按照人口、财富与税基平等分配议席?这里的关节仍然是,不列颠太大,殖民地太小(虽然小却不可以被忽略),不列颠太单一,殖民地太分散。
现代政治学通常认为,在类似这么一个分裂社会(divided society)中实行多数民主制,非但不能弥合分歧,反而会促进冲突的激化。
因为,要想在议会中,而不是在街头上或战场上解决争端,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所形容的“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即必须给双方的基本利益或权利提供最低限度的特殊保护,以便在投票中的失利不会对一方的生存或议价能力产生彻底剥夺。而不列颠所使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政治体系的特征有二: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政治圈子被划分成当政派和反对派。假如一个社会中的多数和少数界限相对固定(如不列颠和北美),凡事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没有给少数以特殊保护)来进行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很可能就会形成多数的垄断,以程序上的平等建立排他性的统治。
要避免这点,有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现代瑞士、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多族群国家所使用的——“协和模式”(Consociational Mode)。该方法有这么一些特色:1,政府组成人员里面包括所有主要社会板块的领导人(不分当权派、在野派,没有政权的轮流);2,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允许弱势一方拥有否决权;3,选举程序采用比例代表制,甚至给予少数族群以超出其人口比例的政治代表席位;4,政治程序极端注重妥协和协商;5,社会、经济资源的分配也按照比例进行;6,各社群内部高度自治,中央地方互不统属。比方说在瑞士,德语人口是大头,但瑞士政治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联邦委员会(瑞士的最高行政机关)中七个成员里面必须有两个人是法裔或意裔出身。
这种现代思想绝少“一统”观念,承认差异与社会分歧,明了异己的存在,对当下的政治现实不以为必然,以及抱定一颗共存的心。当时的帝国诸公恐怕念不及此。
总之,只是往国会里面派出殖民地代表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因为殖民地真正需要的,不是“平等”,而是“特殊”。没有这种“特殊”,殖民地的焦虑无法得到排解。在一个帝国内,指望“平等换忠诚”,是有难度的(更不要提不平等了)。
设计“特殊”
那怎样在帝国设计中体现这种“特殊”,又不至于否认大家还处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内呢?
在1765年后,殖民地居民已经开始提出,大家都是英国人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英国是一个单一国家。大英帝国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政治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北美殖民地人民与不列颠人民的地位是平等的。作为平等的一员,帝国的各个部分应该各自管理自己。殖民地与不列颠的共同点在于,“效忠于同一个君主,法制相通”。 时人如此说道:“(不列颠与殖民地)应该被看成是同一个王国(kingdom)下的不同国度(countries),它们的处境使得它们不能建立一个共同的议会,这使得它们要依赖它们的统治者来作为这么一个分立政体(partial polity)的共同基础,这样才能最好的适应各自的环境。”一个化名为Britannus Americanus的作者在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上发表文章,拿不列颠与汉诺威之间的例子做了比方,认为除了有同样一个国王之外,不列颠议会对汉诺威并无管辖权。杰斐逊在1774年撰写《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的时候,提出,北美与不列颠应该以平等的资格共同拥戴英王,而北美与不列颠之间的关系可类比于未有合并协议之前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只有一个行政首脑,而没有其他必要的行政联系。”换言之,杰斐逊提出了“共主体制”解决方案。
但这个想法也是行不通的。固然,后世有政治学家,如唐纳德·霍尔维兹(Donald Horowitz),认为假如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是通过人口和地域上的绝大多数(Super-majority distributional formula)或转票制(subsequent-preference voting)选出来的,那么比起议会制来说,能更好的弥合社会分歧,使得政治不那么排他。这是因为总统的任期和稳定度都要较内阁首长为长和高,受多数民意的控制要少。由于特定选举制度决定他(她)会是一个稳健派,这样也有利于减轻少数的忧虑。
问题在于,英国国王无法充当这样的角色。首先是因为他得位于世袭,并不需要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归到北美人民的拥戴上;其次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理想是King in Parliament, 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北美,人们对王权都有很强的防范心理。总统无需顾忌合法性的问题,但国王却很难违背任何一个立法机构的意愿,强行执行可能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政策。
换句话说,国王本身实际上起不到帝国枢纽的作用。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吗?有人在1768年提出,可以集合不列颠、爱尔兰、北美诸殖民地、西印度诸岛,成立一个帝国议会,专门负责帝国总体事务(整体防务、规制商贸和海洋等),然后各地保留自己的议会,自行处理一切内部事务(包括收税)。这其实是对往国会派出殖民地代表的改进方案,可以用限制国会权力范围的方式来缓解殖民地被多数压倒的焦虑。但是这个建议不会通过不列颠那关。如果说吸纳殖民地代表还在国会的考虑范围之内(1778年一支不列颠国会的代表团被派往北美,向大陆会议提出和解建议,正式提出在不列颠国会中容纳美洲北美),将自己降为一个帝国总议会的下级机关,恐怕很难被国会接受。大英帝国在美国革命之后至今也从未建立这么一个帝国议会。
还有一个选项是在北美殖民地单独建立一个“大陆议会”。这个方案是一个妥协方案,并不寻求殖民地进入大英帝国的最上层政治结构,但同时各殖民地合力则强,提升它们在帝国正式结构中的地位,以形成倾斜式双头帝国。
殖民地人民曾经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方案。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讨论未来的帝国政治结构上。约瑟夫·盖洛韦(Joseph Galloway)是宾夕法尼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所谓的“盖洛韦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十三殖民地上将会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总议会(grand council),这个议会的成员将由各殖民地议会派出的代表组成。凡不列颠议会涉及北美事务的立法,这个议会拥有否决权。该议会对北美事务的立法,不列颠议会也拥有否决权。与总议会一起,还将设立一位总统或主席,由英王任命,由他来负责北美的行政领导,由总议会来监督与制约。简而言之,这个计划将造就一个倾斜式的双头帝国结构,北美总议会和不列颠议会将构成大英帝国在北美领土的上下两院。当然,盖洛韦计划并没有将北美总议会同不列颠议会并列,而是承认,北美总议会是不列颠议会的下级分支。这个计划被看做是一个向英国递出的橄榄枝,得到了许多代表的支持,从1774年9月28日到10月22日近一个月时间内,第一届大陆会议都在讨论这个方案。到22日,大陆会议进行了投票,结果是6:5,以微弱劣势,该方案被否决。之所以遭到否决,可能是因为很多代表的地方主义情绪,他们对这么一个总的大陆政府的可行性表示怀疑。但这个方案最根本的缺陷是,来的太晚。当时英美争执已深,面对不列颠的步步紧逼,要求殖民地承认不列颠在美洲事务上有立法权,实在是强人所难(这个方案要求殖民地做出让步,让弱者在冲突面前主动退却,实在困难)。此外,不列颠的当政者也不太会考虑这样的做法。如果说将北美代表纳入英国议会算是激进做法,那让各殖民地拥有对殖民地事务立法的否决权,恐怕也不算温和。直到最后,不列颠的统治阶级也没有考虑过这样做。
最后一个政策选项是,不列颠议会以立法的形式将1763年以前的政治潜规则明了——不列颠议会负责总体事务,但将内部事务留给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处理。一批英国政治家,比如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在1775年2月、柏克在1775年3月分别在议会中发表演讲,主张“在实践上,回到经验所一致指明的最好办法。”提出几项基本提议:承认殖民地议会的合法资格,承认其有益于帝国,承认由殖民地议会自愿输将而不是被动纳税才符合帝国利益;帝国不干涉殖民地的宪章。我们从事后看起来,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办法,也许可行,虽然争端的结构性根由没有消除掉,但是把争端的具体理由抹掉,也能得过且过,一如以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故事。但是这个主意的缺陷是,它必须有一个互信的环境和历史清白的基础,而且要求强者(不列颠)首先做出让步。到了1775年,当双方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冲突的时候,这个方案就显得不够让人信服。尽管殖民地可能会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但是大英帝国在直接的冲突中已经赌上了自己的荣誉。而且,这一计划比起1763年体制要更削弱中央政府的权限,后退,很可能在欧洲国家以及大英帝国其他的殖民地眼中,看起来像是可耻的投降与虚弱的表现(盖洛韦方案好歹还给了不列颠部分主权)。
这样,盖洛韦方案和柏克方案都有一些问题。强者和弱者都各自有不能、不愿后退的理由。
至此,宪法选项用尽。可以用来解决英美双边争执的政制方案,由于种种理由,都被否决。剩下的,唯有战争一途了。大英帝国的统治者,没有身处一个多元帝国之内的自觉,他们还在用建设民族国家的思路,来经营一个帝国。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英帝国在美洲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政治想象力与政治智慧的失败。
今人总结美国革命的教训,也许会想,想要避免类似革命,乃至以后在多族群国家里面避免国家分裂,只要反英国之道而行之就行了——给少数族群公民以相应的政治权利和代表,平等待人。简言之,人人有选票。这肯定是一个过分简单的历史教训。为政者不可不察。


- 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失事
- 2025年全国两会召开日期来了
- 中日达成10项共识,涉旅游体育等

- 华丽家族:股东上海泽熙所持全部股份9000万股将被司法拍卖
- 北京市大兴区挂牌两宗地块,起始价23.2亿元

- 世界上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位于哈尔滨
- 中国的国宴以什么菜系为主?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