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青年学者谈|宋念申:以国界为中心来思考现代国家形成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该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围绕图们江边界地区和越界的朝鲜人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问题”。该书在分析理论上另辟蹊径,突破了过去往往以政权中心来理解和定义边疆的传统学术视角,而是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重心和切入点,反过来分析关于交界地区的争议如何塑造了领土和国民这些重要概念在现代东亚地区的形成和嬗变。该书内容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但同时又以“人”和“土地”这两个主线来串联书中的分析,并在各章中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形态,是由其处理土地与人的方式决定的,而对边疆、边界和跨界人群的处置,特别体现了对国家的型塑”。这种以边界和边民为中心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东亚“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转变过程非常重要。
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这本英文专著的成书脉络和理论方法谱系,以及他下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本文为访谈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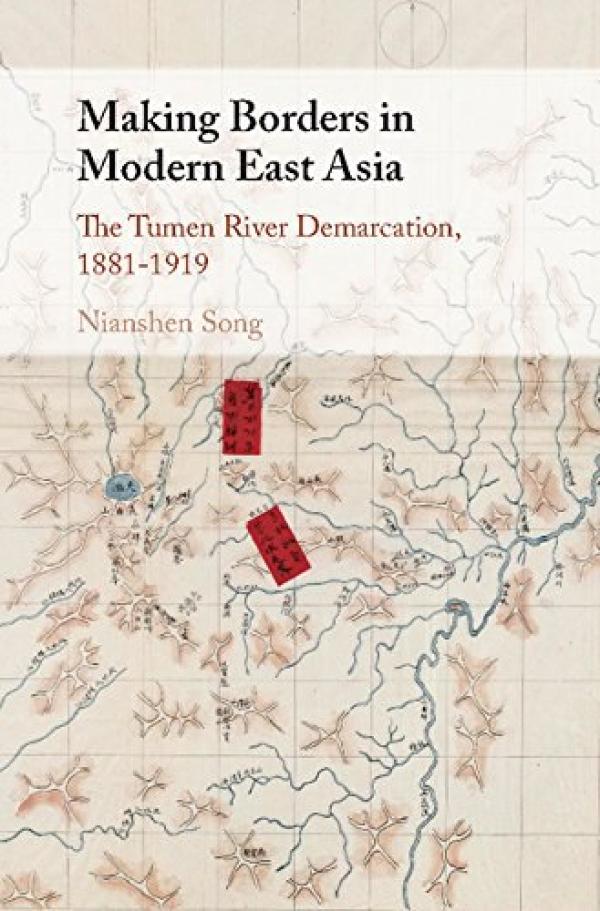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请问这本书选题的背景是什么?
宋念申:我最早接触图们江和朝鲜族,就是前面提到的2004年去东北采访中朝边境。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申遗这件事。一年后,这件事引爆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这也成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论文课题。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就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东亚国际关系总是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大多跟历史认知有极大关系。边界和边疆虽是政治问题,但也是历史认知最为撕裂的地方。而流行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框架,总是谈实力啊、利益啊、结构啊、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拿来解释东亚隔膜都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去分析。在为日本史和韩国史两门Seminar写论文时,我都选择了“间岛”(今延边)交涉: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东亚三个国家,并且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真正引发冲突对立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改变——东亚的区域结构、国家论述、历史观念,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了极大变动,导致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你书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认为是边疆定义了国家。过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是一般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你是反过来从边界看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多说说吗?
宋念申:我在学政治学的时候,开始对“国家”概念产生疑问。我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于英语语境中state(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理清楚。东亚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能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我们一直把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当作一个不用质疑的框架,用来分析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或者整个区域的关系。可是东亚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固化的现代(领土-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和解决,很多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在这三个地方追求国家现代性范式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历史中去看,不要把“国家”想当然地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像边界一样,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理解它的观念变了。随着它的变化,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就都不同了,甚至理解国家的方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是先有了国家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去处理它的边界;还是先有了边界,然后边界以其同时的排斥性和容纳性,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图们江领土争端时,我不想用传统外交史的方式来写。因为在外交史中,国家往往是先验性的,不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和在这个空间里面,恰恰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很流动的。只有当有了划定边界的过程,其领土的形状性质才确立,其国民的内涵也才更新。因此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不是国家定义了边界,而是边界定义了国家。
你这本书和此前的相关领域中哪些学者或者学术议题在进行对话?
宋念申:从问题意识上讲,我的书可能更接近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对边界国家的讨论(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1999),或者通差·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对国家地缘机体的讨论(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1994)。他们不是从一个回溯的角度,问“某一个国家的边界在哪儿”,而是问:这种现代的边界感及边界实践,究竟怎么来,又怎么塑造现代国家?同时,我也想介入对民族问题的探讨。这一二十年中,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作品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很多作品提出边疆民族在帝国或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我想问的是,从帝国向现代国家(不论我们是否称其为“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边疆民族扮演何种角色?东北的边疆民族实践,又为什么与西南、西北如此不同?
说到如何看待现代转变,我不太同意把现代性和传统对立起来。在延边这个地方,现代也是在传统中演化、刺激出来。西方国家介入很少,即便有,也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精英、民众在交涉过程中的实践。
所以你专著的学术价值,不只是挑战盛行的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也包括历史叙述、领土传统,以及东亚的领土争议和国际法本身的适用性等问题。历史上双方可能根本没有这个现代的边界意识,实际就算过去的民众关心边界,他们所理解的边界与国家,都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是这样的吗?
宋念申:对,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框架去分析历史,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也要意识到现有框架的形成,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比如说我们一谈国际法,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规范。可是,看一看国际法形成的过程就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法是殖民主义工具。国际法对于东亚国家意味着什么呢?不要忘了,1905年时候,韩国被由国际法组成的“国际社会”剥夺了国家资格。在书里,我有一小节专门分析“无主地”概念是如何被殖民者操弄,用来为殖民东北作国际法论证的。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总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活在边界地区的民众理解的土地、空间概念,差别非常大。
而且你也提到了,过去我们理解是现代国家塑造了边界,或者说划定了边界,通过不管是争端,谈判或者说国际法。但就如你刚才解释的那样,你的专著实际上是想从边界如何定义了一个现代国家,来理解历史进程。所以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实际上他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边界更为清晰的一种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书可以说是以小博大,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研究这三个在历史上有密切交往的三个东北亚国家,是怎么通过边界争端来理清楚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的。
宋念申:这的确是一个自我身份形成(identity making)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首都,而是发生在边地,这是很多边疆学学者,一直强调的:帝国或者民族国家是边疆塑造出来(empires or nation states are made in the frontiers)。边界也不是由在首都的几个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空间中,由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者一起塑造的。甚至这里所谓的国家不仅指首都中的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它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和中央的边疆逻辑是不一样的。基层官员代表的国家,当地精英代表的地方社会,和非精英的草根民众群体,他们在实践中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很多时候,边界问题是民众和地方社会推着地方政府去提出,地方政府又推着中央去交涉。所以很大程度上,地方的居民、官员,以他们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具体实践,推动、完成了对国家的重新理解。
你的专著除了中文和英语之外,还涉及到了使用了日文、韩文资料和档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研究项目。你当初做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宋念申:一个是你提到的语言,另一个就是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一些档案比较难获得,但进入田野调查能够获取一些补充材料后,发现这也不是最大挑战。
最大的挑战,在于用什么框架去阐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中日韩的历史学界已有很多积累了,需要想清楚自己能从哪里突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不少人一开始会说我的题目是“外交史”。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外交史。外交史关注国家层面的交涉,把边界冲突理解成两个和多个国家,对主权范围的争夺。可是所谓的“间岛”争议不是,在19世纪末之前的图们江地区,行政机构往往是不在场的、远离的:这不是说这个地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说国家的管治方式,是去封禁、搁置它,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开发、利用。正是因为19世纪末的内外压力,这个过去有意空置的地区,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这时候才需要把土地、人民,乃至当地历史,都做一个清晰的定义和分界。这个过程,是现代国家在此“生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概念在此“生成”的过程。而且,它不仅重塑一个国家,而是同时重塑了三个东亚国家、重塑了区域。
想清楚这点后,我也就知道,我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由地方实践塑造出来的国家。我的主题是从地方史,从一个边地,来看几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这是个多边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同时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regional local)和全球性(global local)的地方。从地方史出发来讨论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主流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既定框架和术语,而专注于构成国家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土地和人,看看这两个要素在大冲击、大转变中,如何在与传统的分裂中又延续了传统。
这本书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以及理解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
宋念申:往往谈到中国近代史和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一个大主题就是中西(或东西)间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中韩关系等等,都是在这个大主题之下的分支。如果说我的书存在一个新视角,那可能就是,指出了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封禁的边疆地带,它在没有西方的直接介入下也快速发生了现代转化。这个边疆地带,包括整个中国东北,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东亚最为“现代”的一块场域。在东北的国家建设实践,在二战后深刻影响了所有东亚国家的现代建设。杜赞奇在他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曾经把伪满洲国比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个国家先期在延边的国家建设,可谓是伪满洲国的“试验场”。这给我们充分认知“东亚现代”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
另外,我把国家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土地和人才更具延续性。边界、边民的状态,一面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影响,一面也自下而上地塑造着国家具体而微的样态。你在核心腹地感受到的国际关系,与在边地感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国际关系不只有抽象化的国家视角,也有具象化的、人文性的视角。我们在北京上海感受到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边境居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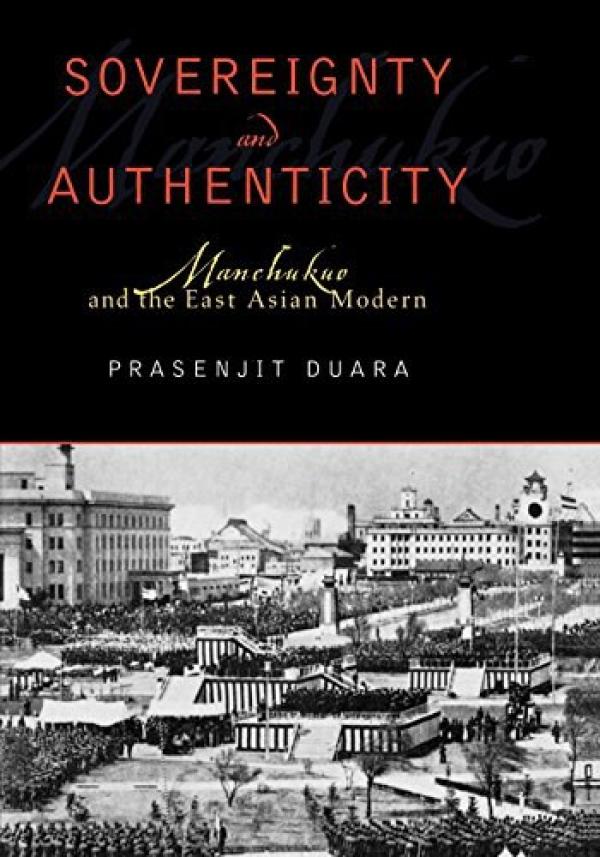
《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你的研究和最近几十年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帝国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有哪些关系和异同?
宋念申:倒没有刻意想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者历史社会学中的帝国研究对话。其中对清帝国、日本帝国和韩国的讨论,更多可能是东亚史学界的帝国研究做回应。比如在我的书中能看到濮德培(Peter Perdue)的影响,他强调帝国建设的全球联结,特别是地图、知识、物质、法律的全球散播,我的书也强调这点。另外,研究日本帝国的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泛亚主义的复杂面向:它一方面是反(西方)殖民帝国的,一方面又是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比如Jun Uchida的书Brokers of Empire(《帝国掮客》)。在帝国如何催生了韩国民族主义兴起方面,施恩德(Andre Schmid)的Korea between Empires(《帝国间的朝鲜》)是个无法绕开的杰作。现在很多日本学者越来越关注到知识生产中的帝国性。我在分析内藤湖南、篠田治策这类帝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借鉴了名和悦子等日本学者在帝国批判框架下的新研究。
我的书比较强调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关系。我虽然没法完全摆脱“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术语对立,但是从对地方的考察中,两者的对立并不明显。举例来说,“入籍”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的“入国籍”(成为公民),和帝国的“入版籍”(以征地纳粮),在地方具体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口流动,和土地分离时,二者之间的断裂感才体现出来,进而对国家的规范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族群的多元性,也并不是帝国的排他性特征,包含朝鲜族在内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本书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的企图。这倒不是说后殖民理论对我没有影响,只是当运用到具体的地方史研究时,后殖民有时候会简单地塑造一种“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把二者作一刀切的本质化理解。延边和东北的近现代史,当然有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叠加性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比单向度的殖民性要更加丰富。我觉得汪晖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
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中,你提到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能再多谈谈你的考虑吗?
宋念申:其实我的书里,有很多地方是受后殖民研究影响的。比如对近代国际法话语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反思等。可是,如果把后殖民框架在东亚放大,就可能把历史上实在的经验也抽象化、简单化了。比如,当我们说“民族”概念是虚构的、想象的,很大程度是对抗殖民主义的产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中国人的身份完全是虚构的吗?或只是近代建构的吗?好像又不完全是。现代中国民族的概念,其实是把历史上不断出现过的身份认同,按照民族主义的方式嫁接、改造了。
后殖民思想深嵌于殖民框架中,但用来分析边疆有诸多问题,很容易过度强调一种内外身份对立,而忽视各种跨界交往的长期、复杂和互动。拿东北边疆来说,谁才是东北的“原住民”?这片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多文化交汇的地方,一直到20世纪都是如此。再比如,今天的中朝边界线其实从明代就基本确立了。如果因为现代边界的观念是殖民产物,而认为连实体边界本身都是现代的发明,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整体欣赏威尼差恭对“地缘机体”的描述,但对他过于强调边界的现代属性的论断(“只有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才需要边界”),则有所保留。
有哪些经验分享给研究类似或者相关题目的年轻学者?
宋念申:我自己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是不同学科,因此常常遗憾自己史学功底不足。芝大也不开方法课,我只好边研究边补课,就好像是直接跳进水里学游泳。但是因为心里没装着既定的研究路径,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见到有用的就拿来。我喜欢到历史现场去看,在实地观察中找感觉。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它让你得到文献无法给你的感悟。所以我也建议初涉研究的学人,多看历史学之外的书,多在实地考察中积累感性经验。
你下一本书准备什么题目?和这次出版的新书有渊源吗?
宋念申:我现在准备写的书稿算是微观史,打算写一个沈阳的一个小街区370年的历史。发现这个题材和前一本书还是有渊源的。作博士论文时去沈阳查资料,一位老师知道我研究朝鲜族历史,特意带我去了沈阳著名的朝鲜族聚居区后来有意查了一下这个社区的形成,发现那里的历史非常有趣。所以我想从一个小空间中反映中国或东亚长时段的演化。
这个小区如果是街道的话,出现在档案里的频率应该比较小吧?
宋念申:其实还好,尤其是当代部分。很大一个原因是沈阳的地方志做得很好。甚至这个街道,还有自己的街道志。我的着眼点,当然还是把小空间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这个空间的意义就不局限于它本身,甚至不局限在它所在的城市。
我刚才听到你用了很多次“空间”,看来你的分析框架是用空间组织你的资料,这对说明你主要的观点是起什么作用?我相信不只是空间的变化和延续,对不对?
宋念申:这是一本比较接近城市史的作品,所以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和人在空间中的关系。不过我最希望突出的还是叙事,想写一个比较好看的故事,而不是用某一种框架去突出一个观点。其实从城市空间入手,我发现我最终落脚的还是国家,是通过小空间讨论大空间的变化。
微观史一直面临的一个批评:太具体而微了(too specific);似乎分析得越细则越没有代表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下本书如何解决这种张力的?
宋念申:我不觉得微观史一定是和宏大叙事对立的。好的微观史,阅读下来应该和大主题历史没有什么不同才对。我选择这个小空间,可能正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以至于我都没有感受到它和代表性之间存在张力。以小写大,其实主要要解决的是视角问题,以及怎样写才能好看。另外,因为本书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长时段吧,我在处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候,会有意识和研究这些时段的著作对话,比如清史、伪满洲国史、社会主义时期东北史等。
(本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招淑英、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罗清清协助整理。)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