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会议︱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与新方法
2020年10月24—27日,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高级研修班,来自海内外二十多所高校的一百多位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报名参加,最终入选研修班的正式学员为二十八名。为期四天的研修班议程,一共举行了五场导师授课讲座,两场学员论文讨论以及一场圆桌对话活动。以下仅就知识分子研修班举办期间的讲座内容与圆桌对话内容,进行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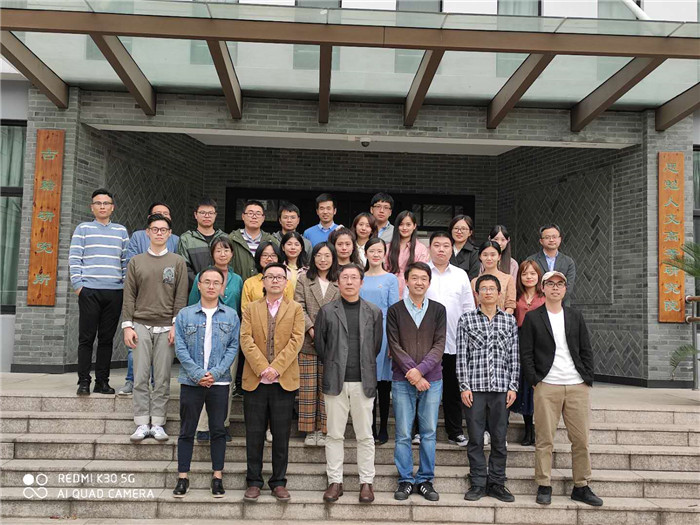
部分与会者合影
孙郁:思想史里的鲁迅难题
24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孙郁教授作了题为《思想史里的鲁迅难题》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为研修班系列讲座第一场。
讲座伊始,孙郁教授指出,“鲁迅难题”的原因,往往在于将鲁迅纳入到片面的解释体系之中,如左翼语境和自由主义语境,进而他从这两种语境出发,分析其难以解释鲁迅的地方。

第一,左翼语境下难以解析鲁迅。从瞿秋白开始,毛泽东、王富仁、汪晖、林贤治都从左翼视角去解读鲁迅。孙郁教授着重分析了鲁迅与苏联的复杂关系。鲁迅主要是通过文学而非政治去认识苏联的。他欣赏托洛茨基的文学评论,并批评中国左翼文坛的“辱骂”和“恐吓”之风。鲁迅译介的苏联文学作品均为斯大林时期以前的。鲁迅没有列宁的政党政治的概念,属于草根左翼,是有自己个性的同路人知识分子。
第二,自由主义语境下难以解析鲁迅。张凤举、周作人、许寿裳、张中行、汪曾祺等强调鲁迅非政治化的方面,侧重其“消极自由”方面。但鲁迅对代议制民主持批判立场,对自由主义者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也有批判。一些学者由此提出了鲁迅易于被专制主义利用的命题。孙郁教授谈到自己对思想学术界关于“胡适还是鲁迅”争论的看法,认为二者各有其特色,简单的扬胡抑鲁或抑胡扬鲁均不可取。
孙郁教授用海德格尔的“本有”概念描述鲁迅,认为鲁迅“让存在打开”,具有对本质主义的学术话语的颠覆性。让我们认识到了鲁迅其人其思的丰富面貌。
章清:“社会”概念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
25日上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发表演讲,题为《“社会”概念的浮现与读书人新的生活形态》。

章教授主要针对“社会”这一概念展开分析,尤其是揭示“社会”从“无”到“有”的历程,以此呈现近代中国概念成长的意义所在。
讲座伊始,章教授先从理论上对历史叙述中的“有”与“无”问题,作了一番说明。章清教授认为,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是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而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所呈现的实际是更重要的“有”。因而,从“有”与“无”的整合性视角看待历史,则是必不可少的。在理论交代后,章教授紧接着从“无”与“有”的角度,切入到正题,即关于“社会”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及变迁的意涵分析。
从“无”的线索出发,章清教授认为“社会”在定名前,存在着种种过渡性的用词,而这些过渡性用词若略加分类,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历史上的“社”与“会”;二是针对society最初的英译;三是根据理解所创造的新词,即“群”、“群学”等。而从“有”的线索出发,“社会”概念的成长,同样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第一是其与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关系密切,因为“国家—社会”的架构,是相互依存的;第二是“社会”的成长有其基本的标识,通过组成“社会”的标识象征物来揭示其内容及实在;第三是将“个人”的成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写照,以及揭示个人在“社会”中的体验,都成为理解“社会”的关键。简言之,章教授从“无”对“社会”考察,侧重揭示通向“社会”之间的各种概念;而从“有”对“社会”的分析,注重阐释的是“社会”存在的具体呈现样态。
在关于“社会”概念的主体内容讲述完毕后,章清教授总结了“社会”作为一种力量的浮现的内外部条件,一是依托于报章、学校、学会等媒介;二是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思想实践。除此之外,章教授还针对目前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人”的缺失问题,二是仅靠“数据库检索”从事研究的问题,都作了警示性的指正,并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够对其局限性加以重视。
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
25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许纪霖教授为研修班学员作了题为《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的精彩讲座。
讲座伊始,许纪霖教授强调,这篇文章采用了“历史与逻辑同一”(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理想类型”(韦伯)的方法。将五四时期流行于中国的各种“主义”区分为两组“理想类型”。第一组是“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前者以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为代表,后者则囊括了当时各种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第二组是“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五四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兼容并包,即“柔性化主义”,而具有一元化倾向的列宁主义则属于“刚性化主义”。

五四时期首先是“知识化主义”与“信仰化主义”发生了分化。代表性事件即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然后则是“柔性化主义”与“刚性化主义”的分化。五四时期流行的社会主义派别众多,有:一、中共系知识人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二、国民党系知识人戴季陶、沈定一、邵力子等;三、研究系知识人张东荪等。三派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曾有短暂的合作,但在要不要接受列宁式建党原则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终分道扬镳。中共则通过对外部与张东荪、梁启超等展开社会主义论战,对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论战两场论战,排除信奉“柔性化主义”的“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使中共成为奉行“刚性化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金雁:19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
26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金雁教授为研修班学员带来了题为《19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演讲。金雁教授的讲座主题鲜明,即通过对俄国贵族与平民两代知识分子的比较分析,以此来揭示俄国知识分子丰富内涵及精神特质。

金雁教授在对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讲解中,突出强调“共济会”在贵族思想者群体中的作用。但共济会因其自身矛盾性内涵,即一方面具有神秘主义特质,使其表现出反体制的愿望;另一方面则为眼光只是向上,从来没有向下联系过俄罗斯下层民众,使他们把变革的希望仅寄托在近卫军官的宫廷政变和影响沙皇的政治取向上。而这两方面思想内容,都对贵族知识分子产生不小影响。接着,金教授就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详细梳理,比如文学中心主义,行动能力的缺陷,永远的忏悔者,痛恨专制却又对农奴制态度暧昧,既倾向西化又厌恶资本家,既充满着救世情怀又存有遁世倾向等。
讲到上述特征,金雁教授对贵族知识分子“行动能力的缺陷”特征进行阐释时,引用屠格涅夫小说中主人公罗亭的形象,来说明贵族知识分子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同时,金雁教授也相并指出,贵族知识分子做国家的反对派,并不是政治革命意义上的反对派,他们只想做“对政府没有危险、有益的反对派”。讲到“救世情怀与遁世倾向”特质时,金教授认为贵族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情结”,即认为自己能够“通晓上帝真理”,承担起救世责任。
在讲解完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特征后,金雁教授转向对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剖析。金教授认为,平民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僧侣阶层,即多为神甫子弟,他们在思想水平上远逊于贵族知识分子,但却具有强烈地行动能力与行动意志,且比贵族知识分子更为激进与功利。在金教授看来,平民知识分子极端功利主义的“善恶标准”,就产生出以动机来衡量正义,以手段来服从目的的处事准则。
讲座最后,金雁教授在对平民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涵进行总结时,还就平民知识分子与列宁思想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重要的说明,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到俄国革命的思想动力资源由何组成,由何促进等。
杨国强:后科举时代知识人面对的文化与政治(1905-1925)
27日上午,第五场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研院研究员杨国强教授带来,他的演讲题目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面对的文化与政治(1905-1925)》。

杨国强教授首先论述了科举废除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兴建学堂需要大笔经费,因此兴学造成了地方的骚扰,加剧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的脱节。表现为社会上层与经济基础的脱节,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脱节,城市与乡村的脱节,沿海和内地的脱节。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皆由学堂产生。但知识人内部同样充满了纷争,彼此之间,是缺乏认同的。
杨国强教授继而通过与后科举时代的对照,又分析了传统科举制的特色。科举是一种公平地录取少数人的制度。科举对应着一种开放的政治权利。科举面前,人人是相对平等的,造成了一个流动的社会。
杨国强教授最后从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废科举的历史意涵,并指出废科举意味着从政治文化一体变为政治与文化的断裂。士人由科举而入仕反映了士人由文化而进入政治,是以文化制约政治。倡议废科举的读书人只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忽略了科举的文化意涵,这反而造成了知识群体的失落。科举废除后,从前与文化合一的政治变成了没有文化支持的政治。新式知识人,要以思想改造社会,依靠的文化的力量。失去了入仕途径的知识人转而以新兴的报纸为媒介影响政治。这与传统士人的公共性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圆桌:作为方法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
27日下午,知识分子研修班最后一个环节,即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与新方法”这一主题,在人文楼3102会议室展开圆桌对话。圆桌对话的引言人,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三位教授,即许纪霖教授、瞿骏教授、唐小兵教授。此次圆桌对话,分上下两场举行:上半场主要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域,下半场侧重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新方法议题。
圆桌对话上半场伊始,许纪霖教授讲道,以往学术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考察,无论是从知识分子的个案入手,或者是着眼于知识分子群体,乃至是聚焦在有关知识分子的事件上,大多是将知识分子作为研究对象来展开,而作为方法的知识分子研究,则往往为学界所忽视。正因如此,若从“作为方法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思路出发,将有可能开拓出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进路。当然,在讨论知识分子研究的新方法之前,有必要先行了解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域。
唐小兵教授指出,近几年来,新革命史的兴起为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在此之前,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话题,一般是将知识分子置于文化与政治,或者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场域中,考察知识分子在“道”与“政”之间的对抗性关系。但是随着新革命史视角的运用,可以深一层地追问,在革命主导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即知识分子在其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并不诚然为时论所描述的那样,是被历史浪潮所裹挟。唐小兵教授通过对于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的革命参与,拥有很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一方面是被革命理想的吸引,是对革命本身价值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参与者,同时也扮演着革命的塑造者角色。因此,探究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共振”部分,将有助于整体性的了解知识分子多元复杂面相。与此同时,唐小兵教授还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提示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中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如此展开思考,无疑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与思想世界,有着更为深刻及独到的体悟。
瞿骏教授接着讲到,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域,未必要靠“新”来维持其活力与生命力。所谓的新,需要从多面性的维度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一则是对西方思想方法的吸收,另则也不要完全遗忘传统性的,经典性的知识分子研究法的作用及意义。只有整合性的对二者加以检讨、反思,才能实现问题与视域的更新。瞿骏教授还从“走进”与“走出”两个方面,谈及知识分子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所谓走进的思路,其实可以用“过去即异乡”(the past is foreign country)来概括。举例来说,就是在研究1920年代、1930年代的读书人时,不要将其等同于今天的读书人,尽管二者有相像的部分,有连接的部分,但是就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二者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学者在呈现这一时间段读书人面貌的时候,有可能是在呈现自己,呈现自己的思想或政治取向,而非作为历史人物的读书人。显然,这些都是需要加以纠正。此外,理解走进的思路,其实是要将理解的重心放置在“人”身上,只有进入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中间,历史的呈现才会贴近真实。所谓走出的思路(“走出”提法来自章开沅先生),简单来说,就是要明白这个世界构成,不仅仅只有知识分子;况且,知识分子还是这个世界构成的一小部分人。历史是由多个乃至无数的要素,一截一截的融合成长起来。因此,走出知识分子的世界,去理解与知识分子共生的其他群体及事物等,才能对中国历史有着整体性的把握。
许纪霖教授从自身的研究经历出发,继续发表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看法。许教授指出,在1980年代最初研究知识分子阶段,因受心理学的影响,主要是从心态史角度切入,以此进入人物的思想世界。但到后来发现,关于知识分子研究,若仅凭心理学的学科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开始注重政治、哲学及宗教等知识结构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九十年代以后,许教授开始转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学界较多的思想史研究成果,往往只注重思想的相关文本分析,即关于文本的脉络梳理与阐释,而对于思想观念何以发生,何以会发生影响,则缺少解答。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只注重文本的内在理路剖析,却存在缺乏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相联系的短板。此后,在方法上,许教授开始结合思想史与政治史,从内在理路与外在语境,即context的双重意义维度出发,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再到后来,许纪霖教授发现,作为“人学”的历史学,若要将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鲜活性地呈现,还得从精神史的层面着手,方能有所收效。这是因为,从精神史出发,它不仅能发掘人物思想的理性层面,同时还对构成整全人物性格的另外两个方面,即情感与意志,也同样被纳入到分析范畴里面,这就使得人物分析,避免了单线性质的阐释,还原了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圆桌会议的下半场,主要围绕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话题的设定,并非把知识分子视为研究对象,而是从作为方法的知识分子研究出发,探究这种方法论是否具有某种主体性,是否存在一些独特的价值等,以此来实现知识分子研究的新突破。
许纪霖教授根据其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经验指出,在方法论上,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注意以下四项要素,即代际更替、空间、阶级及文化品位。从代际差异出发,许纪霖教授讲解了存在于晚清、五四、大革命时代三个阶段各自出现的两代知识分子类型,并进一步对特定的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比如,戊戌变法为何会失败,许纪霖教授就认为这是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各自争夺话语权且彼此不合作所致。从空间视角出发,同样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因为作为实体的中国,因其面积广大,以前的研究往往侧重对于国家产生影响的精英型人物的探讨,而对于地方性知识分子,或者区域性知识分子的考察,则显得较为薄弱,这不仅体现在史学领域,文学领域亦是如此。伴随着研究重心的下移,眼光向下,关注南和北,东与西的地方知识分子,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需要重力发觉的地方。从阶级分析视角进入知识分子研究视野,并不是将阶级应用教条化。阶级分析本身是充满魅力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路易·波拿巴怎样上台,以及谁支持他、谁构成他的社会基础,乃至如何垮台等问题。陈寅恪在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的研究中,同样也运用了阶级分析法,即从家族、地域、血统等关系分析中古政治文化。也就是说,将阶级视角作为一套方法论,来做人物分析,同样会取得一定的解释成效。再如,关于许多知识分子为何会走向革命的问题,许纪霖教授就从阶级背景出发,发现他们的家庭出身,大多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因此,阶级分析本身,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且具有阐释力的方法论知识。从文化品位出发,它使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得以摆脱一味强调政治取向同一性的关联。文化品位,其实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惯习”(habitus)思想相类似。人与人之间的聚集,在某种程度上说,更多的是受知识的类型,文化的趣味,文化的品位等因素的影响。很多人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深厚交谊,而这恰与文化品位要素密不可分。从文化品位出发,它有利于打破固化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而深入到知识分子多元的思想世界与情感世界。
瞿骏教授针对空间在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意义,作了补充性说明。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叙事里面,一些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说法,其实是缺乏空间眼光的。比如,梁启超就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就讲到,近代中国的变革,遵循着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演变路径。梁启超的说法不能说错,但其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忽略了中国的空间。因为,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当这个地方有器物变化的时候,另一个地方可能没有一点变化;当这个地方文化变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另一个地方器物的变革可能才刚刚起步。再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就将近代中华民族的根本问题归结到“能不能近代化”,这其实也存在忽视空间的情况。针对革命问题,瞿骏教授继续指出,南方和北方的实际距离,使得有关革命政策的传达,都有可能因为空间的存在,变成纸面的上文字,变得无法得到具体贯彻与落实。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讲,承认人是做不到一切事情的;承认人的信息,是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得来。而对这些渠道的审视,其实就是借以地方视野来看待问题的表现。总而言之,将空间纳入到知识分子的研究里面,无疑有利于清晰化地把握人的有限性问题。
唐小兵教授对于空间在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价值,同样表示赞同。唐小兵教授提到一个事例,其在五四百年采访余英时先生时,余先生讲了一件有趣的故事,就是在1922年,北京大学招生考试有一道题是“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作为监考老师的胡适,发现考场上有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五四运动”。胡适后来发现,其他考场监考的老师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五四在有些地方的影响,着实是有限的。这也就证明,不能对五四在全国的影响一概而论,而是有必要进行区隔与厘清。除此之外,唐小兵教授重点讲述了中国的文史传统,对于作为方法的知识分子研究的意义所在。唐小兵教授以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例,作了宏观性的说明。以往对于宋代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把它高度的概念化;而余先生则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出发,来看待理学集团中的人物,梳理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外在语境的把握,将重新释放出一个对于宋代理学的阐释空间。另外,余先生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的转变。而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对后来的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影响。唐小兵教授指出,在五四和后五四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的溃败,在缺乏一个政治的网络来影响高层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也转入“觉民行道”,唤起民众。由此可见,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将中国的文史传统纳入到知识分子研究当中,并通过结合外缘性因素与内在理路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贴近到一个本然的面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