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段海洋史?

此外,由于哺乳动物的胚胎是在羊水中妊娠,而羊水又恰好是胎儿在母体中孕育时所需的生理盐水,据此,费伦齐认为,这是人类在生理发育过程中需要找到海洋替代物的表现。费伦齐表示,胚胎发育的这几个月会持续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人的睡眠和性行为都和胚胎发育的状况大有关系。同样地,费伦齐认为,弗洛伊德在 1920 年之后提出的“毁灭与死亡驱力”(the destruction-and-death drive)也可以理解为海洋在迫切地召唤我们,唤我们回归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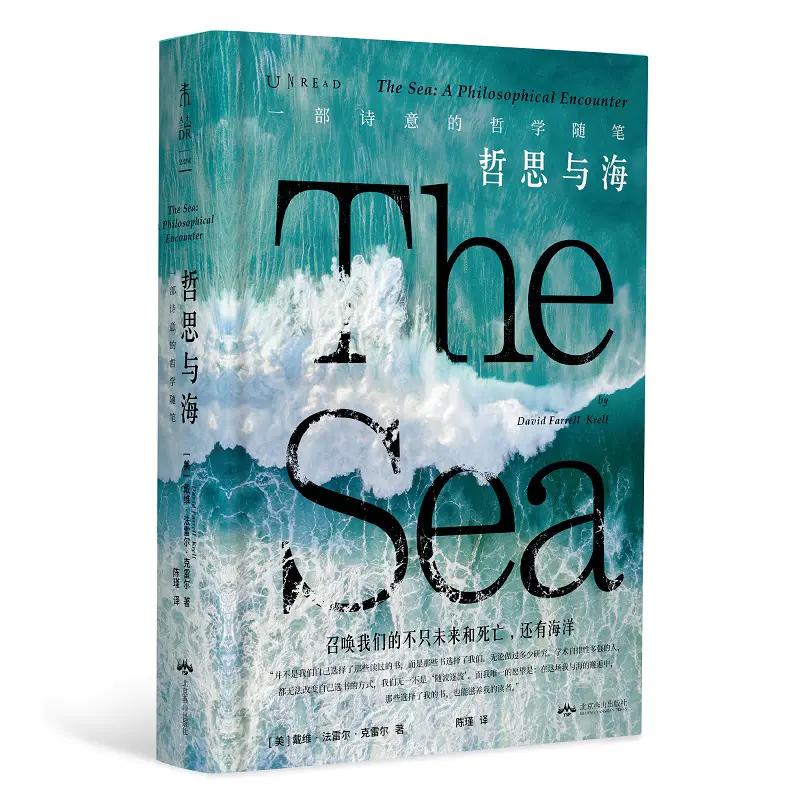
文 | 法雷尔·克雷尔
桑多尔·费伦齐在 1924 年的著作《对生殖力理论的尝试》(《塔拉萨》)中提出,系统发育实际上是后生变态(coenogenesis),即生物早期形态中没有的结构在胚胎阶段的发育,这些结构似乎是生物因外界环境变化产生的适应性反应。让费伦齐印象深刻的新结构是脊椎动物的羊膜囊,其主要功能是保护哺乳动物的幼崽免受干燥、震荡、饥饿、败血症和死亡的威胁。为什么哺乳动物需要这种特殊的保护呢?因为地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灾难史。具体来说,为什么需要羊膜囊及其外部的绒毛膜呢?原因在于,当海洋干涸时——这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灾难——鱼类需要一个可以游泳、产卵并生存的地方。

费伦齐在《对生殖力理论的尝试》一书的第六章“系统发育的并行”(The phylogenetic parallel)中讲述了生物产生性别分化的灾难性演变。该章节的论证并非一帆风顺,其方法论有些混乱,同时文中还出现了奇怪的概念。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第四章中坦言自己的观点只是“推测”,而此处费伦齐却承认自己是在“幻想”。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幻想是一种严肃的科幻虚构,它并不是只能拍出 B 级电影的可疑的科幻虚构。

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匈牙利神经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是弗洛伊德的挚友和门徒,精神分析学发展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简单概括一下费伦齐关于 “系统发育”“后生变态”以及其所谓“生物分析法”的三个章节。
费伦齐虽然对科学领域不算陌生,毕竟他也是一名医生,但由于他还称不上是专家,所以他首先对涉足该领域表示了歉意,之后他说出了自己的主要“想法”——他要探寻“一种个体出生灾难与性行为过程中重复的灾难在历史上的并行”。
文章一开始,费伦齐便告知了读者他与奥托·兰克之间多年的合作关系。兰克的著作《出生创伤》(Trauma der Geburt)与费伦齐的《对生殖力理论的尝试》出版于同一年,也就是 1924 年。

1909年拍摄于克拉克大学。前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斯坦利·霍尔,卡尔·荣格;后排:亚伯拉罕·布里尔,欧内斯特·琼斯,桑多尔·费伦齐。
同年,弗洛伊德也发表了《受虐狂的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该书是这位精神分析大师阐述毁灭与死亡驱力这一概念的重要著作之一,而他首次提出该概念是在其 1920 年的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
费伦齐首先指出,他涉足进化生物学的灵感来自象征主义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费伦齐对符号的解读采用了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诺瓦利斯)在18 世纪末发明的词汇:就像当初商博良(Champollion)试图搞清“原始象形文字铭文”一样,费伦齐作为精神分析学家也想要“解读文字”,而他的“解密方式”包含了目前“物种进化过程中最大的秘密”。
不仅诺瓦利斯和他在埃及赛斯(Saïs)的学徒认可这种阐释性的解密方式,弗洛伊德本人也支持该方式。同时弗洛伊德还敢于在多个场合就系统发育问题做出推测——这也是他惯常的行事方式。弗洛伊德曾多次使用“系统发育”(phylogenetisch)一词,但多数情况下他想表达的意思是早期人类的特殊经验。相比之下,费伦齐使用该词则是为了回顾生物进化史,甚至是追溯地球的无机历史——也就是黑格尔所称的恒星历史。

(一)性交行为;(二)男性生殖器;(三)母体内胎儿的状态。
费伦齐坦言自己突然有了一个“离奇的想法”,那就是鱼类不仅象征着男性进入女性的生殖器或婴儿在母体发育,同时还可能是“人类起源于水生脊椎动物的系统发育片段”。如此看来,这不仅只是一个奇想,同时还是一种“见解”,或者说一个“知识”(Erkenntnis)要素,尽管它们具有隐蔽性。就鱼类在系统发育中的转变,费伦齐举出的证据是一种属于鳃口科的原始鱼——文昌鱼。该鱼通常被认为是所有哺乳类脊椎动物的祖先,同时它也是脊椎动物生物学中的模式生物。有了这个想法后,费伦齐有了进一步的推测,尽管该推测很大胆,但似乎也无可厚非——以下斜体段落将费伦齐的兴奋和好奇表露无遗:
当时我们想过,如果高等哺乳动物在胚胎中的整个发育过程,只是它们对鱼类时代存在形式的重复,如果动物生产只是个体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重演,会怎么样?但可以确定的是,多数动物以及人类祖先在海洋干枯后不得不适应陆地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得不放弃用鳃呼吸,发育出能够吸入空气的器官。
原始鱼类“放弃”了鳃和“发育”了肺,这样的人格化当然会引得人类发笑,因为人格化需要让寻找肺的鱼飞跃成为皮兰德娄作品中那些寻找自我的角色。费伦齐坦言他不仅信奉拉马克学说,而且还崇尚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重演说。这两点会让费伦齐受到表观遗传学家(epigeneticists)之外的当代研究生物学学者的鄙夷。但是,费伦齐与海克尔不同, 他支持谢林派的自然主义者洛伦兹·奥肯(Lorenz Oken)和后浪漫主义的倡导者威廉·伯尔舍,他宣称自己的主要兴趣是研究胚胎的“保护措施”,即羊膜囊及其液体的后生变态。

诚然,过去存在于这个(男性的)部件,一个人鱼的部件中。此处人类回归到了原始的鱼类状态,尽管进化之前的那段历史早已消散在过去的迷雾中。永恒的人鱼(Der ewige Nix)完全向前演变成了这个部件。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还发现了一条通往人性至高点的途径……一条启蒙之路, 但同时这条路上也存有疑惑、错误和诅咒。当无花果叶坠落的那天,一条光明之路便会开启…… 终有一天,伟大的变革必将来临,我们会在涉及性的问题时不再盲目。零星的自我保护会自行消失,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个真相,一个过去就存在的公开秘密:人鱼其实不是人和鱼的结合体,而是半神半人。
这里先言归正传,让我们继续讲费伦齐的观点。尽管费伦齐十分认同伯尔舍对科学启蒙所做的积极努力,但他承认自己所说的系统发育的并行同时涉及子宫和羊膜囊,这就好比地球母亲和海洋一样都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救助者。如果人类像体内寄生虫一样开始生命,那他们很快会变成体表寄生虫,一开始靠母乳生存,长大后在餐桌前进食。然而,尽管拥有得墨忒耳般的资质,费伦齐还是将这个比地球更古老的原始符号看作海洋生命和孕育的象征。在《安提戈涅》(Antigone)第二段著名的合唱曲中,索福克勒斯试图说明,人类为何如此不可思议。首先他提到了在水上定期往返的船只,它们“跨越夜晚/海洋”。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笔下的鲁滨孙曾对地球示爱——毕竟他在海难溺水后是陆地挽救了他的生命—但他的本性仍恐惧干燥的气候,渴望潮湿的环境。宙斯将分化后两性的生殖器官移到了前面,为的是让生物能够相互交配,而不是像蝉一样通过尘土飞扬的陆地繁殖后代,这对那些依靠阳光、陆地或月光进行交配的雌雄个体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演变而来的。

在奥托·兰克关于出生创伤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对于海洋的矛盾情绪:海洋既能孕育生命又能溺死生命。羊水可以让胎儿免于脱水,而生产让婴儿免于溺水或窒息而亡。人在出生时处于睡眠状态,也不会记得生产的过程,但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也不能开启生命。在面对这种矛盾情绪时,他在文章中写下了既冲突但又相通的两个词,即快乐和焦虑。快乐是一种过程和“象征行为”,这涉及:
(一)在母体羊水中漂浮时,个体由其存在而产生的快乐(Lust);
(二)对于出生的焦虑;
(三)新生儿经受了生产风险后的快乐。
这种矛盾心理会扭转局面,让个体向焦虑的方向发展:既然个体(费伦齐的作品中暂时还没有区别他和她)通过生殖器进入女性阴道或将精子射入女性体内,仿佛进入了女性身体的洞穴(die Leibeshöhle des Weibes)这种行为来认同自己,那么个体还会面对象征性的死亡危险,就如同其先祖“在海洋干涸的地质灾难中”(die grosse Eintrocknungskatastrophe)面临危险一样(同上)。

费伦齐大胆支持拉马克和海克尔的学说,而非达尔文的学说。达尔文宣称,物种的生存是由偶然变异和自然选择的机制决定的,而拉马克认为进化靠的是越发复杂的生物为适应严峻的外界环境所做的努力(“生命的力量”的表现),这种努力能够让有用的后天获得性特征遗传给下一代。和弗洛伊德一样,费伦齐也倾向于认为,驱力不仅在个体当中,还在整个类群中发挥作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费伦齐曾试图完善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 — 关于性的“精致的二元论”以及毁灭与死亡驱力——为此他将前瞻性、推进力、建设性、统一性的驱力,与回归和最终退回大海的致命引力做了对比。如果试图将 Zug 翻译成英语,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引力像是一种拉动(draw)、征召(draft)或者“拖拽”(tug),毕竟这个德语单词有多层含义;但或许最对等的英文单词应该是 undertow(逆流),尤其是考虑到生物有回归海洋的倾向,那是一种能将我们带回海洋的 Zug,或者至少它会让我们产生对大海的梦想和幻觉。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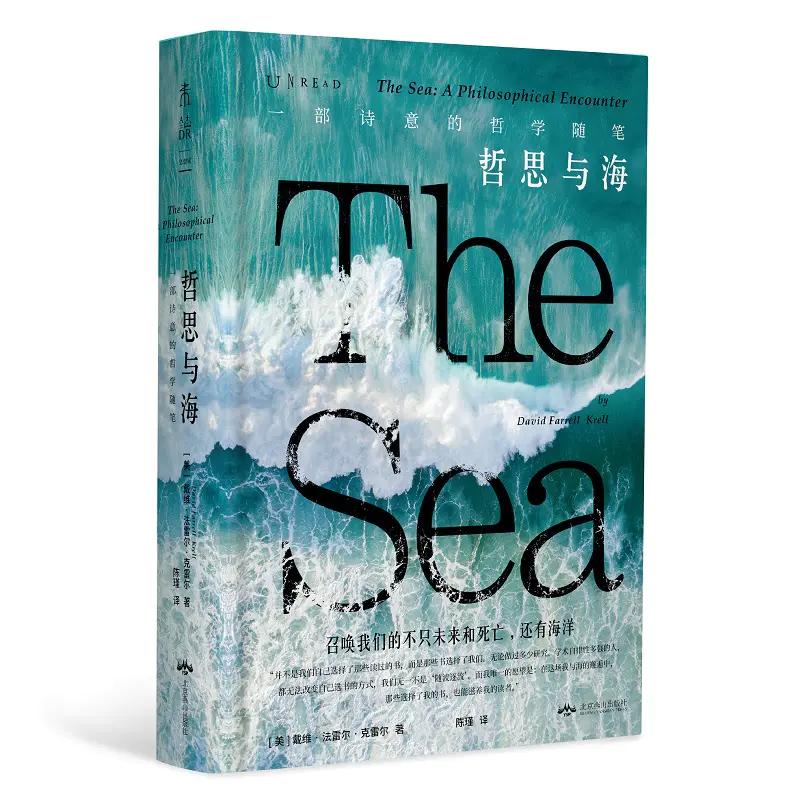
人性、神性、悲剧性、无边的灾难之海与有限的生命,伴随这些主题,读者可以跟随作者在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荷尔德林、梅尔维尔、伍尔夫、惠特曼、尼采、海德格尔、谢林、费伦齐、弗洛伊德的论述中探寻人类与海洋的复杂关系,揭示我们的冲动、焦虑、死亡和爱。
原标题:《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段海洋史?》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