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孙青:悼念司佳
2020年10月11日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司佳病逝。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系列追忆文章,以念斯人。
今秋的天空似乎特别明净,阳光灿烂。10月15日那日却是个阴天,我们要去送别她。九点半的时候,姜鹏发微信给我,说写好了我们近代史教研室为她准备的挽联。一共两副,一副是他自己用颜体写的,另一副是他请了一位书家用隶书所写,让我们选择到时候挂哪一副。我告诉他,等结束与学生的约谈就上去找他。手机嘟嘟响,港城大的张为群老师留言,说今早又仔细推敲修改了一下平仄,即使姜鹏来不及改写了,也可以在将来出纪念册的时候更动。大家都想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努力一些,再努力一些。
学鉴东西,遍历五洲,颜色焉随宝镜灭;研穷新旧,宏观千古,精神常伴文字存
我们想用这些近乎细节偏执的坚持去挽留下一些什么——她的美貌,她的追求,她的热爱,她的收获……一位老师曾在她的讣告圈文下留了王国维《蝶恋花》的词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我们终于发现,相比于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坚强与执着,这些都微不足道。

司佳(1978-2020)
初识司佳,是通过耳闻。18年前负笈海外,交换留学。海外不少师长听说我是从复旦历史系来的,便总会问我是否知道有一位差不多年纪的学妹,极为优异。于是我便对她的美声誉时有耳闻。我做博士论文用到马礼逊字典,脉络生疏,便去查考相关研究史。还记得前数据库时代,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复印她写的《早期英汉字典所见之语言接触现象》。细细读来,对那史料梳理扎实细致,文风老练周到印象深刻。掩卷时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司佳吧。
再见司佳,是做了同事。大学全职教师排课时间不同,平时交集并不多。常常在全系大会,或教研室讨论时,见她笑容甜美,语音娇柔。同教研室的女老师不算多,我们的研究方向又接近,便开始熟悉起来。科研与教学工作的压力是无形迹的,外人不知,总以为我们不用早九晚五,没有日日排课,似乎很轻松。每每在系休息室的咖啡机前遇见,有时我们便会把这些误解当笑话讲,说其实是鸡叫睡觉,鬼叫写字,全年无休。我们都在各自尝试自己的减压方法,有时也会交流。她之前是做瑜伽,近几年生育后,似乎还打过一阵拳击。我则笑称,运动不适合我,我信奉的是龟息大法。她总是哈哈哈笑,然后说自己吃得很多。夸我身体好,吃得少,又能一个一个通宵熬夜瞎折腾。
生育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坎。从18岁开始习惯的恶劣作息无法再继续。白天必须早起,不再有整段的时间由得我们泡图书馆,查资料,任性地一口气写完稿子迎头痛击各种deadline。我们必须适应如何利用被割裂成丝丝缕缕的时间,用于思考与写作。这对于需要凝神持续思考才能有点滴收获的我们而言,不太容易。司佳在2015-16年间集中完成她的中文书稿。女儿还小,她就与先生两个人换班。白天先生来工作,她带孩子。下午三四点,换她来。有时她到了学校,会先来我屋里聊几句有的没的。有时笑着说,今天想赖皮写晚一些回家,多蹭先生一些时间。我给她看我电脑里收集的资料,未打磨的文稿,给自己挖的那些选题坑。她给我看她那些蟹行的英文手稿,说多看看就不怕看了。还记得她申请到国家课题时高兴的样子,跟我反复念叨自己的选题有多值得去做,要怎样怎样再怎样。微信是个奇怪的东西,人走了,对话却还生动地留着。我翻看我们的对话框,去年12月3日,有一条是她问我本室小戴老师的电话,说是要咨询他的结项经验。听说她的国家课题结项评分优秀,算来,结项时是她生命最后的阶段了。写到这里,我的心里有些痛。不,很痛。
我们的轨迹有不少重合的地方。2016年一起在港城大工作坊,2018年一起在关西大学组panel参加文化交涉学年会。我还记得坚尼地城的海风,她说她给我拍的照片比我自己举相机拍得要美,人看起来比较瘦。她的胃不好,包里总是随身带着一小包一小包的饼干或巧克力。我们都怕低血糖,似乎也都曾经因为低血糖在课堂上晕倒过。我还记得京都平等院外的宇治川,我们在那里坐着吃抹茶冰激凌。我说平等堂的飞天观音好美,她说她想吃河边那家店的寿司。
2019年6月她病了,生日是在医院过的。几个月间开了两刀。我和晓莉去看她,她坐在病床上,神完气足,说刚刚拔掉全身的管子。问她痛不痛,她说,插着管子的时候很痛,现在不痛了。2019年8月,我上暑期课,在校园对面的六教。有一天下课,她发微信给我,说她来学校了,问我要不要见面聊聊天。我问她饿不饿,给她从The Press买个面包和果汁去。我问她口服化疗药感觉怎么样。她边吃面包边说,前两天肠胃道反应比较厉害,后面就好了。不难过的时候,她就努力吃,让自己多一些抵抗力。我记得她的书柜里放着她的英语专著和新译的汤因比《中国纪行》。这书的反响很好,她笑眼弯弯地告诉我,连她的主治医生都喜欢读,竟然会去买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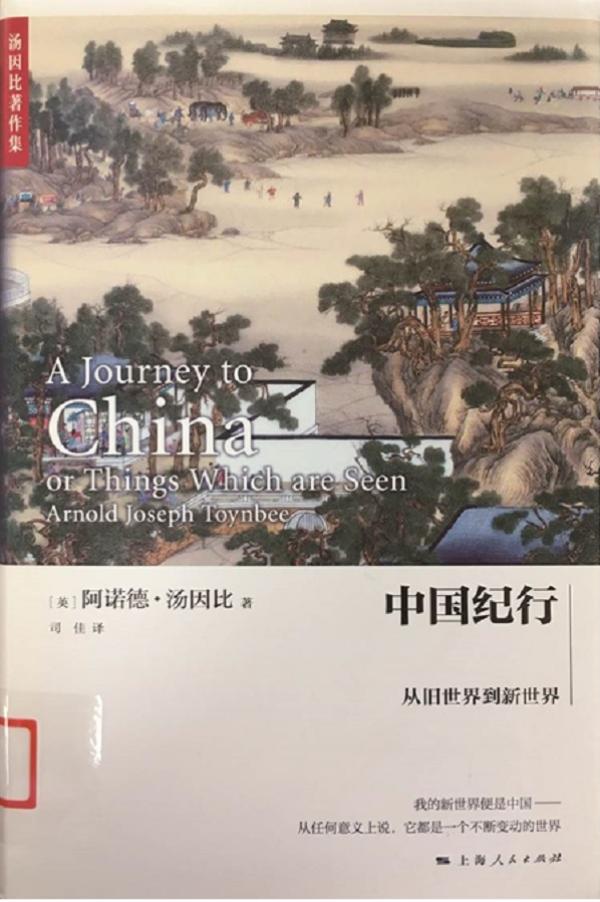
《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2019年11月,我下课回家,追公交车摔了一跤骨折,做足踝加固手术。她坚持要来医院看我,说顺便走路锻炼。她塞给我一块黑巧克力,说术后没体力,她知道的。然后眼神突然暗淡下来,不知道想起什么,说也许自己某一天就这样走了。
2020年天下大疫,我们都龟缩在家观察世界,很少通信。偶然联系,是她约我看她研究生的预答辩稿。6月份她给我打电话,说今年想好好过个生日,让孩子们在一起玩一下。我让女儿穿上大红色的衬衫,去给她唱生日歌。南京大学陈蕴茜教授因病去世,小半个近代史学界都在哀悼。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很难受。我问,你和陈老师有交往?她说没有,只是突然想到自己也许……我说,你不要瞎想。当时想的是,她不是稳定了么,看气色这样好。谁又能想到呢?7月5日她留言告诉我合生汇一楼有一个很好玩的打电玩的地方,她一家三口玩了一整天,让我也带女儿去。7月31日问她最近可好,她留言说“还行,医学我们又不懂,跟着感觉走”缀一个微笑的表情符。9月30日她发了一条圈文,是小女儿在试穿粉色汉服。10月4日,我知道她病势急转直下,行将不起,却又不欲亲朋看到她的憔悴。连日噩梦不断,发了一条朋友圈减压,第二天居然看到她的点赞……
6月22日,我最后一次跟她讨论了学问。我读了她《传教士缘何研习圣谕广训》的文章,问她方言圣谕广训集解的脉络。她说,我跟你电话说。然后发了自己拍的几个方言版本到我邮箱,留言说“让你晚上有点事情做做”。我回复她将来成文,第一个注就鸣谢“司佳教授”。她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符给我,如今想来,不胜悲……
寒潮初起,风意如水。秋日又晴朗起来,我跟几位系里仍在为她深切悲伤的女同事说,不想再沉溺在这样的情绪中了,我们必须送走她。可是,一时之间,这真的可以做到么?
是以为记,临稿哀戚,难以重读。
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深夜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