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卡尔维诺 | 文学:搭在虚实两岸的危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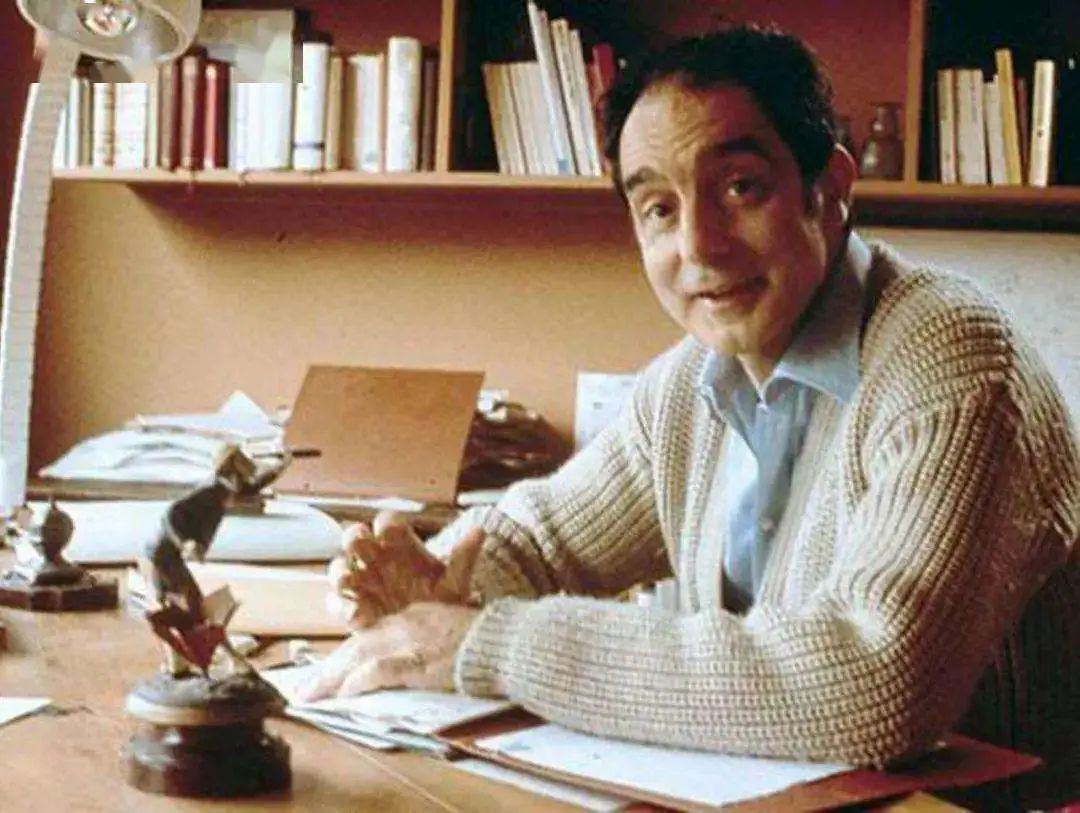
在节选的部分中,卡尔维诺从自己的作品《看不见的城市》出发,讲述他对文学的理解。
本文选自卡尔维诺著作《新千年文学备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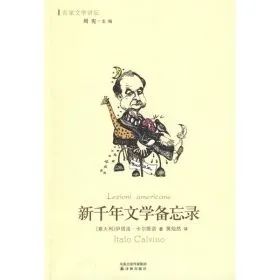
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每一个概念和价值都变成包含双重性——就连精确也包含双重性。在其中一段描写中,忽必烈汗成为一种知识倾向的化身,它倾向于理性化、几何学和代数学,把有关他的帝国的知识简化为棋盘上棋子的组合。忽必烈汗还在黑白格上对城堡、主教、骑士、国王、王后和兵卒作出各种排列,用来代表马可·波罗巨细靡遗地向他讲述的各个城市。经过这番部署,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他要征服的对象,无非是一个棋盘,上面摆着一些棋子:虚无的象征。可就在这个时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马可·波罗要求忽必烈汗更仔细地看清楚他眼中的虚无:
忽必烈汗努力集中精神下棋:可现在他却忘记了下棋的理由。任何游戏的结果是输赢:但输什么赢什么呢?到底赌什么呢?将一死,王被胜利者的手推掉,王脚下便什么也没有了:一个黑格,或一个白格。大汗剥掉他的征服的皮肉,把它简化为内核之后,他得出的运算结果:最后的征服,而皇帝多种多样的珍宝只是这征服的虚幻外壳;这征服被简化为一块木板上的方格。
接着,马可·波罗说:“陛下,您的棋盘是由两种木嵌成的:乌木和槭木。您的慧眼所凝视的方格,是从一根树干的一个年轮切下来的,那一年是干旱年:你看见它的纹理了吗?这里隐约有一个节疤,它是一个芽,努力要在早到的春天抽出来,但夜里的寒霜把它抑制了。”

这时大汗才发现这外国人懂得讲何等流利的本地话,但使大汗讶异的不是他语言流利。
“这里有一个较厚的黑点:他许是一条幼虫的巢;不是木蠹,因为木蠹一生出来就得蛀木,而是一只毛虫,它啃树叶,这也是这棵树被选来砍掉的原因……这个边缘被雕木工用凿子刻过,使它楔入下一个较凸出的方格……”
一块平滑的小木板竟包含如此丰富的知识,着实把大汗给镇住了;这时马可·波罗已经在谈论乌木森林、顺流而下的装满圆木的木筏、船埠、窗口的女人……
从我写这段文字那一刻起,我便明白我对精确的探索,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把次要事件简化为抽象图案,再根据这个抽象图案进行运算,证明定理;另一方面,是文字所作的努力,旨在尽可能精确地表现事物可触可摸的方面。
事实是,我的写作总要面对两条分叉的道路,它们呼应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一条道路伸入由没有实体的理性构成的精神空间,你可在其中追踪各种汇合的线索、各种投射、各种抽象形式、力矢量。另一条道路穿过一个布满物体的空间,试图通过在纸上填满字句来创造与那个空间对等的空间,其中涉及最小心、谨慎的努力,要使写下的呼应没写下的,呼应一切可说和不可说的。这是两条通向那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精确的道路,前者无法完全达到精确是因为“自然的”语言永远倾向于说得比形式化的语言更多——自然的语言总是包含一定数量的噪音,影响信息的实质——后者无法完全达到精确则是因为在表现我们周围的世界之密度和延续性时,语言便显得有缺陷和破碎,相对于经验的总和而言永远说得不够。

在这类追求中,我心中总是牢记诗人们的实践。我想到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他如此精细地描写仙客来的叶子,使我们可以清晰看见花朵绽放在他为我们描绘的叶子上,从而把仙客来的雅致赋予诗。我想起玛丽安·穆尔,她在描写穿山甲、鹦鹉螺和她的动物寓言中的其他动物时,把来自动物学著作的资料与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意义糅合起来,使她的每一首诗变成一则道德寓言。我还想到埃乌杰尼奥·蒙塔莱,他在《鳗鱼》一诗中可以说综合了两者的成就。这首诗只以一个非常长的句子构成,仿似一条鳗鱼。它描写鳗鱼的一生,并把鳗鱼变成道德象征。
但我尤其想到弗兰西斯·蓬热,因为他以那些小散文诗在当代文学中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体裁:类似学童的“练习簿”,他的练习办法,是安排词语,把词语当作是世界的外貌的延伸,然后经历一系列反复的试验、草稿、“近似本”。蓬热在我心目中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他的《事物的目的》和他其他风格相近的诗集里那些谈论一只虾、一块卵石或一块肥皂的短文本,为我们竖立一场搏斗的最佳榜样,这场搏斗就是迫使语言成为事物的语言,从事物出发,再回到我们这里时都已改变了,都带着我们赋予事物的所有人性。蓬热申明他的意图是要通过他那些简短的文本及其复杂的变体,来创造一部新的《物性论》。我相信,他也许就是我们时代的卢克莱修,通过难以捉摸的、粉末似的文字的微尘,来重建世界的物理本质。

在我看来,蓬热达到与马拉美同一水平的成就,尽管他是从分叉和互补的方向达到的。在马拉美那里,文字通过达到最高层次的抽象和通过揭示虚无是世界的终极实质,而获得最极致的精确。在蓬热那里,世界以最谦逊、不显眼和不对称的事物的面目出现,而文字则是用来唤醒我们的意识,意识到这些不规则的、无比精细地复杂的形式的无限多样性。
有些人认为文字是获取世界的实质的方式,那终极、独特和绝对的实质。文字不是表现这实质,而是等同于这实质(因此仅仅把文字视为达到某个目的手段是错的):文字只知道它自身,其他关于世界的认识都是不可能的。尚有另一些人,他们把使用文字视作孜孜不倦地探索事物,不是要接近事物的实质,而是要接近事物的无限多样性,触摸事物那永不会枯竭的多种多样的表面。一如霍夫曼斯塔尔所言:“深度隐藏起来。在那里?在表面。”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至于隐藏着的事物……我们不感兴趣。”
我不会这么激烈。我想,我们总是在寻找某些隐藏的事物,或仅仅是潜在或假想的事物,一旦它们浮出表面,我们就追踪它们。我想,我们的基本精神步骤,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遗传给我们的,可追溯至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他们是狩猎者和采集者。文字把可见的痕迹与那不可见的事物,那不在场的事物,那被渴望或被害怕的事物联系起来,像一座用于紧急事故的摇摇欲坠的搭桥,架在深渊上。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恰如其份地使用语言,可使我们小心翼翼、集中精神、谨小慎微地接近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敬重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所无言传达的东西。
《花城》2020年第5期
目录
中篇小说
内吸 / 胡学文
雪山之恋 / 丁颜
呼啸而过的悬疑 / 夏榆
旧画 / 黄小初
短篇小说
羊群过境 / 弋舟
唐云梦的救赎 / 凡一平
花城关注
本期关键词:世界时区
栏目主持人:何平
斯普利特:寻找戴克里先的幽灵 / 柏琳
路易逊的伦敦 Lewisham, London / 王梆
雅各与天使摔跤 / 吴雅凌
速写南非 / 陈济舟
本期点评:地球村幻觉和世界行走者 / 何平
诗歌
清河县(Ⅲ) / 朱朱
散文随笔
孙桥村遗梦 / 吴周文
花城译介
栏目主持人:高兴
软的故事(外三篇)/[法国] 弗朗兹·巴赫特尔特 著 赵丹霞 译
思无止境
从新历史主义到重建历史总体性
——兼谈中国当代作家的历史意识 / 陈培浩
纪录片
批判并不是要坠入黑暗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花城》访谈实录 / 贾平凹 温晨
域外视角
伤口即世界:三个美国印第安作家 / 凌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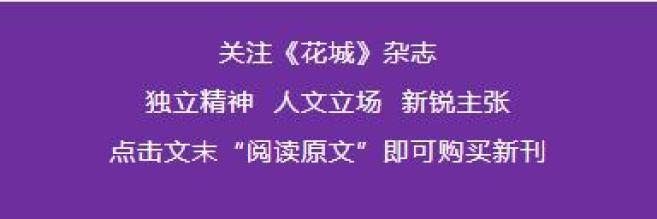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592311
微信公号:huacheng1979(可在微店中购刊)
刊号:CN44-1159/I
邮发代号:46-92
海外代号:BN661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20元,全年定价120元。
原标题:《卡尔维诺 | 文学:搭在虚实两岸的危桥》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