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和我的家乡》,有一种家乡叫远方
原创 过蝈8433 秦朔朋友圈

· 过蝈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我和我的家乡》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合一,有人说这个长假像在过年,看《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最应景不过。在电影两个半小时里,有哭有笑,感觉是近年来难得的好电影。
这些年宏大的主题有:医保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旅游、沙漠治理、乡村振兴等,这部电影则通过五则故事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战略政策的价值。和以前喜欢讲述脸谱化的“大人物”主旋律相比,《我和我的家乡》是在讲述“大时代里的小人物”,讴歌了小人物对时代做出的贡献,就连他们身上的小心思、小缺点都显得真诚、可爱。
不过笔者觉得这部电影的名字有点问题,除了第一则《北京好人》讲述了衡水农村人在北京看病的小故事,涉及了宗族乡情,并最终阐明了农村医改的主题,比较紧扣“家乡”这个主题,其余四则故事,更多传递了时代的共鸣,而不是家乡的共情。
导演的视角,多是放在农村的奋斗者身上。这些奋斗者有的是本地人,也有外来者。但现实里,一直生活在家乡的人对家乡情感未必这么深沉。对家乡更有感触的,恰恰是在外奋斗、逢年过节回到家乡的人。
在城乡之间,在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在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在追求理想或辛苦谋生的过程中,感受着撕裂、孤独、幻灭的人们才会对家乡更有深情。
在“家乡共情”这一点上,另外四则故事颇有缺失,笔者认为这部电影的名字更应该叫——“我和我奋斗的地方”。
在这里笔者不想继续讨论电影本身,因为有一些问题萦绕在脑海:“家乡”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出生地都叫做家乡?笔者倒是觉得,家乡恰恰是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地方,尤其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成长的80后而言,家乡,成为了最熟悉的“远方”。

家乡,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
余光中曾经感叹:当你不在中国,你就是全部的中国。地理上的距离才会触发我们对家乡的情结。而我们中国人,又恰恰是“思乡”情结最为浓郁的。
小时候我们最先背的唐诗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年少得意时,诗里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际遇失落时,诗里说“几年凉月拘华省,一宿秋风忆故乡”;待退休年老,诗里又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外混得好,要“衣锦还乡”,混得不好,则是“近乡情更怯”。
总之,我们国人对“家乡”有一千种讲法,一万种情感。少年时我们读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所占篇幅最多大概就属“思乡”题材。那些细腻惆怅的情感,伴随流水落花、西风瘦马、夜泊孤舟等诗意的形象徐徐展开。
对远离家乡的人而言,故乡就是心河上的一轮弯月,稍有微风,就会吹散。有趣的是,我们古人提到故乡,多是境遇不顺,或者官场失意,有点“人生不幸诗歌兴”的意味,对他们来说,故乡是一份对心灵的慰藉。
家乡是心灵的慰藉。只有当身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对故乡的依恋和责任才会油然而生,并感受到故乡对自我精神的塑造和占领。
所以,家乡,首先就是一份文化认同。
就像沈从文描述诗意的边陲小城,自比是“乡下人”;莫言在高密高粱地里塑造着豪放野性的乡土文化;鲁迅虽然对故乡犀利抨击,但对绍兴鲁镇还是有深沉的追忆。对家乡的文化认同都不自觉地在作家笔下流淌,构成了极具诗意的“文学地图”。
但我们普通人对家乡的文化认同,又是认同着什么呢?
笔者认为有三样非常重要:乡音、乡味和乡情。乡音、乡味是外在的形式;乡情则是内在的风俗人情,礼仪传统。
就以笔者的家乡苏州为例,来讲讲这些年的转变,也是应景写一下“我和我的家乡”这一主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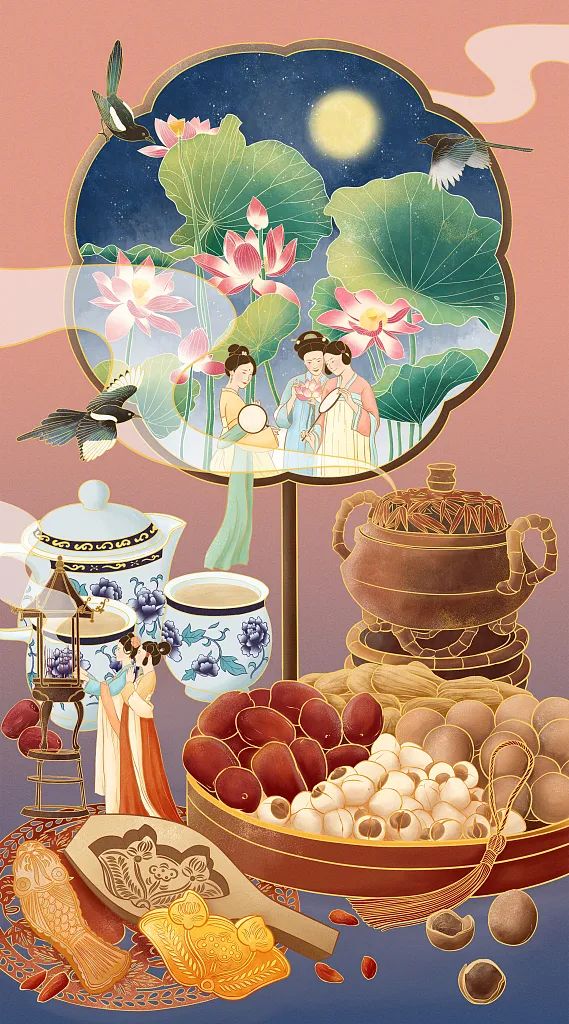
先说说乡音。
贺知章写道:“乡音不改鬓毛衰”。这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太难了。很多人已经一出生就只会说普通话——各地的方言正在消失,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在苏州,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苏州话,是一门非常优雅的方言。老话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作为一门古老的语言,苏州话里有很多古汉语的痕迹。比如,“下雨下雪”念作“落雨落雪” ;“老婆”念作“家妇”;“衣服”念作“衣裳”,等等。还有很多叠词、语气词的多重用法,总之,苏州方言既有苏绣一般的生动描绘,更有园林一样的通幽之径。
苏州是仅次于深圳的第二大移民城市,人口结构中一半以上都是新市民。在普通话大力推行的当下,苏州话正逐渐消失。有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后苏州本地出生的孩子,能够熟练掌握苏州话的不到10%,甚至有40%的孩子竟然都听不懂苏州话。
苏州话是吴方言的代表,吴方言的整体处境都十分堪忧。吴方言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目前吴方言分布于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福建等地,使用人口约8000万。在国际语言排名中,吴方言在中国排第二位,在全球排第十位。
早在2011年,就有专家称“吴方言或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民众对普通话的依赖,吴方言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
作为苏州人,对吴方言的式微感到心痛。语言不应该放进博物馆或者史册里,而要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同样推行普通话的广东,粤语却依旧是强势方言,和普通话并驾齐驱。很多人都很乐意学粤语。为什么吴方言就要没落呢?早在明清之时,全国的文人雅士都以学吴方言,特别是苏州话为风尚呢。
如何保护我们的方言,既要在普通话之中有生存空间,又不造成沟通阻碍,最好能让更多外来移民愿意学、乐意说。方言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守护。

其次,我们认同的是乡味。
味,味是味道。“味道”二字在我们的文化里饱含多意,既有舌尖之味,也有嗅觉之味,还可能是抽象的气质“味道”。
苏州味道,变化最大的当属舌尖之味——美食越发趋同,逐渐失去了特色。一方面,这和“苏帮菜”的“甜度”密切相关,糖在古代是奢侈品,苏帮菜的“甜”在古代带一点精英色彩。但现代人对“糖”敬而远之,苏帮菜的甜味确实有违健康的饮食方式。
另一方面,苏帮菜追求时令,古有“不时不食”的说法,因此价格不菲。同时讲究手工刀工,耗时费功夫,在追求快节奏的饮食下,已格格不入、逐渐衰落。
比如,《舌尖上的中国3》中有这样一道菜,它是把萝卜切成丝,将萝卜轻煮熟,然后加上葱花油,这道菜就熟了。这是传统的苏邦菜之一,它看似简单却非常复杂。做成这样一道菜,如果按传统做法大约需要5个小时。
我们现在吃的苏帮菜,多半是冷冻的半成品。试想一条松鼠桂鱼,如果当场活鱼制作,怎么也得等上半日吧,光是刀工就得花多少功夫?在追求效率、性价比的当下,苏帮菜的式微在所难免。
客观的说,苏帮菜的衰落固然惋惜,但苏帮菜里也有一些奢靡风气,追求奢侈浪费,并不可取。比如苏帮菜十分注重“手工”,一碗199元的三虾面,饱含了虾脑、虾籽和虾仁,悉数手工剥落,和面条一起烧制而成,笔者也没吃出石破天惊的美味来。还有一种俗称鸡头米的芡实,也是一种夏季时令美食。市场上的鸡头米,手工剥和机器剥的价格要相差3~4倍。尽管如此,苏州人还是喜欢买手工剥的,并能讲出手工的各种好处。对很多人来说,追求手工剥的鸡头米已经不是味道的问题,是对手工的执念与保护,也是一种内心小小优越感的体现。

有了地理,有了人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地方性格和结成的情谊就是乡情。
乡情很难描述,更多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朴素真诚的情感,就像《北京好人》里张北京和表舅之间的情谊。
近年来大家感到乡情也不浓郁了。其实乡情不是孤立的,乡音的消失、乡味的改变、让家乡的“性格”越发趋同。
各地的方言乡音、美食土味、传统手工正成为了强势文明中的脆弱生态,要么濒临稀缺关进博物馆成为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要么消失得无声无息、无人关心。
笔者曾在苏州地方台新闻里,看到老年花匠急于寻找传人的新闻。该花匠在园林花圃工作,有一身种植月季的经验和手艺。但当下却少有年轻人肯学了。传统没有传承,以往缔结在人们身边的仪式也日渐消散。人们对关系的维系越来越表面和功利,乡情淡薄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的家乡,乡音、乡味、乡情——传统上的文化认同都日渐瓦解,它们都在被一种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大城市”文明所侵袭、同化。
这种过度的大城市文明,正在让多样性消失。我们消失了语言的多样性、美食的多样性,然后是民族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最终消失的将会是人性的多样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理解越来越少,隔阂越来越深。
尤其像苏州,这种从小城市转变为大城市的“家乡”,从“熟人社会”转变到“生人社会”,前者依赖的是血缘,后者依托的是契约。契约社会里,很多本来“熟人”间的亲密、默契正逐渐瓦解。人们的边界越来越分明,行为越来越文明,但沟通和理解却越来越少。
就像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早安》,里面展现着日本人的都市生活:大家站在火车的月台上,互相鞠躬道早安,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些敬语和礼数,但永远也不会交换内心的心事。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姓名和身份。
我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进步成果,又何尝不是在忍受工业流水线般枯燥单调的日常生活?忍受不被理解、无处诉说的抑郁之苦?相比仕途失意的古代文人,我们又何尝不也要用故乡来慰藉呢?
人们正在经历丰盛的物质乐园,却开始了精神的“失乐园”。
蒋勋曾这样说:整个社会却愈来愈孤独了。每个人都急着讲话,每个人都没把话讲完。快速而进步的通讯科技,仍然无法照顾到我们内心里那个巨大而荒凉的孤独感。
但“孤独”这种话,蒋勋说是可以的,但普通人却不敢这么讲,因为怕被评论成矫情。
南拳妈妈的歌里唱到,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多少人就这样,一直在路上。
生活在越来越大的城市里,就像漂浮在无尽的大海上,我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又患得患失。家乡不再是我们的土壤,而成为怀念、慰藉的彼岸和远方。
「 图片 | 视觉中国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开白名单:duanyu_H
原标题:《《我和我的家乡》,有一种家乡叫远方》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