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青年学者谈︱吕博:中古的服饰与政治
中古史领域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从前些年的80后的学者,到近两年涌现出的85后学者,不仅在学界内颇受关注,一些作品在学术圈外也有不俗的表现。今年初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头饰背后的政治史》即是一例,此书一度登上当当网专业史新书排行榜,作者吕博,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这本书由其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一篇学术论文的内容扩展而来。学术论著走向市场,受到公众的喜欢,于一位专业史学者而言未尝不是一件令人欣喜之事。近期,澎湃新闻就邀请吕博谈谈《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澎湃新闻:你的研究特别关注“幞头”从北周至五代的样式变化,由此观察这一时期政治之演进。请先介绍一下作为日常头饰的“幞头”,它在历史上,特别是武后推行这个形制改变之前的情形如何?
吕博:幞头的最早形态应该是鲜卑风帽。武家诸王样之前,流行一种叫“平头小样”的形制。这点在史书里有明确记录。孙机先生在《中国古舆服论丛》中《从幞头到头巾》一文中也有详细的梳理。我是注意到《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幞头这一头饰变化的几个时间节点,刚好都在重要的政治事件之后。而且在我的认识里,两《唐书》著录的每次服饰变革常常都是政治事件。我认为只有将每次唐代服饰变革嵌入到事件编年脉络里,才能准确发掘服饰变革的历史意义。武家诸王样之前,几种著名的头饰的记录也都和著名政治人物相关。比如北周文帝的突骑帽、隋文帝的乌纱帽、宇文述的许公帊势、太子李建成曾佩戴“花搭耳帽子”等。他们究竟在视觉层面呈现的形态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和具体政治人物的形象搭配的?由于时空变幻千年,今天的历史学工作者恐怕很难重现。但是我们要有一种意识就是,今天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是依靠文字记录去复原历史,但其实文字之外有更多样的历史细节、历史场景需要我们去努力捕捉和尽可能地想办法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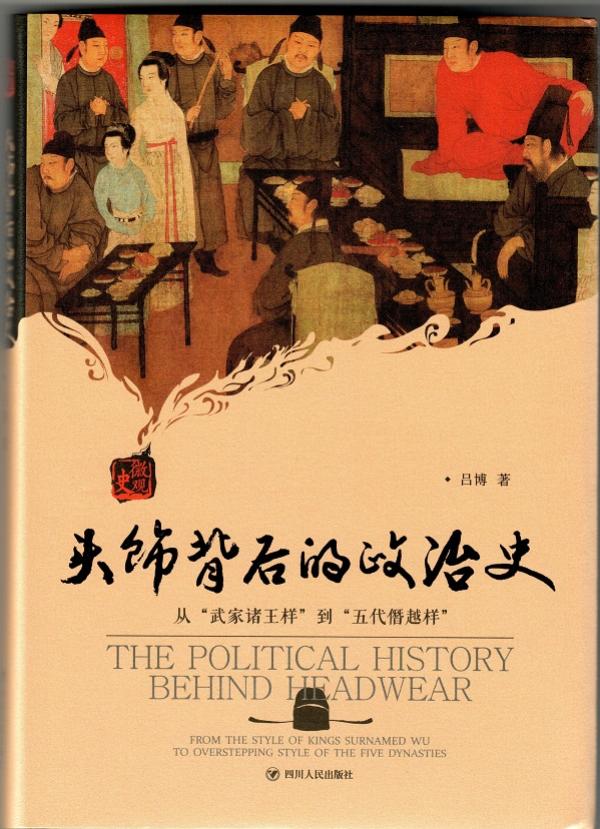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
澎湃新闻:你在这本书中讲从“武家诸王样”到“五代僭越样”,这一头饰风尚的改变多为帝王或政治人物所引领,而他们去做这一番改变,是要申明一种政治表达。我想,这种被引领的时尚是不是更易、更直接体现在“制度”层面(比如官服)或者说更多影响的是上层人群?——书中也有提到服饰对政治人物身份的标识意义。而我注意到,书中利用、呈现了很多图像资料,涉及人群是更广泛的,所以,头饰风尚之改变以及这背后的政治权力的表达,它在不同人群,特别是一般民众这个群体里如何体现的?
吕博:黄正建先生研究大和六年王涯有关舆服制度的奏议时,曾指出唐代规定冠服制度的基本是《衣服令》,而规定常服制度的主要是《礼部式》。无论是令还是式,目的都是通过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进行权力等级划分。也就是说官服是严格按照官品等级确定的。这样的服饰只是行政等级的标识,类似于今天的“制服”。有唐一代,服色、服等有变革,但变革的理由都是和官僚等级有关,很难和时尚挂钩。而幞头是个人化色彩很浓厚的一种头饰,它的形制变动经常由著名的政治人物来引领。有特殊政治地位的人一般都会花心思装扮自己的头饰甚至服饰,标识自己的形象、身份。布尔迪厄曾解释道:“不同阶级(利用服装)自我表现的兴趣,其所投注的注意力,其对所得利益的意识,及其实际花费的时间、精力、代价和照料等,都与他们合理期望的自己从中获得物质利益与象征利益的机会成正比。”墓葬里很多壁画里的人物,从朱绿的官服或者其他服饰特征来看,他们都属于官僚阶层,自然头饰也能跟上层人群的时尚变动。
幞头没有等级,普通人也佩戴。但普通人的服装记录很少。在唐代诗歌零星的描述里,经常是衣不蔽体。他们最先考虑的大概是衣服的物理功能,遮寒保暖,大概跟时尚无关。王梵志诗里有一首叫《贫穷田舍儿》就对穷苦的农民着装有描述: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犹似一食斋。
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开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
澎湃新闻:论及北周至五代的政治演进,即有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更迭,而服饰风尚的变化,似乎是可以随时可发生的。作为一种政治表达的外化形式去看,你会认为中古时期(或具体说北周至五代这一时期),服饰风尚更与政治相关吗?
吕博:今天的时尚风潮主要是由娱乐明星、时尚界人士引领的,随时可能发生变动,变动的频率也很高。当然有时候政治人物也会引领时尚,比如有一年唐装突然流行,大家也都有记忆。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可以很容易观察到。但中古时期的官服主要是在改朝换代之后才更迭,变动频率很低。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权力与服饰的关系,首先表现的是社会、政治关系的界定,即“臣僚对君主”的服从。服从关系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臣僚穿着君主推行的“冠带”。因而,新王朝的开国皇帝有一个重要的立国策略,便是根据所属天命、德运更改服饰色彩图案,然后强制推行。中国古代服饰、发式的变动从来不像今天这么随意,改变官服、服色肯定是重要的政治事件,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北魏孝文帝汉服改革、满清入关后的留发不留头等等。《通典》卷五十五《历代所尚》就记述了每个王朝根据德运所指定的不同服色。《礼记·王制》曰:“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早期的儒家经典中,已将服制变革看作是叛乱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服饰改革确实是颠覆秩序的政治事件。
幞头“贵贱通服”,没有律令等强制的制度规定,但就我的观察来说,这种头饰也主要在大的政治事件之后,才会有新样式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代表新势力的政治人物驱动。至少我们从史料里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普通民众很难和服饰时尚有什么特别直接关系。所以认为中国古代的服饰随时变动大概是一种误解。
澎湃新闻:这本书比较关注的是政治力量在服饰风尚方面的影响,促发的变化,而在此之外,时尚的流变还与当时的社会风俗、经济等其他因素有关,那么北周至五代这个时期,你有关注其他方面因素对服饰的影响如何吗?
吕博:这个问题有些难回答。我换一种方式来回答吧。
其实对于一种服饰为何会流行,学者们本来就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服饰的流行有自生的内在逻辑,并不受社会力量的制约或者外部条件的驱动。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阿科贝(A.L.Kroeber)认为女性服装一般遵循着每五十年循环流行这样一个“内在的”、“本质的”规律,基本不受外部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英国当代的艺术史家吉姆斯·拉维(James Laver)认为,研究服饰的历史就是要克制从社会史中寻找动因,相反,要从服装自身的发展演变中探寻变化的趋势。但这种看法遭到了历史学家罗兰·巴特的批判。1957年,罗兰·巴特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与服装社会学——方法论的观察》。他说:“服饰应该看作是一种风俗惯习,应该在社会层面来加以研究,而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美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能仅仅研究品味、潮流和方便性。他们应该厘清、协调并且解释那些(出现在服装史中的)整合、运作、限制、禁止以及抵触的规律。他们要研究的不是图像,或者风俗的特征,而是关系和价值。”他说:“研究服装特别之处在于必须研究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结构,从它身处的历史之中去把握;同时,也不能忽视它自身结构的构成。”(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学术史梳理,可以参考汤晓燕《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巴特观点,可以参考[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熬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我自己倾向于罗兰·巴特的看法,服饰作为人的装饰保暖必备物品之外,内涵多种社会信息。中国古代的服饰除等级外,也常常传达着文化、社会地位、职业、道德与宗教关系、婚姻状态等社会信息。如果将一个时代比作一个鲜活的个人,正像一个人具备某种性格一样,这个时代也有某种“时代格”。此种时代格,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日用物品上。在共同的时空或者文化语境中,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物品”辨识出相关的文化讯息。如果不同的团体对于同一件服装解读出不同的涵义,则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处在同一知识和经验语境。相比于博物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服饰史的使命就在于需要从服饰变迁的历史上看到更多的政治、社会信息。我想最简单的问题便是:什么力量驱动服饰变迁?
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服饰变革主要是政治因素的驱动。当然也会有经济因素,比如奢侈性消费。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如上官婉儿、韦后这样的权贵穿戴奢侈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还是为了“区隔”,标识自己的身份。所以布尔迪厄说“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他通过对上述“文化符号”的研究指出:“文化不能免于政治的内容,而是一种政治的表达。”

北齐娄睿墓壁画头戴风帽的骑马武士

王处直墓所见二脚上翘的幞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著:《五代王处直墓》,彩版47。
澎湃新闻:或许上一个问题还可以扩展到权力外化的其他形式,比如你关注的礼制的一些方面,由另一个权力外化的形式去考察权力本身,它与从服饰的角度看会有什么不同?
吕博:没什么不同。我自己只是尝试从服饰的这个角度来观察权力运作本身。我当时写《头饰背后的政治史》的初衷是想扩大政治史的考察方式。就是强调研究者在考察政治史时,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在关注这些问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到,政治及其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服饰即是一种表达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从服饰这种微观角度切入也可以考察很多政治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途径切进考察。但从实际的写作中,感受到从服饰考察中古权力运作,其实很难。这里说的难主要是因为史料寡少。比如有关中古服饰带来的视觉感受,就很少有史料记录。所以有时候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论证会很曲折,经常是举例、类比夹杂,绞尽脑汁的感觉。我此前也围绕礼制建筑明堂写过一些文字,写作体验就很不一样。比如写《明堂建设与武周的皇帝像》一文,就是你事先预想到的每一步,后来都找到了典型、有力的史料支撑,这种写作体验就比较好。当然,这也是因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帮了大忙。要说不同,就是研究、写作难度不一样,观察的基本方法、视角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澎湃新闻:你在后记中讲到“同龄朋友纷纷声称要告别政治史”,我想了解这是中古史学界的一个动向吗?何所谓“告别政治史”,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吕博:也没想到一句带有开玩笑性质的话,能引起一些争议。(哈哈)我没有特别因为这个问题问过朋友们,我只是努力地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有一度他们说有点厌烦政治史了,我开玩笑说与其厌烦不如“告别”吧。后来就看着大家也都在用“告别”这个稍显“决绝”的词语。我想同龄的朋友们要告别的是旧的政治史,并不是说他们不研究政治史,而是想换一种新方式研究政治史。比如去解构各种权力现象。2018年侯旭东老师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写了《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就在熟悉的师友们中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学者都在尝试,我们也多点耐心吧。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另外,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历史终究要回归对人的关怀,帝王将相也是人,应该从人的角度观察政治人物。事实上,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理念。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因此,从那时起梁启超就倡导新史学应该关心普通民众。政治史关心帝王将相比较契合一般大众的兴趣,总是拥有最多的阅读者,但很难说政治史就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学者们最应该关心的历史问题。比如社会经济史一直关心的是芸芸大众的生存发展史。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信仰生活等关涉到历史当中的大多数不被记录的人群。而通常所见的政治史一般涉及到的只是几个人的勾心斗角,其实离普通人的生活距离、生活体验很远。
第三,我猜大概是因为“影响的焦虑”,觉得研究中古政治史无法超越前人吧。有关中古政治史,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先生的相关研究登峰造极。年青学者从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就学习的是这些名家名作,当然受这些学术作品的影响也最大。如果你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读这些高超的作品确实是享受,因为只是纯知识的学习,大概能体会到历史学家智慧,就很满足。但当你从一个学生向一个学者蜕变的时候,尤其是你要把学习过程变成创造过程的时候,前面这些伟大的作品带来的就是“影响的焦虑”。我的观感是,我们85年后的中古史青学者们(大多是熟识的朋友)有时候在学术思考上面比较“撕裂”,一方面大家都有创新的自我期待,想要做出和前人不一样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从开始接受学术训练起,又不得不受旧的学术话语潜移默化的影响。前辈学者们都太厉害,年青的学术工作者或多或少都会在旧的学术知识与新的创新期待中间有些“挣扎”和压力。换句话说就是“创新的焦虑”。他们大概觉得在中古政治史领域内,有太多的伟大作品,创新很难,自然会另觅他途。其实,他们都是有学术理想的学者,有学术理想的人一般都会有更多的学术想法,进而“见异思迁”。我总告诫自己对有学术理想的朋友,要多些倾听和了解,少些先入为主的偏见,
另外,前两年中古史研究领域上有边缘和核心的说法,一度老流传“核心陷落,边缘崛起”之类的话,大概是说政治史是核心,宗教文化之类的是边缘,好像在豆瓣、微博什么的讨论比较热烈,我也没有特别关注,都是听说。就是觉得这种说法好玩。网络常常会把严肃的学术看法,变成诙谐的段子传播。大意是说在音乐界有歧视链,古典音乐艺术家看不起摇滚乐手,摇滚乐手看不流行乐歌者,流行乐又觉得民族唱法太土。网友说中古史学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歧视链,政治史和制度史居高临下看不起宗教史和文化思想史。社会经济史早就没了市场。
我并不同意这种简单的划分。其实所谓的核心与边缘都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如果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最终努力的目标是认识那个时代。那么经济、宗教、文化、政治哪一个研究领域都不能缺。其实,翻开唐长孺先生的八卷本《唐长孺文集》看看,我想任何在学术领域上的狭隘想法,都应该打消吧。那一代的杰出学者们,常常以一己之力,在很多领域都能纵横驰骋,贡献非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学术目标是认识中古历史的时代的特征。诸如时代特性这样的问题不是政治或者经济一个研究领域能解答的。我们今天好像没什么理由变得更狭隘。实际上,没什么好争议的,无论是古典还是民族,无论哪个领域,只要能唱好就行了。
澎湃新闻:目前在研究什么?做什么样的具体工作?
吕博:好像谈了很多和中古服饰无关的话题。
一方面是我想就自己有关礼仪实践与唐代政治社会变迁的研究结个集。但是还差一章有关中晚唐历史的研究,考虑了很久,加之自己各方面的修养、积累不足,断断续续也写了两年,还是不能完整呈现。所以还是焦虑。我在后记里曾说过,有过学术写作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写易改难。如果文章的思考高度提升不了,再怎么修改,也只是文字上的润色,修改迁延也只能让人有徒劳无功之感。这是我经常有的感受,不满和挫败是常态。
唐代礼制是我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此外,为了避免学术上的“路径依赖”,我自己也在努力尝试进入一些新的领域。比如目前最想完成的一本小书是《唐代的三个府兵》,试图通过唐代早中晚三个不同府兵个案,研讨一下“统一制度下的不同个体”。中古史很容易写出自上而下的,研究国家统治的文章。但很少或者说很难做出自下而上的视角,关心普通民众生计状态的研究。我想试试吧。
我记得近年有一次“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会后闲谈,大家聊到如何避免路径依赖这个话题。就是说起当下我们常常复制自己的成功经验,很多论文是尽管题目不同,但其实都是在同一思考、同一模式下产出的,经常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突变。用现在时髦的词语来说就是“内卷化”。当时大家都说我们要想避免路径依赖就是进入另外青年同行的领域写一篇论文。我大概就是受到这些优秀青年同行的感召,也想要换一些研究课题。另外我自己长期关注一个领域的问题,也多少有点厌烦。如果连尝试新问题都不敢,那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挑个良辰吉日告别这个职业吧。太无趣了。我自己在吐鲁番文书里找到两个府兵,第三个找了很久,目前有点眉目,但材料零碎,也迟迟不知道怎么下笔。前段时间,刚刚看了宋怡明先生写的《被统治的艺术》,很多想法比较契合。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技艺差,而是我们所从事的断代往往受到材料稀少的限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是中古史写作的常态。也着急不来,慢慢完成吧。另外,我也想跨断代,想在南朝学术文化史领域里写一些文字,前两年写过两篇习作,目前都没有发表,好像也并不太成功。但新鲜的尝试总是需要的。总之,学术工作对我来说是场负重旅行,一边尝试一边向前走吧。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