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反思西方疫情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西方各国的政府和群众时常作出令人困惑不解的应对举措。无论是前期由英国最先提出“群体免疫”的抗疫理念,还是后来部分国家不顾疫情急于复苏经济,抑或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谈及群体免疫,这些做法都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争议和不满。虽然没有政府公开将“群体免疫”作为目标,各国经济解封的进程也受到社会多重阻力的限制,甚至特朗普昨日也正式确诊为新冠阳性,但发人深省的是:为何欧美国家长期有这么多政客精英用“群体免疫”、“经济优先”等理念来粉饰种种消极抗疫的举措,而且被这么多民众所接受?其中一个值得反思的原因是,它背后反映着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传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
一、从“自然选择”到“适者生存”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社会达尔文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人类族群同样受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规律影响的学说,其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作由适者生存法则支配的生存斗争。然而,学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涵争论不休,因为它在历史上常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等不同的社会思潮相关联。但无论何种阐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核都涉及三个关键短语,即:“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生存斗争”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受其启发,观察到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存斗争。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随着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这势必会导致生存斗争,“或者同种的这一个体同另一个体斗争,或者同异种的个体斗争,或者同物理的生活条件斗争”。在此情况下,达尔文发现有利的变异往往会得到保留,不利的变异则会被毁灭,其结果是新物种的形成,这一过程被称作“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原理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精髓。事实上,达尔文尤为注重科学性,在书中仅阐述了生物界的情况,而没有直接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也绝不鼓励对其理论进行某种社会解释。在他看来,自然选择依赖复杂的偶然性,“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因此,当友人提醒达尔文“自然选择”一词具有拟人化色彩的弊端后,他赞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的“适者生存”更为准确,并从《物种起源》的第五版开始将这两个术语并立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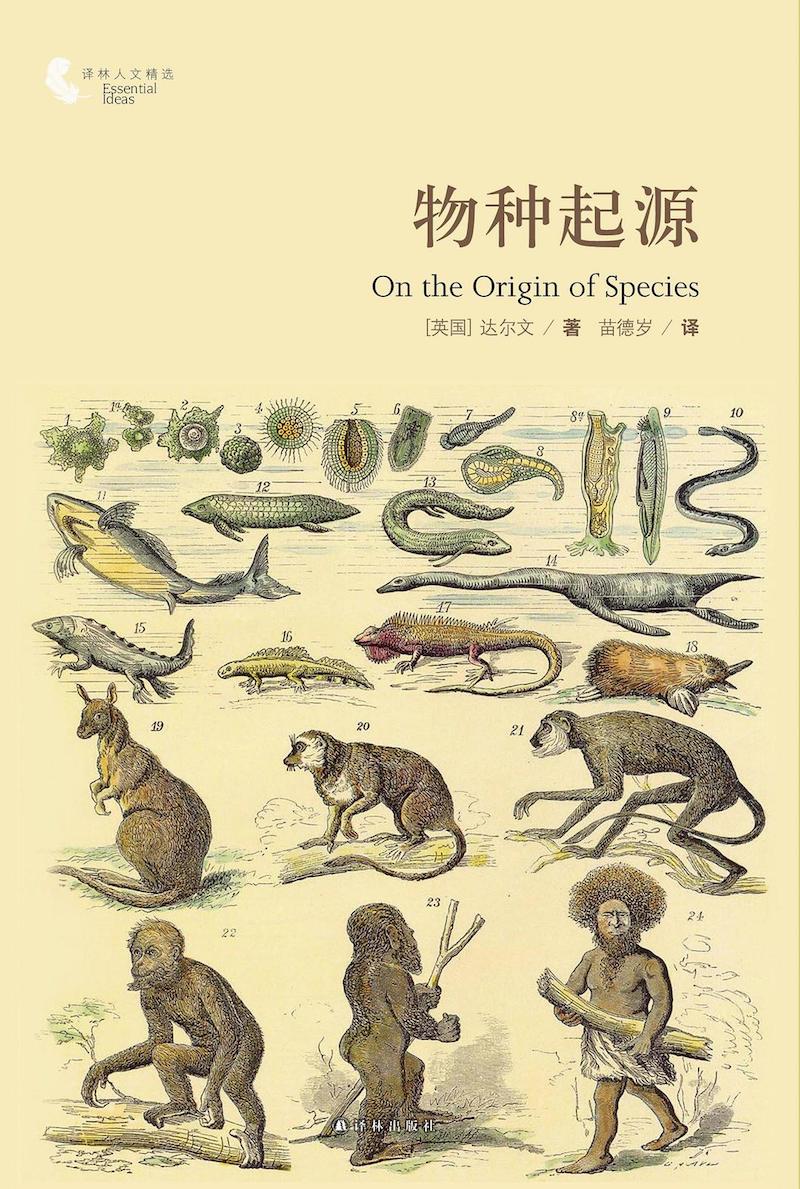
《物种起源》
然而,斯宾塞理解的“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却不尽相同。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斯宾塞就开始思索生物学理论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社会有机论。他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比,一方面视社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既独立发挥某一功能,又相互协调有机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社会有机体也服从生物的适应规律,不断地为适应外界条件或环境而作出改变。对于这种改变,斯宾塞采用了拉马克主义的立场,认为后天性状可以遗传,而生存斗争会诱导人类主动适应环境,提升身心机能,然后传给后代。因而社会有机体必定从低级逐步走向高级,“人类的各种机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应于社会性状态”。在他眼中,“进步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这构成了他社会进化论的重要前提。
在阅读完《物种起源》后,斯宾塞发现达尔文为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被吸收到我正在阐释的一般进化理论中。”1864年,斯宾塞在《生物学原理》一书中首次用“适者生存”这个短语来表达“自然选择”。但他的论述从未脱离社会有机论,只是把自然选择看作是保持物种与外力间建立平衡的一种手段,认为其能够使有机体在所处的环境中产生适应性。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在本质上是指,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那些结构不太完善的个体在他们产生后代之前就死亡了,留下那些结构适应性更强的来产生新一代”,推动整体的发展。他将适应和进化等同于进步,又因这种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所以反对国家政府的干预。斯宾塞指责称,对穷人、弱者、缺陷者的强制救助将导致“不适者”的增加,同时阻碍“最适者”的生存,危害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他强调竞争才是进步的关键。
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本是“中立的工具”,但被斯宾塞延展到社会的维度,以“适者生存”的概念曲解了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正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指出,“适者生存”的模糊性对“自然选择”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导致很多人认为“适者”指的是“最优秀”或者“最高等”的人。进化论与社会有机论的结合赋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宿命论的色彩,极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道德伦理,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自19世纪下半叶始,基于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适者生存观念很快就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套话语与逻辑被用来为各种思想和社会利益服务,充当合理性的解释,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和优生学。斯宾塞倡导个人自由是幸福的第一要素,干预制度不仅限制人们的自由,而且往往保护不适者,破坏进化法则。这种思想还备受美国镀金时代资本家的推崇。以萨姆纳(William Sumner)为代表,他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自然选择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不相信适者生存,那结果只会是不适者生存。他把生存斗争视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支持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萨姆纳的理论后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流。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亦可为某些方面的人为管制辩护,如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的优生学。由于社会进化论承认人类存在优劣之分,并且这种差异可以遗传,为了避免生存竞争中不适者的过度繁衍或最适者的繁衍不足,高尔顿呼吁政府介入,阻止那些有不良特征的人生育,鼓励更有价值的人延续后代,从而改善人类社会。但一旦这些理念被运用于国家争斗、帝国扩张和种族问题等范畴,则会酿成巨大祸害,其极端形式就表现为纳粹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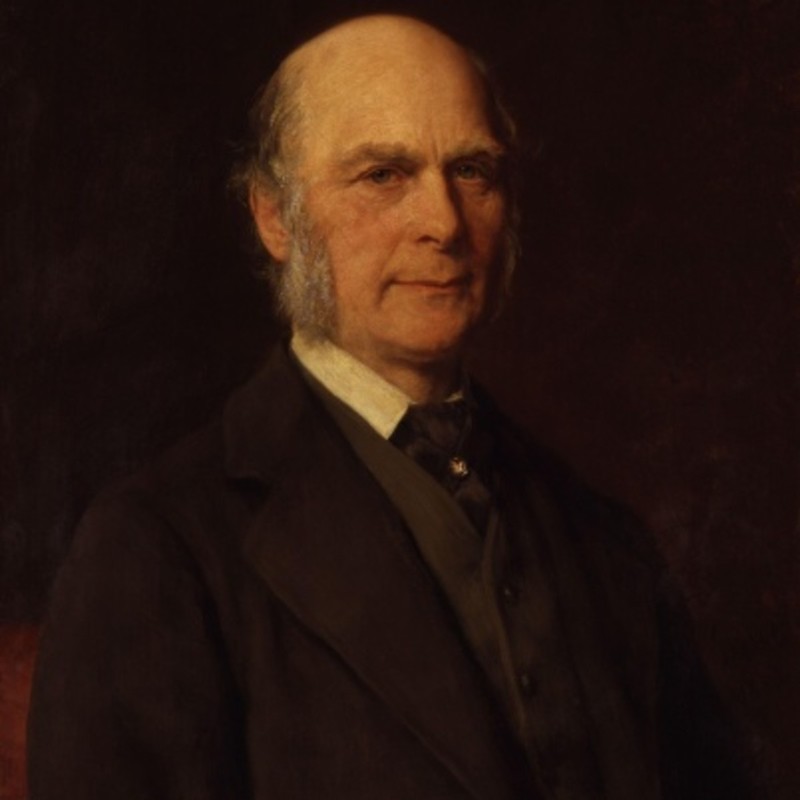
高尔顿(Francis Galton)
二战结束后,社会达尔文主义遭到各界的猛烈抨击,它被指责为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提供了意识形态和伪科学动机。而福利国家的出现使得西方社会重视政府干预和社会保障,试图缩小贫富差距和缓解社会不平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说法似乎不再被大肆宣传,但事实上它从未消失,只是转为社会的暗流,等待再一次显现。
果不其然,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以及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出台,人们意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死灰复燃。正如方纳所指出,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政府不应试图干预和影响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财富的分配反映的是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历史环境的局限;那些较为不幸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种族,他们之所以不幸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如同在19世纪末期,社会对穷人遭遇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被当成是一种现实的迹象,而并非是一种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借着自然法则的幌子早已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每当生存问题成为国家或社会意识的中心时,它就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复兴。
三、新冠疫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
新冠病毒的肆虐使西方世界又一次面临生存斗争。这种困境不仅是国家和个人能否攻克病毒,存活下来,而且还在于能否拯救受疫情重创的国民经济。在此情况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发动机又重新运转。
首先,我们来看“群体免疫”,它本是医学术语,指当很大一部分群体对一种疾病免疫时,能为其他易感人群提供保护,从而阻断病毒的传染,它主要通过接种疫苗的手段来实现。但目前由于还未研制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若想达到“群体免疫”,只能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英国所谓的“群体免疫”策略,其核心只是延缓疫情高峰,而非压制疫情传播,寄希望于国民整体建立起免疫力。这种自然免疫的方式将会带来重大的风险和代价,据钟南山院士称,它需要一个国家60-70%的人感染病毒,大概会造成全球3000-4000万人的死亡。
然而,许多西方人并非从科学的角度理解“群体免疫”,而是将适者生存的逻辑镶嵌其中,赋予它新的社会解释:一方面将其视作疫情的最终出路和必然结果,天真地以为获得免疫的群体就能适应新世界;另一方面忽略自然感染过程的残酷性,原本以保护弱者为目的的“群体免疫”被渲染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和更好的未来。这种理念一直萦绕在政府决策和许多人的脑海中。
具体而言,在防疫上,欧美一些国家并没有采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策略,而是主张轻症在家自愈,老人自觉隔离,只有重症患者可以接受检测和入院治疗。其反映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资源该如何优先分配?在紧缺的条件下,弱势群体就成为可被牺牲的部分。其中处境最糟的是老年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新冠死亡病例中,欧洲有超过95%是60岁及以上的人,美国有80%是65岁及以上的人。在这些国家,养老机构的死亡人数众多,它们很少得到政府的帮助,受感染的老人也常被拒绝到医院救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还承认,若遇到二选一的生存抉择时,生命维持设备将优先被用于更年轻或更健康的病人,老年人便沦为了“不适者”。
其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还用以支持“经济优先”的政策。疫情之下,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惧促使西方某些政治领导人和民众呼吁重新恢复经济活动。在他们看来,确诊病例只占人口比例中的少数,且大部分感染者并不会死亡,但严厉的封锁措施则会摧毁经济,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更严峻的生存危机,反而将造成更多人的死亡。因此,他们认为如果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自然免疫是最终归宿,那么为了保障整个国家和大多数“适者”的利益,就应让健康强壮的人复工复产,尽管会导致一部分人死去。甚至有美国政客荒谬地提出“老人应主动为经济而牺牲”。
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生存斗争命题,唤醒了西方存在已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这一观念使他们容易相信两个错误的预设:一是生存困境,即在新病毒的袭击下,只有“适者”才能在斗争中存活,而有限的资源只有分配给他们,才能保证社会有机体适应新的环境;二是自然决定论,认为自然免疫是一种客观规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循,无论生与死都是自然结果,是社会进化的一部分,人类不能因此停下社会发展的步伐。然而,这两个前提都经不起推敲。因为生存不是只能通过斗争,更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关爱。所谓的“适者”也不具普遍性,只代表具体的利益集团,且往往是富贾与权贵。而疫情的暴发决不能听之任之,任何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生命和健康权,没有人的牺牲应被视作理所应当,战胜它需要社会集体的力量和人为的积极干预,例如世界各国的协同抗疫和研发疫苗。
如今,全球已进入抗疫常态化阶段,但世界疫情依旧严峻,而且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都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种族等其他问题上。随着他们疫情的反弹和确诊人数的持续增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逻辑仍将继续发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若特朗普感染康复后,他是否会自以为自己获得抗体,成了所谓的“适者”,从而进一步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融入其宣传话语与应对疫情的举措中?这对未来世界疫情的走向将造成更多不确定性的影响。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