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宋红娟:西方情感人类学研究50年
文 / 宋红娟(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产生了一套男女有别的机制,男的跟男的在一起,女的跟女的在一起。为什么这样设置呢?他认为这是因为情感是易变的。在现代社会中,恋人分手、夫妻离婚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被誉为个人追求真爱的勇敢之举,但在强调稳定性的传统社会里,这样的事情是可怕的,传统社会需要的是稳定的结构与稳定的关系,经不起折腾。生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可能有一种深切的体会——我们随时都在表达自己的各种情绪,尤其是在动荡的年代或面对社会突发状况时,我们更会处在情感的洪流之中。可以回忆一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对于武汉封城之举,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抒发或宣泄了多少情感;在对“方方事件”的讨论中,甚至有交往多年的朋友因意见不合而断绝往来。情感不仅影响我们的感受、判断,甚至决定了我们行动的方向。
无可否认,情感充盈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平静得几乎不被察觉的情感,有激烈得难以控制的情感,有导致善的情感,也有导致恶的情感。但对于情感究竟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在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回答。专门性的情感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心理学的范畴,但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有一群人类学家开始尝试在不同文化中展开有关情感的经验研究,这一尝试被后学继承与发展,成为一个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新领域——情感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motion)。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情感具有模糊性、易变性[即休谟所说的可入性/渗透性(penetrability)]以及难以把握的特点,这使得情感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困境一目了然。但不管怎样,西方情感人类学至今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从研究视野上看,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去本质化的努力、反思文化建构主义、多学科的重新融合。

情感人类学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可以划定在1970年至1990年,核心观点是认为在不同文化中,情感的特质是不同的,文化决定了情感表现形式。实际上,在发展之初,情感人类学尚无明显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较早进行情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罗伯特·列维(Robert Levy)、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他们提出,人类学要进行情感研究的主要原因是不满当时心理学和哲学中对情感的本质化表述,譬如将情感视为人类内在的、固定不变的一种特质。他们认为,心理学和哲学所犯的错误在于将西方文化中的情感特质视为全人类的普同情感特质;而情感人类学主要依托田野调查得来的经验材料,从而展示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中情感特质的差异。三位先驱分别在菲律宾、法属波利尼西亚及密克罗尼西亚展开田野调查,因此早期的情感人类学研究又被称为“太平洋民族志研究”。
1972年,米歇尔·罗萨尔多开始在菲律宾的伊隆戈人(the Ilongots)中进行调查,当时这个群体仅有3,500人,以狩猎和简单园艺为生。她的研究主要围绕当地社会生活的核心人物猎头(headhunting)展开,搜集了一系列与猎头有关的地方性情感概念。该研究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猎头的情感世界是我们理解和阐明伊隆戈人社会生活的核心与基础。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讨论了激情(passion)与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让人遗憾和悲伤的是,她在后续的田野调查中不慎从山坡跌落身亡,她的丈夫罗纳多·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为了祭奠妻子,后来一直在该地从事田野调查,继续推进妻子的研究。也有学者指出,罗纳多·罗萨尔多的研究弥补了米歇尔·罗萨尔多对历时变迁的忽略。

伊隆戈人的猎头:
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
[美]米歇尔·罗萨尔多 / 著
张经纬、黄向春、黄瑜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罗伯特·列维1973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很有意思。他在塔希提岛(Tahiti)的研究表明,塔希提人没有诸如痛苦和悲伤的情感词汇,他们往往将情感困扰理解为一种生理性不适。对此,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男子在被妻子无情抛弃后,便开始到处问医,他觉得自己病了,基本的症状是乏力、没精神、很疲惫、身体很沉重。
列维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情感上的不适,但塔希提人没有这类情感词汇,因此他们没有办法确切描述出自己或他人的情感状态。就如他提到的另一个例子:一位男子在亡妻坟前哭泣,村里人不认为他陷入了悲伤,而认为他的哭泣仅仅是出于他的某种道德上的懊悔。列维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person-centred anthropology),认为在谈论文化差异时,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情感、感受、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比关注民族性(语言、服饰、习惯等)更为深入。
20世纪80年代,凯瑟琳·卢茨在密克罗尼西亚岛的埃法卢克小岛(Ifaluk)开展的田野调查也颇为重要。她发现,这里并不存在像西方文化那样将女性与情绪化相关联并加以贬低的现象。当地有两种较为显著的情感,分别是song和metagu,类似于正义、正直之类。这两种情感与政治权威有关,当地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表达这类情感的机会。基于丰富的田野经验,她指出,埃法卢克小岛上的人是根据具体情境定义情感的,他们的文化中不存在情感与理性的区分。

以上三位学者的研究主要反思的是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对于情感的本质化认识。在他们看来,情感不仅是自然(natural)的,也是文化的,不同文化中情感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基于他们对情感文化属性的强调,随后的相关研究者将他们称为“情感文化建构主义者”。大概从1980年末起,情感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对这种文化建构主义产生不满,转而强调人及其经验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包括里拉 ·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南希·舍佩尔-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罗伯特·德斯加雷斯(Robert Desjarlais)等;他们的核心研究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将情感视为话语(discourse),一种是将情感视为具身化(embodiment)思想。
将情感视为话语,是由凯瑟琳·卢茨和里拉·阿布-卢赫德在1990年共同提出的,这显然深受福柯的影响。在二人合编的《语言与情感政治学》(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一书的导言中,他们提出情感研究应该围绕“话语”展开,探寻情感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情感话语——后来也被学者称为情感交谈(emotion talk)——主要包括与情感表达相关的叙述、对话、表演、诗歌等。1986年,里拉 ·阿布-卢赫德出版的民族志《蒙面纱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中涉及大量的情歌。里拉·阿布-卢赫德发现,一方面,贝都因是一个具有严格等级的男权社会,总体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的荣誉和德性,其中对情爱和性的冷漠是一个人获得德性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贝都因社会中又存在着数量庞大的情歌,这些情歌在年轻人和女性中传唱。
里拉·阿布-卢赫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与丈夫离婚20年的女人对里拉·阿布-卢赫德说自己从未喜欢过前夫,而且对离婚无所谓。但几天后,里拉·阿布-卢赫德偶然看见一群妇女围坐在这个女人家中,当大家提起她的前夫时,这个女人忽然唱起了情歌,歌声饱含对前夫的谴责、对离婚的悲伤,情绪非常激动。她认为,女性和年轻人通过传唱情歌,表达了一种被压制的情感,情歌是贝都因社会中具有颠覆性的权力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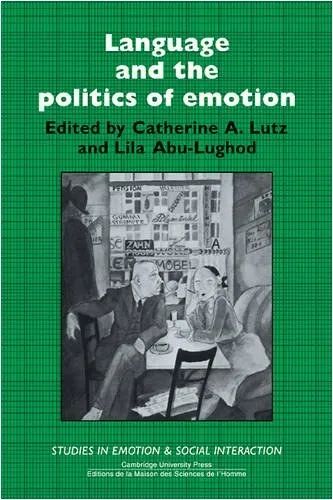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Catherine A. Lutz、Lila Abu-Lug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06
与此同时,有学者指出话语理论对情感研究的运用存在不足,认为将情感单单解读为权力关系下的话语实践,有些本末倒置的嫌疑;将情感转换为话语、将情感语言理解为一种语言游戏,是一种简化论(reductionism),忽略了情感的“主观”面向。在这一反思脉络中,具身化(embodiment)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实,情感人类学先驱之一米歇尔·罗萨尔多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具身化这一概念,她认为情感是一种具身化的思想。在人类学里,embodiment的提出是为了调和身体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分,情感的具身化研究深受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下面要提到的两位从事情感具身化研究的人类学家都有从医的背景,并且在田野点都充当了医生的角色。
正如南希·舍佩尔-休斯指出的,生物与文化的区分是一种伪区分,情感既属于文化的一部分,也与人的生物性密切相关,它有一套产生、积累、控制与释放的身体机制。
舍佩尔-休斯在巴西东北部地区的博耶苏斯·德·玛塔(Bom Jesus de Mata)棚户区做了25年的田野调查,最开始是作为一名医生参与其中的。她曾说,在棚户区的调查和随后的研究中,她对现实与困境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理论探讨。田野调查期间,她参与和推动了当地儿童医疗和培育方面的诸多项目。她对当地婴儿、儿童高死亡率的关注最后写成了一本民族志——《没有哭泣的死亡:巴西的日常生活暴力》(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这是情感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舍佩尔-休斯在这本书里集中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当地婴儿的死亡现象以及母亲们的情感反应。她想讨论的是,在匮乏、疾病与死亡时刻伴随的情境下,作为一种生物本能的母爱如何变得无足轻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信任如何受到影响等问题。她认为,人的情感是生物性和社会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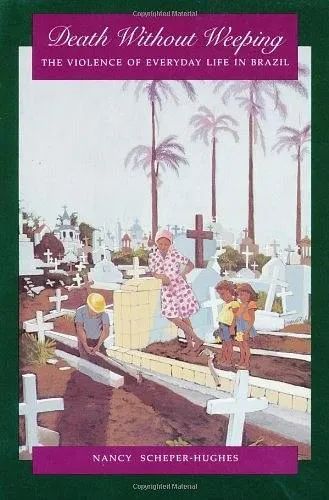
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Nancy Scheper-Hugh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11
罗伯特·德斯加雷斯的田野点在尼泊尔中北部Helambu地区一座叫作Yolmo Sherpa的村庄,这里信仰藏传佛教,他在村里跟着师傅研修精神治疗。根据在这里的调查,他出版了民族志《身体与情感》(Body and Emotion: The Aesthetics of Illness and Healing in the Nepal Himalayas),这本民族志是与情感话语理论的直接对话。
基于尼泊尔的田野调查,德斯加雷斯认为对情感的研究应该从话语回归情感本身,人的情感经验应该是被关注的焦点,话语理论虽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情感表达所嵌入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但情感话语背后包含着人最寻常也最深刻的身体体验。
德斯加雷斯搜集到的一首当地民间歌谣中有这样的歌词:“我的警告是对老人的/他囚禁了年轻人的自由/那个被遗忘的东西,称为爱/感情,欲望,还有燃烧的火焰……”如果按照里拉·阿布-卢赫德的分析框架,那么这首歌词无疑表达了年轻人的一种反抗,但德斯加雷斯认为,除此之外,歌词中还包含着当地人对情感的一种身体体验。
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英语中的悲伤(grief)、难过(sadness)、痛苦(pain)在当地语言中有一个统称,叫作tsher ka,但它又不能完全覆盖英语中的这些概念,tsher ka尤其与分离、忧伤,以及与别人进行内心交流时的无力感相关。德斯加雷斯认为,当地人的认同首先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继而通过家户、家庭和村庄,形成基于血亲、地位等级以及资源与食宿式交换的关系网络。有人去世或离开,首先会引起人们身体上的不适,即心痛,这种分离意味着认同的危机,没有群体对生活的指引,人们将会迷失、不知道自己是谁。德斯加雷斯指出,当地人很害怕tsher ka,不敢谈论,害怕其会附着在自己身上,对这种情感的表达不仅是语义学上的,也是一种深层的身体体验。

2000年之后,人类学的情感研究呈现出全新的局面,一改发展初期的批评与反思基调,开始试图将情感人类学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重新融合,强调相互借鉴与理论对话。
在心理学和哲学方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84年发表的《情为何物?》(what is an emotion?)一文又被重新提及;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2001年出版的《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一书对2000年之后的情感人类学影响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中的情感转向,如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Rosenwein)、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莫妮可·希尔(Monique Scheer)、简·普拉姆珀(Jan Plamper),他们的研究与情感人类学之间存在对话。其中,芭芭拉·罗森宛恩在关于中世纪早期的情感研究中提出了“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ies)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克里丝汀·杜若(Christine Dureau)借鉴,用以解释位于所罗门群岛西部的辛博岛(Simbo)上的母爱。20世纪90年代,她在辛博岛上做了22个月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就是母爱这个主题。她在研究中发现,母爱虽然被视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情感,但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她运用芭芭拉·罗森宛恩的“情感共同体”概念来解释辛博岛人的母爱在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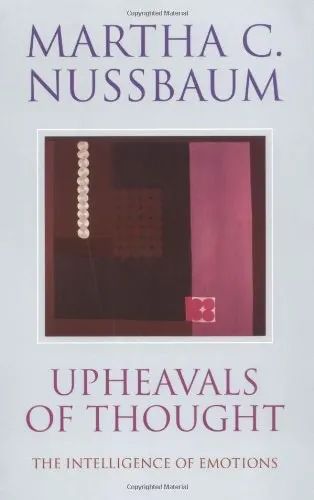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Martha Nussba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04
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情感人类学对文学理论的借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彼得·戈尔迪(Peter Goldie)和安德鲁·贝提(Andrew Beatty),他们主要尝试将叙事学方法融入情感人类学的研究中,提出具体的情感研究方法——包括理论提升与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两个方面。
其中,贝提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视。他在印度尼西亚有两个田野点,一个是西苏门答腊的尼亚斯岛(Nias),一个是爪哇。基于在这两地为时5年的田野调查,贝提指出,语义的、结构的、话语的方法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对于人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产生了情感。他认为叙事学方法能够弥补这个缺陷,抓住情感的特殊性。情感的特殊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始终与我相关,二是具有时间深度。简单而言,叙事学方法就是将人物的情感置于历史和情节中,并按照这两个维度来分析与理解当下的行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情感,看到人物内在和外在间的冲突与张力,而不是将人简化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产物。
贝提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尼亚斯岛的故事。他做调查的那个村子的村长去世了,按照惯例,村长的副手要在其葬礼上发表讲演。贝提注意到这样的细节,这位副手在一夜之间将自己的头发染黑、穿着自己最庄重的衣服,他在葬礼上的演讲没有以悲伤开始,而是从得意扬扬、意气风发开始,最后以哽咽、表达悲伤结束。贝提指出,对这个场景以及当时这位副手的情感的理解需要回到他与村长的恩怨故事。大概在20年前,就在这位副手结婚当天,村长当众羞辱了他。随后,副手又因祖母和侄子与村长不断发生冲突,怨恨在二人之间不断增长。通过这样的叙事,副手在葬礼上的表现及其情感和内心世界就被呈现出来。贝提认为,副手在葬礼上抑扬顿挫的声音和年轻的外表都暗示了他因村长的死而获得解放。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所呈现的情感是个人的、特殊的,而不是整个村庄的人普遍的情感类型。
除了借鉴叙事学方法,情感人类学也在尝试与同情理论、情动(affect)理论结合。总之,在情感人类学发展至今50年的时间里,理论与研究方法都在不断推进与拓展。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现代社会求新、求变,强调个人生命的意义。的确,充满易变性、模糊性的情感恰恰彰显了生命的强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但随着个人情感的解放,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情感人类学尤其值得我们进行本土化的努力与尝试。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