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辛德勇:社会大众需要怎样的历史读物
9月18日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三联韬奋书店做了一场题为“社会大众需要怎样的历史读物”的演讲,本文系演讲讲稿。

辛德勇教授
如果不做任何限定,从字面上泛义地去理解,所谓历史读物,当然应该包括所有以历史为主体的文字。若论所述历史知识的层次,专业的研究性著述自然位居顶峰。不过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社会大众需要怎样的历史读物,这样,以社会大众的眼光来看,就不是所有专业性研究著述都适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了。
那么,社会大众的口味是什么呢?有人一谈到社会大众的喜好,很容易地就想到“通俗”。要是把“通俗”的“通”字解释为文字畅达而易为读者接受,讨读者喜欢,那么,这样的联想当然是合理的,可“通”不一定和“俗”要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通”不一定非“俗”不可。因为“俗”的涵义很清楚,它意味着平庸,意味着卑微低下,甚至意味着下里巴人的情趣,乃至有些猥琐的心态。
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并不需要这种低俗的历史读物,因为它背离了我们清楚、准确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愿望。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虽然很复杂,但那种低俗的历史读物,我理解,大致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戏说”来代表其基本特征,即一不严谨,二不准确,甚至还都不同程度地展现着荒唐:荒唐的史事,再加上荒唐的解说。这样的需求有没有?当然会有,甚至会有很多,但读这种读物的读者,大多也都知道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他们只是把它当作“故事会”来读,这只是一种娱乐性的消遣。
真正想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通常都希望能够看到专业研究者写出的严谨的历史书,而且也只有专业的研究者才能写出适合社会大众的历史读物。再说,从理论上讲,专业的研究者,本来就都是干这种事儿的人,他们就是靠给社会提供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写的这些东西,绝大多数,社会大众根本看不懂。
真心关心历史的社会大众,他们所需要的历史读物,只能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来写,也必须要由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来写,而他们写出来的东西社会大众往往看不懂。好了,问题就这样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的“社会大众需要怎样的历史读物”这一问题,就从这里说起。
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问题倒过来看,即主要不是来探寻社会大众为啥看不懂,而是和大家说一说专业的研究者为啥不努力去写一些社会大众看得懂的东西。
首先,专家们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和实质性内容应该是深入探讨学术问题。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专家们所探讨的这些问题,难免生僻;他们的表述形式也要力求学术的精准性和规范性。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或者说是社会大众对专家学者的期望与想象,实际情况却与此有很大出入,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真正深入、严谨的学术探讨永远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骨干,很大一部分研究者只是用行业内通行的规范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无可非议,而且还要予以高度的肯定与赞扬。我把这样的研究和表述形式,称之为经典的学院式的范式。因为对于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做这样的工作,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社会大众对他们的研究,应该是只求其深,不厌其深。事实上也就是这样。
问题是这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真的那么富有学术意义么?实际情况,同社会公众头脑中看似理所当然的印象有着很大的差距。
在我比较熟悉的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我估计,至少不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所谓研究论著,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这些论著,或毫无新见,甚至读者(这指的是行业内部的专业读者)完全弄不懂作者到底是想说些什么;或粗疏不堪,根本不值一读;或所做论证缺乏最基本的史料基础,任意信口开河,等等。这类以“学术论著”面目出现的东西,实质上等同于垃圾,按照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说法,是“大便纸(指擦屁股的手纸),多几个字”。这样的东西,不仅对学术研究无益,而且还很有害;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基本判别能力的社会公众,为害尤其严重。
那么,剩下的那一半呢?这剩下的一半左右“学术论著”,其中还要有一半左右,也就是大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圈内,是很高大上的,甚至可以说是时下学术圈里那些顶端名流所极力表彰的前沿性成果,是他们所极力引领的学术新潮流、新方向,可是恕我无能,云里雾里的,玄乎得很,根本看不懂,因而也就完全无法领略其意义与价值。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责任:首先我就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因而始终弄不懂历史学研究的章法是什么;其次是自己先天素质低,思维方式太“滥污”,总也想不明白人家怎么就从这儿跳到那儿去了,总也看不明白人家得出那些高大上观点的依据是什么,所以也就怎么看也看不明白。不过我毕竟也在这个圈子边上混迹大半辈子了,好歹也混了个教授、博导的头衔了,要是我都看不懂,那么,对于所谓“社会大众”,当然也就更没有意义了,除非你特别崇拜某某著名教授。因为崇拜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当然也不需要看得懂你崇拜的名流讲得有没有道理,膜拜就是了,但那只是个别人针对特定对象的特例。所以,这类著述,我们在谈论社会大众的历史读物时,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活动现场
大家别听我这么一讲就以为研究历史的专家学者都是光吃干饭不干活儿的混子了,那不还剩下有四分之一的人么。你要是想想中国一年毕业多少历史学博士就会明白,这剩下的四分之一历史学者,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话说到这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夸脱历史学者同大众阅读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是这些历史研究者愿不愿意撰著大众读物。在这一方面,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学者,是他就根本不想撰写任何形式的著述。这类学者虽然人数不多,但都是真心喜欢历史、琢磨历史的人。他们的书只是给自己读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人生,提高自己的素养。你只能有幸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谈得来,他们才会同你聊对历史的见解,向你侃对历史的认知。总的来说,就我们谈论的这个论题而言,这个类型的学者,基本上等同于不存在,我们只是向他们致敬就好了。
第二种类型的学者,在这一夸脱学者中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只想遵循学院式的路径,一板一眼地干好自己的活儿,把问题研究得真真切切。这都是些真学者,写出来的也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至于社会大众看懂看不懂、爱看不爱看,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都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和兴致。但不管你看懂还是看不懂、爱看或是不爱看,你都要知道,若是没有这些研究,也就不会撰写出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读物,不管是谁都写不出来。这些专门的学术研究,是各种大众历史读物的渊源和土壤。
第三种类型的学者,他们既潜心去做深入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愿意并且也能够撰著面向社会大众的历史读物。这类学者,当然数量不是很大。这里面既有个人的喜好和能力问题,更有管理体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后者,只能说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但若是稍微仔细想想,就可以说,道理,你懂的。就学者个人而言,恐怕只有极个别人会不做其他专题研究而一心一意地去为社会大众撰写历史读物;而且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这样做也不会做得很好。原因,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所谓学院式的研究,是撰著大众读物的基础。
眼前的情景,就是这样:在庞大的研究群体当中,实际上只有很少很少一小部分学者,愿意并且能够分出部分精力来为社会大众撰写历史读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一小撮学者选择什么问题做研究——他们研究些什么,社会大众就能看到什么样的历史读物;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们若是多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主体、即社会大众需要怎样的历史读物,社会大众就能读到更多适合自己的历史读物。
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生活千头万绪,历史同样万象千般。但我们研究历史,有一个看似浅显却又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需要高度注意——这就是所谓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大家不要以为这话很简单,太大白话了,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复杂,更有很深邃的历史内涵。
社会大众对历史的关注,往往会聚焦于那些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或是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乐于去阅读这些人物的传记或是其他那些性质、形式与其相通相近的著述。在我看来,人物传记或是以人物关系为核心的历史故事,就是最被社会大众需要、也广受社会大众欢迎的历史读物。
可是,在历史学者的专业领域内,大多数专家却对撰著历史人物传记或是讲述历史故事抱持一种轻蔑的态度。大多数专家学者们更关注那些抽象的问题,更在意解释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在机理,至少也是考述那些制度性问题。
不过这只是当今史学界的状况,中国古代学人治史的传统却不是这样,中国古代位居魁首的史学家司马迁就特别重视人物传记。司马迁撰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本纪和列传,是这种纪传体史书的核心构件,本纪承自《春秋》之类的编年体史书,而列传这种体裁则是司马迁的伟大创建。所谓列传,基本上就是人物的传记。司马迁选取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为他们撰写传记。以后历朝历代所谓正史,也都是沿用这种纪传体裁。这也就意味着自从司马迁撰著《史记》之后,中国历史记述的核心,就一直是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若是再进一步区分一下,司马迁著《史记》,这是在记述历史,也就是书写历史,而现在像我这样的大多数历史学者只是在研究历史,再现历史。写历史既然都以人物的命运为核心了,研究历史就更应该重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那些代表性人物;特别是我们若是能够注意到上面讲的这一重大史实,就会很具体、很实在地理解,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关注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并不是迎合非专业读者、也就是所谓社会大众的“低俗”趣味,历史人物本来就应该成为我们吃这碗饭的人最重要、最核心的研究对象。
这样,我们就在内在实质上找到了专业治史者同社会大众读史需求的重大契合点;若是从历史读物出发来看待这样的认识的话,这等于大大拉近了作者同读者的距离,让他们彼此之间贴得很近很近。若是有更多的学者像我一样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学者们有没有能力做好这样的研究以及他们是不是能够很好地表述自己研究的问题了。
以具体的人物为核心来研究历史,并不妨碍其他各个方面历史问题的研究,反而还会带动相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这是因为所有人类社会的问题,都是由具体的人造就的,都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此人同彼人的差异性,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还有伴随着时代进展所不断发生的蜕变和演化,使得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特质,这些又都不是抽象的模式所能概括的,也不是呆板的制度设置所能规范的。
一个人一个样,一件事儿一个理儿。对于我来说,研究历史的目的正是基于一般的社会背景来阐释这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儿,而不是相反,不是要把每一位具体人物所参与的具体史事概括或是抽象成为一个干巴巴而又玄乎乎的“定理”。
每一个学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一个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内涵也都各不相同,具体怎样研究、怎样表述各个历史人物,当然也不会千篇一律。最好雅俗共赏,一举两得,但若是一时做不到,也不妨先撰写给专业同行看的学院式论著,在这样的基础上再专门来为社会大众写历史读物。
今天我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谈论我对社会大众所需求历史读物的看法,很大程度上缘于几年前三联书店张龙先生约请我撰写并帮助我出版的《海昏侯刘贺》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这样一本面向更多读者的历史读物。虽然这本书做得并不很好,但广大社会公众对我这一尝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这鼓励我进一步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并在继续从事深入学术探讨的同时,尽可能地用更多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表述我的认识。
谈到社会大众所需求的历史读物,在我看来,仅次于历史人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专业历史学者应该及时响应社会大众对重大考古发现以及其他重要文物的关切。
连续多少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土木工程建设,到处热气腾腾,再加上盗墓贼趁火打劫,地下宝物层出不穷。这不仅引得考古学家和一些历史学者大喜若狂,也激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兴趣。另一方面,博物馆里,收藏家手中,还有无数以往发掘出土的或是世代传承下来的重要文物,社会大众同样十分关切。我想稍微看过一些考古新发现和其他古代文物展出的朋友,大多数人都会很不满足。因为主事者对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物展出普遍缺乏深入的解说。不管是历史背景,还是某一文物的来龙去脉,大多都太简单,太含混,甚至充满了各色各样的谬误。
这种局面,给专业的历史学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人们热切地期望学者们能够及时对相关考古发现和那些重要文物做出深入的阐释,写出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历史读物。但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这对很多很多学者、甚至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恐怕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然很多所谓学者不会像我这么坦诚,他们会努力装出很不屑的样子;特别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分之一左右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很高大上学者,更是如此。但这不过是声张声势以掩饰其空虚无能而已。因为这样的事儿做起来实在很不容易,既需要很广博的知识储备,同时还需要很敏锐的学术眼光。要有条件看出问题,还要有能力解析问题。这用一句更形象的话来讲,就是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只会说大话,是翻不过去这座山,也越不过那条水的。
就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现状而言,要想一时间做好这样的研究,确实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这实际上带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专家学者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难道社会大众的热切关注点,不正应该是我们需要努力从事探索的问题么?至少我愿意努力来做一些相关的工作,而不是抽身回避。事实上刚才我提到的拙著《海昏侯刘贺》以及后续的《海昏侯新论》,就是由于考古工作者发现刘贺墓室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人们也迫切希望历史学者能够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我才努力写出这些著述的。
如果再举述一个社会大众所关注的历史知识领域的话,我想就应该数到衣食住行之类的社会生活史知识了。这方面内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同上面谈到的考古、文物研究具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做过很多工作,但实际的成果,仍然相当薄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内容资料的分散性,是缘于很多知识的专门性。总的来说,学术界已有的积累,还不足以给社会大众提供出较多合格的历史读物。

《海昏侯刘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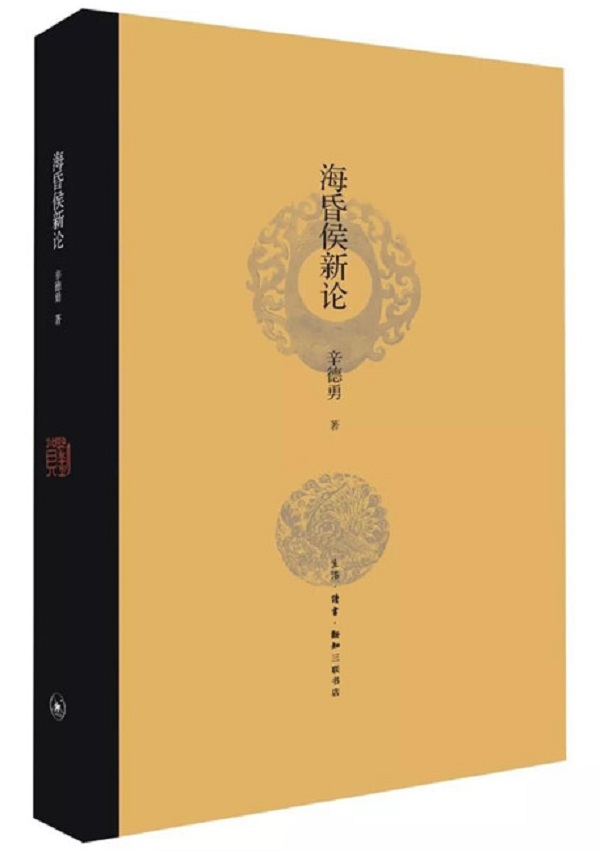
《海昏侯新论》
听我这么一讲,我们很多非专业的朋友可能觉得有些意外,但这就是我看到的实际情况。尽管作为一名职业的历史学者这有些窘,但我只能实话实说。
在这一方面,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做出很多研究,但我写过的一些版刻史、印刷史的论著,比如《中国印刷史研究》等,大致也可以算作这一范畴之内。只是其表述形式还过于专门,过于学院式。希望以后能抽出时间,写出稍微大众化一些的书籍。其他如去年我结合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教学,对中国古代面食品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近些年来对中国古代的金石铭文和天文历法知识,更写出一批文稿。这些文稿,都不同程度地在主观上做了更适合普通读者的表述。最近三联书店帮助我出版的《辛德勇读书随笔集》里,就收录了一些这类文稿。像《天文与历法》这一分册里对二十四节气的考述,就与通行的历史读物,有很大不同,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为准确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事实上这一整套《辛德勇读书随笔集》,其文章撰述形式,都贯穿着使更多社会大众易于接受的思考。
当然在社会生活史这一广阔领域之中也有一些分支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学术基础,可还有另外一重因素,限制着大众读物的出版——这就是文字表述的问题。
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写给社会大众的历史读物,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字能力是天生的,而后天努力能够提升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能有更有才华、更适合的学者当然更好,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在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更为迫切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看到,社会大众是很宽容的,并不一定会对历史学者的表述形式和文字技巧提出更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从另一角度看,社会大众需求的历史读物,也是可以划分出不同层次。这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历史读物表述形式和文字技巧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今天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大学本科以上的非历史专业人士,在我们谈论的这个“社会大众”群中是占据了很大很大一个比重的,只要主题喜欢,这些读者可能更在意历史读物的实质性内容,而不一定首先关注其表述形式。在我看来,很多理工农医专业的历史爱好者,理解和接受的能力是很强的,只要历史学者在文字形式上稍稍用心做出一些努力,这些读者都是能够很好地接受和理解的,关键还是要有实质性内容。
至于内容和形式都很完美的历史读物,它的大量涌现,那是一个社会问题——出版业只要充分市场化,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