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村上春树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反思
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中讲述过这么一件事:二战结束后,一家日本公司的总裁自杀谢罪,叙述者“我”和朋友三宅就此事讨论起来。三宅说:“我们总裁似乎觉得要为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负责。两个元老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但总裁显然觉得这还不够。他的行动是代表我们向战争中遇害的家庭谢罪。”
因为总裁的自杀,“公司上下如释重负。”他们“现在觉得可以忘记过去的罪行,展望未来了。”讽刺的是,“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结果反倒是我们总裁那样的人慨然赴死。许多人又恢复到他们在战争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战争罪犯好不了多少。”

《浮世画家》
这是一个暧昧的悲剧。试想一下,当总裁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公司的其他高管和员工是什么心情呢?悲伤是表层,但透过石黑一雄的叙述,悲伤里还有一丝庆幸,因为在他们眼里:总裁的死犹如一个象征,是集体对过去罪行的交代。好像总裁一死,集体的罪责就洗清似的,其他人都能因此赦免,面向未来。如此就出现了一种心理——参与到战争的人们倘若失败,就希望有人代表他们去死。而他们将很乐意地进行哀悼。那么,这种忏悔是否严肃呢?其中是否存在伪善、侥幸的成分?
恐怕,追问其是否严肃是自讨苦吃,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严肃是肉体为掩盖灵魂缺陷而做出的一种虚伪姿态。如果严肃不应当适合这个定义,如果严肃的意思应当是注重实际的严肃态度,那么这整个规定就会失去意义。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在马克思看来,与其严肃,不如“认真”,不必强调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严肃还是轻薄,应当直击它的实质,那个真的部分。是什么,便指出什么。而在《浮世画家》所描绘的这个场景中,与其说公司的领导、员工们深感自己在战争中负的责任,不如说他们希望有一个象征物,好让自己与过去划清界限,从残酷真实的历史中脱逃,好活在自己的安稳之中。显然,总裁之死成为了这个象征物。真正忏悔的人死了,历史依然被生者规避。
在《浮世画家》中,这样的忏悔并不少见,这是一本直面二战创伤的小说,石黑一雄在小说里主要处理两个问题:经历且参与二战的人该如何自处;战后的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反映在主人公小野身上。他在战时通过作画推崇军国主义,成为社会红人。战后却因军国主义的清算浪潮而倍感自责。他曾相信自己的国家做着正确的事,而他作为国家一员,理所应当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战争的失败和日本政府所犯下的累累罪行让他无法视而不见,这一矛盾成为小说的张力来源之一,而石黑一雄在日后也重复了这种“荒谬”,《长日留痕》中的英国管家就是例子。1949年,当小野先生拜访故人佐藤博士时,他说:“当时我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做事的。我满心相信我是在为我的同胞们谋福利。可是您看到了,我现在坦然承认我错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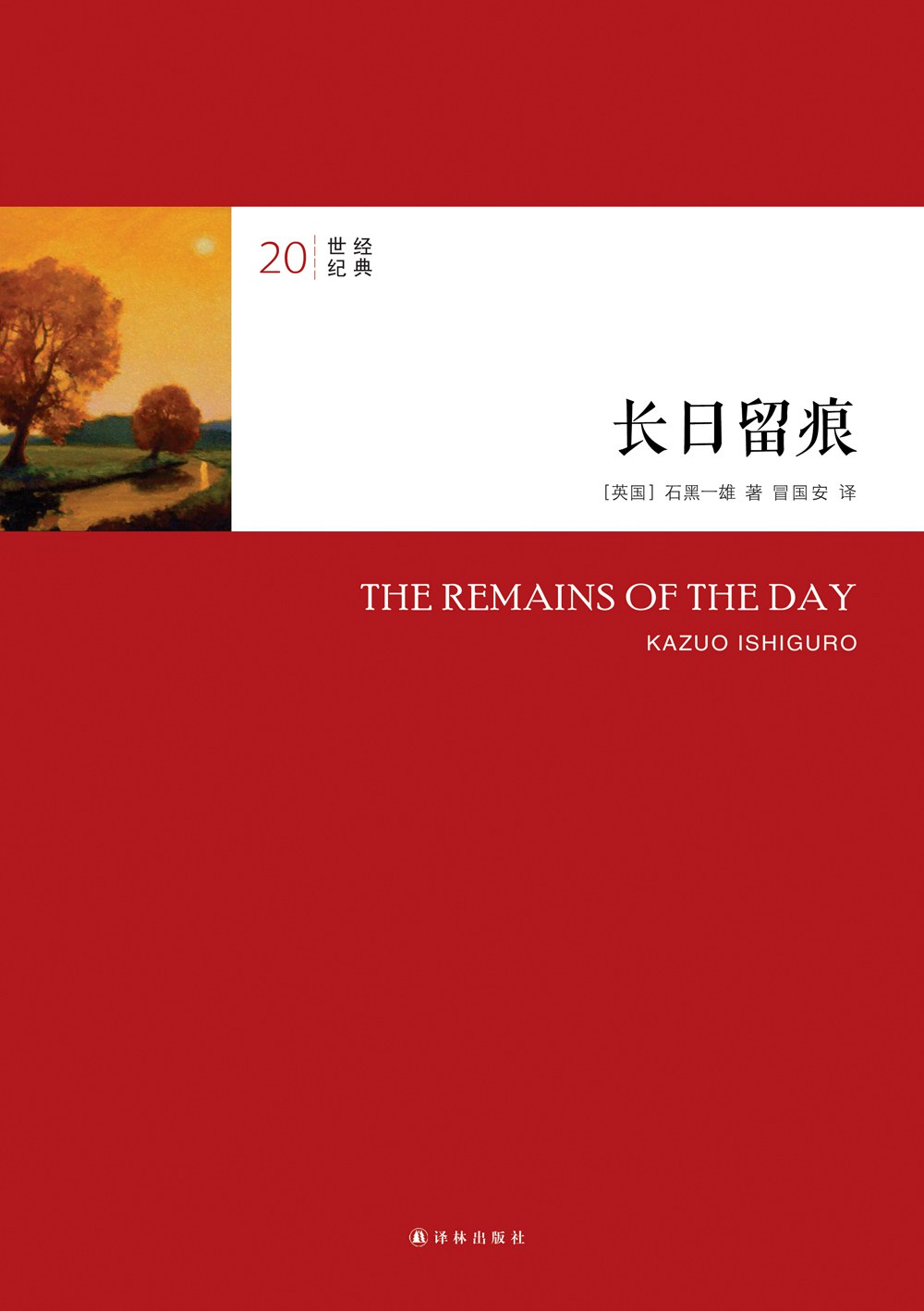
《长日留痕》
而第二个问题则贯穿整部小说。宫本武藏、美国的牛仔、乌龟象征着不同的价值选择,画家小野在与朋友松田的对话中,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松田说:“事实上,在这样的时期,当周围人民越来越穷,孩子们越来越饥饿、病弱,一个画家躲在象牙塔里精益求精地画艺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落在贪婪的商人和软弱的政客手上,这样的人会让贫困日益加剧。除非,我们新生的一代采取行动。但我不是政治家,我关心的是艺术,是你这样的画家。有才华的画家,还没有被你那个封闭的小世界永远地蒙蔽双眼。”
无独有偶,在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中,战后成长的主人公同样对二战进行了追溯。村上春树以画、洞穴、骑士团长为线索,展现出一位老年画家与记忆伤痕的博弈。忏悔再次成为重点所在。
《刺杀骑士团长》的故事可以这样梗概:主人公“我”是一位36岁的职业肖像画家,他遭遇婚姻危机,心情低落之下决定离家出走,寄居好友父亲的老宅,也就是《刺杀骑士团长》作者雨田具彦的旧画室。主人公后来发现这部画作,继而遭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事件,神奇地进入洞穴,在历史、现实与幻境之间,回顾了自己和画家生命中的重要事件,进行了一次意念上的时空穿梭,最终实现精神救赎。
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围绕着“老画家”的故事尤其值得注意。“老画家”的故事集中出现在小说第二部分,骑士团长告诉“我”:老画家的一个弟弟曾参与中日战争,他曾被迫砍掉三名俘虏的脑袋,这让他从战线撤回国内后却羞愧自杀。而老画家则在维也纳参加过一次针对纳粹的暗杀行动,画中的骑士团长,原型可能正是这次行动中的某位纳粹军官。通过老画家之子的描述,我们发现:老画家是一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格格不入。老画家一直因为弟弟因战争中的死亡而耿耿于怀,更为自己的苟且偷生感到内疚,他一生最后的心愿,就是再现“刺杀骑士团长”的场景,弥补他没有刺死那位纳粹军官的遗憾。他将自己无法完成的刺杀纳粹军官的心愿寄托在画里,将自己生命的救赎托付于“刺杀骑士团长”这一行动。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为何夹杂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尽管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在小说中只占十几页的篇幅,但这部分内容绝非可有可无。村上春树借人物之口问的:“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和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这句话直指日本右翼政府的软肋,后者一直有意在报告中减少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可是,即便是死10万人,难得就不是屠杀了么?他们犯下的罪行就可以被谅解吗?显然,日本当局的说辞经不起推敲。

《奇鸟行状录》
村上春树是一位坚定的反战派,从《奇鸟行状录》到《刺杀骑士团长》,他都对日本右翼以正义之名发起的战争展开过批评。在《刺杀骑士团长》中,村上借战后成长的主人公对老年画家的追寻,揭开了二战对个体及民族造成的心灵负担。和艺术家宫崎骏类似,村上并没有回避自己的国家在历史上的污点记录,他在作品中主动“旧事重提”,为的不只是和部分日本人的虚无史观作斗争,也是要追溯日本人近代以来的精神史。从昭和男儿的热血沸腾,到太阳族的反叛传统,再到九十年代经济危机后相对平缓的“低欲望社会”,大和民族的状态变化绝非一日而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村上写过去,也是在和今天做比较,低欲望的、轻飘飘的新日本世代常常被人批判,可是那个热血沸腾的日本,真的就值得旧梦重温吗?村上警惕的是:在那片热血之中,翻滚的往往是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之血。

《刺杀骑士团长》
所以在长篇散文《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中,村上再度提起侵华旧事,通过书写父亲如何被强征入伍、参与中日战争,表现出战争对个体造成的不可磨灭的创伤。文中提及,“我”的父亲被分配到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连队,“作为辎重兵,被这样送到了血雨腥风的中国大陆战场”,“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杀人的事情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命令新兵和预备兵去处死抓捕的中国士兵非常常见……杀害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当然是违反国际法和不人道的行为。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根本没有人对此有所考虑。父亲说,从1938年开始到1939年,作为新兵的自己刚刚来到中国大陆,一个下级士兵即使被强迫做很多杀害俘虏的行为,也完全不是奇怪的事。父亲后来回忆说,士兵开始是用枪上的刺刀杀死俘虏,后来是用军刀残杀。”(村上春树:《扔猫,关于父亲我想说的话》)
村上的父亲曾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村上的童年里,父亲经常去参拜佛像,面对一个小玻璃盒子念经,“他说,你知道我是为了谁念经么?我是为了很多此前战争中的死难者。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是的我的战友,还有作为‘敌方’死去的中国士兵”。村上坦言:“用军刀砍掉人脑袋的残忍情景毫无疑问强烈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
通过这篇文章,村上重申了自己的反战立场。更进一步,他希望探讨在战争年代,国家机器如何煽动意识形态,并采用强制手段造就一幕幕杀戮,使民众成为冰冷的杀人工具。当悲剧发生后,当事人试图通过暧昧的态度来逃避历史责任,以看似中立的观点模糊是非,但恰恰是这种暧昧,导致暴行的重复成为可能。
相比起村上,石黑一雄在《浮世画家》里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军政府进行了更为辛辣的讽刺,这在小说人物池田的话里可见一斑。池田说:“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