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系统论法理学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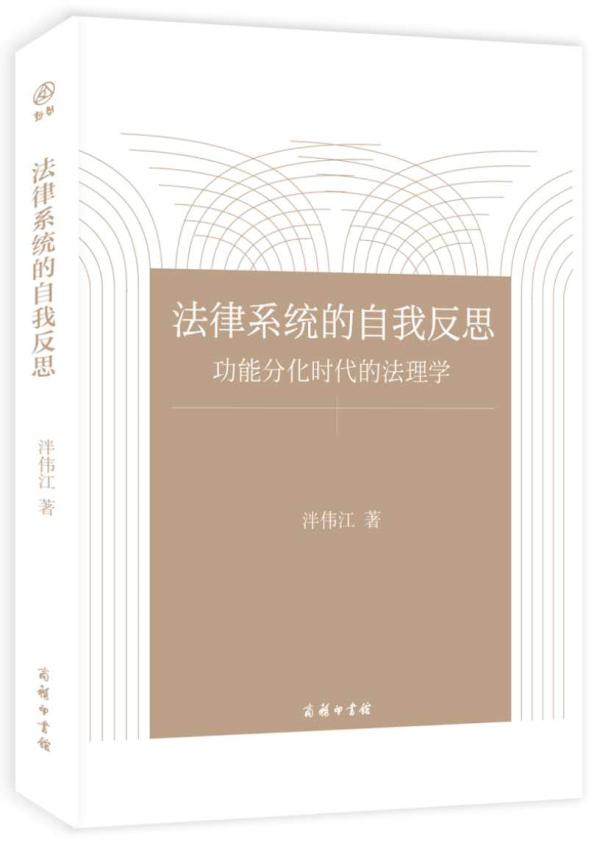
零、系统论的两岸之旅
几个月前,我接到泮伟江老师的邀请,为他的论文集《法律系统的自我反思——功能分化时代的法理学》作序,泮老师是中国法学界年轻一辈中研究系统论的佼佼者,能够有机会为他的系统论论文集作序,对我而言是很荣幸的事。
五年前,我受北航大法学院的邀请,出席一场讨论“部门宪法学”的高端论坛,首度与泮老师见面,可惜当时没有机会交换意见,这几年,在一些研讨会上,我有缘与泮老师见面几次,由于同为系统论的爱好者,自然而然就聊起来了,当时得知,泮老师正在翻译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社会的社会》一书,倍感钦佩,非常期待卢曼这部大作的中译本问世。跟泮老师几次闲聊有很大的收获,除了经典人物卢曼的思想之外,我们也针对另一位知名的德国系统论者贡塔·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交换心得。泮老师并引介我认识几位中国当前的系统论研究者,这让我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喜,原来,在海峡彼岸,有不少系统论同好,正在如火如荼地深入系统论的迷宫,而且发掘出越来越多的宝藏。
我本身的专业领域是法理学与宪法学,然而作为系统论的爱好者,一二十年来,我因缘际会地撰写了不少篇系统论的学术论文,几年前原本有出版计划,但是总觉得在系统论的理解上仍不够成熟,因此仍有所保留,论文已经集结,出版计划仍未启动,得知泮老师将出版他对于系统论的一系列基础与运用的研究,不由得产生一睹为快的欣喜,尤其是他行文流畅,可以使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来阐释并发扬卢曼的思想,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学术功力。
我最早接触卢曼的著作是在1987年,当时我仍是就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的本科生,选修了台湾大学国发所张志铭老师开授的“法理论与法社会学”课程,虽然对于古典社会学理论我已经有几分掌握,但是从来没有听过卢曼,不清楚他在当代德国社会学界的经典地位,更不知道他理论的抽象难懂,于是天天拿着卢曼的法社会学成名作之一《法社会学》的英译本(1985年甫译出),土法炼钢地啃了一个学期仍如堕五里雾中。由于有了这个痛苦的阅读经验,当我1993年负笈德国慕尼黑大学就读博士班时,就下定决心,在留学期间一定要以阅读德文原典的方式,好好地研究系统论一番。当时适逢卢曼退休后,在1993年冬季学期,于慕尼黑大学做了一系列系统论的演讲,并掀起了慕尼黑大学一阵卢曼热,除了卢曼亲自的演讲之外,慕尼黑大学的社会学系、哲学系与法律学系,都有教授开授了系统论相关课程,求知若渴的我,就如获甘霖般的啜饮着知识的飨宴。当时,在卢曼任教与退休的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有两名台湾地区留学生就读社会学系,并以系统论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客体,他们后来成为台湾社会学界研究卢曼的知名学者:鲁贵显教授与汤志杰教授,除了个别的研究论文之外,他们一起或个别翻译了不少卢曼的重要著作。
卢曼出身法律人,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由于这个求学背景以及担任过公务员的经验,在卢曼的长期研究生涯中,法律或法律系统始终是他关注与探讨的对象,他以自创的系统论为基础撰写了许多有关于法律的著作,就成为法律学者想要一窥究竟的堂奥,而不只在德国法学界如此,在台湾地区法学界或是我所知道的日本法学界、韩国法学界亦然。在2012年,政治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们曾自组了一个读书会,以一个学期时间阅读与讨论卢曼晚期探讨法律的经典著作《社会中的法》,我亦以客宾的身份,受邀进行了三次导读。即使许多法律学者或学生对于卢曼的理论有兴趣,由于入门的门槛很高,在台湾能够持续关注与研究卢曼著作的学者,多年来仍旧寥寥无几,也没有形成卢曼研究学群,所以当我认识泮老师以及当代中国鲁曼研究学群时,有着他乡遇故知的欢喜。
一、系统论作为认识世界的迷宫
系统论的难以入门,即使在德国亦是学界家喻户晓之事,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德国社会学家,有如此多学者为其思想与理论做引介与批注,持续几十年的卢曼学,已经蔚为学术奇观,而且仍在持续当中。然而,即使有二手导引书作前导,无论从卢曼的任何一本原典入手,都会遭遇到如迷宫般的概念与命题,卢曼带读者进入他思想世界的方式,就是先让你跟先入为主之见保持距离,先疏离,再理解!所以要读懂系统论,就必须以系统论的方式,才有办法,这是着重系统自我指涉的系统论,对于读者的要求。这意味着,无论你以哪里做起点,当你的思想循环进行次数已经够多,你已经逐渐熟悉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思考方式,你就有机会以你的方式进入卢曼的理论。作为读者,你在卢曼这本著作里无法理解的某个观念,可能你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里会豁然开朗。
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同门师兄,同样在战后德国公法学重镇彼得·雷尔谢(Peter Lerche)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现在是当代德国青壮派公法学者的奥利佛·雷普西斯(Oliver Lepsius)教授,对于卢曼系统论的看法与我不同,我曾经跟他谈及卢曼著作的艰涩难懂,他告诉我,一个人的著作,如果你阅读了三次还是不能理解,那就是作者的问题了,他甚至还曾经写过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论文,试图说理证成“卢曼系统论抵触德国基本法(宪法)”的命题。或许雷普西斯教授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对于卢曼的系统论而言,恐怕必须另当别论。我从来不觉得读不懂卢曼是卢曼的问题,对于一个高复杂性并具有说明一切企图心的理论,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研读与理解,乃自明之理。泮老师让我非常欣赏的地方,就是他能够非常踏实的阅读卢曼的经典,能深入浅出使用容易理解的表述方式,来阐释卢曼的基本构想,并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的语境,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历史是很好的筛选机制,滚滚长江东逝水,浪淘尽多少英雄人物,真正深刻的思想,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益愈展现其对于世界的洞察力,即使同一时代的人多所不解或是有所误解。卢曼的系统论,正是一个这样的理论,从他初期以“开放系统”为典范建立其系统论以来,中间经过“自我指涉系统”与“自我再制系统”(“自创生系统”)的典范转移,跨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二十年,迄今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作为社会学家的卢曼在德国哲学界曾经被誉为二十世纪的黑格尔,卢曼在德国的重要论敌哈贝马斯,虽然跟他有过激烈的论战,却持续受到他的理论发展所影响,甚至在卢曼过世前,还曾经称誉卢曼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卢曼的门生或是继受他思想的学者,无论在他生前或是过世之后,都将他的理论以各自的方式发扬光大,即使是以卢曼可能不会赞同的方式,其中,德国国际私法学者暨法社会学家托依布纳,对于卢曼思想的批判性继受就是一个著例,他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为主的一些学者,就企图建立所谓的批判系统论,他们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至少就托依布纳的理论而言,对于卢曼系统论的偏离,虽然扩展了系统论对于法的观察与描述,将其延伸到全球法与跨国法的领域,然而其副作用可能是理论严格性的降低,以及理论不一致性的增强,在这一点上,我与泮老师所见略同。
二、系统论与法学研究
系统论首重更好地说明现代社会,而非批判或改革,对于现状的描述与说明经常被解读成为现状辩护,这固然是一个误解,却是一个以科学性为职志的理论典范必须承担的批评。问题是,虽然以对于社会现实具有更高程度的说明力为其任务,但是系统论并没有主张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它毋宁是承袭了社会学诞生以来的传统,以社会现实的揭露为其目标,此即社会学批判性格的展现。就此而言,即使将主要任务设定在更佳的说明社会现实,并不会直接让一个理论成为保守与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认真对待真理/真实,对于真实的认识,毋宁是古希腊时代以降哲学的主要关怀,也是当代社会科学(学术)系统的社会功能。既然认识真实是学术沟通的功能,同样履行此一功能的系统论为何会被不少学者,尤其是左派学者认为具有保守性格?除了过快的(短路的)以右派/左派的区分来观察它之外,并使用保守/进步的区分来观察它,将其标示为保守的社会理论。对此,系统论可以反驳说,在科学(学术)系统中,真理/非真理的区分才是重点,远比保守/进步的区分更为重要,如果没有先探究与确认真理,要如何确认批判理论所主张的进步具有真正的基础?
系统论对于法学到底具有何种意涵?系统论对于法律与法学的研究属于法学吗?是许多法律学者深感兴趣的问题。系统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典范,主要的任务在于探求社会真实,与一般所理解的法学,其任务主要在于解释法律,并提出有关于法规范内容的主张,两者之间,不但学科性质回异,而且属于不同社会系统的沟通网络,前者属于科学系统的沟通,后者属于法律系统的沟通,基于社会系统自我再制的运作封闭性,两者在运作层面上相互分离,那么“系统论法学”如何可能?“系统论法理学”如何可能?泮老师的这本论文集,就是在理论层面上,以系统论的论述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响应。
如果暂时将目光转向德国,卢曼早期著作《基本权作为制度》,主张基本权利的功能,在于防止各个社会系统过度扩张侵犯其他系统的界线,就在德国法学界引起广大回响,学者纷纷从这个角度审视基本权的功能与任务;其另外一本早期名著《透过程序的正当性》,亦成为当时德国法学界探讨法律程序面向的重要参考,甚至卢曼一本讨论法释义学功能的小书《法律系统与法教义学》亦是德国法学界探究法教义学性质与任务时,无法忽略的一本专著。在卢曼进行“自我再制”的典范转向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并没有引起德国法学界较大的回响与继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 年代期间,其他的系统论学者,包含黑幕特·魏尔克(Helmut Willke)与托依布纳在内,与卢曼进行了一场有关于法律调控(Steuerung)的论战,开启了“自我再制”典范下的系统论如何响应传统的法律工具论或是法律社会工程学的讨论。1990 年代之后,托伊布纳在越加回归到“自我再制”典范的同时,开启了一些有关于法全球化的讨论,试图响应全球层面上法律的新多元主义与法的片段化(条块化)发展,除了在全球法层面建立一种系统冲突论之外,托伊布纳提出所谓的柔性的冲突法则以作为解决方法,这方面的努力暂时总结在托伊布纳与其学生费雪–雷斯卡诺(Fischer-Lescano)合著的《体制冲突》一书。其后,托伊布纳对于全球法的探索并没有止步,不但将全球法与“住民法”的冲突纳入考虑,还以系统论为基础,重新诠释并建立新的“社会立宪主义”。除此之外,系统论对于德国1995 年以来的新行政法发展,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最后新行政法学所依据是政治学领域发展出来的调控理论,但是系统论作为一个相竞争的理论典范,仍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形构基础,争议点就在于:法律有否可能成为社会调控的工具?这个问题当然必须先回到一个基本层面,先确定法律系统的功能才有可能回答。无论德国法学界对于卢曼系统论的运用成功与否,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卢曼系统论半个世纪以来对于德国法学的影响。
可见,想要在法学中引用或结合卢曼系统论的洞见,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出现在德国法学的论述之中,并引发了支持与反对阵营的论争。然而,关键点还是在,这样一种跨学科的尝试,是否建立在一个合理并可行的基础上?以及,具体的成果是否具有说服力以及是否在某个程度上能够被正当化?泮老师在这本论文集的相关论文,走在同一个方向上,在理论上同样必须面临社会系统的运作封闭性,必须解决法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沟通的系统指涉问题,如果采取泮老师的用语,就是必须同时面对法理学的实践性与科学性的问题。纯就系统论而言,其系统指涉并无疑义,系统论作为社会学理论归属于科学系统,在系统论的观点中,法理学作为法律系统的自我描述,在法律系统内反思着法律系统的一体性、功能、自主性等等议题,即使自我描述有别于法律系统内一般的自我观察,并不在将个别的运作归列为系统内的结构或运作,但是作为自我描述的法理学仍然归属于法律系统。于是“系统论法理学”无法回避其定性的问题,到底“系统论法理学”是系统论(异观察)还是法理学(自观察)呢?抑或存在着的三种可能性,一种连结异观察于自观察的法理学?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回归到系统论的主轴,系统指涉的基本问题还是有必要解决。
三、系统论法学的建立与展望
泮老师对于系统论的研究相当扎实,而且着力甚深,从他在论文集里所收录的著作就足资明证,泮老师对于卢曼使用的概念术语、卢曼的理论架构、卢曼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有很好的掌握与理解,这也是泮老师有能力翻译卢曼《社会的社会》的重要条件。作为一位当代中国法理学家,泮老师的角色定位自然不只是作为一个卢曼系统论的引介者,而是一个具有特定问题意识的系统论研究者,如果没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与法治建设的关心,没有对中国法学暨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关怀,泮老师的系统论研究就可能欠缺学术活动最重要的活水源头,因为学术活动虽然必须深植于但是并不能仅止于正确的经典导读,而必须能够解释与说明所处的社会,并尝试处理所处社会遭遇的问题,无论是在总体社会层面、特定社会层面,还在特定学术领域,这些问题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客体,同时是学术研究的视域。套一句二十世纪德国经典哲学诠释学家迦达默(Hans- Georg Gadamer)的话,理解同时是解释,解释同时是运用,理解、解释与运用是进行诠释时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以说,泮老师这本论文集里的文章,就是将系统论运用于观察、说明,甚至解构当代中国法学各个相关问题的学术努力。泮老师学术对话的对象,不但是同为系统论研究者的其他教授,还包含中国法理学界多所探讨的各种当代法理学流派,例如英美法理学的主流,以哈特为主的分析法实证主义、德沃金的诠释性法理论,还有德国法理学思潮,无论是法学方法论与法律诠释学,或是批判理论宗师哈伯玛斯的理论。此外,由于置身于中国法学界之中,泮老师早就处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以及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的论辩场域。泮老师所采取的系统论研究观点,恰恰是一个可以响应各个论辩的第三种取径,在多面向的对话中,为“系统论法学”一步一步奠立基础。
当然,一个以“自我再制系统”(“自创生系统”)为典范的“系统论法学”,已经预设了所处社会的主要分化形式,已然从阶层化分化演化至功能分化,在世界社会的层面上,这个默认固然没有问题,然而如果是以中国社会为讨论的语境与研究客体,就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加着墨。泮老师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理论与其置身社会的问题,而是观察到中国仍处在转型期,尚未进入真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然而如此一来,是否能够采用立基于“自我再制系统”(“自创生系统”)典范所发展出来的各种观点,来解决中国法治与社会的诸多问题,就有更多探讨的空间。例如,为了调解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之争,以系统论的观点指出,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结构耦合形式,以及宪法因法政系统功能分化所具有的两面性,在论述十分精彩,并能精确地掌握卢曼的想法,然而是否能够运用在尚未达到功能分化的社会,就是一个理论上有待更多说明的难题,然而理论难题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失败,反而是理论向上一着发展的契机,系统论既然具有说明一切的企图心,迄今为止,对于以现代功能分化社会暨其各个功能系统,开展了强大的说明力,系统论能否用以适切的观察与说明正处于转型期(隘口)的中国社会与法秩序,就成为系统论在中国(法)学界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这样的处境也是所有后卢曼的系统论研究者所必须接受的挑战。立基于卢曼的丰富理论遗产,并对其做创造性的发展与转化,让系统论可以随着世界社会的发展继续展开其强大的说明潜能,不但是系统论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激励系统论者的美好愿景。
将近二十六年前,我坐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大演讲厅,似懂非懂地听着卢曼以北德优雅德文腔调讲述他近三十年的理论努力,告别古老欧洲传统,以真正属于现代社会的语汇来观察与说明现代社会,是卢曼一生的学术志业。即使已经建立了一个偌大而简单华丽的理论建筑,即使已经成一家之言,已经退休的卢曼在娓娓道来时并不骄傲也不坚持,一刹那间,我仿佛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系统论只是卢曼与这个世界游戏的玩具,在他的讲述中,系统论充满着弹性与试探,而非艰涩与固着,系统论充满着冒险的精神,一直在探索这个世界的前沿。二十六年过去了,留下的记忆并非系统论如何有意义的与如何精彩的说明现代社会,反而是卢曼的演说时的神情以及所展现出来的实验精神。
作为一个出身欧洲,并曾经学访美国的社会学家,卢曼已经完成他穷其一生所能做的,“告别古老的欧洲传统”。然而我们要问的是,系统论已经完成了吗?不,系统论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研究方案与计划,我们不应将卢曼的丰富著作视为已经完成的理论建筑,毋宁说它们是卢曼在不同阶段面对现代社会时的观察与描述。两个例子就足以证明系统论是具有发展性的理论计划,其一是,当1980年代卢曼到巴西做了几次学术访问之后,面对与欧美社会相当不一样的巴西社会,卢曼提出一组可以中和掉其他功能系统二元符码的超级符码:“纳入/排除”,才有办法适切的描述与说明巴西的社会现实。其二是,卢曼在《社会中的法》一书最后一章“社会与法”结尾时,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见解,指出我们不能够以为,当前社会如此具有主导性的结构——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将一直持续下去。功能分化对于卢曼而言仅仅是社会演化的产物而已,法律系统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全社会暨其他功能系统对于法律符码正常运作的依赖,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欧洲反常现象,世界社会的继续演化可能会偏离这个形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固然不宜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卢曼的理论成果,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对于系统论研究而言,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参考卢曼的研究成果,以及如何运用卢曼已经发展成熟的概念工具与方法,贴切地观察与描述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件事难度当然很高,但是就是因为难度高才成为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志业,在这一个方向上,泮老师的系统论研究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
泮伟江所著《法律系统的自我反思——功能分化时代的法理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为东吴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张嘉尹所撰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