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徐之凯:恶意之绊——评《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
追溯“恶意”
无论在二战还是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之中,“邪恶”一词都是充斥字里行间却又让人讳莫如深的话语。人们手捧史书思考评论之时,都习惯于将纳粹分子视为道德败坏、毫无人性之徒,如黑洞般敬而远之不屑深究;然而在端笔挥毫,放声阔论这段历史之际,往往也不免暗自滋生这样一种难以抗拒的念头:如何理解驾驶德国战车走上毁灭性道路的这群人?这些曾受过良好教育,深受文化传统熏陶的人怎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人看待昔日纽伦堡的那场惊天审判,与其说是关注于“谁犯下了这些罪行”的法理调查,毋宁说更倾注于“他们为何犯下这些罪行”、“怎能如此丧尽天良”?(第8页)身兼精神病学家的社会历史学者乔尔·迪姆斯代尔,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迎来了一位纽伦堡法庭行刑手带来的文件,开始了对于纳粹战犯“恶意”来源的心理追踪之路。而这一旅途,要从著名心理学家莫莉·哈罗尔对他讲述的纽伦堡战犯罗夏墨迹测试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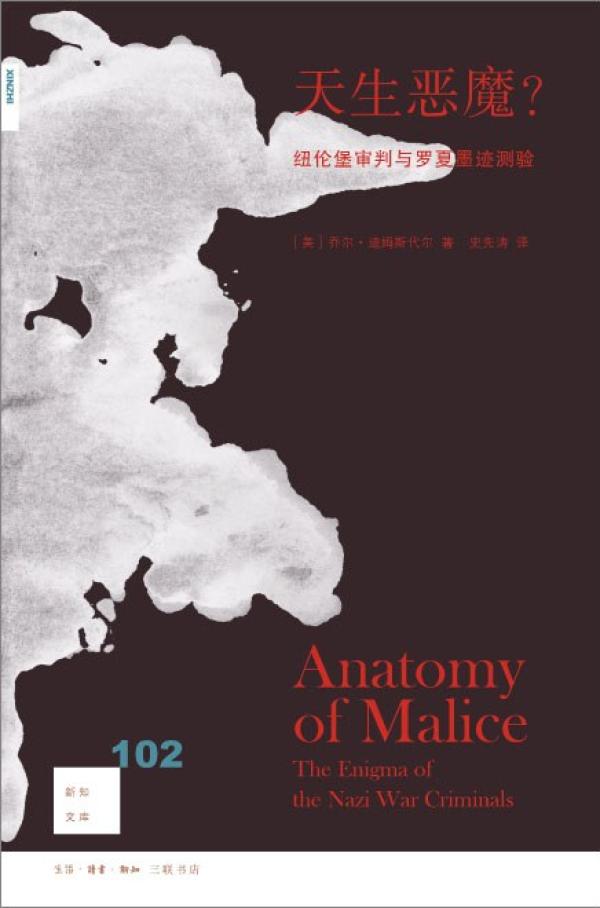
《天生恶魔?纽伦堡审判与罗夏测试》,[美]乔尔·迪姆斯代尔著,史先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出版
1945年5月中旬,卢森堡市奢华的王宫酒店被改造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营垒,盟军代号“垃圾箱”。这里即将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住客——被俘的纳粹高官。他们将跻身于此,并由此走向纽伦堡的法庭,迎来正义的审判。然而这些人前光鲜亮丽的第三帝国显贵,在拘押之中暴露了瘾君子、酗酒者的病态本性。生怕其健康状况危及日后审判的监狱方急于寻求精通药学、擅长药物依赖和心脏病治疗的医生与相应的专业翻译。军医道格拉斯·凯利与军中翻译的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相继应召而来,为这些问题人物受审保驾护航。
然而,这两位专家的到来其实另藏深意。1945年6月11日,纽约一批知名教授致信纽伦堡审判负责人杰克逊大法官,要求“研究”纳粹分子——此时战犯审判远未开始,学术界却已计划解剖这些纳粹领导人的大脑,并明确要求对他们进行罗夏墨迹测试,用十张卡片解读纳粹头目的心理状况。三天后,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要求在纽伦堡设立精神病专家委员会,指出“这场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从法律、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事实和解读整个纳粹领导层,从而让后是相信这些事实。对德国军事、政治和工业领袖的心理状态进行全面科学研究,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77页),并且明确要求团队中必须包括罗夏墨迹测验专家。作为20世纪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学测验方法,此举获杰克逊首肯,以求澄清这些战犯的精神状况,“阻止未来的德国人编造他们是超人的神话”。(78页)于是才华横溢,善于交际的世界著名罗夏墨迹测验专家——甚至还是美国魔术师副主席——精神病医师凯利,与同样有着心理学背景且更具战俘审讯经验的吉尔伯特,开启了乔尔·迪姆斯代尔笔下的历史追溯之旅。
审判“恶意”
1935年,第三帝国议会在纽伦堡通过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开始了罪恶的压迫与屠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后,这座城市成了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战犯的“起点”。这样的矛盾似乎贯穿于这场世纪审判的方方面面:同盟国希望以国际审判破除纳粹战时宣传的“伟人”印象,彰显法治和公正重回德国,却又担心生理情况与精神状态会使罪大恶极之徒免于出庭或逃脱惩罚。通过医学检查和墨迹测验鉴定战犯身心状态之责,落到了两位心理学家身上。但本应秘密合作的两人,却处在争锋相对的竞争之中。这场审判给心理学家提供了罕见的机会,得以在法庭、监狱观察战犯。但凯利和吉尔伯特各有所长,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凯利将自己的职责视为一个有趣的任务,乐于与战犯轻松地打交道,以让自己丰富的医疗、法医病理学经验更加完整。而吉尔伯特则认定这些纳粹战犯是邪恶化身,并不将自己当成翻译,而是作为审讯者对精神道德问题大加挞伐。二者的分歧在对四位战犯典型的心理评估中逐渐展现了出来。
领导“德国劳工阵线”的罗伯特·莱伊有着口吃和酗酒的顽疾,狱中自杀的结局使其成为了盟国学者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所有战犯中,只有莱伊因早早上吊提供了全面细致检查其大脑的机会。鉴于其在一战经历的大脑严重损伤、长期酗酒与遗书中的悔罪,研究人员认为他的邪恶是由病态的大脑驱动的。在他自杀之前,凯利就其墨迹测验情况指出“他绝对忍受着大脑额叶受损所引发的病痛折磨……是最有可能自杀的犯人之一”。吉尔伯特方面,由于莱伊在他到来之后两天就自杀了,因此观察甚少。
与莱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傲慢的“二把手”戈林,其自始至终将自己视为战犯“领袖”,与审判方大唱反调;且与莱伊因悔恨早早自杀相反,他为了羞辱盟国而在处决前一小时吞了氰化物。凯利认为戈林的测试表现出他有能力应对审判,且“表露出显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强大的情感驱动力”(120页);而吉尔伯特对戈林的邪恶面更为警觉:“就像典型的精神病态者,戈林不愿受到约束的行为方式,反映了他摆脱不了婴儿期的自我内驱力”(121页)。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对戈林测试时,并不知道凯利早已测试过,但他也就此发现了戈林在观察图片时试图擦除“血迹”的著名小动作,由此认为他在有能力采取行动时却只逃避责任加以掩饰的“懦夫”心态,是个假装“亲切的精神病态者”。这一判断无疑与手握氰化物,却到最后一刻才使用以体现所谓“尊严”的行为暗合。
而纳粹早期的高层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表现出的是纯粹的“恶”——他吹嘘自己此前就已经在纽伦堡被审判过“十二次或者十三次,我出庭过太多次了,不足为奇”(130页),甚至曾命人在关过自己的牢房挂了一块匾,尊为故居。不同于之前两位的自夸态度,这位曾以演讲和文章煽动民众仇视犹太人,并且以谎言和臆想诋毁身边每一个人——甚至纳粹——的恶徒坚称自己无辜,表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超人(希特勒)造成的”(133页)。吉尔伯特根据测试认定“他不是施虐狂,也并非不知廉耻;他只是个性冷漠、麻木不仁、极度偏执。”(138页)而凯利的侧写将他描述为了一个“精神抑郁”的“偏执狂”(139页)。这位终生造谣反犹的纳粹恶党,在绞刑后讽刺地以犹太名字进了骨灰瓮。
如果说莱伊用自杀提前结束了审判,戈林用尖牙利嘴对抗了审判方,施特莱彻用卑鄙无耻恶心到了参与审判的每一个人,那鲁道夫·赫斯可能是唯一真正用自己的精神问题让法庭大挠其头的人。这个时时刻刻担心自己被下毒,动不动失忆且举动神经质的人似乎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毕竟1941年5月10日他驾机飞往英国时,希特勒就宣布以“精神分裂”解除了他的副元首之位。然而法庭认真考虑他律师提出的因精神状况不出庭理由时,他又忽然起立大喊他是在“假装失忆”,表示“接受审判、为自己辩护、质问证人或回答问题的能力没有受任何影响”。(156页)可即便法庭接受他的发言继续让他参加审判,诚如在场律师所言:“只有疯子才会在那种情况下愤然起立大声宣告自己一直在装病”。(158页)凯利根据测试认为赫斯是个装病的心理分裂者:“如果主干道代表精神健全,人行道代表精神错乱,那么赫斯这一生最重要的时光都是走在二者之间的马路牙子上”(164页),而吉尔伯特则认为其在罗夏测试中有所隐瞒,“故意抑制自己大脑中闪现的回忆……严重的情感受限,缺乏感情交流,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人格”(167页)。莫衷一是的法庭最终将他的精神状况作为了减刑依据,让他成了斯潘道监狱中无期徒刑的囚徒。
从表面看,凯利和吉尔伯特对纽伦堡审判中这四位“恶意”载体的判断可谓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除了赫斯,其他被告人都没有精神错乱,并非精神病患者。但同样诊断背后的依据却大相径庭:社会心理学出身的吉尔伯特从病理学诊断这些人是自恋的精神病态者,是病态的德国文化导致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扭曲;而精神病理学和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凯利却从社会心理学认定这些被告是普通人,行为为所处环境所塑造,深受官僚体制和谎言影响——他甚至强调称这与德国无关,“这种人哪儿都有”。不同的视角与判断,将“恶意”的论争延续了下去,成了审判落幕之后悬而未决的话题。
剖析“恶意”
纽伦堡审判之后,二人针对纳粹战犯的测试论争并未结束,“最早来到纽伦堡”的凯利与“在纽伦堡待的时间更长”的吉尔伯特不但没能按照原计划共同出书,反而发生了决裂。在一场又一场的出版大战后,即便是两人都信任的罗夏测试专家莫莉·哈罗尔都已无法再做调停。二人在1945年心思各异的合作与后来不体面的出版竞赛,使得珍贵的资料雪藏了半个世纪无人问津。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家对于人性“恶意”的讨论在不断进行: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的“旁观者冷漠”实验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都在尝试着对“恶意”的解构。
乔尔·迪姆斯代尔认为,所有这些研究都认同了凯利的论断——即邪恶容易在“恰当”的社会环境滋生,但也都共享一个前提:认定人大脑最初都是白纸一张,是与他人的交往逐渐塑造了自己的思想。那么,如果有些人与生俱来内心阴暗呢?比如像吉尔伯特所认定的,纳粹领导人脑中的“恶意”构成了一种原罪般的特殊邪恶?戈林自己就曾向吉尔伯特坦承说,他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够策划并实施大规模毁灭性行为,而其他肉食动物只是在饥饿的时候为了获取食物才猎杀。”(228页)迪姆斯代尔综合了神经精神病学、神经成像、神经内分泌生理学与法医学对于“恶意”的看法,做出了结论:在纽伦堡审判中进行的罗夏测试,实际上是关于“恶意”的理念碰撞——有人认为恶意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疾病,有人则将其看作行为连续体的一环——戈林被视为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自恋型精神病态者,他冷酷无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施特莱彻暴躁冲动,犹如无法理喻的恶魔;莱伊的大脑损伤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但矛盾的是他却是最具忏悔之心的人;赫斯像一个谜团,但大部分观察者都认同他受妄想性障碍折磨,确不正常。莱伊自杀,戈林和施特莱彻的诊断没有影响对他们的量刑审判,赫斯虽得减刑但仍受审,纽伦堡审判本身的法理价值并未受到人类社会“恶意”判断论争的多大影响,但精神病和心理学家借测试战犯将“恶意”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意愿无疑付诸东流——迪姆斯代尔在凯利与吉尔伯特尘封已久的故纸堆中,发现了诸多共同的缺陷。他们针锋相对的论点是从很少的样本中选定推论的,无论是四个典型人物,还是全部22名受审战犯,都是未直接参与屠杀的高层人士,与手下真正面对面进行大屠杀的“杀人工具”心态有天渊之别;在战败后的囚笼、破灭的希望与可期的死刑判决下进行的心理测试,真能够解释这些人大权在握生杀予夺时的心理吗?
事实上,围绕纽伦堡的激辩勾勒出了恶意的轮廓,却并未给出所谓的“答案”。当然,较之1945年,今天的人们有着更多更新的研究工具、手段与理念;但纽伦堡战犯研究,首先源于二战后国际共识下罕见的天时地利人和——人们普遍认知纳粹之恶,各界都认为对此“恶意”审判追溯之必要,并愿意以一切手段加以尝试。后来任何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难再重现这一幕公正、大同之举。事实上,2012年司法心理学家在研究了近年来的国际战争罪行审判后,惊讶地发现:“对被判犯有战争罪的人并没有进行过经验心理学研究”,纽伦堡审判的罗夏测试成为了沧海遗珠。罗夏测试的特别之处在于窥探战犯的潜意识,但测试也同样依赖观察者的判断。观察者的存在本身干涉着结果的解读,正如凯利与吉尔伯特类似诊断下的分歧依据,以及后世围绕“恶意”的看法纷争——人们主观期待“恶意”是单一的,好针对性地将其封存弃世;而纽伦堡的罗夏测试与之后的研讨争论显示:恶意的基石是一系列不同的行为和疾病,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纳粹曾掀起的血腥屠杀与惨烈战争,可能无法简单归咎于病变的大脑或扭曲的人生;对症下药防微杜渐的天真心愿,并不足以应对人性恶意在人类前进道路埋下的绊脚石。或许诚如迪姆斯代尔文末坦言:“凯利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邪恶的一角,吉尔伯特则发现了某些人独有的心理暗面——他们二人都是对的”。(253页)面对这混乱之恶,爱尔兰哲人埃德蒙·伯克的箴言更显可贵:“邪能胜正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无所作为”。纽伦堡审判中寄托的“恶意”探索固然未能如愿,二战中正义力量同心协力降服邪恶之举,又何尝不是我们直面黑暗的英勇垂范?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