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梅贻琦日记之“珊”:“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长四十馀年……襟抱宏伟而敬业不迁,陶铸人才而谦自牧,洵士林之楷模,邦国之耆贤”(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藏1962年10月20日蒋中正褒扬令)。为了纪念这位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2001年4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梅贻琦日记(1941-1946)》;2018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实为前书之修订本。
无论旧版《梅贻琦日记》,或者新版《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其内容大都是纯粹记事,“总体显得过于精简”(梅祖彦《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第3页),而且绝少发表议论或者流露感想。即便间有抒情,也基本上一笔带过,点到为止,算不上酣畅淋漓或阐扬尽致。
倒是1941年5月14日梅贻琦所写的“三信写完已过一点,院中凉月满阶,〔阶〕前花影疏落,一切静寂。回忆珊信中语句,更觉凄闷,不知何日得再相见也”(日记引文均从新版,第36页),融情于景,借景抒情,真有“这一番无限心情,都被那碧天凉月,迷却相思神不定”以及“憔悴江蓠人不见,满庭凉月照相思”之感,从中看到了梅贻琦极力克制而极少表露的个性化情绪,让人惊异这位“寡言君子”的敏感与柔情,同时也让人好奇那一个令其凄闷而思念的“珊”究竟是何许人。其实,“珊”这个人在日记内出现了六十馀次(一日内重复出现的不计),仅次于梅贻琦夫人韩咏华的八十馀次,可以算作所牵涉人物之中提及最多的一名家庭外异性,但新旧两版均未对其人作出注释,不得不令读者引为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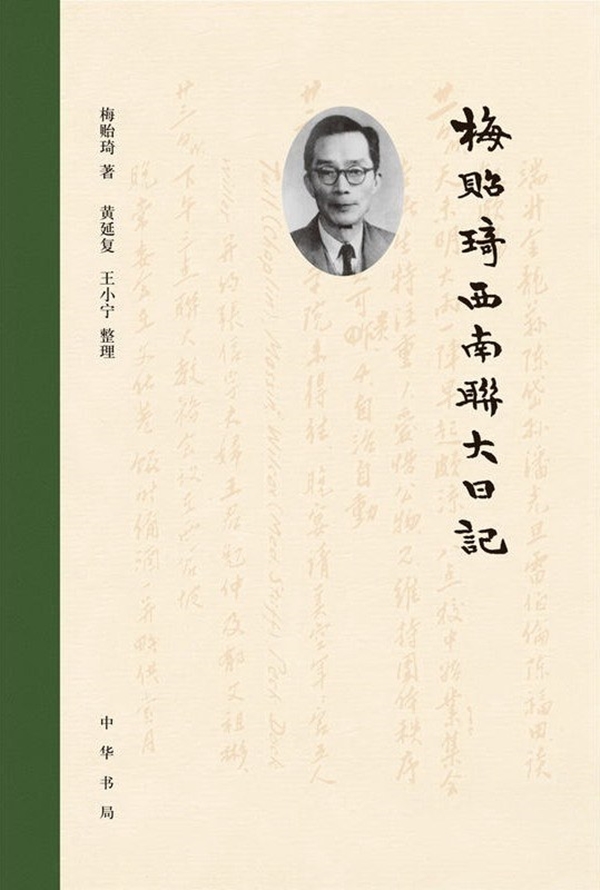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一
读过梅贻琦日记后,不难发现,“珊”有时候也写作“净珊”,如1946年6月29日,“净珊于饭后来坐。二点馀偕珊至顾养吾家稍坐后归寓”(第272页),并常与朱经农或其“朱家”一同出现在日记的行间字里,如1946年6月6日,“顾六先生以车送至朱家,时将七点,珊等方起,经农在沪犹未归也”(第264页)。
据朱经农《爱山庐诗钞》(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净珊”乃其继室,杨姓,本名静山。其长公子朱文长说,朱经农从美国留学归国之后,与原配许思澄“不和,经协议离婚。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卅日经农公乃与继配杨静山女士结婚”(《爱山庐诗钞》,第112-113页)。
朱经农与杨净珊的婚事有过一段“曲折”。1924年5月23日,朱经农致函胡适说,“因为杨小姐的家庭变了心,想解除婚约,把她另嫁富室,她的娘很可恶”,于是“我此次竟不能不逃脱礼教的束缚,于服中结婚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669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而在胡适看来,“经农在友朋中,可算是一个道德最高的人”(《胡适全集日记》,第29卷,第445-44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急烦如此,“她的娘很可恶”当可想见。
虽说“此次婚礼,一切从简,除本埠友人外不发通告”,但消息其实已然尽人皆知了。原因在于,1924年5月21日,殷芝龄与王竞华举行婚筵,次日《申报》“婚礼汇志”专栏报道其事并评论说,“尤妙者,男傧相为朱经农君,女傧相即为朱君之未婚夫人杨静山女士,下星期内朱君与杨女士即将结婚云”(《申报》1924年5月22日,第20版)。另外,《科学》1924年第4期“社员通讯”专栏亦谓“朱经农君四月间在沪与杨女士结婚”(第488页),是关于婚讯之传闻恐怕“四月间”之前早不胫而走,不待胡适等人为之“代守秘密”。
朱文长说,《爱山庐诗钞》之命名固然是“采的‘仁者爱山’的意思。但据我猜测,大概也是因为我继母的名字叫静山的缘故”(《爱山庐诗钞序》,第2页)。此外,朱经农还曾以“静山”名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除较著名的致胡适《长沙通信》(《独立评论》1936年第209号,第17-18页),尚有《苏联教育劳动者的组织》(《东方杂志》1932年第8号,第24-28页)。至于“净珊”,应当是以谐音所订取的别号,但朱经农的朋友们又将“净珊”讹变成了“静姗”(《胡适全集日记》,第32卷,第196页),或者“静珊”(《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而梅贻琦在日记内有时又称杨净珊为Z.S.(第17、19页),当是其英文名Zing shan之缩写法。

杨净珊(左)
二
《爱山庐诗钞》记载有朱经农写给杨净珊的诗词若干首,并附载了朱文长关于本事的笺注以及行述的撮录。据之,大致可知杨净珊婚前在上海担任教员,婚后朱经农在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上海特别市教育厅、大学院、教育部、中国公学、齐鲁大学等处供职,杨净珊便随侍左右,抚育子女,或居上海,或转南京,或迁济南。1929年左右,即朱经农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长期间,曾发生过一件可写入近代婚恋史的小故事。据朱文长回忆,“陶曾穀女士与先父继配净珊夫人婚前均在上海某私立中学任教。后陶嫁先父好友高仁山先生……不久仁山先生成仁,曾穀女士携孤南来,净珊夫人迎之于南京,为之安置。先父乃介绍曾穀女士入教育部工作。时蒋孟邻(梦麟)先生为教育部长。日久双方乃发生情愫……孟邻先生离教部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终不能克制情感,乃与陶氏成婚于北平”(《爱山庐诗钞》,第49页)。这故事的梗概,因有“胡适证婚……致词,极佩服其勇敢,谓可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申报》1932年6月19日,第4版),于是知者匪鲜。但个中的细节,即朱经农与杨净珊所作“铺垫”,了解的人估计不多。
1932年9月,朱经农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入湘,杨净珊仍居鲁。抗战军兴之后,约在1938年春,杨净珊挈子女南下避难,“自越南入滇居昆明”(《爱山庐诗钞》,第65页)。1941年左右,杨净珊始至湘,与朱经农相聚,寓于耒阳。1943年2月,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由耒阳迁重庆,但杨净珊并未同时随行,而是迟至下半年才起身赴渝(《爱山庐诗钞》,第84页),寓于求精中学之内,直至抗战结束。因而《爱山庐诗钞》“包括战时在湖南、四川;战后在京、沪所作”(《爱山庐诗钞序》,第3页)。
尽管《爱山庐诗钞》得名于杨净珊,其内直接涉及其人的基本信息却很少,尤其是籍贯及家世之类,无一可知,但在同时人记载里并非没有痕迹可寻。
据侯鸿鉴《西南漫游记》,1934年1月,侯鸿鉴“来长沙,即电询朱经农厅长……晤其夫人杨静珊女士。谈次,知曾在锡女师任英文一年者”(无锡锡成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77页)。“锡女师”就是无锡女子师范学校,惟不知与“在上海某私立中学任教”孰先孰后,又或两者本属一事,朱文长与侯鸿鉴有一人失记而已。又,据居浩然《八千里路云和月》,1943年,居浩然自长沙调耒阳,任特务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遇见过杨净珊,“我小学四年在江苏宝山县的杨行镇,而朱太太正是杨行人,用杨行土话交谈,特别感觉亲切”(《传记文学》1962年第4期,第40页)。而朱经农虽生于浙江浦江县,但祖籍江苏宝山县,与杨净珊可谓“同乡”。
朱经农对于杨净珊家人,除了觉得“她的娘很可恶”之外,并无片言齿及。而梅贻琦在日记内则先后提到了杨净珊的父母及兄弟,虽然简略得很,但起码提供了一点线索。
1941年3月12日,梅贻琦致函杨净珊,“兼报告为其母取款事”(第17页)。此时杨净珊在耒阳,梅贻琦在昆明,似杨净珊家人并未随其入湘,而是暂居在大后方。1945年2月19日,梅贻琦到重庆开会。3月8日,“下午购糕饼数种,往朱宅为杨老太爷贺寿”(第195页),则杨净珊父母应是在其之后从昆明迁到了重庆。而其弟杨志恩稍晚,1945年9月29日,方才“自昆抵渝”(第207页)。1945年10月,正中书局长沙分局重新开张,由杨志恩担任经理,“他的姐夫朱经农曾在湖南任过教育厅长,此时任教育部次长。他利用朱的政治力量推销教科书……解放后……杨志恩逃到台湾去了”(吴起鹤《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5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三
居浩然说,“在耒阳做了一年多营长,成为一个十足的军官。惟一稍为恢复文学生态度的时候乃是在朱经农厅长家……朱太太读过中英文小说极多,富于文学修养,因此谈话不会缺少材料”(《八千里路云和月》,第40页)。1941年2月23日,梅贻琦读完了Rachel Field的All This and Heaven Too(编者注:美国作家雷切尔·费尔德的《卿何遵命》),认为“此书写得颇好,情节亦颇有趣”,于是生出与杨净珊“奇文共欣赏”之想,“不知能续借寄耒阳一阅否”(第13页),则杨净珊之学养与兴趣,可见一斑。据吴宓说,杨净珊还是邵可侣的女弟子。1939年4月2日,吴宓“至北门街邵可侣宅,赴法文谈话会。遇朱经农夫人杨静珊女士”(《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似对法文也该有一定兴致或修养。
当然,杨净珊的兴趣似乎并不限于西方文化。就在那日法文谈话会上,杨净珊“颇注意观察宓,因谈及彦”(《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所谓“吴宓苦爱□□□(谓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诗集》,第26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于是“朱夫人谓曾读宓《诗集》,宓尽布其所作诗,可谓爽直”(《吴宓日记》,第7册,第15页)。杨净珊读《吴宓诗集》固然有猎奇成分在,但其也并非不知诗。盖以《爱山庐诗钞》之内,朱经农寄给杨净珊的诗数量不多,但时间跨迈了二十馀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略具基础,故朱经农评杨净珊“一片天真惟我知,锦函语语可成诗”(《爱山庐诗钞》,第57页)。另外,吴研因有《悼亡》八首,其二之尾联谓“人生今日曾何有,踽踽徒吟残破诗”,句下的小注说“杨净珊有‘人生能相爱至是,即以相与推挽粪车为业,亦所至乐’等语,陶行知并以‘人生之诗、诗之人生’等语评赞”(《凤吹诗集》,第86-8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是其不惟知诗,且并能诗。
或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杨净珊之为人活泼,较为自我,时而好与人作谑语,这从傅斯年、张治中、吴宓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出来。
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在长沙湘雅医院救治,朱经农电招傅斯年来探。12月22日,当傅斯年见到丁文江后,“丁太太提出一问题,即将在君移京休养……一一驳之,不得结果”,当晚“在朱家论此事,朱太太劝弟直作主张,坚持所见”。杨净珊的果敢直言,对傅斯年次日“在经农席上,弟更大申不可移京之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终“移京之说可以息矣”(《傅斯年遗札》,第694-696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
1938年1月15日,张治中与朱经农等通宵达旦商讨《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两个草案。过了两日,张治中到朱经农宅赴宴,才一相见,杨净珊便向张治中“抗议”:“自从主席来到湖南以后,经农就常常深夜不归。譬如最近一次,他在15号晚上八点钟出去,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才回来,这在我们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哩!”张治中以“这是大家的共同行动,也是大家的兴趣所在”辩解,于是“朱夫人的抗议也消灭在来宾的笑语中”(《张治中回忆录》,第116页,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
1935年2月,毛彦文不为吴宓的“苦爱”所动,委身于熊希龄做了继室。而熊希龄亡室朱其慧,乃朱经农之五姑母。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吴宓闻讯之后,“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述爱彦之深情,及今兹悲悼之意。请其以彦现在情形及住址相告”,只是“此函竟未得复”(《吴宓日记》,第6册,第281页)。直至1939年4月2日,杨净珊方才向吴宓当面解释“宓前致伊夫函,伊夫以双方为难,故未作复。又云,彦现今甚幸福,宓可放心”(《吴宓日记》,第7册,第15-16页)。
1939年8月5日,邵可侣与黄淑懿举行婚筵。“宓与朱经农夫人杨静珊为介绍人。礼毕,宴……朱经农夫人频与宓戏谑,谓希望宓亦出众不意,宣布在此举行婚礼云云”。待散席后,“宓故意询朱夫人‘彦已否在重庆’,伊答‘在上海’”,而吴宓却“疑其有意误指引”(《吴宓日记》,第7册,第45页)。
四
除学识广博与性情爽直外,据谭化雨所亲见,杨净珊“貌甚美”,令其大为诧异“朱近五十的人了,如何得此佳人”(《不速之客朱经农》,《文史笔记》未刊手稿)。《图画时报》1927年第351期第2页载有“朱经农夫人杨静山女士及其女友”照片,可一睹其芳容,“脸若银盘,眼似水杏”,酷肖《红楼梦》里面的薛宝钗,谓之“貌甚美”,尚非虚词。谭化雨见杨净珊是在1941年,此时朱经农已五十五岁了,杨净珊乃“一中青年女子”。
据说,杨净珊在婚后曾爱慕过胡适,多次匿名或以英文名Zing shan去函索爱。而胡适却“劝其决绝”,杨净珊到最后“除了想象与梦,什么都没有”(张书克《“是谁记念着我”:一位让胡适费尽猜测的女士》,《东方早报》2013年11月24日,第B10版)。直到梅贻琦的出现,情况因之起了变化。
至于梅贻琦与杨净珊是如何结识的,由于现存日记并未记载,不得而知。但日记内1945年10月3日说道“与珊……回忆九年结识”(第208页),据之逆推,则相识于1936年,具体何时,大概有三种可能性。
其一,“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华北形势日益紧急,清华预先在心理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4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故决定在湖南筹设分校。1936年2月,梅贻琦与顾毓琇等十馀人赴湘考察(《申报》1936年3月11日,第13版),与湖南省政府签订《在湘举办高等教育及特种研究事业合定办法》。目前,虽无资料以证实朱经农亦预其事,但其曾经是清华学校津贴生,且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职守所在,并在日后所撰《十年回忆》之内着重强调“梅月涵校长来湘,何主席毅然以岳麓山省立高农土地大部捐赠清华,又得顾一樵、何梦吾诸先生之敦促,迁湘之议乃定”(《湖南教育月刊》1942年第34期,第5页),揆之以理,谅或有之。如是,便为杨净珊与梅贻琦的相识提供了条件。
其二,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并伴有胸膜炎,不治去世,“5月3日在长沙银宫举行追悼大会时……国内外要人学者无不翩然莅止”(《申报》1936年5月7日,第9版),其中就有梅贻琦。在追悼会上,“朱经农报告筹备追悼之经过,并谓丁先生来湘不仅系考察煤矿,尚负有为清华学校在湘选觅分校地址之任务”(《申报》1936年5月4日,第3版)。次日,丁文江被安葬在岳麓山的左家垅。《申报》、《益世报》、《科学》等报刊对此事均进行了报道,《益世报》并且附有照片,“为下葬时,蒋梦麟、朱经农、梅贻琦……等,在墓前合摄”(《益世报》1936年5月9日,第7版)。而此前之3月22日,朱经农对胡适说,“在君坟地,弟建议在清华新校址内选择一亩,已得月涵先生同意”(《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5册,第715页),是梅贻琦与朱经农往来有日,则其入湘以后与杨净珊晤面或亦理之当然。
其三,1936年7月,清华大学按照合定办法第四款之“拟与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合办农业研究及农业试验”约定,在岳麓山设农业研究所,积极实施农业教育,“清华任研究工作,高农任推广工作”,并制定了合作办法,“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湘教育厅长朱经农、高农校长罗敦厚三人签字”(《申报》1936年7月9日,第16版)。那么,梅贻琦得与杨净珊相识,此间条件也较成熟。
以上三种会见结识的可能性,究竟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乃或兼而是之,兼而非之,是所未详。另外,梅贻琦与杨净珊彼此情愫之历变过程,因史料不足也无从获解,如以《牡丹亭》题记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来作字面上形容或阐释,尚属贴切。倒是《吴宓日记》内有处记载或可提一下,换个角度来探索两人的关系。
这一处记载出现在1937年11月19日,吴宓自北平避乱到长沙,“至湘雅医院内朱经农(教育厅长)宅。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吴宓日记》,第6册,第257-258页)。此前“‘七七’事变时,月涵不在北平,他恰好在7月6日离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日本兵开进清华园……月涵在庐山无法回平,辗转到了长沙”(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见《文史资料选编》第18辑,第62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其后不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筹设长沙临时大学,以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朱经农等为筹备委员。吴宓至朱经农宅内“先见朱,次梅贻琦校长出”,则梅贻琦或当寄寓于此。“迄年终首都沦陷,武汉震动,乃西迁入滇。大部员生步行,于廿七年(1938)2月20日离长沙,4月28日到昆明。并奉教育部命,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梅贻琦与朱经农夫妇相处了半年有馀,朝夕与共,生死依存,于杨净珊有所好感,也是人情之常。

梅贻琦
五
因长年战乱与两地暌阔,梅贻琦与杨净珊彼此相见较少,大多数时候是见不着的,惟以鸿雁往还。据粗略统计,起于1941年1月9日,讫于1946年9月20日,梅贻琦与杨净珊的往还信函约有二十馀通,但考虑到日记有间断及缺失,则事实上恐怕不止此数。
在交通受阻而通联不便的抗战岁月里,“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待短书来破恨,应迟”,等候那迟到的书信是相当苦闷煎熬的。如梅贻琦1941年1月16日“早发与珊短信,前晚所写者,伊又久未来信,不知是否又病了”(第5页),令之惦念不已。又1941年8月23日,梅贻琦自重庆经香港返昆明,其后由于公事与杂务比较多,整一个月未曾与杨净珊通函,到了9月24日,“晚,常委会,十点散”,方才抽出空来“作信与净珊,此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悬念矣”(第100页)。而杨净珊确实“更悬念矣”,盖以“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得时常把音书赐,两字平安抵万金”,于是杨净珊迫不及待地于9月26日拍发电报给梅贻琦“问‘无恙否’”(第101页)。“人违两地,书抵万金,往来遗问间,即尺幅而性情见焉”,杨净珊这“无恙否”三字,“善述牢愁,感喟缠绵”。当然,迟到书信的另一原因还包括“稽压”。昆明与耒阳的往还信函是通过香港递转的,邮程一般约为一个星期,很少超出半月。但梅贻琦1941年5月10日说“近一周接珊来信二封,一为4月26写,而一为3月27写,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为港方所稽压,可憾之至”(第34页)。
令人疑惑的是,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写给杨净珊的信多数写于夜间,乃至睡前,韩咏华居然对之无异词。原来,韩咏华于1919年6月与梅贻琦结婚,婚后因工作与时事的缘故,聚少离多。据韩咏华回忆,“1938年夏,我带着五个孩子……到了昆明,和月涵团聚,开始了在西南联大七年多的生活……我们的家先住在昆明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上是月涵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63页)。既是夫妇分居,难怪乎韩咏华对梅贻琦的私隐无所知闻了。
至于梅贻琦与杨净珊的相见,屈指可数,约有二十馀次,并分散在1945年2-3月间、9-10月间、12月间,以及1946年2月间、5-6月间,共计五个时段。前面四个时段相见均在重庆,盖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移驻重庆,其教育部在郊外青木关,而西南联大的“三位常委原定每人轮流任两年主席,但因张伯苓、蒋梦麟两位先生均在重庆另外任职,月涵只好一人办理日常事务,遇到大事再找他们两位商议”(《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2页),故梅贻琦有时候出差到重庆,间或居停求精中学朱经农处。此时朱经农虽主持求精中学校务,但身为教育部政务次长,在青木关时间较多,故多由杨净珊来接待梅贻琦,其实也不过是陪之谈天、吃饭、购物、访客、看竹而已。
当然,最令梅贻琦低徊的,还是无旁人在,与杨净珊“闲谈”。如1945年10月7日,“珊仍患呕吐,不能多进食。饭后闲谈,至九时睡”(第209页);10月9日,“室空人静,殊得闲谈。珊病似仍未愈,但兴致甚好”(第210页)。而两人在1945年10月3日所作夜谈,多少有点幽愁附着其中。梅贻琦说:“晚在朱处,饭后颇静,与珊得闲话。回忆九年结识,经许多变动,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今后经历如何,尤难测度。但彼此所想颇多,可领悟于不言中也。”(第208页)抗战胜利,复员在即,梅贻琦归北平,杨净珊返南京,似成定局,一切生活恢复原样,而彼此的暧昧恐怕也将难以为继,不得不为“今后经历”做点打算,只是两人均不愿意明说。随后数日,彼此交往如常,但在10月5日,梅贻琦午饭后“至朱处小息。晚饭后珊竟自青木关归来,初闻其须下星期一方能运物归者,经归家甚讶,如此巧遇,似以为必有前约者,可笑哉”(第209页)。对于朱经农的“甚讶”,梅贻琦虽一笑置之,但郑重地写入日记,并说“如此巧遇,似以为必有前约者”,其内心里或已觉察到了过从稍密而不防嫌,易于落人口实,招来误会。
1946年2月22日,杨净珊将于凌晨乘飞机从重庆往南京,梅贻琦本想与之作临行“闲谈”,即使2月21日“一日仍在求精未他往”,可是“来客数起,收拾零物,竟无静谈机会”,只得“十点握别,因明早四点馀起飞,不得往送矣”(第239页)。别后两月左右,梅贻琦于4月8日“晚座间兰花盛开,香气颇觉袭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第249页)。一个半月之后,也就是5月24日,梅贻琦赴南京,在下关站下车,“珊与文华、文光则于站栅外始得见”(第260页)。从此以后,直至6月29日,是梅贻琦日记内两人相处的最末一个时段,谈天、访客、吃饭、看竹诸事仍然,偶尔还有游陵园、听西乐、饮啤酒、喝咖啡等,但均有旁人在,并无惟两人独处的时光。6月29日,“晚未出门。九点俊如来坐颇久,净珊与有骞皆晤谈。客去后珊等出代购纸烟,归后闲谈,至十二点馀始睡”(第272页)。次日,梅贻琦便乘飞机赴汉口。其后,转重庆,归昆明。
六
从日记看,进入1946年7月以后,梅贻琦时而在昆明,时而在重庆,时而在北平,忙于各处应酬以及复员诸事,与杨净珊接近于失去联系的状态,惟有9月20日夜归之后“作致珊信”,并且写得过了凌晨“一点半睡”(第291页)。从此以后,直至日记止于10月19日,杨净珊其人便不曾再出现了。但这并不说明梅贻琦与杨净珊是失去了联系,或断绝了通问。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发起平津会战,势如破竹,席卷华北,北平解放只在旦夕。12月21日,“政府派专机飞平救援各大学名教授……21日下午5时,分乘专机两架先后飞抵京,其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申报》1948年12月22日,第2版)。到南京后,“孙科内阁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的委任令,他坚辞不就,但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于上海老友朱经农的家里”(黄延复《梅贻琦传》,见《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5卷,第13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而朱经农先于1948年11月14日出国至黎巴嫩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三届大会,“为首席代表”(《申报》1948年11月14日,第2版),故梅贻琦与杨净珊不惟重逢沪上,且在同一屋檐之下,可惜此间并无日记,其交往之详情无从得知。
另据胡适日记所载,1949年2月21日,在上海的胡适“与经农夫人及梅月涵同去看电影”(《胡适全集日记》,第33卷,第717页)。此处“经农夫人”自然是杨净珊,其对胡适有过爱慕之事,与梅贻琦又有暧昧之情,这样的三个人相处一起,不知各自作何感想,反正胡适只说了句“我三年不看电影了”(《胡适全集日记》,第33卷,第717页)。
同去看了电影之后,1949年3月,梅贻琦“由上海至广州,方得与梅夫人在香港会面”(顾毓琇《梅贻琦年谱》,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1年第4期,第102页);4月,胡适自上海至美国(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8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两人离开之后不久,“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然宣告结束。从此梅贻琦与胡适便归不得故土,均旅居在美国。至于杨净珊则绝迹无闻。
而朱经农出国以后“未及返国而中共已进占京、沪。遂决意暂留海外,讲学以渡馀生”。1951年3月9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遗继配杨氏夫人,子文长、文华、文光、文衡,女文曼,而临终无一人能随侍在侧”(《爱山庐诗钞》,第124、118、125页)。
七
1955年11月,梅贻琦自美国赴台湾,“奉召回……准备清华复校”(《梅贻琦年谱》,第102页),于是从此长居台湾。而其1956年1月至1960年4月日记尚存,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由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以《梅贻琦文集日记》名义整理排印,第1册(1956-1957)出版于2006年10月,第2册(1958-1960)出版于2007年4月。据日记载,1957年3月,梅贻琦赴美国参观访问。4月5日,在纽黑文遇见了朱文长,“与朱文长谈文华病状,似颇见好。1.设法接其母由澳门至台湾;2.如文华愿至台工作最好;3.如彼愿留美,设法使文长接其母来美”(《梅贻琦文集日记》,第1册,第180页)。朱文长为许思澄出,朱文华为杨净珊出。许思澄于1938年初去世,此处梅贻琦所说的“其母”必然是杨净珊。既谓“设法接其母由澳门至台湾”,或上海解放后杨净珊避居在澳门。
梅贻琦晚年日记内关于杨净珊者,虽然惟此一处,但其惦念故人之殷,尚可于此见及,不禁令人想起胡适的诗,“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五年后的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湾大学附设医院,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内,名曰“梅园”。
前揭张书克文发表之后,岳秀坤在微博说杨净珊“这位女士后居台湾,享高寿,如果没记错的话,她特别嘱咐后人将骨灰撒向大海,而不是与朱经农先生合葬”(见《胡适博士又多了一颗星》,《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日,第B15版),则杨净珊应是听从梅贻琦的建议,迁居到了台湾,直到去世。不知梅园花开时节,杨净珊是不是来过此地,折下一枝,聊寄其遐思呢?就像当年,梅贻琦以兰花寄意一般……
八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梅贻琦对杨净珊是发乎情而止乎礼的,其之所以“情动于衷”,一方面,自然是杨净珊有其独特可爱之处;另一方面,可能是梅贻琦在战乱岁月里获得情感慰藉与精神寄托的需要。据韩咏华回忆,“在昆明期间,月涵虽然仍像在北平清华时一样地忙于校务,但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忧愤山河沦陷,思念亲朋故旧和他付出了心血的清华园”(《同甘共苦四十年》,第65页),而这种不平静的心情在日记内是有体现的。
1941年3月28日,梅贻琦说,“此日为阴历三月一日,四年前之今日适逢月圆,江轮情景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第2122页)。其中“四年前之今日”,即1937年3月28日,阴历三月十六,因民间有“(月亮)十五不圆十六圆”之说,故谓“适逢月圆”。据当时的《申报》报道,“中国考政学会定7日在京举行二届年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由平抵京……闻梅约留一月始返平”(《申报》1937年3月5日,第4版)。3月28日,梅贻琦已然登上了江轮,当是年会与公务完结后,从南京取道大运河水路返回北平。孰料数月后宛平城一声炮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国破家危,妻离子散,流亡他乡,奔走终岁,到了1941年,梅贻琦已然是“五年漂泊泪由衷”,因而慨然而思“江轮情景”,喟然而叹“不知何日能再得之也”。1945年3月27日,梅贻琦以“归寓后廊外月明如洗,伫视不忍离去”,继而感叹“八年前景物如在目前”(第198页),其铭刻于心而念念不忘者,与之前的“江轮情景”实无别致。
职是之故,梅贻琦长公子梅祖彦说,“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学校事务对他精神上的重大压力”(《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第2页),因而梅贻琦将杨净珊作为情感交流的对象,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或也是可理解之事。
本文发表于《掌故》(第六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掌故》(第六集),中华书局2020年7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