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绿衣女骑士——记首位耶鲁大学最高级别女教授
2012年的一期《耶鲁大学校友杂志》写道:在20世纪60年代末或者70年代早期,耶鲁大学英语系仍然浸淫在古旧的空气中,笼罩着一层对女性不友善的氛围。如果你曾在这个阶段进入英语系学习,除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之外,你一定会被一个人吸引,她就是玛丽‧博洛夫(Marie Borroff,1923-2019)。
机缘巧合,当我们决定在耶鲁大学校园周围购置一个公寓时,年届九旬的博洛夫教授正在抛售她位于纽黑文的公寓。那会儿我对她一无所知,仅知晓她是文科教授。她将主卧打造成书房,卧室四面,两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架,一面是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阁楼上的储藏室也被书架占满。当我知道她不仅是位诗人,也是首位获得耶鲁大学最高级别教授的女性,即史德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时,我开始有一种想了解她生平的欲望,毕竟曾经的男子大学,耶鲁大学本科学院迟至1969年才迎来第一届女生。
结缘中古英语
博洛夫教授1923年生于纽约的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歌唱家,母亲是钢琴家。她自幼接受专业的音乐训练,母亲希望她能够成为音乐家。事实证明,她不仅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中古英语研究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音乐家。她不爱公众表演,但经常在私人聚会上即兴表演,还会作曲,喜欢英国乡村舞蹈和戏剧表演。1984年1月,耶鲁大学伊丽莎白女王俱乐部举办了一场伊丽莎白一世的诞辰450周年和加冕典礼425年庆祝活动,博洛夫扮演了女王。那也是时隔25年后才举办的一次重大活动。比她年轻两岁的妹妹, 伊迪丝‧博洛夫(Edith Borroff,1925-2019)则选择了音乐学,于1958年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历史音乐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是一名杰出的音乐学家和作曲家。

玛丽‧博洛夫
博洛夫15岁毕业于纽约私立高中——友谊学校(the Friends Seminary School)。在这所学校,老师评价她为“学术天才(scholarly prodigy)”,善于钻研。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她专攻文艺复兴至二十世纪时期的抒情诗,主要集中于英语领域,同时涉及一点法语和一点点德语。在一个正式场合,一位美国当代诗人不确定地告诉我,她可能至少通晓五种语言,土耳其语为其中之一。她非常喜欢“伊斯坦布尔华尔兹”。二十世纪前半叶,芝加哥大学教授基本都是男性。博洛夫在校时期,英语系只有一位女教授——诗人格拉迪斯‧坎贝尔(Gladys Campbell),她只见过坎贝尔一面,并无交集。她的学术训练主要得益于三位男性教授——文学评论家罗纳德‧克莱恩(Ronald Salmon Crane)、文学家诺曼‧麦克林(Norman Maclean)和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埃尔德‧奥尔森(Elder Olson)。这三位教授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形成了“评论界的芝加哥学派”。跟随这三位老师,她在“文学评论”领域里得到了极好的专业训练。不仅如此,她在诗歌创作方面也突飞猛进。虽然自幼开始诗歌创作,却是麦克林教会了她如何增强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和力量。为此,她停笔两年,未曾创作。之后,她的诗歌屡获奖项,得以在知名刊物上发表。
在芝加哥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位之后,博洛夫没有立刻继续学业,而是出国转了一年,在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教了三年书。正是在史密斯学院期间,她意识到自己需要大力加强英语语言史的学习。1951年,三年聘期结束,她辞职去了纽约,一边从事钢琴演奏工作,一边寻找编辑岗位方面的工作。她想依靠编辑工作谋生,休闲时间创作诗歌,最终成为一位诗人。后来,她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读博士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期望在大学里谋职。她喜欢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和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诗歌,又接受过文学评论方面的专业训练,她想比较不同诗人的诗歌语言和风格之异同,并结合文学评论开展研究。她向一直保持联系的克莱恩教授征求意见。克莱恩建议她去找耶鲁大学教授和语言学家海尔格‧科克里茨(Helge Køkeritz ),认为他可能会对她有帮助。当时,科克里茨正在研究莎士比亚,正尝试结合语言学和文体评论开展研究。最终,博洛夫在科克里茨的建议下申请了英语文学和英语语言学的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她是当年唯一一位被选中的学生。
在只招收男性本科生的特殊年代,耶鲁大学的500名艺术与科学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教工,清一色全是男性。她的老师里还是没有女性。她跟随约翰‧波普(John C. Pope)教授学了一年古英语(耶鲁大学称之为盎格鲁-萨克逊语(Anglo-Saxon)),这也是当时所有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然后又随E.塔伯特‧唐纳森(E.Talbot Donaldson)研究中世纪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与科克里茨进一步学习古英语方言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不知不觉,她一步步迈进了中古英语的世界——一个她未曾踏足,却有着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等待她去挖掘和寻宝的地方。
通过博士资格口语考试之后,她开始着手准备论文,但是选题还没有着落。她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和抱负告诉了波普,波普建议她研究英国诗歌《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尽管这首诗歌的创作年代与乔叟活动时代相同,但当时她对此一无所知。对比研究莎士比亚等其他熟悉的课题,她认为难以超越前人,她最终采纳了波普的意见。此后,她和高文诗歌结下了一生之缘。高文诗歌的研究也为她加入耶鲁大学,成为英语系第一位女教授奠定了基石。值得一提的是,《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是一部14世纪末期的韵文传奇叙事诗,是中世纪英语最佳文学作品,是目前发现的五部高文诗歌中的一部。博洛夫在《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的1967年译本中介绍到,该部作品语言深涩难懂,使用了大量地方方言和古英语,非一般人士所能解读,因此鲜为人知。这部作品与《纯洁》、《珍珠》和《耐心》等三部作品流传于同一个手抄本,后来,人们还发现另外一部同时期手稿——《圣艾肯瓦尔德》(Saint Erkenwald)——在采用的方言和意象方面与之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这五部作品因此被认为出自同一位作者,但作者的具体身份难有定论,被统称为高文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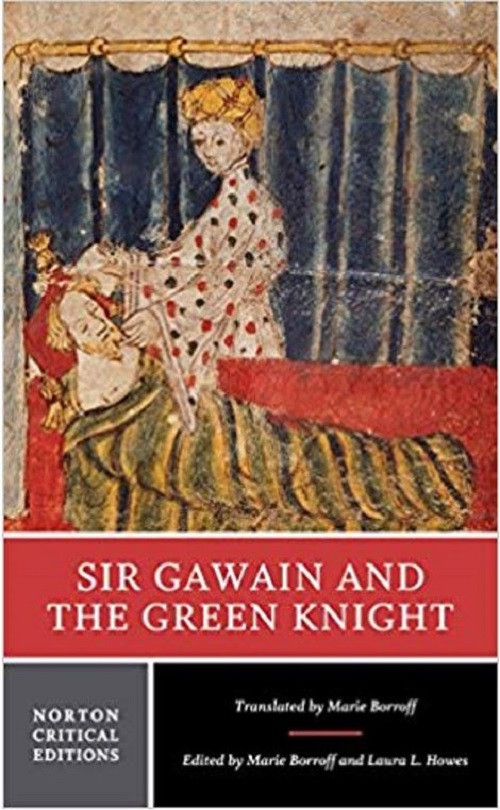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博洛夫译本
闯进纯男性世界和无数个“第一”
1956年博士毕业后,她手持几份的工作接受函均来自女子大学,这都在她意料之中。在上世纪前半叶,不仅仅是耶鲁大学这样的男子大学,就是其他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职工也几乎都是男性,女子学院则另当别论。考虑到自己曾经在史密斯学院教过书,有熟悉的朋友,喜欢那儿的乡村环境,她选择重返旧地。碰巧的是,在工作第一年,科克里茨去了瑞典休假,她受邀到耶鲁大学代课,教授博士生的必修课——《文艺复兴时期的英语》。1958年秋,科克里茨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系里需要她。随后,她被聘为耶鲁大学访问副教授,任务是教一门关于诗歌分析方面的课程。
早在之前,她曾收到过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出书邀请,但她一直束之高阁,直到耶鲁大学给了她一个提议。耶鲁提出,如果在当年学年结束时,她能够完成《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文体和材料研究》(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A Stylistic and Material Study)一书书稿,并被出版社接受,她便可以获得英语系副教授职位。书如期完成,1959年,博洛夫成为第一位在耶鲁英语系任教的女性。1962年,该书问世。1965年,她获得终身教职,也是当时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中,被授予终身教授的两位女性之一,另一位是知名女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

1967年耶鲁大学英语系全体终身教授,博洛夫是唯一的女性。(资料来源:耶鲁大学英语系)
据耶鲁大学高级顾问佩内洛普‧劳兰斯(Penelope Laurans)介绍,博洛夫在职称晋升的道路上发生过一段小插曲。许多单位曾向博洛夫伸出过橄榄枝,甚至在早期,一所女子学院聘请她当校长。一位关系亲密的朋友建议她带着新书、简历和聘请书去找系主任。几天之后,她便获得了终身教职。据博洛夫自己推测,她之所以能够获得耶鲁教职,可能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课程需要。波普的古英语课程需要科克里茨的课程作为后续补充,但是科克里茨有些弱点,性格温和,却不善于教书;文笔好,口才却一塌糊涂;次之,他身体欠佳,博洛夫求学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下滑。在博洛夫加入耶鲁大学几年之后,他便离世了。二是几位关键人物的开明态度。她猜测唐纳森教授是倡议者,因为他曾经在她读书时便说过:“我相信你能教好男生。”重要的是,还有波普和科克里茨两位教授鼎力协助。
为什么是能教男生?51年前,耶鲁大学本科学院才姗姗来迟迎来第一批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英语系路易斯‧马茨(Louis Martz)和梅纳德‧麦克(Maynard Mack)是“男女同校”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博洛夫入职时,马茨刚好是系主任。不管如何,歧视女性的氛围依然笼罩着耶鲁大学。据一位20世纪60年代就读耶鲁大学英语系的女研究生回忆,当时,人类学和英语这两个领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她的同学在芝加哥大学读人类学,那里男女生比例均衡,但是没有女教授。她在耶鲁大学英语系,系里只有博洛夫一位女教授。她的导师直白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读这个研究生?”接着又说,“或许,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教授当夫人。”她的导师还建议她改变形象,注意穿衣打扮,因为她笑太多,太活泼,对人太友好。也许老师自认为是一片好心,但她却感觉受尽了侮辱, 背地里大哭一场。由此可知,作为教授群体里唯一的女性,博洛夫必须具备强大的抗压性。但是,在耶鲁任教第一年,作为第一位“全雄性群体的入侵者”,博洛夫没有感觉到任何人对她有何不满。
“没有人不满”不代表她完全融入了一个纯男性群体,博洛夫自己也很清楚这点。就连她取得终身教职这样在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都成为老教授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阴阳怪调地说道:“你看,我们授予了一位女性终身教职。”她一直和上述提到的几位男性教授保持着友谊,但社交活动仅限于私人聚会,比如说波普家里或是唐纳森家里,或者和科克里茨在教工俱乐部吃饭。为什么不能是其他场合?作为女性,她没有机会参加一些非正式教授午餐会,因为他们在纯男性会员的莫瑞(Mory’S)俱乐部进行。她也没有参加过基于联络教工感情的,系里组织的其他非正式活动,比如去位于校园内的某知名披萨店或者其他咖啡店。博洛夫对此没有想太多,她太忙了。在纽黑文,她的时间被教学、备课、委员会会议和学术占满。周末,她便离开纽黑文。她很感激唐纳森,在个人职业发展过程中,是他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明智的建议。
耶鲁大学英语系主页上的系史简介里,只放了一张照片。照片摄于1967年,当时25位教授里只有博洛夫一位女性,她身着裙装,双腿并拢,身子坚挺地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文雅端庄。尽管位于她身后站立的是身材异常高大的威廉‧威尔斯特教授(William Wimsatt,1907-1975),据说他身高6英尺4英寸,约合1.93米,但博洛夫像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夺人眼目。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耶鲁大学对待女性的态度也逐渐转变。英语系陆续聘请了多位女性学者,午餐会也改了地点,不再在莫瑞俱乐部。1991年,博洛夫成为第一个获得史德林教授的女性,这是耶鲁大学最高级别教授职位。2008年,耶鲁大学一个新的讲席教授职位(endowed chair)以玛丽‧博洛夫命名,这也是耶鲁大学第一次以女教工名字来命名。她还是校内外无数个委员会中的第一位女性,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尽己所能
或许肩负责任太多太重,她终生未婚,没有子女。有人评价她的仙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充满学术和美丽的时代;一个对过去崇敬和对卓越奉献的时代。
在二十世纪后期,博洛夫成为许多耶鲁女性的榜样和引导者。她很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最钟爱的事情便是做学问、教书和写作。她也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为各种名利诱惑所动,深得学生爱戴。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堂里,学生们将花束、帽子和一切手边之物抛向空中,为之庆祝。她常常建议学生:“尽己所长(Do the work that only you can do)。” 她对学生提出哲学般的建议:“追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要跟风。”退休之后,她最怀念的就是学生,怀念漫步校园,走进课堂的美好时光。作为一位荣休教授,已经没有指导本科生写作的义务,但是只要学生有求,她仍然耐心指导,定期请学生到自己的公寓里讨论,像对待学者一样严格要求学生。
许多读者应该对“A River Runs Through it”这部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不会陌生,它于1991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中文译名之一为《大河恋》。该书作者,也即上文提到的芝加哥大学麦克林教授曾在致谢中向博洛夫表达了崇高的谢意。他认为如果没有博洛夫的建议,就没有《大河恋》。当他写完第一个故事时,他请博洛夫给出意见。博洛夫批评他花了太多笔墨讲故事,没有努力用尽他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具备的才能。他慎重地采纳了她的意见,在创作后来的故事时做出了巨大调整。
博洛夫专攻中世纪和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英语,同事称之为中世纪主义者(medievalist)和现代诗诗人。哈罗德称赞她是一位伟大的中世纪主义者,是现代诗歌的优秀评论者,对待所有事物都很人道。他还把她比作一个理智和清亮的响钟,钟声一响,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明亮。很多教授在退休之后感觉不适,朋友向博洛夫抱怨道,退休之后的生活像行尸走肉。终身热爱教学的她开启了另一种生活,她一边选择教学,线上教学系统关闭之后,她又继续走进真实的课堂,乐此不疲,一边着手长期的翻译工作。在88岁高龄,她出版了最高成就——《高文诗人: 全集(The Gawain Poet:Complete Works)》,一部囊括了所有五种高文诗歌的译本。她的译文完全遵循原著的韵律和结构,还原出悦耳的音乐效果和美妙动人的语言,充分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89岁那年,刚刚经历了一场流行性感冒的博洛夫,还能站在讲台上,中气十足、吐字清晰、抑扬顿挫地讲授一堂“华莱士‧史蒂文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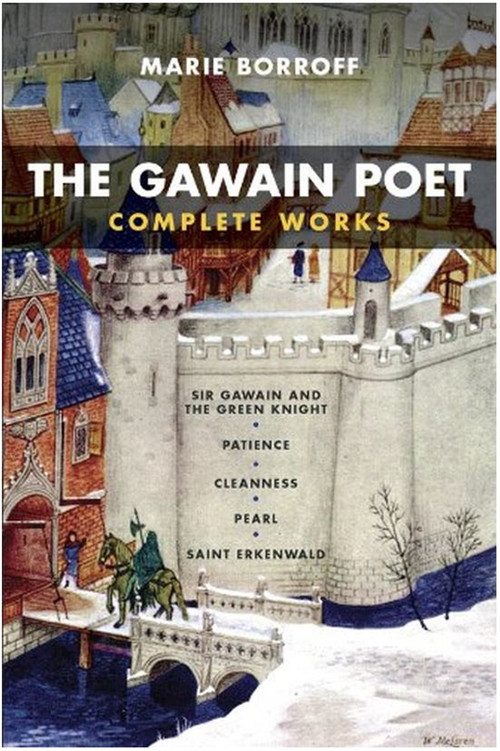
《高文诗人:全集》
博洛夫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世纪主义者,她觉得自己不够专心,在这个领域里花的时间太少。在其它领域里,我们也能见到她的身影,她喜欢现代诗,喜欢二十世纪美国的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和玛丽安‧摩尔,后来又喜欢上了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 。她甚至还是研究计算机诗歌艺术(the art of computer poetry)的先锋人物。她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耶鲁人眼里,她创作过的诗最美莫过于,“In Range of Bells”。

博洛夫个人诗集
这是一首赠给原耶鲁本科学院院长理查德‧布罗德黑德(Richard Brodhead,曾担任过杜克大学校长)的诗。耶鲁大学校园有相当一部分区域是沿山而建,山丘顶上分布着各个基础学科所在系,生物、化学、数学和物理等等都在其中,小山缘此得名科学山(Science Hill),山边有一条路,称作展望街(Prospect Street)。科学山是诗人从公寓走到校园里的必经区域。每天,她沿街而下,迎面与一群群到科学山上课的学生相逢。彼时,附近耶鲁神学院的教堂钟声响起。钟声提醒她时间的流逝,生命的轮回。科学山就像是母亲的乳房,哺育着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使得他们在科学知识的殿堂里茁壮成长。这首诗被布罗德黑德和现任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学生致辞中多次引用。
我时常漫步在耶鲁校园,在哥特、英格兰,还有现代的建筑空间里来回穿梭,混迹课堂,身临其境,对这份情感有着深切的体会,读这首诗时常常产生强烈的共鸣。可惜笔者不才,无法用自己的语言以诗歌的形式翻译出这首诗。在此,我特别邀请北美华文女作家,诗集《城门下的烟雨》的作者,也是《遇见,桑央嘉昔情歌》的英文译者,常少宏女士将它译为中文,供读者欣赏。
《在钟声回荡的地方》
—— 为理查德·布罗德黑德
(作者: 玛丽·博洛夫; 译者:常少宏)
我走在钟声回荡的地方
沉默(一个接着
一个)划掉每一次钟声敲击时告诉我们的
时间结束过,时间开始过。
每日走下展望山街道
钟摆不停地数着(九,十)
诉说一个永恒的愿望
时间带给我周而复始。
并且带我去上学途经此处
循着乳房的线条向上爬坡:
眼睛,脸,年复一年,
年轻,并且越来越比我年轻,
而钟声敲响一声接着一声,承载过去
就像树叶被从一棵树上吹落,
告诉时间的分支如何紧紧抓住我们
只为把我们抛向自由。
诗的原文:
In range of Bells
For Richard Brodhead
I walk in range of bells
where silence (one
by one) marks off each stroke that tells
time ended, time begun.
Daily down prospect Hill
the tally keeps( nine, ten)
telling with what a constant will
time brings me round and round again,
and brings me schoolward here
to breast the advancing line:
eyes, faces, year by year,
young, and more young than mine,
while bell on bell, borne past
as leaves blow from a tree,
tells how time’s branches hold us fast
only to cast us free.
主要参考资料:
1)Marie Borroff,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W.W. Norton&Company, 1967.
2)Susan Chira, Yale Group Pays Homage to Elizabeth I, the New York Times, 01/24/1984.
3)Jane Chance, Woman Medievalists and the Academ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789-802.
4)Alison Baker, It’s Good to Be a Woman: Voices from Bryn Mawr, Class of ’62, Publishing Works Inc, 2007.
5)Norman Maclean, A River Runs Through I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缅因州当地报纸,https://www.boothbayregister.com/article/marie-borroff/121410
7)Marie Borroff, Stars and Other Sig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8)耶鲁大学校友杂志。
9)沈弘译注:《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台北:书林出版社,2009年。
10)博洛夫朗诗。https://chartable.com/podcasts/poetry-readings-by-marie-borroff
11)https://yalereview.yale.edu/creativity-poetic-language-and-computer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