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
- +1301
专访旅行作家刘子超:旅行是我的工作状态,很少有度假的心情
本文为镜相栏目独家首发访谈,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访并文 | 刘成硕
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或者别的什么形式,作家刘子超的选择是旅行写作。
这和在枯坐中就能实现的天马行空完全不一样。他需要对准沟壑纵横的土地上,把自己毫不保留地空投下去。异乡在发生什么,发生过什么,那里的人们在抱怨什么,期待什么。所有的命题没有显露的答案,全凭他徒手刨掘。
辽阔的中亚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不被注视的他者。很少有中国旅人前往。苏联解体后,那儿像失去引力的卫星,涌现出失落之心和所托非人的希望。刘子超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当他在中亚街头,在车上,酒吧和餐厅里,向他们搭讪:你叫什么名字?你结婚了吗?因为惊异于他孤身前来,很多人乐于奉上自己的故事。
他当了多年记者,职业素养和敏感度都用上了。他知道上哪儿找人,如何吞下观察到的一切,避开危险,把枯燥和索然无味转化为持久的兴奋感。
他推崇的是西方那些优秀的旅行作家,保罗·索鲁、奈保尔,拥有长达一生的探索精力和写作热情,到年老了依然走得动,写得好。
刘子超出生在北京,成长过程平顺,但咂摸起来始终有些寡淡。他记得高中时候全班坐火车去陕北玩,几十号人挤在窑洞里过夜。那是2000年,那时候家长还不像现在的父母一样,焦急地为孩子谋划一个又一个开阔视野的机会。那次是他为数不多的少年旅行经验,再次忆起依然津津有味。他的外表看上去有一种沉稳感,但自认为内心不像外表看着那样稳。
2016年,“创业”像诱饵一样在空气里招摇。哪怕是文艺青年,也无法保持岿然不动的心。他只在那会儿摇摆过一阵子。“后来想通了”,他说,认清自己不适合干别的,“写作挣不了大钱,也饿不死”。
他至少怀揣一样自信。在同样的领域中,恐怕没有人能像自己一样,愿意花费巨额的时间、精力,去制作一部充沛的作品。这是一项需要高投入度的工种,付出孤勇,才能交换得到迷人的故事。《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就是这样得来的。
他记得在中亚的某些日子,午夜时分,自己被运送到一个新的地方,走出空旷的车站,外头是一无所知的土地和夜空,只有一种广袤的陌生感像摄魂怪一样聚拢在他的脚边,这个时候,一个天生的旅行写作者会分泌出巨大的兴奋感。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刘子超 著
新经典 出品
2020年7月
以下是镜相栏目与刘子超的访谈:
镜相:这本书是在9年探访中亚的基础上完成的,前后去了几次,总共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第一次是2011年,去乌兹别克斯坦待了半个月。那次没有任何计划性,是偶然认识了一个乌兹别克斯坦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人,他邀请我过去玩了一趟(后来这个人也与我失联了,中亚就是这样)。那次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写不了什么。
2017年,我自己又去了一趟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这当中几年,想去中亚很难,签证办下来难,也贵。如果不是有人邀请我,帮我办好邀请函,过去是非常困难的,其他几个国家比乌兹别克斯坦还难。到了2017年,签证政策有松动,同时如果你乘坐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航空,经阿拉木图或阿斯塔纳转机,可以免签72小时。我当时正好从圣彼得堡回国,然后就坐阿斯塔纳航空的航班到阿拉木图,待了三天。
当年10月我又去了一趟乌兹别克斯坦, 2018年再次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2019年,我用单向街“水手计划”的资助基金又去了一次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是一直没进去的,到了边境也没让我入境。后来我在国内又申请过两次。一开始以为也许签证官看我一个人去土库曼旅行很奇怪,所以找了两个朋友陪申,结果他俩都过了,我依然被拒。不知道为什么,没理由。接下来如果这本书有幸再版,我想把土库曼斯坦的部分补上。

镜相:第一次去了以后,为什么会有写不出来的感觉?
那时候我不了解中亚,完全不知道应该把那里放在怎样的维度上打量。当你去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如果你想有把握去写这个地方,首先得把它放到一个观察的维度里头,这实际上是长期积累了解的结果。直到后来慢慢了解多了,然后去的次数多了,我才能把它重点放到一个维度里,就是这个书名的提炼——失落的卫星。中亚在历史上经历过那么多复杂的变化,但自始至终都是在大的文明的边缘,无论是唐朝、阿拉伯帝国还是苏联,受着周围更大的文明和势力的影响,得出这个结论,我就有了观察和写作的角度,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可以包进去,并且有信心就算舍弃某些部分,也不会对我的写作有任何影响。
镜相:当你带着这种眼光去观察,会不会像是在找素材去在印证你的观点,这样是否会过滤掉一些事实?
我认为我是了解之后的提炼,不是先入为主,我去并没有预设任何立场,是把所有得到的东西归纳之后,写作的时候提炼出来的思路。
镜相:《失落的卫星》里大部分内容是你与当地人接触、交谈的结果。你在当地是如何快速融入人群,与他们建立关系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本领?
我其实没这本领,我只是比较善于观察,在意细节。我以前是做记者的,跟采访对象聊天经常冷场,经常不知道怎么发问,怎么接话,比较笨拙,但是我捕捉能力强。比如昨天下午和一个新朋友见面,我们俩聊天一个多小时的期间,我发现——他用的是苹果电脑,戴着苹果手表,穿一件优衣库的绿色 T恤,一条牛仔裤配Converse帆布鞋,他是92年生人,原本大学毕业想去中青报,没去成,所以进了上海的一家媒体。他是那里年龄最小的人,他喜欢吃附近一家叫“弄堂小馄饨”的店……他或许随口一说,但我会捕捉到并且记住。细节性的、生活化的东西看似不重要,而写出来却有意思,也更能跟读者有一种亲近感。
其实重要的不是我去谈,是让他们谈。会倾听是更重要的,不需要我像常规意义上的采访或者电视节目上的对谈,展示自己的聪明和机敏。那种感觉像是把自己往下沉,让对方更主动。我问的问题可以非常简单,随便聊。我不是那种看上去有攻击性的人,随意的交谈,对方不会有戒备心。有些故事也不是我主动问的,只是被我记住,捕捉到了而已。然后,我会跟有的人说我们再约时间,问对方明天有没有一小时的时间跟我再聊会儿。奈保尔提到过,他可能采访一小时,拿到六千多字的素材,就能写出来1万多字的稿子。其实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尽量捕捉更多的东西,然后把它的细节、纹路描绘出来。

浩罕小巷的卖馕少年(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刘子超拍摄)
镜相:你会对哪些人做进一步的交谈?
主要看能不能跟这个人做有效沟通,这很重要。因为大部分人接触以后发现做不了有效沟通,我可能就放弃了,有的时候受限于语言,谈不了很深的东西,也可能这个人不那么善于表达。也许十个人中有七八个人在接触后我没有再往下追,只有一两个人是有意思的,他们会表达,有交流的渴望,他们的故事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侧面。
旅行写作与别的类型写作不一样。你怎么去掌控节奏,做到什么程度收手,感觉到“我对这个地方了解的差不多了”?
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可能永远都没有到“够”的程度,只能说够自己写。一般像中亚那种普遍规模的城市,如果能和至少四五个人做过有效交流,他们有不同的背景,反映不同的侧面,我觉得能达到的我写作素材量。中亚的城市大部分还是比较简单,一般四五个人,你差不多能通过他们的故事把这个地方给解剖出来。但如果是孟买,上海或者纽约这种地方,那就远远不够了。
镜相:他们对你的好奇在哪?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没怎么见过中国人。可能见过一些去中亚做生意的中国人,或者做基建的工程人员,像我这样中国旅行者几乎没见过。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些跟团游客,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他们对我的好奇一般是,为什么来这里。因为他们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玩的,你来干嘛呢?
其实大部分人很难做具体的发问。这有点不公平,当我们站在发展时间线更快的坐标,去往时间线慢的地方,我是知道怎么发问的。如果我去了时间线靠前的那些地方,我觉得就不太好问,可能问出来非常荒诞,或者没办法提出切实的问题。比如他们问,中国人是不是都吃狗肉,或者以前看到过一个什么视频,向我求证是不是真的。

镜相:你抵达一个城市以后,行程是怎么规划的?
一般从外部进入,肯定是先到首都,最大的城市,再一点点往下沉,中小城市,乡村,最后再返回大城市。
镜相:充斥在旅行之中的不适感怎么克服?有负面情绪的时刻多吗?
没别的,忍着扛着,不然还能怎么办。吃得差的、洗不上澡的时候都有。条件上的艰苦肯定是旅行的一部分,是早就做好心理建设的。有人可能会有这种不适感,有一个哈萨克向导告诉我,一个英国摄影师去哈萨克拍荒野,他必须要有西式马桶才能上厕所,所以非常痛苦,到了荒野可没地方给他找能坐下来的厕所。
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很多,比如坐十五六个小时的车,夜里一两点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地方,之前订好的旅馆联系不上,也完全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情况。这时候站在街头就会有点沮丧,也有点兴奋。这种戏剧性的东西对旅行来说是悲惨的,对写作来说又是好事。
有时候,一天下来没遇到合适的人,没找到值得写的东西,连着好几天都没什么收获,感觉自己进不去核心、一直在表面打转。这时候也会有很大的焦虑感。
镜相:你每时每刻都是在一种工作的心态中?
肯定的。个别一两天有度假的感觉,比如在伊塞克湖,一片蔚蓝色的湖泊,有沙滩,还能游泳,不远处是天山,跳到湖里的一瞬间是幸福的;在乌兹别克看到撒马尔罕的建筑也会有这种感觉;看到玄奘看到过的佛塔遗迹,也觉得值得。但是这种时刻很少。
镜相:书里似乎没有特别书写那些惊险的情形,这种情况是没有碰上还是都化解掉了?
我想有过一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在天山徒步的时候,在山谷里去找一片湖,途中完全没有人,那里没有信号,也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帮助,身上没有带补给,天上又开始下暴风雨,脚下的泥泞几乎把我的鞋给淹没了。那时候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还有好远的距离。后来幸亏遇到了当地牧民,坐上他的马才被带了回去。

天山深处的阿尔金-阿拉善山谷
这个地方按当地人的说法,天气好的时候是容易走的,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候也会去踏青。所以我就没觉得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但一是下雨,二是没有当地人那么熟悉山谷的环境。本来听说是三个小时能走到,但没有地图,也没有导航,就不知道走到哪了。
还有一次是,我在塔吉克斯坦,经过一条从杜尚别去往帕米尔的路。那条路在我离开之后的几天,听别的旅行者说有恐怖组织ISIS出没,杀了两个骑行的旅行者。
除了少数时刻,我觉得中亚整体是比较安全的,我很少在那里遇到来自别的恶意。
镜相:中亚五国在外人看来是一片比较相似的地带。你看到了其中的差异性吗?
差别挺大,每个国家之间都有纠葛,互相看不上,彼此也没有任何兴趣。除了塔吉克人是波斯人,其他四国基本是突厥人,这两个民族之间有纠葛。除此之外,国与国之间也有边界冲突,暴乱,族群之间的仇杀等等,关系一直很紧张。记得有一个我有个朋友曾经问过一个乌兹别克人,问中亚这几个国家会推出一个统一的签证,这样不是更便于大家去玩。对方表示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彼此之间的冲突矛盾太多了,不可能达成一致。
镜相:他们身上有与中国人的相似之处吗?
吉尔吉斯斯坦人、哈萨克斯坦人有的跟中国人长得非常像,在吉尔吉斯斯坦街头看到的一个大妈,与上海北京街头看到的差不多。更多的相似是大家对生活的期待,怎么活下去。所以书写他们的故事,我们也能理解,因为生活的本质,各国都是共通的。

镜相:为了中亚的旅行,你掌握了哪些语言?
我在国内报班学过俄语,其他语言比如语乌兹别克语就是买了书,在当地一边走一边用,能说一些简单的是字词和短语,可以问出类似于你叫什么名字,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这样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为了impress一下他们,拉近距离,表示我很尊重他们的文化,也在努力想跟他们交流。实际好处当然是买东西吃饭解决了不少,或者打上车,司机不收我钱。
受过教育的人英语说得都不错。苏联解体之后,英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美国在中亚办过很多学校,比如有中亚-美国大学。他们对英语的重视比我们可能更甚。
镜相:我想聊聊你早期的成长环境和经历。
我是北京人,但好像不太喜欢北京,只不过这里刚好是出生长大的地方,没有特别的感情。我们家在西城区,周围都是机关大院。我爸妈对我没太管过,成长比较比较顺,一路上的是比较不错的学校,不像很多作家有过的残酷青春。这也是我想从旅行写作入手的一个原因。
高三毕业以后,我独自去了一趟丽江和泸沽湖,那时候去那里的游客还不多,回来以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当时的写作还是比较基于自己的旅游体验,真正有旅行写作的概念要到成为记者以后,去国外旅行开始。
镜相:北大中文系是你自己选的吗?
对。上大学之前读了很多小说,先锋派那一批作家,余华、马原、孙甘露都是高中读的,还有国外的海明威、乔伊斯、卡夫卡。选了中文系,现在来看有点后悔,还不如学语言,法律或者是历史。中文系好像没给我什么帮助。
镜相:那中文系给了你什么?
给了我一个文凭。肯定也有人学到很多东西。但如果想当作家,其实跟中文系没什么关系。把文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镜相:你当了很多年的记者,这对你在之后的旅行写作有哪方面帮助?
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比如去哪找人。我做过几年调查记者,很多时候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要找到愿意对你开口的人,这需要技术,需要突破能力。另外一点是对人的关注。做了人物记者之后,觉得应该通过人的故事来反映时代和国家,而不是直接写历史。
镜相:你有过迷茫期吗?
2016年。从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就没工作了。当时大家都在创业,纸媒停刊的很多,媒体人转行的也多。当时那种状态下,我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该追随这个潮流。当时我觉得要么选写作,要么做一个压根跟写作没关系的事,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后来,我接受了自己是文艺青年的现实。创业或者找份每天坐班的工作都不适合我这种人,还是想专注在写作上。其实有的工作跟写作也不冲突,但我没办法,必须得用尽所有能力,才可能让自己满意。
镜相:那时候你就很确定旅行写作有它自己的价值?
当我开始决定写中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写出来会是好看的,信心一直都有。因为没有别人写。对时间的投入,对语言的要求,对旅行技巧的要求,对写作能力的要求,所有的要求加到一起,别人可能写不了。
镜相:你担心人们爱看吗?
我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反响还不错。另外,后来我想通了,反正靠这事发财是不可能的,当然也饿不死。想通之后简单了,一往无前地去做就好了。我希望像喜欢的作家那样,到了七八十岁还在从事旅行写作。比如保罗·索鲁,已经快80岁了,去年还在出了关于墨西哥的游记作品。我也在锻炼,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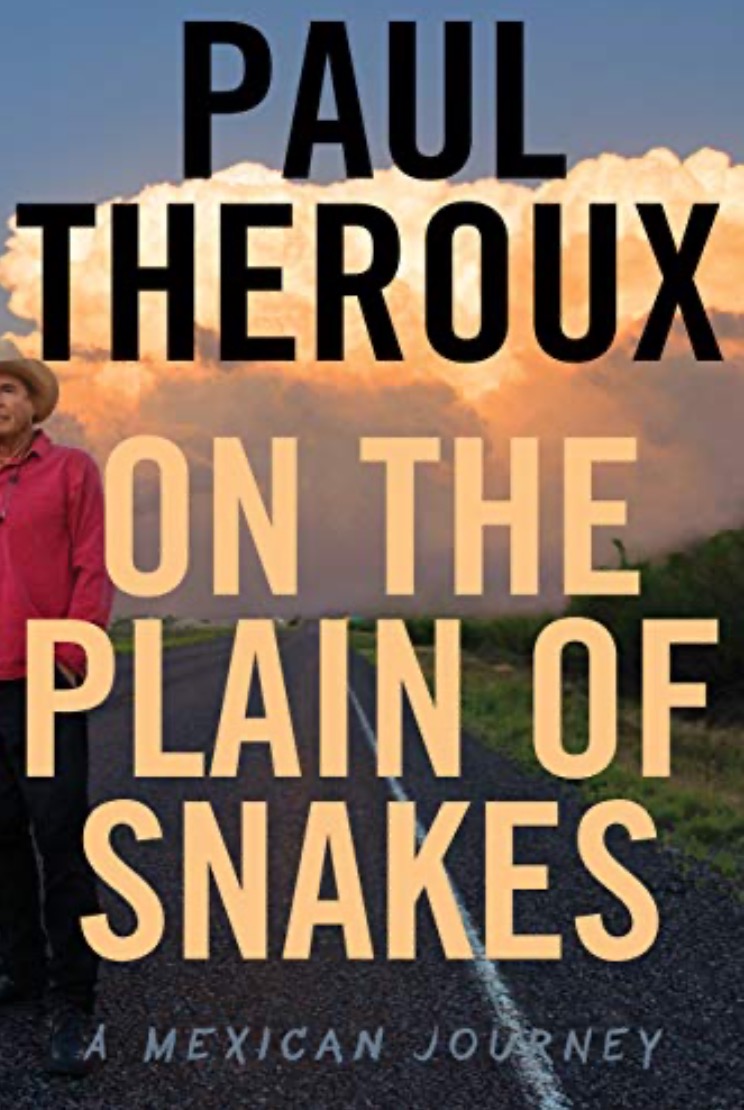
镜相:你觉得身为一名中国的旅行作家,和那些西方作家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我们永远是用自己的文化打量别的文化,我对世界的看法肯定深受到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影响,比如我怎么呈现伊拉克的后萨达姆时代,肯定与西方作家的视角是不同的,我的视角肯定是与中国的文化历史有强烈的关系。传统中国会认为稳定更重要,美国作家肯定会觉得推翻独裁更重要。
镜相:如果没有赞助方的支持,你也会去完成自费的旅行吗?
只要能承担,钱不是阻止我去旅行的障碍。欧美国家有很多这类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国内几乎没有,鼓励旅行写作的奖项也很少,这是遗憾的一点。比如《纽约客》有个记者是90年的,叫本·陶布,他获得2020年普利策奖的作品《关塔那摩最黑暗的秘密》也是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先拿到钱,再去做调查采访。这种机制国内比较少,官方也没有鼓励深度国际报道的奖项,即使有,也很难给我这种自由职业的人。
很多时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重要。其实有能力的中国企业不在少数,很多企业的业务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没想过做生意的基础之一也建立在本国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有没有对这些地方的观察之上。大家也许觉得写作和生意没关系,但如果一个地方有几部中国作家或者记者写成的关于当地的书,那国人做生意也好,或者是跟当地人有其他的往来也好,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镜相:接下来写什么呢,如何避免陷入自我重复?
环黑海和环地中海。我要找有冲突感的地方。冲突感就像一个舞台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上演的各种故事。在好的布景下写出好的故事,是最好的。
环黑海有斯拉夫文明带和土耳其文明带,其中有克里米亚、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每个地方之间都不一样,这一圈走下来,把其中人的故事给挖掘出来,大概想想都觉得挺丰富的。环地中海更丰富,北非,巴尔干,希腊,中东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有历史、有现实、有冲突、有未来,各个维度都有。只要疫情结束,能让我出国,随时可以开始实施。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关税大棒挥向汽车
- 何立峰与美贸易代表格里尔视频通话
- 举报“台独”邮箱收件323封

- 我国首个海洋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完工
- “超大X光机”建设再进一步,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启动带光联调

- 网络流行词,企业规定员工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下班,不能随意加班
- 我国领土最南端位于南沙群岛的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