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杨长云:为什么美国城市总是发生骚乱?
2015年4月19日,非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在被巴尔的摩市警察局羁押一周后死亡,此后一直到5月初,巴尔的摩陷入骚乱。彼时,我正在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访学,得以近距离见证了城市骚乱的发生。虽然学校和我的临时住处远离骚乱爆发的市中心,但骚乱依然波及附近社区。从抗议、骚乱,到掠夺、纵火,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关注事态的进展,并且谈论着各种传闻。五年后,美国中西部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由于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致死,又一次引发全美示威、抗议甚至骚乱,对此,我毫不吃惊。这五年里美国不同城市零星发生的种族冲突事件,以及我在卷帙中读到的四百多年来北美城市骚乱的历史,早已使我对“城市骚乱”见怪不怪,甚至认为,骚乱不过是美国城市的常态。

2015年巴尔的摩的街头抗议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德华·温斯洛·马丁就编撰过一本有关美国各城市骚乱史的书:《大骚乱的历史》(Edward Winslow Mart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iots, 1877)。该书介绍了1877年的“骚乱之夏”,这些骚乱或罢工发生在巴尔的摩、费城、芝加哥、圣路易斯、旧金山、纽约、匹茨堡等城市。J. T. 黑德利则记录1712年至1873年间纽约市发生的骚乱:《纽约市1712-1873年间大骚乱》(J. T. Headley, The Great Riots of New York, 1712 to 187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Co., 1873)。该书详述了北美殖民地时代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间发生在纽约市的11次骚乱,既有种族冲突,又有殖民反抗,还有社会动乱、食品骚乱等。十九世纪末是美国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城市社会问题突出;因为种族主义、民族问题、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等,美国历史上城市骚乱在各大城市此起彼伏。美国城市为什么总是发生骚乱?这个问题在美国学者乔安妮·雷塔诺(Joanne Reitano)所著的《躁动不安的城市:殖民地时代至今纽约简史》(The Restless City: A Short History of New York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Routledge, 2018)中以个案形式得到回答。纽约超越费城、摆脱芝加哥的竞争,成为美国第一大城市,进而成为全球大都市。在其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鲜为人知的辛酸、丑陋、冲突,而这些背面又与纽约荣耀的正面一起被记录、流传。
《躁动不安的城市》以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为起始,涵盖从1609年到2015年的时间跨度,突出每个时代的主要发展动向。每章均以大事记和序言开篇,内容着重关注能够突显城市变革的人物、事件和运动。全书一共九章,每一章的标题都反映了纽约在该时期的典型特征。正因为如此,中译本将书名译为《九面之城:纽约的冲突与野心》(以下简称《九面之城》,所引页码为该书页码)而且,每一章都包含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政府和警察的角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平等的内涵、改革的范围和社群的意义等。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亦仍无定论,那些历史上的不和谐音符依旧回响在当今纽约乃至全美的上空。从通史意义上来说,本书所涉内容并不全面,但如作者所言,“只为探讨纽约市的特殊性格,探访这个具有独特活动,兼具多样性、创造力、韧性和全国影响力的大都市”。读罢此书,书中的文字快速地在我脑中合成为一个个历史图景,每一个历史图景都离不开两个字:骚乱。而这些历史图景及其蕴含的张力以多个面向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美国城市总是发生骚乱?”这一问题。“不满之都”纽约提供了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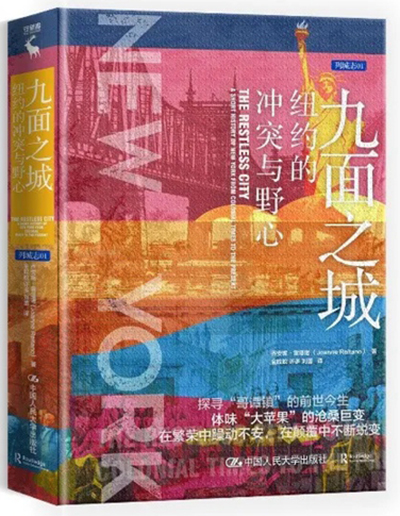
《九面之城:纽约冲突与野心》
第一是种族或族裔因素。雷塔诺贯穿在此书中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冲突是纽约永恒的主题。因为纽约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是多族裔在合作、竞争或冲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纽约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作为殖民据点建立之初,骚乱主要是在殖民主义话语下,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例如,在1655年,一个荷兰人射杀了一个在他围栏果园里偷摘桃子的印第安女人,引发了长达三天的暴力冲突,被称为“桃树之战”,是欧洲移民的殖民要求与本土印第安人自保要求之间的冲突。当印第安人不构成对白人的主要威胁后,黑人成为种族骚乱的主角。作为北方自由城市,纽约却存在奴隶制度。纽约的奴隶制度催生出无数的种族和现实困境,建国前发生过两起典型的骚乱事件。1712年奴隶叛乱和1741年对奴隶蓄谋叛乱的血腥镇压。这些事件暴露出纽约的种种缺陷:一个向往自由的殖民地却追求非自由政策,一个利润至上的群体却被经济迫害而产生的问题所困扰。还在殖民地时代,奴隶制度就揭示了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局限。(第25页)
到十九世纪中叶,北方的种族偏见被一些反战派利用,他们警告,如果废除奴隶制度,大批被解放的黑人将北上冲击白人劳动力市场。部分雇主曾雇用黑人来破坏白人的罢工。1862年,纽约、布鲁克林、布法罗、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出现白人劳工针对黑人的骚乱和袭击。1863年4月,爱尔兰码头工人在纽约连续三天发动针对黑人的袭击。进入二十世纪,1900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名黑人女性在第41街和第八大道交界处等待男友亚瑟·哈里斯时被便衣警察怀疑为妓女。赶来的哈里斯与警察发生冲突,并刺死该警察。之后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于是大规模的骚乱爆发。一万多名白人暴民在西区第20街到第30街之间袭击黑人。主流报纸抨击警察的暴行,说:“在这个城市中,有色人种多年来一直被警察粗暴、不公正地对待。”(第210页)1919年则经历“血腥之夏”,从得克萨斯州到内布拉斯加州的26个城市爆发了种族冲突。马库斯·贾维认为,黑人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被平等对待。但是,雷塔诺提醒读者:在哈莱姆和布鲁克林,本土出生的黑人与从加勒比和美国南部搬来的黑人之间也存在着冲突。种族骚乱揭示出的问题就是瑞典学者冈纳·米达尔所指出的,“美国困境”的核心问题仍然挥之不去,即在一些人奉行“自由、公平和……机遇”的同时,却剥夺了另一些人的相同权利。
第二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虽然冲突是永恒的主题,但雷塔诺显然在书中也贯穿着另一条甚至比种族冲突本身更重要的线索,即自由理论和自由主义传统。她认为,冲突推动了自由理念和制度的诞生。冲突是富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对施托伊弗桑特专制统治的反抗、莱斯勒反叛、曾格案、国王学院争议,所有这些事件都使自由主义日趋合法化。这些非暴力冲突塑造了纽约的特殊个性,这一特性已经成为多元化、宽容、世俗主义和民主自治的标志和典范。纽约是“自由之子”组织的诞生地,1765年《印花税法案》导致的骚乱是一次维护自由原则的冲突。此举动摇了英国的统治,使地方自治愈趋合法化。在取得胜利后,纽约人竖起了“自由之柱”,传达出的积极向上的意义使城市社群更加团结。作者认为,纽约越是珍视自由,就越能在面对国内外敌人侵害时发起反抗。奴隶制、莱斯勒反叛、印花税危机、麦克杜格尔事件,以及革命后的骚乱,都反映了纽约作为冲突中心的事实。(第49页)自由的传统在20世纪中叶后仍然是纽约特性之一。纽约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共产党议员的城市,即本杰明·戴维斯。1945年,戴维斯再次当选市议员,他的支持者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甚至还包括坦慕尼协会成员。人们有理由相信,纽约正在成为“美国最自由的城市”。1964年以后,“白人反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语境,纽约自由派担心自由主义消失,这也是他们支持约翰·林赛当选市长的重要原因。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为代表,学生的激进抗议运动与自由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而学术界以外的人更多地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激进主义。白人族群针对民权运动,以及运动带来的对峙和变革发起反抗。很多白人并不接受全国都应为少数族裔的困境负责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少数族裔是自作自受,同时担心帮助别人就意味着损害自己的利益。
关于这一点,人们容易想到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关于自由权利的规定。果不其然,雷塔诺在该书第八章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她说:纽约社会契约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它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一以贯之的支持,这铸就了纽约对差异和异议的宽容传统。久而久之,这种罕见的城市精神孕育出范妮·莱特、亨利·乔治、爱玛·戈德曼和马库斯·贾维等拒绝墨守成规的人。(第364页)
城市骚乱发生的第三个因素是阶级冲突。在施托伊弗桑特时代,他推出了很多广受支持、为大众谋福利的措施,如制定消防法,以及建立学校、邮局、监狱和救济院。他还组建了一支由九人组成的夜间安全巡逻队。但他推出的一些旨在加强社会控制的措施却不得人心,比如要求居民必须去教堂做礼拜,周日的工作和娱乐活动都要受到限制,斗殴、同居、同性恋者均将被施以严酷体罚,他还要求所有酒馆和旅店在晚上实行宵禁。这些措施引起广泛不满。他还试图对经济进行更多管制,如设立工资、酿酒、烤面包、屠宰标准。他还禁止猪和羊在街道上游荡,无视这些牲畜对家庭维持生计的重要性。对底层移民社群来说,个体主动性、自由经营和商业机会是基本信条,而过于严苛的管制则粉碎了这一社群基础。雷塔诺还分析了1796年凯特尔塔斯骚乱,认为阶级冲突是这次骚乱的最主要特点。到十九世纪初,城市管理者采取措施规范城市发展依然会引发骚乱。比如纽约市政府捕杀在街道上游荡的猪,就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引发多次骚乱。参加骚乱者包括屠夫、手工匠、女性、黑人、爱尔兰移民,是华盛顿·欧文笔下“像猪一样的”大多数人。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街上游荡的猪有碍观瞻。但对于纽约的穷人来说,猪却是家庭食物和收入的来源。无产者试图继续坚持公共街道和公共土地为大众使用的传统;有产阶级却拒绝接受共有产权这一古老的概念,他们坚持拥有私有产权。纽约市阶级之间的紧张局势愈演愈烈,在1834年达到巅峰,这一年被称为“骚乱之年”。这一时期,美国多个城市都爆发了骚乱。主要反映大众民主的历史特征,凸显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冲突。
1849年阿斯特广场骚乱也典型地体现了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冲突。骚乱是由两个代表不同阶层品味的演员引起的。英国演员威廉·麦克雷迪的舞台风格是贵族风范,代表精英阶层的品味;美国演员埃德温·福里斯特则受到下层观众喜爱。5月7日,一群“衣着花哨、满腔热血的中产阶级青年”在麦克雷迪表演的阿斯特广场剧院闹事,他们痛恨麦克雷迪刻画出来的精英人物,带领人群开始向舞台投掷臭鸡蛋和马铃薯。纽约上层阶级被激怒,派出警察保护麦克雷迪。结果酿成骚乱,造成士兵向人群开火。当时有一派观点强烈地认为,亟须通过压制骚乱、维护法律和保护私有财产来拯救民主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纽约的问题在于政府控制不足。一位牧师认为,举全州之力来镇压“废奴运动骚乱以来最令人发指的骚乱”是正当合法的。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应享有抗议的权利而无须担心生命安全,民事和军事领域应当被明确划分,生命权也应凌驾于财产权之上。从这个观点来看,阿斯特广场骚乱又可以说是政府管制过度的例证。(第113-114页)这场骚乱看起来是关于两个演员之间的争吵,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关于权势、地位、种族等复杂社会问题的戏剧化表现,是纽约不同阶层之间“最直接、最激烈的冲突。”
政治纷争也是城市骚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57年6-11月间的三场骚乱是当时纽约社会、政治和经济紧张情绪自然发展的结果。骚乱不仅包含了城市的内部斗争,也包括了纽约市与纽约州,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角力。当时,地方自治问题相当急迫,而被政治和经济利益复杂化的种族关系紧张则是雪上加霜。骚乱蔓延到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此外,骚乱还反映出纽约在国家体系中的困境:纽约市只是纽约州的一部分,而不是拥有自治权的城市。纽约发展得越快,它与纽约州的冲突就越激烈。(第118页)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性骚乱事件是1863年《征兵法案》引发的骚乱。它“准确地描绘出当时正处于内战煎熬之中的美国,以及被阶级、种族、族裔政治和经济冲突所撕裂的城市的痛苦。”(第127页)骚乱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征兵法案》是国会共和党提出的,正如州共和党一样,这种做法似乎侵犯了纽约的城市自治。在整个骚乱中,纽约缺乏领导控制力的问题暴露无遗。亲共和党报纸抨击民主党州长霍雷肖·西摩公开宣称征兵非法,从而撺掇暴力活动。共和党还批评西摩在纽约冲突正酣时在新泽西无所事事。当时的纽约市市长、共和党人乔治·奥普戴克在骚乱爆发前两天则袖手旁观。当然,《征兵法案》骚乱也不仅仅有政治骚乱的线索,也有阶级冲突、种族纷争的因素。
1871年的奥兰治冲突是针对十九世纪末纽约市政腐败的。冲突双方是爱尔兰新教徒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是本土人对移民,是中上层阶级对劳工阶级。这一冲突开始动摇特威德帝国的统治。《纽约时报》称这起冲突为“坦慕尼骚乱”,目的是篡夺纽约的城市权力。
事实上,所有的骚乱都或多或少与经济状况有关,但有些城市骚乱则确乎主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比如,1902年,由于按犹太教规屠宰处理的肉类价格持续上涨,正统犹太教妇女们在纽约下东区发起一场长达三周的抗议活动,上城区、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随后也爆发了类似示威。雷塔诺指出,接下来的十年里,各类冲突不断袭扰纽约。1917年2月,食品短缺和高物价带来又一波骚乱潮。食品危机从纽约扩散到其他州,成为全国性话题。1902年和1917年爆发的食品危机反映进步主义运动的基本面貌,同时展示出这场运动的优势与不足。一方面,改革的影响具有明显局限性。反托拉斯法案固然不错,却没能成功分拆大部分托拉斯,也未能解决普通民众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另一方面,大众热情推动了公民对进步主义运动的参与,同时也将这种革新精神扩散到中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移民和女性也开始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些人超越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开始突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男性与女性、本土与移民之间的界限。(第219页)
另一个更典型的经济骚乱发生在1975年4月。当时,纽约所有银行都拒绝再购买市政府发行的债券,市政府濒临破产。直到1977年,随着一场大范围的停电,城市骚乱爆发。与此前的骚乱不同,七十年代的城市骚乱并非围绕种族议题展开的,而是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普通人发动的。当时的失业率高达30%,这一数字在少数族裔男性青年中更是高达60%。这次大停电还因为发生在炎热7月的一个晚上九点半,几乎在停电的同时,骚乱就发生了。纽约历史上第一次,五大区所有贫民窟同时发生骚乱。城市骚乱的一般形式再一次重现:趁乱打劫、纵火,商店被洗劫,然后被付之一炬。其中既包括白人的店铺,也包括黑人的店铺。人们明目张胆地抢劫衣物、食品、家用电器、家具,甚至汽车。从1902年的食品骚乱到这次的大停电骚乱,人们不得不正视《纽约时报》的呼吁:是时候直面种族和贫困等长期问题了。全国城市联盟执行主席弗家·E. 乔丹更是敦促人们,不要将骚乱仅仅视为纽约的悲剧,这不是一件技术性问题,而应该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冲突。

1977年纽约大停电期间,人们从百老汇商店抢东西
第六个因素是文化价值观念。十九世纪中叶,纽约的文化活力对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有补充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城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和战争令其文化活力日益复杂化,其结果就是阶级、种族、族裔、教育、劳动力和自治相关的新一轮冲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纽约一半被捕的嫌犯是爱尔兰天主教徒,70%的受救济人群来自爱尔兰。为了应对本地街头黑帮的欺压,爱尔兰人组织自己的帮派进行反击,黑帮开始盛行,又加之酗酒文化盛行,共同塑造了十九世纪中叶纽约强大、无法无天、暴躁的城市形象。(第105页)文化紧张感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继续发酵,新教教徒决意使爱尔兰天主教徒改变信仰,他们在向穷人发放面包的同时,也发放圣经,在给他们提供救济的同时,也发出宗教性警告。结果就是1853年的三场骚乱。纽约当时的反天主教、反移民的本土主义情绪非常复杂。它利用了由显著的人口成分变化带来的族群焦虑感,辅之以种族和宗教差异带来的分歧。人口和文化因素进一步复杂化,起因是工作竞争,背景则是频发的经济衰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主义通过将天主教移民妖魔化,以及歌颂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取得强大的心理优势。(第107页)
二十世纪初,纽约市的波希米亚反叛震惊美国,格林威治村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聚集使得社会控制让步于年轻文化、避孕、自由言论和创新精神。《大众》(The Masses)杂志代表了波希米亚反叛的全部精神。马尔科姆·考利指出,这是美国首个挑战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文化运动,将“波希米亚与资产阶级对立,将贫穷与发达对立”(第203页)。该杂志将进步主义运动在文化层面推向了极致,同时也拓展了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维度。《大众》与波希米亚反叛、摄影独立运动和垃圾箱画派一起,确立了纽约作为美国文化革新源头的地位。纽约在历史上是多元和宽容的避风港,也因此是新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合理诞生地。在进步主义时代,纽约激励了美国人去重新审视一些最根本的文化和社会定式。
雷塔诺揭示的第七个因素是深层次的种族主义,这里与前文所述种族或族裔因素有区别。开始所谈的2015年巴尔的摩骚乱和2020年的明尼阿波利斯骚乱,黑人城市骚乱的方式都相差无几,袭击警察、砸商店、抢商品、纵火等。这种特征的产生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城市骚乱有关。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作为纽约市市长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城市改革。但是,在其任内的1935年和1943年,纽约爆发了两起大规模城市骚乱。与传统的白人针对黑人的种族冲突不同,这两起骚乱都发生在黑人社区内部,并着重表达了对白人社会的愤怒。黑人遭受的长期歧视、以及黑人的抗议传统,是滋生骚乱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拉瓜迪亚在1935年骚乱发生后,比他所有前任都采取了更多的种族平等措施,但仍然没有阻止第二起骚乱的发生。就如阿兰·洛克评论的那样,骚乱的导火索并非单个事件,而是“长久以来的心理状态”。霍华德大学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弗雷泽领导的哈莱姆情况委员会认定,针对警察的憎恶长期积聚,以至于任何“火花”都能轻易被“引爆”。(第267页)委员会警告,在哈莱姆地区日益增加的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委员会建议解决哈莱姆“最根本问题”才是正道,包括保障黑人工作机会,提高工资水平。委员会还呼吁市政府对房租进行控制,为黑人提供与白人同等条件的学校设施。委员会敦促哈莱姆医院员工应实现完全种族融合,并新建一所医院。委员会还警告警察部门不应再对警员暴行持包庇态度,并建立一个公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关于警察行为的投诉案件,一旦发现警察确定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将严惩不贷。(第268页)
这两场种族骚乱标志着美国进入一个新时期,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城市骚乱埋下伏笔。与早期黑人主要处于防御态势的冲突不同,哈莱姆居民采取了攻势,针对社区内的种族歧视现象发动攻击,尤其是白人警察和白人商铺。这两场冲突也被称为“商品骚乱”,因为骚乱者主要针对财物进行破坏,而非以前种族骚乱中以攻击人为目的。这种新趋势反映出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新动向。骚乱改变了美国关于种族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应对种族议题的紧迫性。
除了以上七个主要因素外,雷塔诺在《九面之城》中也谈到了女性主义和空间争夺。首先,她揭示女性地位自殖民早期以来是下降的。在殖民地初创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女性可以成为工匠、店主和商人。相反,独立战争后的法律却限制了女性的选择。1793年爆发的妓院骚乱诠释了当时女性面临的困境。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波针对妓院的骚乱,醉酒的男人冲进妓院,砸毁家具,殴打并扬言要强暴妓女。其次,从1916年《分区法案》到“罗伯特·摩西帝国”,到太阳城,公共住房问题,甚至公园、海滩等公共空间,纽约城市骚乱中的空间冲突始终与其他因素相伴随。比如,1986年12月皇后区的霍华德海滩骚乱;1988年8月的汤普金斯广场骚乱;或者仅仅像1989年8月,一个16岁黑人男孩在布鲁克林的意大裔社区被杀害。以及更典型的是1991年8月,黑人和犹太人在布鲁克林的种族冲突。犯罪、住房和犹太人在公共场所的宗教活动,以及针对社区委员会的控制都是骚乱的焦点。虽然导火索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些偶发事件,但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城市空间不足、空间控制权的争夺。
二战结束后,纽约被卷入冷战对抗。五十年代,针对城市发展规划,纽约各个族群间的紧张情绪日益升温,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六七十年代,围绕政治、种族、教育、同性恋权利、住房和战争的冲突达到顶峰。可见,城市骚乱的成因日益复杂化。纽约所有的痛苦都暴露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对矛盾:本土居民和移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乡村和城市、共和党和民主党、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穷人、工人和雇主、警察和市民之间的分裂,这些矛盾和困境凸显出国家发展的潮流,也预示了这个国家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
进入二十一世纪,纽约在很多方面都变得不同。“9·11”“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化”“自然灾害”“新冠疫情”等都对纽约的城市秩序、安全、身份认同进行了重新定义。许许多多的问题令人怀疑纽约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机遇。因为它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分化的城市:贫富分化,市中心与郊区分化,不同族裔分化。社区的中产化、警民关系、教育改革、城市与联邦的关系都有待解决。人类的历史和纽约的历史一样,是正面与负面、进步与反动、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的迷人结合体。尽管未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雷塔诺直到著作的最后仍然很坚定地认为:纽约的躁动不安将是纽约最宝贵的财富。而纽约历史上发生的城市骚乱是美国城市骚乱的缩影,其发生骚乱的种种原因具有典型意义。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