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读︱欧阳晓莉评《巴比伦》:多元的材料与笔法
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近东研究领域素有非专业学者撰写通俗读物的传统。代表作有C. W. Ceram在1949年首次出版的Götter, Gräber und Gelehrte: Roman der Archäologie。它的最新中文译本《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由张芸、孟薇基于德文原版完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C. W. Ceram为库尔特·W.马雷克(1915—1972)的笔名。他是罗沃尔特出版社的记者和总编辑,曾发表了多部通俗专业著作,该书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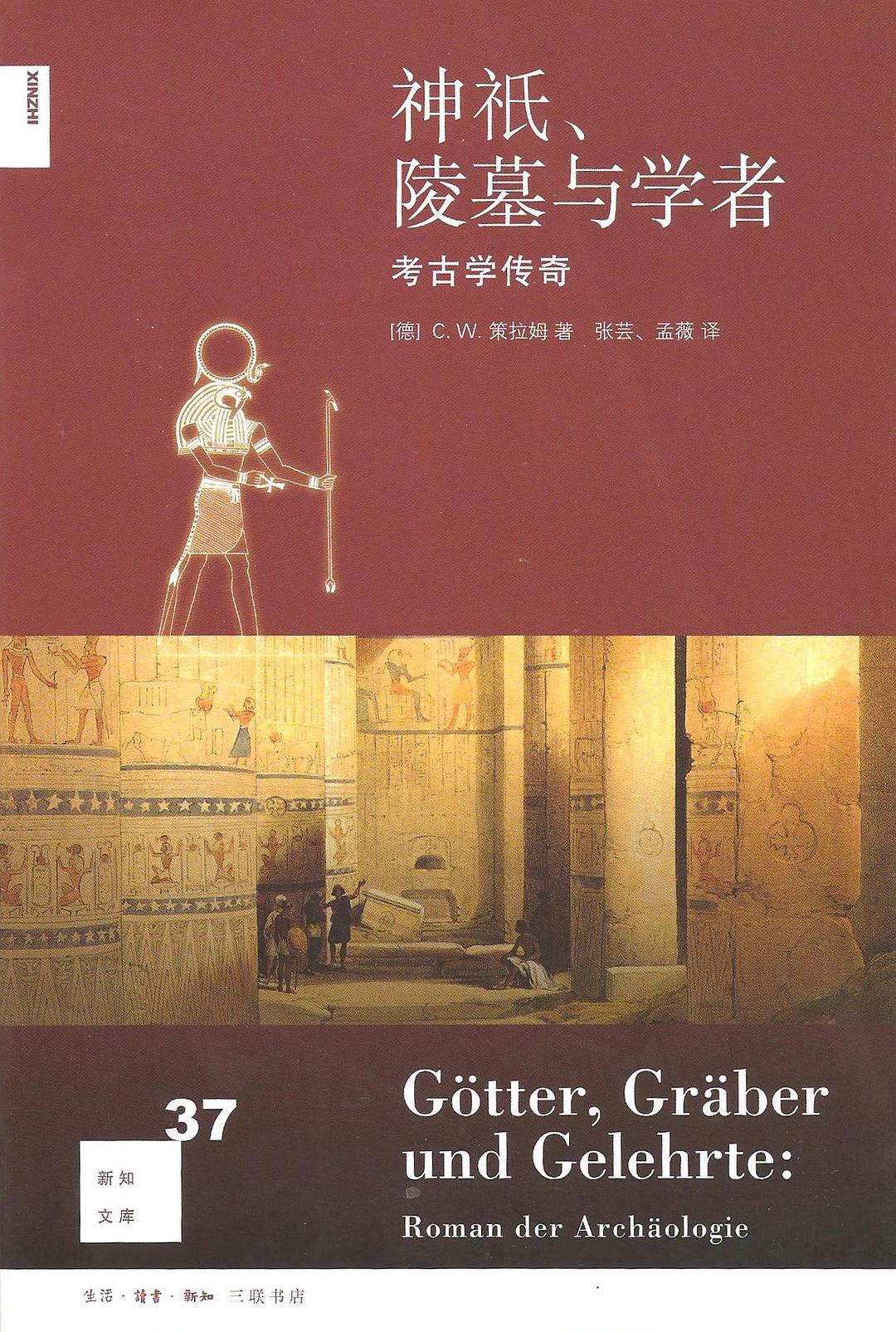
《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法国学者Georges Roux(1914—1999)在1966年首次出版的Ancient Iraq(《古代伊拉克》)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此类作品。他出生于一个法国军官家庭,9岁起随父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生活了12年。后来他在巴黎学医行医的同时,孜孜不倦地研习古代近东文明。1950年他加入伊拉克石油公司任首席医生,在卡塔尔和伊拉克先后工作了9年。除《古代伊拉克》之外,他还在两河流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若干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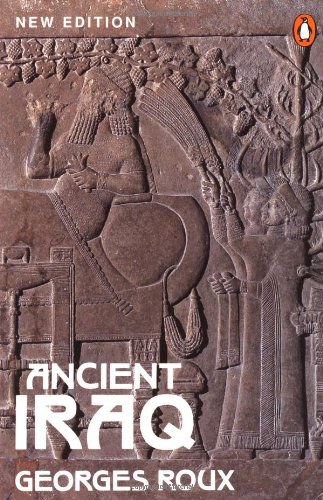
《古代伊拉克》第三版
本文所评的《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一书,其英文原版出版于2012年。作者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1937年出生于维也纳,自1970年起在BBC任职长达25年,曾任BBC全球服务频道中亚事务部负责人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英]保罗·克里瓦切克(Paul Kriwaczek)著,陈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
本书第一章为导言,其余九章按时间顺序组织内容。第二到四章围绕着古代两河流域的史前文明展开,第五到十章依次讲述了城邦称霸、第一个统一王朝、苏美尔文化复兴、古巴比伦王国、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对两河流域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会注意到上述名单中缺席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加喜特王朝(约公元前14—12世纪)。作者仅在第八章末尾论及古巴比伦王国亡于赫梯军队的进攻时,寥寥数笔带过了赫梯军队撤退回国后加喜特王朝的统治。
导言部分充分体现了作者从事新闻工作的背景。他简要回顾了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继承者——伊拉克——自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两伊战争(1980—1988)、两次海湾战争(1991和2003)和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2006年12月30号被处以绞刑。本章以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结尾,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也呼之欲出——以史为鉴,通过考察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来理解现当代伊拉克的局势和动向。
第二到第四章聚焦于两河流域的史前文明,此间该地区居民经历了两次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首次变革始于约公元前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又称农业革命),生活方式由狩猎采集转变为农耕定居。包括两河流域北部在内的“新月沃地”因此被誉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约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南部遗址乌鲁克又发生了城市革命:人口大规模聚集居住,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贸易和商业兴起,阶级分化,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字的雏形出现。乌鲁克因而获赞为“人类最早的城市”。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文字材料尚未出现,仅能借助考古遗迹和源自后世的传说与神话来构建当时的社会生活。作者选取了两河流域最南端遗址埃利都(Eridu)的神庙作为史前考古遗存的代表。虽然该神庙供奉的神灵已无从知晓,但根据后世传统,苏美尔人的智慧神恩基(阿卡德语名字埃阿)就诞生于埃利都。在苏美尔神话《伊南娜与恩基》中,女神伊南娜把父亲恩基灌醉后,成功地从他那里盗走了110余种“道”(苏美尔语me,可理解为文明要素,见拱玉书论著)并带回乌鲁克。恩基先后派出六波追兵也未能将其追回。文明从此降临该城。
随着楔形文字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发明,两河流域跨入了历史时代。早期的楔文泥板出土于乌鲁克的伊南娜神庙区,记录简单的经济管理活动。在后世作品中,《吉尔伽美什史诗》生动地反映了早期的城邦生活和社会结构。它携手乌鲁克的遗迹和文物(尤其是瓦尔卡石瓶和乌鲁克女神像,瓦尔卡是乌鲁克的现代名称),使我们得以窥见公元前四千纪乌鲁克城市革命的过程与结果。神庙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早期祭司可能凭藉其沟通神界与人界的特别职能获得了政治上的特权,进而成为城邦的首领即“祭司王”。然而乌鲁克的强大与扩张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受挫:以神庙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崩溃,与周边地区(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的人员交流和商贸往来路线被切断。原因可能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降水减少,外敌入侵和内部矛盾又加剧了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一枝独秀的乌鲁克城邦就此衰落了。

《吉尔伽美什史诗》泥版
城邦、王国、帝国
自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起,两河流域南部进入了小国林立、互相争霸的城邦时代,城邦数量一度超过三十个。一个城邦通常包括一座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和环绕四周的农田及村庄。城邦之间时常因为争夺水源和灌溉设施而爆发军事冲突。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霸主地位在不同城邦间易手,“你方唱罢我登场”,类似于中国古代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时代。在武装冲突中,城邦首领征战沙场、保家卫国的责任日益突出,赫赫战功取代了沟通人神作为王权合法性的来源。有的城邦首领开始采用“卢伽尔”(苏美尔语lugal,本意为“高大的人”)的头衔,它后来成为了两河流域国王的标准称号。该时期的乌尔王陵以其价值连城的陪葬品见证了社会分化的剧烈程度:城邦统治者死后不仅坐拥巨额财富,还享受着人殉的陪伴。
结束城邦争霸、一统两河流域南北部的是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50—2154)的创建者萨尔贡。他原是基什城邦国王的侍酒官,篡位上台后首次建立了统一王朝。为笼络南部苏美尔各古老城邦的人心,他委任自己的女儿担任当地月神的祭司。他的孙子纳拉姆辛则反其道而行之,自我神格化,将自己抬高到神的地位。后世传统对两人形象的塑造迥然不同:萨尔贡的身世与《旧约圣经》中的摩西类似,都在神的庇佑下成就了一番伟业;纳拉姆辛则备受诅咒,他僭越人神界限的行为被认为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尽管阿卡德政权亡于他的继任者在位时,被来自东部伊朗山区的古提人所灭)。
随后兴起的乌尔第三王朝以流存于世的大批文献著称,初步统计已超过十万块泥板。文献数量众多的原因是该王朝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此外,不同于阿卡德王朝的官方语言阿卡德语(最早的闪米特语),乌尔第三王朝使用了城邦时期的苏美尔语,因此也被称为“苏美尔复兴时期”。
得益于《汉穆拉比法典》的知名度,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2000—1600)是读者最熟悉的时代。它代表了两河流域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诸多作品现存的抄本都出自这一时期。其中的讽刺文学独树一帜。在一篇作品中,“一个犹豫不决的主人向他的奴隶提出了几个不同的想法,旋即又改变了主意,但可笑的是,他的奴隶总有办法迎合主人的决定”(第253页)。
略过加喜特王朝后,本书直接进入了公元前一千纪的帝国时代。首先兴起的是源于两河流域北部的新亚述帝国。这并非亚述人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早在公元前两千纪早期的古亚述年代就有一批商人前往安纳托利亚经商,把纺织品和锡运到那里,交换为金银后带回两河流域。中亚述时期(公元前两千纪下半期)的法典则以其残酷而闻名,其中关于女性外出时需要蒙住头部的条款可能影响了后世穆斯林女性戴头巾或面纱的传统。新亚述帝国的建立始于公元前9世纪,经历了数代国王的励精图治(抑或穷兵黩武)后在公元前7世纪实力达到巅峰,但不久就在来自东部山区的米底人和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人的夹击下覆灭了。作者把新亚述帝国的意识形态概括为“一个王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

亚述猎狮浮雕
建立帝国最迅速、最便捷的途径是征服一个帝国。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6—539)征服新亚述帝国后,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后者大部分的势力范围。此模式也再现于后来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建立。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使用字母文字的阿拉姆语(Aramaean,即《圣经》中的亚兰语)因为其书写方式简便(用墨水写在陶片或纸草上)和符号数量较少,逐渐取代了使用楔形文字的阿卡德语,最终导致以楔形文字为载体的两河流域传统文化走向衰落。
虽然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民族征服另外一个民族的叙事方式来框定波斯帝国对两河流域的征服,但后者的本土传统在波斯早期并未中断,巴比伦城是波斯帝国的王都之一。尽管如此,波斯时期阿拉姆语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楔形文字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只保留其作为宗教和学术语言的有限功能。年代最晚的泥板是公元1世纪的一份天文观测报告,此后楔形文字正式消亡。
多元的材料与笔法
有别于以传世文献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古代近东文明研究在其发轫之际就以出土文献为基础,所以研究者非常关注文献的出土语境乃至考古学的相关进展。加之研究对象年代久远且缺少传承,对文字材料的准确理解往往需要借助图像资料和考古遗迹,这进一步推动了对艺术史和考古学相关知识的利用。此外,源于“他者”的文献——尤其是《旧约圣经》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保存了诸多关于古代两河文明的历史记忆,能够为特定问题的论述提供信息。因此,书写两河流域历史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相关材料。本书在取材上就充分体现了两河文明研究的上述特点,尤以最后一章第十章(“薪火相传:终结与启程:公元前700年以后”)为甚。
作者行文时自如地转换于客观叙事、主观感想和史料引用之间,三类内容浑然一体,提供了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在史料征引上,第一人称的王室铭文以及神话故事、英雄传奇和讽刺小品(本书第237—239页引用的故事《校园时光》,它的中文翻译和评注已由拱玉书发表;详见其《最早的校规》,《国外文学》2019年第4期,第136—143页。)都是其亮点所在。这些引文都出自专业学者的现代语言译本,其准确性和可信度得以保证。
商榷之处
在本书中,作者纵笔挥毫,大胆评议了两河流域文明自始至终的发展特色和兴衰成败。其中有若干观点或结论,笔者不敢苟同,在此试举两例以求教于方家。
作者的非专业背景可能导致了他在应用某些现代术语时过于随意。在第二章末尾(页46),作者试图揣测苏美尔神话《伊南娜与恩基》的创作动机,提出了“这也可能是为了强调文明的实现必然要依靠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解放,并以此来解释或证明城市生活中性放纵的合理性”一说,还认为“当时的城市中不乏交际花和妓女,同性恋者和异装癖者”。“纵观历史,这种性放纵的思想总为乡村居民所批判,其中自然也包括古代的乡村居民。”姑且不论上述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即使在语文学层面上,“交际花和妓女”以及“同性恋者和异装癖者”等词语的翻译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作者随后提及《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妓女”莎姆哈特时如出一辙,将她形容为“厚颜无耻”。
作者在论述个别问题时行文前后不一致且遗漏了关键史料。在第四章《大洪水:历史的休止》中,他首先声明“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的分界点是大洪水,口述传统和文字记录的分水岭也是大洪水”(页84)。在第91—92页,他进一步解释了大洪水的故事传统在两河流域产生、发展的原因是该主题在两河文明的历史观中具有关键的结构性作用。“对于苏美尔人而言,大洪水是文字出现前和文字出现后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也是民间传说的时代和人类记录历史的时代的分界点。更准确地说,它是划分美索不达米亚的两大文明阶段的分水岭……”这两大文明阶段,即上文所述的乌鲁克城市革命和城邦争霸的早王朝时期。后一引文再未提起“神话时代”。
除了《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脍炙人口的洪水故事,“洪水”还出现在关乎两河流域早期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苏美尔王表》中。现存的最早抄本来自公元前两千纪早期,记载了从王权伊始一直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两河流域诸王朝的王位传承情况。根据其记载,当王权首次从天而降后,来自五个城邦的八位国王共统治了385200年(平均一位国王的统治长度近5万年),之后大洪水降临。当王权再次从天而降后,乌鲁克是继基什之后的第二个统治王朝。洪水之后的国王其统治时间从一两千年到几百年乃至几十年不等。显然,部分国王依然属于所谓的民间传说的时代。
可见,作者仅仅基于考古遗存提出了洪水叙事在两河流域文明史上的分界点作用(笔者认为不无道理),却忽视了同类叙事也出现在《苏美尔王表》这样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中。而且他的分界点一说在“王表”的语境中似乎并不成立。
此外,译者在翻译部分常用术语时未采取约定俗成的译名,如:第70页起的cylinder seal应为“滚印/圆筒印章”(不是“滚章”);第77页的clay token应为“陶筹”(不是“泥制标记”,参见[美]丹妮丝·施曼特-贝瑟拉著,王乐洋译:《文字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8页起的重量单位shekel依《和合本圣经》应为“舍客勒”(不是“谢克尔”);第184页的“青铜”不是一个头衔,应为“持青铜者”(苏美尔语zabar-dab);第186页的重量单位依《和合本圣经》应为“弥那”(不是“迈纳”)。译文中还有少量错误,如:第7页舒什距两伊战争前线的距离应为“3000多米”(不是“3000多千米”);第48页的脚注2中,苏美尔语的长度单位danna在英文中常译为league,1里格约合10千米(不是“4.8千米”)。
译者在个别地方对原文的理解欠准确。如第120页,“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城,……这种转变就是通过建造一个绝世奇观——一座惊人的宗教建筑来实现的。”后半句原文为“[t]he transformation seems to have been achieved by mounting an outstanding dramatic spectacle, a stunning piece of religious theatre”。联系上下文,划线部分意指乌尔王陵,此处比喻为“一出惊人的宗教戏剧”(非“宗教建筑”)。在第289页,“对神的超然性的信仰取代了对神的内在性(immanence)的信仰。”Immanence一词译为“内在性”在上下文中语意不通。该词在宗教语境中指神祇无所不在,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中。在第288页上作者对同一词的翻译“无所不在”更为准确。
本书译者非从事两河流域研究的专业学者,出现上述疏漏在所难免。笔者不揣冒昧,大胆建言出版社或考虑延请专业人士审读整部译稿,力求术语的翻译更合乎约定俗成的规范,同时能够反映国内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
虽然本书存在若干可资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它是一本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极具个人见解的著作。译者成功地在译文中再现了原著的上述特色。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