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诗人的赃物与战争——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
【编者按】
2020年8月26日,是法国著名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诞辰140周年。下文摘自作家李炜的新书《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作对的西方诗歌史》,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年8月26日-1918年11月9日)
赃物
“我从没见过这家伙。”毕加索忍不住抽动起鼻子。
检察官只问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他是否认识坐在他面前,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没洗澡的男人。
艺术家走进审讯室的那一刻,这男人顿时神采飞扬;听到答案后,脸色又晦暗了下来。憔悴苍白的他,确实不再像阿波利奈尔——巴黎先锋派中的享乐达人。此外,他应该比谁都清楚:祸不单行。每每如此。这是他人生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使连他的拜把兄弟此时都抛弃了他,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好在检察官是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艺术家的伪装。更何况,经历了一连几天的严厉审问,而且没有他心爱的烟斗安抚情绪,萎靡不振的阿波利奈尔早已招认了。所以毕加索才会局促不安地坐在这里。到头来,诗人还是供出了好友的名字。

阿波利奈尔肖像,1910年由梅金杰(Jean Metzinger)绘制
至于两人的窘况,简直是一出滑稽剧。一出几乎只有阿波利奈尔才有可能想出来的戏剧,闹哄哄地搬上舞台,或直接放在《被杀害的诗人》这种讽刺小说里。只可惜故事先发生在了他身上。情节大致如下:
在一家不入流的金融杂志供职期间,阿波利奈尔结交了一个和他一样玩世不恭的朋友。后者遇到了经济方面的困难——他试图敲诈杂志老板,最后拿到的却是一张解雇通知单——阿波利奈尔二话不说就敞开大门,让朋友住进家里。
一方面是为了赢得主人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是个性使然,诗人的新室友从卢浮宫里偷出了两件小雕像。根据小偷自我吹嘘的说法,盗窃“不仅需要勇气、急智、想象力,也需要坚强的意志,若有必要,还得杀人如芥或从三楼跳下”。
事实上,入卢浮宫行窃简直就像顺手牵羊。一则,当时没有监控设备。二则,展示伊比利亚半岛史前雕像的大厅,基本上无人问津,连值勤保安都懒得踏入。阿波利奈尔的室友只需把雕像塞进大衣里,再光明正大地走出大门。唯一的难处是防止雕像掉落地上,摔成碎片。
多年后,诗人声称自己看到赃物时,大惊失色,然后一再恳求室友归还雕像。十有八九,他连眉头都没皱过。他可是个激进分子啊,一度和意大利未来派的艺术家一起呼吁:博物馆,连同一切过去的杰作,都必须破坏殆尽,为新艺术腾出空间。
因此,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诗人得知情况后,不禁喜溢眉梢。当室友提出要把赃物卖给毕加索时,他更是乐得咯咯直笑。那时,这位拥有伊比利亚血统的艺术家正好迷上了“原始”艺术。

从卢浮宫中盗窃出来的雕像之一,创作于公元前500年至300年之间,在如今西班牙境内发现。阿波利奈尔声称自己曾试图说服毕加索把雕像还给博物馆,但后者“为了创建立体主义,正全神贯注于美学的研究中”,谎称自己“已损坏了这些雕像,目的是揭示它们蕴含的古老秘密,以及制造它们的野蛮艺术”。事实上,借用了它们的原始风格来完成《亚威农少女》后,毕加索便把雕像扔进橱柜,把整件事置之脑后。
在黑市上,钱一转手,事情就结束了。在阿波利奈尔的世界里——无论是他虚构出来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总能变得错综复杂。因此,这笔交易造成了两个后果,一好一坏。好的是雕像激发了毕加索的想象,帮他创造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亚威农少女》。这幅描绘了五名妓女的油画绘于1907年,可谓第一件成熟的立体主义作品,不但树立了一个崭新的风格,还让已经张皇失措的保守派艺评家更是不知要如何接招才好。

毕加索,《亚威农少女》,1907年。这件现代艺术的里程碑之作,画的是巴塞罗那窑子里的妓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重要的美国学者称它为毕加索“黑人时期的杰作”。艺术家为此闷闷不乐,于是请了一位法国艺术史学家来澄清误解。后者宣布,该作并非源自“非洲雕塑”,反而与伊比利亚艺术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身为西班牙人,毕加索自然以伊比利亚传统为荣,虽然作为艺术家,他特别喜欢掩饰自己的灵感来源,似乎只为了误导批评家。事实上,《亚威农少女》同时受惠于伊比利亚和非洲艺术。
坏的后果则是招来的横祸。雕像的小偷在国外混了一段日子后,回到了法国。渴望引起注意的他,很快又从卢浮宫顺走了一尊雕像。照理说,这一次也不会出问题。不巧的是,三个月后,又有人盗走了《蒙娜丽莎》。这一回,连嗜睡的保安都发现博物馆里突然多了一面空墙。
一家深谙自我营销的报纸立即悬赏重金,寻找名画的下落。这下子可好了。阿波利奈尔的昔日室友马上联系报纸,一方面为金钱所诱,一方面也为自己的风头被他人抢走所恼。以“过来人”的身份,他写了篇报道,揭秘如何从法国最大的博物馆牟取暴利。为了证明自己言之有据,他交出了才窃取没多久的雕像,同时披露自己在四年前也盗走过一对。
找不到其他线索又面临巨大压力的巴黎警方,轻易说服自己此文作者就是偷走达·芬奇杰作的大盗。法网越收越紧。阿波利奈尔只好帮助前室友逃离巴黎,更进一步地把自己卷入了案件。
所以他家的门才会突然被敲响。被逮捕的原因是涉嫌参与“国际走私集团”。害怕自己会吃上好几年的牢饭,诗人只好乖乖供出雕像买家的名字。
不消说,最终这出闹剧以皆大欢喜收场。三尊雕像都找回来了。就连消失了两年又三个月的《蒙娜丽莎》也回到了“娘家”。美中不足的是,虽然针对阿波利奈尔的指控撤销了,他的名誉却因为一连串的负面报道而受损,更别提他还白白在牢里受了四天的苦。
他唱起歌来:
困在四面光秃黯淡的
墙壁之间确实百无聊赖
这张纸上停落了一只苍蝇
俏步走过我缭乱的诗行
我会有怎样的遭遇哦上帝
你知道我的痛苦是你带来的
请怜悯我干枯的眼苍白的脸
以及上了枷锁的椅子的哗啦声响
短暂的刑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这些都将深深影响阿波利奈尔的余生,尤其是他在即将席卷欧洲的那场风暴中的所作所为。
战争
夜晚的凉风轻拂着他的头发。一条胳膊搭在车门上方,他漫不经心地打起拍子。他和他的插画家朋友此刻都没心情说话。
返回巴黎的路程,和前往多维尔的,简直属于两个世界。他俩受一家报纸派遣,去报道这座海滨度假城一年一度的赛马会。谁知,在逗留期间,德国竟然向法国宣战了。
诚然,不祥之兆早已显现。但老百姓大多选择视而不见。即使在诗人和插画家匆忙赶回巴黎的途中,仍可看到一辆接一辆满载着乘客的轿车,一路欢声笑语地逆着他们驶去。这便是阿波利奈尔诗作《小汽车》的创作背景:
一九一四年八月的第三十一天
我在子夜前乘坐鲁韦尔(André Rouveyre)的小汽车
离开多维尔
连同司机我们一共三人
我们道别了一整个时代
愤怒的巨人们正在欧洲崛起
越过毫无疑问是阿波利奈尔作品里最不同寻常的中段,这首发人深省的诗歌如此结尾:
我们在枫丹白露
度完下午后
抵达巴黎
正好赶上四处张贴动员通知
我和我的同伴明白了
小汽车载我们驶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我们早已成年
但我们才刚诞生
之所以说《小汽车》的中段“不同寻常”,是因为它写到一半突然妙笔一转,变成了一首“图画诗”:

阿波利奈尔别具匠心地排列这十行诗句,使它们在视觉上接近一台汽车,而且配有两个轮子和一个方向盘,同时让它行驶在公路上(道路由最上方和最下方的两行诗构成)。若以正常格式排列,这首“诗中诗”的内容如下: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趟一路沉默的夜行
哦有三盏车灯故障熄灭的严肃离别
哦战争前夕温柔的夜晚
哦打铁匠被匆忙
召回的那些村庄
在子夜和凌晨一点之间
驶向一片深蓝的利雪区
又或许
金碧辉煌的凡尔赛
我们中途停了三次更换爆胎
尽管如今看来依然新鲜,以诗作画的手段其实早已有之。古希腊诗人罗德斯的希米亚斯(Simmias of Rhoades)就以形状奇特的诗歌为名。这种写法在当时被称为“τεχνοπαíγνια”,字面之意为“展现创作者技艺的游戏”。希米亚斯利用长短不一的诗行,制造出接近实物轮廓的图像。他一首名为《翅膀》的诗歌,形状就像一对鸟翼。
但这些早期范例均是粗略的模仿,无需在排版布局上花太多功夫(《翅膀》不过由两段近似三角形的诗节组成)。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世上才会出现一位真正尝试用文字作画的诗人。一向热爱革故鼎新的阿波利奈尔曾对毕加索说,他的理想,是结合经典与现代。难怪他图画诗里的诗行或弯曲,或扭转,或倾斜。它们时而构成圆圈,时而方块,时而三角,在风中翩然起舞,却又遵循地心引力。这些图画诗更新了源自古希腊的文字游戏,恰如埃菲尔铁塔彻底改造了罗马拱门(从不落伍的阿波利奈尔,自然也用过这座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建筑来“画”诗)。
其实,从荷马时代起,诗人便不厌其烦地试图用文字媲美绘画。最著名的例子仍属《伊利亚特》第十八卷:火神赫菲斯托斯为主人公阿喀琉斯锻造了一块盾牌。荷马以一百多行的篇幅,详尽描述了这件防御武器,一个细节也没放过。
这种手法被后人称为“造型描述”(来自古希腊语“ἔκφρασις”,即“描写”的意思)。它的初衷其实极其朴实:只是为了协助读者想象出一件物品的样子。在实践中,它却往往成为文人自我陶醉的契机。无一例外,这些段落都由密密麻麻的形容词、方位词和比喻句组成。像五花八门的包装盒一样,这些缺乏叙事动力的文字堆积在一件作品的主干道上,让读者无法迅速抵达终点,又不足以诱惑他们停下车来,耐心拆开一个个纸箱,仅仅为了鉴定它们是否空洞无物。
这自然是阿波利奈尔插手解决的问题。通过他的创新,诗行的形状也成了描述的一部分。譬如他的《雨》。五行诗句如丝丝细雨从天空飘落,既有诗情也有画意。
虽然在一八七一年,年仅十六岁的兰波就已发现,波德莱尔“是先知之首,诗人之王,名副其实的神。但即便是他,也活在一个美化过度的世界,而他饱受赞誉的诗歌形式,其实早已老套。要写出无人写过的作品,需要全新的形式”。难道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波利奈尔才赋予了文坛他的图画诗?
当然,不厚道的看法——也是在阿波利奈尔有生之年最普遍的观点——则是,这些图画诗不过是噱头而已。乍听之下,倒也不无道理。比阿波利奈尔早一代的文人和画家时常高喊“为了艺术而艺术”,而他,阿波利奈尔,有时确实只为了创新而创新。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如果一切皆以用途为评价标准,那么,绝大多数艺术创新都显得多此一举。恐怕连诗歌本身都达不了标。既然一般文字也能传情达意,为何硬要把句子拆分成诗行,加上韵律?
所以,仔细想想,确实也没必要一味否定阿波利奈尔时常带着点诙谐的标新立异。盛世期间它们无伤大雅;乱世期间即使起不了其他作用,起码也能愉悦人心。
事实亦如此。不然,他大部分图画诗也不会创作于战争年代。从多维尔返回后,不到四个月他就入伍了。虽然身为外籍人士,他没有义务为法国效力,但他还是积极地报名参加。或许连“积极”都不足以形容他那颗热切的心。极有可能他把从军当成洗刷卢浮宫事件之耻的最佳途径。也有可能他真的信奉自己一年前写下的话:“法国不仅属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属于所有那些想要找到——或希望保留——美和文明的人。”
当他在巴黎的申请被拒绝后,他在尼斯又试了一次,终于成功。这意味着尼斯的官僚没那么条条框框。又或者,短短几周之内,法国已意识到自己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包括蹲过监狱的外籍流氓。
“流氓”或许倒还不至于,但积习的确难改。说句公道话,尽管阿波利奈尔生活散漫,似乎在游戏人间,他仍是一个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的好汉。这足以说明他为何再三伸出援手,无论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是一流的艺术家还是三流的小偷。行侠仗义的美德也能解释他为何在一战时,把自己的命运与法国的紧紧连在一起。在他看来,危在旦夕的是文明本身。
他唱起歌来:
今晚我忆起印度戏剧孩童的战车
一名小偷登上舞台
他在墙上钻孔前苦苦思索
该赋予这个洞怎样的形状
要如何打洞美才能免受践踏凌辱
哪怕是在犯罪之刻
我觉得我们
在垂死之际我们这些诗人这些男人
在这场战争中应该抱有同样的心态
难怪他会成为一名模范军人,不断晋升,很快还得到一枚英勇勋章。“我感觉当兵才是我真正的职业”,他向一位友人写道,虽然“我比周围大多数人都要老十五六岁,但我成绩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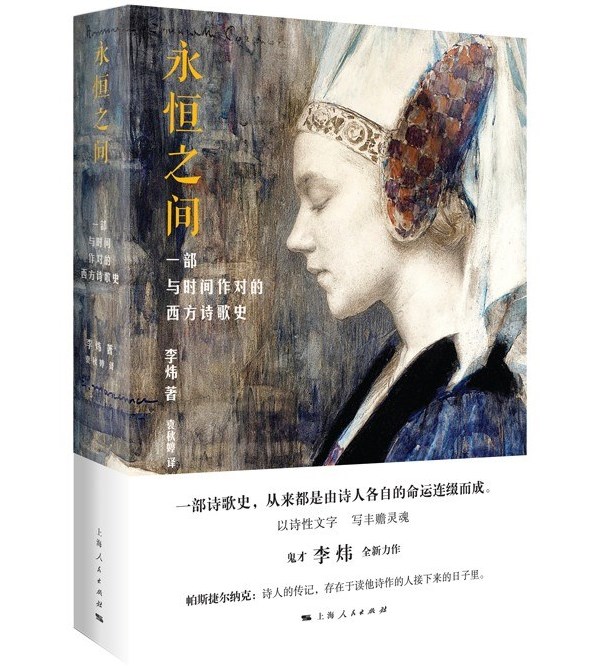
《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作对的西方诗歌史》,李炜/著 袁秋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