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赵惠俊读宇文所安︱谁妆扮了北宋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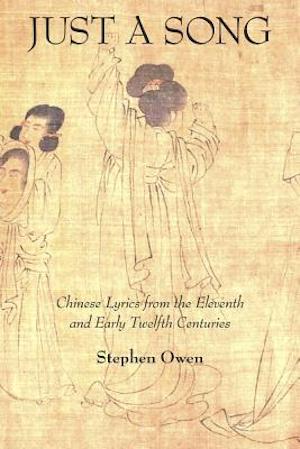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Stephen Owe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pril 2019, 430pp
宇文所安教授的新著《惟歌一首:中国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初的词》在201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尽管北美汉学界近年来对词学研究的关注度稍显提升,出现了诸如田安(Anna M. Shields)的《缔造选本:〈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艾朗诺(Ronald Egan)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等重要著作,但是像宇文所安这样直面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北宋词史的宏观性研究,还是本世纪以来的头一回。众所周知,宇文所安教授的学术专长在中国中古诗歌,完全没有渊源于清代浙西、常州词派的现代词学研究学缘师承,也就基本不受体系与观念完备谨严的中国词学研究范式影响,使得本书展示的观点与方法充满颠覆力量,也颇具启示意义,其间的优劣短长,更有助于今日的宋词研究反思浙常传统的得失。

宇文所安
一、发现胭脂水粉:解构词集及词作文本的作者权威
从全书的标题“just a song”就可以看出,宇文所安尤为重视词体文学的流行歌曲性质,特别是对于词体初起阶段的认识与研究,首要的考量元素就是即席歌唱表演。由于建安以来的中国诗歌以案头欣赏为主流,从而作为应歌之曲的词在创作生态、作者心态、结集流传等方面就与诗歌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词体文学又完成了从应歌到案头的雅化进程,使得传统研究者在重视音乐性之余,还是会采用与古近体诗相同的方式处理版本流传、词人词作关系等问题,这其实又与应歌之曲的性质相违背,从而带来了误读与遮蔽的可能。或许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宇文所安在导论(Introduction)与第一部分(Part I)便直击词集与词人形象的生成,从应歌之曲的角度对传统认识予以解构式的质疑。中国学者并不会对以明清词集丛刻丛抄为主要载体的宋人词集有太多怀疑,同时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文论观念以及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强大影响力下,也不会对直接将词人代入词中故事的阅读方式有太多顾虑,但二者在尤为强调“惟歌一首”的宇文所安这里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宇文所安的质疑与解构首先从词集开始,他的思考起点是词集的结集时间与词人活动时间往往有着长达一两个世纪的滞后性,而且北宋词人并不会主动保存自己的词作,于是不仅明清本宋人词集的文本不甚可靠,就是在宋代即已问世的词集也同样很可能并不那么真实。
为了更好地支撑这个质疑,宇文所安对宋人所撰的词集序跋以及重要的北宋词人词集的问世时间做了详细的梳理,整理出了一些重要材料。比如陈世修编于嘉祐三年(1058)的冯延巳《阳春集》,距冯延巳去世已过了近百年,甚至连晏殊都在三年前逝世;乾道九年(1173)高邮军学所刊的《淮海集》,较秦观逝世晚了七十三年;陈元龙注本《片玉词》刊于嘉定年间(1208-1224),距周邦彦去世亦有百年之隔。宇文所安从中提出了一个词作文本写定的命题,即这些从宋代流传至今的词集提供了一个标准文本或写定文本,成为今日理解词人及其词作的基准点,然而由于时间滞后性的存在,这些后出的文本究竟能反映多少真实便非常可疑了。在“惟歌一首”观念下,结合北宋前期词作的诸多异文,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人之间的大量互见词,以及词作文本中出现的歌女唱词甚至撰词的信息,宇文所安认为词作最初的流传靠的是口头直接记诵,歌女是最初的表演者、传播者与文本写定者,而此时的词集并不是案头读物,而是演唱脚本,使得词作在传唱的过程中,文本是流动而富于变化的,从而后出的写定文本并不是文本的原貌。晏幾道《乐府补亡自序》中的内容想必给了宇文所安充足的信心,因为晏幾道明确表示他的词作在自己与友人的家道中落后,“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传于人间”,而且他亲自题序的词集是由范纯仁“缀辑成编”的,完全是词作由歌女流传、词集由他人从歌女处搜辑成编的词人自道。宇文所安也确实由此判断在北宋词人的活动时空下,并不存在一个标准文本,也不太再有如《小山词》那样被词人本人见过的词集。当然,《乐府补亡自序》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范纯仁的缀辑成编还意味着这本《小山词》只是晏幾道词作的一部分,很可能还存在数量可观的词作被范纯仁没有找到的歌女带到了其他地方,它们在那里被歌唱流传,以至于被另一位酷嗜小晏词者掇拾成编,出现了范纯仁与晏幾道都不知晓的另一种《小山词》。这为词集的写定与流传又带来了空间上的错位,宇文所安也注意到了此点,并从唐代文学研究中借来了“小集”概念,以定义这些可能流传于不同区域却又互不相关的同一位词人的词集。
这样一来,词作的写定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其间包含着歌女、编者、流传区域等诸多环节,任何一处都会产生有悖于词作原貌的变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宇文所安便认为,歌女并不会在意词作者是谁,也不会予以作者考辨,只会记得最优秀的词人及其词作的主要体貌,从而会将一些风格相近的词作直接冠以最优秀词人的名姓。同时,歌女为了更好地流传自己的作品,往往也会在歌唱自己词作的时候声称这是某位最知名的词人(比如柳永)所填。这使得最著名的词人成为了一种箭垛——风格相近的他人之词、作者难考之词以及歌女之词纷纷归入其名下。而又因为写定文本问世于词人去世百余年后,从而时过境迁,人们已难辨认其间作品的真伪,于是只能将其沿用固定下来,成为今日理解的基础。尽管这个假设很难被完全证明,但在宋词材料非常有限的前提下,确实也足以成为理解为何冯延巳、晏殊、欧阳修颇多互见词以及宋初百年无杰出词人等问题的较好方式。
既然词作写定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存在着层累元素,那么词人自然也会在这距离空间中被添上各种意识下的附加物,使得今日被人熟知的词人形象与其本人相比,发生了强烈的拓展与讹变。宇文所安在解构词集之可靠性的同时,也在试图剥离词人形象上的种种层累。最核心的人物当然是柳永,宇文所安在论述柳永部分的开篇便明确表示《乐章集》是由许多不同来源的内容拼合而成,这些内容建构出了一个柳永形象,与真实的柳永差异甚大。不过本书对柳永形象的论述算是点到为止,比较完整的叙述见于他近年发表的《“三变”柳永与起舞的仁宗》。此文就明确表示:“我们经历了一个词人被‘生产’的过程,在其间一系列大受欢迎的轶事共同创造出一个很可能与原历史人物大相径庭的文化身份。”“我们把柳永看作一个‘角色’(persona)——一个曾经真实的历史人物被其声誉包裹、吞噬后所变成的‘角色’。”“柳永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应该是’柳永所作挑选了‘柳永’作为作者的词。”(林宗正、蒋寅编:《川合康三教授荣休纪念文集》,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页、246页、255页)这些判断完全可以作为本书的注脚,也就是说,许多无名氏的作品、歌女的作品甚至本来明确属于另外词人的作品,只是因为“像”读者所认为的柳永词,从而在后出写定文本中被归入柳永名下,而这些词又在传记式阅读方式下反过来强化着读者对柳词及柳永的先入之见,从而使得今日之柳永形象与真实的那个柳永越来越远。更甚的是,在柳永身后还不断涌现出根据词作敷演出来的香艳本事,这些本事使得柳永形象愈发地朝着后人期待的方向发展与强化,最终固定在完全不是词人本人的形象上。不仅柳永是这样,冯延巳、秦观、李清照、周邦彦等词人同样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今日已经看不到李清照的“坏女孩”形象,但李清照又确实存在许多“离经叛道”的行为。
在这样的观念下,今日我们熟知的北宋词人形象往往是被妆扮过的,那些被归于其名下的诸多可疑的词作、词人身后不断增加的香艳词本事、历代读者反复强化的先入成见,都是浓妆淡抹的胭脂水粉,如果要更好地理解北宋词人词作及其发展进程,自然需要把这些后世渐次涂上的妆容卸去。这实际上是在解构作者对于作品文本的权威,因为传世文本是经过诸多人手才最终写定的,经常会产生作者始料未及的剧变,从而文本与作者之间也就并没有太过强烈的捆绑系联。这样的观念改变当然会带来异于传统的认知,宇文所安便做出了诸多颠覆性的判断,如冯延巳的《阳春集》是晚唐词、后蜀词、南唐词及宋初词集中归于冯延巳名下的聚合;同时不见于曾慥本《东坡词》、元刻本《东坡词》以及傅幹《注坡词》的东坡词题序,往往出于后人的敷演增添;曾慥《乐府雅词》并不是通行意义上的词选,而是曾慥所藏词人小集的汇编,类似后世词集丛刊的性质;陈元龙注本《片玉集》并不是那么可信等等。尽管有些判断确实值得商榷,但多数还是和上文提到的“箭垛式”词集与词人一样,不啻为对于许多词学悬案的一种有效的解释可能。
二、素颜之态:解构之后的文本解析
当词人对词作文本的权威被解构,甚至今日认识中的词人都不再完全是其本人的时候,所谓的作者本意也就难以存在,只剩下一个个独立的文本,供读者自行分割归类,探索文本内部的发展线索。宇文所安便从第二部分(PartII)开始,对北宋重要词家的词作予以精细的文本解读,分析不同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章法结构等文本特征,同时借此探索北宋词由应歌表演发展至案头欣赏的雅化轨迹。对于词体文学来说,这种词人与词作密切关系的解构其实非常有必要,毕竟应歌之曲填成之后是交付演唱的,词人除了自我表情达意,还需要考虑到听者的审美趣味与理解能力,从而词中的个性化情绪相对微弱,抒情主体与词人自我的关系也就比较疏离,而且越是面向世俗听众的歌词,这种文体特征也就越是强烈,奠定了词体自我的写作规范与传统。所以若要深入理解探究词作的文本艺术与技术操作手段,必须要尽量贴合写作生态的样貌,将词人从词作中抽离出来,才能尽量接近词体文本的真实,更好地揭示诸多“别是一家”的文体现象与文体生命历程。宇文所安就在予以词人与词中女性合理有效之抽离的基础上,才能如此细致地逐一分析柳永、晏殊、晏幾道、苏轼、秦观词的女性形象选择与描写建构方式,逐一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晏殊令曲往往会将老去情绪直接点破,而不似南唐词泛泛地描写闲愁;晏幾道词不再能够被任何一位歌女演唱,其需要特定的演唱者方能表演,这意味着旧传统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孤独幽闭的传统女性形象虽然重现于秦观时代的词作,但此时的词人会为女性的孤独赋予肯定的意义等等。很明显,这些本自不同词作的文本解析,也悄然总结出了词体由应歌到案头的变化消息。女性形象之外,本书对词作文本时空结构的解析同样也有如此特征。宇文所安首先指出“宴饮当下”与“往事重现”是令曲中两大时空模式,随后便抓取代表词作分析这两种时空的不同运用实践。如晏殊词习惯泛言宴饮当下的惆怅,而晏幾道词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回忆某一特定具体的宴饮事件;柳永的羁旅行役词每每在上片描写眼前景色后,便于下片转入京城往事的回忆,周邦彦词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记忆的不断闪回跳跃,并在不同回忆的组合间形成“潜气内转”的时空转换联结方式。这些都是需要将词人与词作文本时空予以相当之抽离后,才能得出的重要结论,对于阐释“要眇宜修”“狭深幽微”等缥缈模糊的词学命题颇具启示意义。
实际上,传统词学研究并没有忽视词体应歌的性质,词人与词中人的关系始终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对此还产生了“男子作闺音”“代言体”“艳科”等重要概念术语。不过知人论世的传统实在过于深入人心,从而随着词中人的性别逐渐向男性过渡,论者愈发坦然地将词中人与词人紧密系联,忘却了词体最基本的代言传统,忽略了词中男性也可能只是词人的应歌表演而已。到了奠定现代词学研究基本范式体系的常州词派那里,“男子作闺音”也被消解,借用自《楚辞》香草美人传统的比兴寄托说将男性词人与词中女性也捆绑在一起。尽管常州词家后来也提出了“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补正之说,但依然改变不了对于比兴寄托的强烈指引,严重地遮蔽了其他的文本意义可能。于是宇文所安的解构尝试也就有了另一层的启示意义,我们对于继承传统的应歌之曲观念并予以持续深入的挖掘当有充分之信心,这是词体文学自身的写作传统,不仅对北宋前期词影响巨大,相关痕迹就是到了南宋也应当犹有留存。此外,卸去严妆的方式其实不止宇文所安这样的解构,传统词学批评话语与理念已然足以完成深入文本的解析并得出与之相近的结论。笔者的博士论文以十至十二世纪的词体雅化进程为核心讨论点,于2017年提交,后经删改修订,以《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为题亦于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笔者在书中并没有解构作者对于词集、词作的权威,只是在应歌之曲与代言体的观念下对晏殊、柳永、周邦彦等词人的词作予以词人与词中人相抽离的文本分析,得出了不少与宇文所安教授一致的结论。笔者在撰写书评的时候其实与宇文所安教授保持着邮件沟通,他对二书之间的共通感到惊喜,认为这是颇具意义的事情,并告知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他同样也在2017年将本书定稿提交给出版社。也就是说,笔者是和宇文所安在同一时段各自独立思考与写作,最终按照不同的学术理路抵达了同样的终点。其实这也不那么奇怪,毕竟宇文所安与笔者关注的文体与时段是一致的,同时也都尝试突破传统词学研究范式的局限,在宋词研究材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也就很容易产生相同观点了,倒是验证了钱锺书先生的那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宇文所安对于“惟歌一首”的格外强调,实际上也是为了深入有效地讨论北宋词由应歌到案头的发展线索这一核心问题。于是苏轼及苏门学士同样也是他的考察重点,相关论述主要见于本书体量庞大的第三部分(Part III)。一旦涉足苏轼,任何一位宋词研究者都需要面对传统词学研究最经典的研究框架“婉约豪放”,或承继传统,或予以突破。不过海外学者完全没有中国学者在面对“婉约豪放”时所要承受的强大影响焦虑,他们不需要先行梳理头绪纷杂的“婉约豪放”生成史及其优劣得失,并谨慎地于其间闪转腾挪,从而为他们的论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宇文所安便坦然直接地完全抛弃了“婉约豪放”的论述框架,并在讨论秦观词的部分直截了当地对“婉约豪放”予以批评,指出豪婉对立仅在词体文学中存在,这使得宋词研究无法与宋代其他文体对话,似乎宋词与宋代诗、文、小说等不是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番批评完全击中了“婉约豪放”的最关键处,尽管其为宋词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与丰富成果,但独立于宋代文化与其他文体之外的特质使其无法与宋代文史研究形成广泛密切的互动,使得当下宋词研究在“别是一家”的小天地中愈显局促。然而绝大多数的宋代词人并不是专力填词者,北宋词人的身份主要还是士大夫,诗文写作是他们首要的安身立命事业。南宋词人依然如是,今日仅以词名的辛弃疾无疑高度参与政治,而落魄江湖的姜夔同样也有显赫的诗名。于是宋词研究的发展必须正视“婉约豪放”的功过,积极主动地与两宋文史研究各个领域互动碰撞。当然,“婉约豪放”的传统并不能抛弃,只是需要予以新的阐释,一如王水照先生受诗歌之正变二体的启发,将婉约豪放阐释为传统之正与革新之变。宇文所安实际上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也在论述秦观的章节里提出了自己对东坡词之豪放的理解。他首先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指出,传统词作的文本空间是隔离于公共生活的,作为高度参与政治的士大夫,词人鲜有愿意长期居于其间,但却总想时不时进来看一看。在经由苏轼革新之后的秦观时代,词人已经习惯将自我情绪写进词中,于是他们会将自我在外部世界的种种苦闷写入歌词,并在词体中使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抗公共世界、理性世界与道德世界。苏轼同样是在这样的词体功能认识下展开词体写作,但他选择了“别是一家”之外的话语表达方式,并没有如秦观这样将来自“理智”(外部世界)的种种元素包孕在“情感”(词体文本内部世界)之下。词作的文本空间与真实世界的离合应当是宇文所安的个人新见,不过由此推导出的阐释其实在传统词学中早有相关话语,即“以诗为词”与“本色”。在“婉约豪放”的研究框架下,“以诗为词”属于豪放,而“本色”属于婉约,二者因豪婉之对立而各属一端,形成了苏轼-秦观、稼轩-姜夔等泾渭分明的对照组。但如果改变豪婉截然对立的二元思维,就能够很容易地发现“以诗为词”与“本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苏轼和秦观之间当然存在交互。实际上,将诗歌的语言典故及题材内容引入词作,是北宋后期词人的共性,只不过在“以诗为词”的时候,是否还要坚持词体文学的基本写作传统,是否依然保持词体文学的主流风格体貌,不同的词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如苏轼这样保留得少一点,又对某些词体传统做出明显颠覆式突破的,便是豪放;如秦观这样保留得比较丰富,从文本外观上与传统应歌之词差异不大的,便属于婉约。这是苏门学士与苏轼之词学观念的根本性差异,也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得以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笔者的小书就在这个思路下对“婉约豪放”做出了突破尝试,只不过在影响的焦虑下,笔者的论证过程要远比宇文所安复杂缠绕。
一旦从豪婉截然对立的思维走出,就能够看到以往研究体系下各个对照组之间的融通性,不仅苏轼与秦观之间存在联系,柳永与苏轼之间也同样暗流涌动。宇文所安便指出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的承袭痕迹,认为苏轼在填词初始需要对前代著名词人予以充分摹习,掌握词体写作基本规范后,方能进行革新尝试。只不过苏轼实在过于天才,他往往在模拟的同时便予以创新,至少会有意识地藏起摹效的痕迹。笔者的小书同样也论述到了此点,并与宇文所安一样,举了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满庭芳》(蜗角虚名)与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凤归云》(向深秋)等词为例,来论证柳苏之间的承变。不过宇文所安没有注意到的是,苏轼的这种摹习柳词的痕迹主要存在于慢词之中,他在令曲方面则选取欧阳修词为主要摹习对象,相关痕迹与特征表现得也更为明显。与柳苏之间相似,周邦彦也与苏轼存在密切的互通,宇文所安不仅指出周邦彦词一方面体现了徽宗词坛的主流风貌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也与苏门词人恪守本色的以诗为词非常亲近,同时也发现了周邦彦在北宋后期寂寂无闻,其词名是在南宋后起的现象。笔者的小书在论述周邦彦的时候再次与宇文所安不谋而合,甚至也同样做出了强焕所编《清真集》近似小集性质的判断。当然,笔者在论证上还是无可奈何地比宇文所安辛苦许多。
三、究竟有多少妆容:解构的边界与其他的思考路径
如同宇文所安从唐诗研究借用来小集概念,《惟歌一首》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来自对中古文学研究的借鉴,毕竟文本写定时间严重滞后于作者活动时间的现象本就是先秦子书与汉魏诗歌的常态。宇文所安在其早年名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中,便认为现今所见的汉魏古诗,都是经过后代文人的重新编订,在抄本媒介下通过《文选》《玉台新咏》等总集和更晚一些的类书的重新写定和保存,经历了后世的收集、校勘、改写到流传的复杂过程,从而今日所见之汉魏古诗文本也就未必是原初的面貌了(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很显然,在《惟歌一首》的解释系统里,北宋词相当于汉魏古诗,口诵歌唱相当于抄本媒介,歌女相当于抄手,现存最早的词集刻本或抄本相当于《文选》等总集或唐初类书,可谓将其思考研究中古诗歌的框架模式完整迁移了过来。由于宋词在流传文献不足、词人生平影像模糊、词人在世时罕见词集流传等方面与汉魏古诗存在高度相似性,故而这样的思维框架整体借用对推进宋词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解深入上还是极为有效的,是以北美学者早已将其运用在词学研究的实践中,他们尤爱发现词人与词作文本上的厚重妆容,并将之逐层剥去。如宇文所安的学生孙承娟《亡国之音:本事与宋人对李后主词的阐释》便尝试卸去宋人逐层附加在李煜形象上的自我文化价值取向;同样师承宇文所安的罗秉恕(Robert Ashmore)与丽贝卡·多兰(Rebecca Doran)则完全从歌唱表演的立场出发,分别探析晏幾道与柳永词作文本的幽微意义;艾朗诺的近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更是通过对现存史料的穷尽式爬梳,探究千年来的历代读者附加给李清照的层层累赘,并将其逐一揭去,尝试重构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形象与易安词文本。不仅如此,北美的中国史研究近来也愈发流行这样的思路,如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新近出版的中文论文集《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便关注南宋史家的不同历史记载,梳理相互之间存在的文本间性以及各自的产生或被编辑的时间顺序,以还原历史文本的形成历史。随后再结合史料形成期间政治和思想中发生的变化,探索文本随着政治与思想变化不断改变的动态过程。蔡涵墨还特为捻出“文本考古学”一词,以定义他的研究思路。可见《惟歌一首》与中国传统词学研究体系一样,也有着自己的传统与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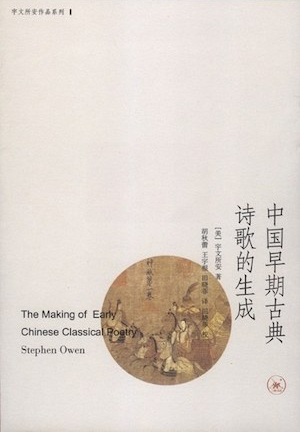
宇文所安著,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不过任何的研究体系都会带来思维的局限,如果该体系又长期稳定地被研究者使用的话,相关束缚也就会更加严重。宇文所安似乎对于清真词的回忆有些过于在意,以至于忽视了周邦彦更为擅长也更加频繁使用的当下、未来之设想,这或许就是来自《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的思维定式。因此,《惟歌一首》在有效突破“婉约豪放”的局限及遮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因思维体系局限所致的误解、遮蔽与过度阐释。其间最令人怀疑的一点就是北宋词人及其词作文本,是否真的有那么厚重的妆容?
不可否认,宇文所安发现的胭脂水粉大多可靠,后世刊印的词集特别是清人的宋词丛刊丛抄也的确存在颇多的文本问题,但这些现象应该还是不足以做出诸如“我们常常提到的柳永与那个曾经存在过也确实填词的柳永其实大相径庭”“今传《珠玉词》与宋代流传的《珠玉词》截然不同”等完全颠覆式的判断或假说。宇文所安向笔者郑重表示过,他不认为本书的工作是在解构,而是“彻头彻尾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然而如同蔡涵墨的“文本考古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史源学,宇文所安基于文献学的考辨梳理同样也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差异较大,从而在中国学者与读者看来,还是一种对历史思维、固定关系的解构,无法真的称得上是历史主义。比如宇文所安对现存宋人词集版本与宋人论词材料做了详尽周密的考察,但他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先从资料汇编与今人词集笺注成果中搜辑汇录资料,再以此作为考察辨析的基本数据库。这样的方式可以达到传统文献学的基本程度,并在不同的思路理念之助下补其不足,然而他本人终究没有词集版本校勘以及历代目录爬梳考辨的实践,对古代目录家的记录极度缺乏信任,甚至也充分质疑明清藏书家影抄影刻的宋本词集是否真的是宋本,这些问题使其未能关注到传统文献学视野下相对易得的大量信息,导致了某些结论与判断的偏误。最为典型的便是他根据北宋后期才逐渐兴起对唐五代词的重视以及今传最早的《花间集》版本是绍兴十八年(1148)晁谦之建康刻本,而对《花间》《尊前》二集的可靠性深表怀疑。如果仅从写定文本之滞后性来看,《花间集》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在传统文献校勘学的层面上来看,花间诸词明显呈现出敦煌词与宋初词的中间文本形态,大量与敦煌词相合的句法参差及分片布局更是时过境迁后的南宋人无法想象编造出的内容,从而作为后蜀歌词总集的《花间集》,依然相当可靠。
宇文所安在《花间集》质疑中出现的问题还反映着《惟歌一首》的另外两重信息缺失:一是对唐曲子词的回避,一是完全没有来自音乐层面的考量。作为宋词的前身,唐曲子词已经孕育了许多宋词的重要文体特质与写作传统,甚至在中晚唐即已经发生了从歌唱到案头的雅化,从而对于宋词源头的讨论是绝对不能割裂掉唐曲子词的发展面貌。同样地,作为应歌之词,词作文本的参差短长与音乐旋律密切相关,音乐的发展变化对词作文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是必须予以关注考察的要素,否则又怎能称得上“惟歌一首”呢?这两方面的缺失使得宇文所安的一些判断并不可靠,主要集中在他对于歌女即席制词以及词人所填的齐言歌词会被不同的歌女即席唱成互有差异的杂言形式之假说上。实际上只要结合隋唐燕乐的发展史即可知道,随着西域诸多打击乐器的引入,燕乐本就有节奏繁促的特征,从而许多西域音乐成分浓厚的燕乐曲子并不适合用齐言诗的体式来填词,只能直接填以长短错落的杂言体式。而那些齐言诗体的歌词,基本是配合融汇不少江南清乐元素的曲子演唱。同样地,《乐章集》中的慢词也是依照宋代新声旋律直接填制的杂言歌词,如果大量存在宇文所安推测的那样由齐言诗改造而成的杂言慢词情况,那么文本中必然会留下齐言原唱的痕迹,但在现存《乐章集》中并不能找到这样的痕迹。此外,从唐曲子词的发展情况来看,晚唐令曲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体式格律规范,俨然已经从应歌表演过渡至案头欣赏,至少是表演与欣赏共存的阶段。也就是说,词在晚唐五代已经进入文人写作的领域,在表达方式、语言词汇等方面形成了与世俗歌女乐工的巨大雅俗差异与隔阂,不仅歌女没有自由撰制文人歌词的知识结构,从而无力独立填制符合诗客期待的曲子词;同是文人的作者与在场听众也不会愿意歌女又将他们的清词丽句改回俚俗之态,这便是欧阳炯《花间集序》结尾所谓之“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于是乎,对于北宋前期词的理解认识,既要重视表演现场及应歌写作生态,也不能忽视其已然具备的案头欣赏性质。
这样来看,后世为北宋词人描上的妆容并没有宇文所安描绘得那么厚重,剥离层累自然极具价值,但光靠消解词人与词作的系联以突显文本之地位也是不够的,仍然需要承继传统词学研究中的版本校勘、声律校订、音乐研究、批评框架及术语,并在不断反思中予以意义的再发现。此外,两宋终究不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环境、文化风尚、审美趣味等皆有显著差异,因此也无法全然以中古度两宋。正如宇文所安在书中反复强调理学(道学)对词体观念及写作的潜在影响,两宋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也是宋词研究不能放弃的考察基点。当下对于宋词研究实现突破的方式,也初步形成了两条路径的共识,即将宋词放置于两宋社会历史大环境下予以观照,以及深入宋词文本内部的精细探析,而这两条路径的实现,就是需要以上述研究视野的综合融通为基础。当然,对于一部专著来说,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某一方面实现深入或开拓,弥补传统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就足以承担颇具分量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宇文所安的这部《惟歌一首》,无疑是文本内部精细探析之路径的优秀案例。听闻宇文所安最近凭借本书获得了儒莲奖,足见海外汉学界对其的高度认可,也的确实至名归。而本书的中文版也已翻译完成,相信待其出版之后,也能够引起国内学界更为广泛深入的讨论。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