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图书馆农民工到小镇做题家,在乡土中找到饱满精神的形象
关于“乡土中国”的想象是怎样的?是封闭的人情社会,是远离乡土的人回望时充满愁绪的遥远的怀念,还是受够了城市的拥挤和淡漠而主观地将其理想化的桃花源和田园居?而关于乡土,有没有另外一种讲述的可能?最近出版的《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中,作者罗雅琳尝试去描述那些在新时代时尝试去建立某种崇高性的地域及人群。
如同标题“上升的大地”指出的,罗雅琳旨在找到一种关于“乡土”的新美学——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乡土中找到拥有饱满精神状态的典型形象。大多数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将人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状态联系在一起,觉得落后地区的人的精神状态相对而言不够饱满。书中的每一章中,罗雅琳的叙述重点都在人的精神状态上:
“‘上升的大地’体现于埃德加·斯诺笔下愉快的革命者为落后的西北所带来的全新感觉,体现于革命知识人将已成‘中国之殇’的黄河转化为中国人在世界秩序中展开竞争的力量源泉,体现于路遥为农村年轻人所寻找的在城市中获得正当成功的道路,体现于刘慈欣以第三世界革命经验为科幻文学赋予的精神底色。与同时代同主题的其他作品相比,这几个案例中包含着三个特别的面向:现代性不只发生在都市,更发生在乡土;乡土不光有土,更有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中一直包含着对于乡土的关怀,哪怕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之后依然未曾断绝。”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该书作者罗雅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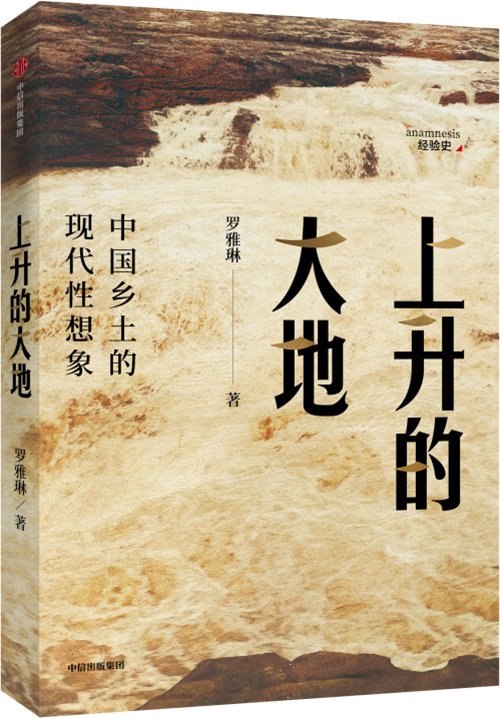
书封
孙少平、东莞图书馆的读书人、“小镇做题家”:乡土中崇高的可能
如果读者对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尚且陌生,我们不妨从最近媒体费了不少笔墨来讲述的东莞图书馆的一位读者吴桂春讲起。今年6月24日,这位读者在图书馆的留言簿上写:“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十二年……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这位农民工在十七年打工漂泊生活的最后时刻以读书人的身份体面地告别。

吴桂春
而另一边,则是豆瓣一个聚集了9万人的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用以自我指称的标签——小镇做题家,虽然凭借着刻苦读书跻身大城市的名校,但却因出身和阅历不够丰富缺乏视野与资源,大家只能抱团取暖、暗中自嘲。
这正是罗雅琳在《上升的大地》中关注的问题:城市与乡村的分野是否已经大到能为出身于其中的人写好截然不同的命运?而在乡村、在小镇出身的人是否也有获得崇高的可能?
罗雅琳回溯了文学史去为这个问题找答案,她谈到,像《平凡的世界》中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这样拥有着饱满的精神状态的人的发现,无疑可以很大程度地更新人们对于乡土的认识。而提起乡土,更多的是想到,《白鹿原》《废都》中那种奇观化的、落后而神秘的前现代景观,成了西部农村和中国乡土的代言。而路遥建立的孙少平这样的在各种处境中都以阅读以知识来充实着自己,拥有高贵的人格的形象则在逐渐消散。罗雅琳认为这和陕西文学史的发展有关:
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陕西是文学发展的重镇,写《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和写《创业史》的柳青都是陕西作家。20世纪60年代,关于怎样写农民是一直存在争议的,比如作家严家炎就指出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理论活动过多,脱离了“那种农民的气质”。而柳青和一直追随他的路遥则都认为所谓的“农民的气质”绝不该固化为一种见识短浅、平庸俗气的形象。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白鹿原》中前现代景观的乡村美学
1980年代,随着知青回城和城市改革的开展,大家的关注点都从乡村转向了城市,较多地关注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厚夫的《路遥传》记载了一个细节:当评选第一届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时,陕西作协没有推荐作品,这是因为从“文革”结束后到1985年,没有一位陕西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可见,当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文化中心全面转向城市和沿海地区之后,陕西文坛有多么凋敝。路遥也在当时被认为是“恋土派”,不够新潮和洋气。因而,他创造的孙少平这样一种农民的可能性,也就因为时代的原因,以及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路遥在1992年的逝世,逐渐失落了。“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废都》所代表的乡村最终定型下来,成为一种绝对主流的乡土美学。”罗雅琳在书中写道。
《平凡的世界》中在塑造孙少平时用了许多浅近却非常动人的表达,如对孙少平读的书的剖白:“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而吴桂春正是孙少平这种精神的当代承继者。
“说回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他在其中包含了很多对当时出现的最新的生产因素的讨论,比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类的农村改革。孙家的三兄妹之所以会有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是因为他们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推动之下诞生的新人。当代中国如果要讲述关于乡土的新故事,也需要找到在当下的全新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条件下出现的新人。我们不仅要表现田园牧歌,还要发掘新人,这才是理想中的新乡土美学的核心要义。”罗雅琳说。

城市白领和农民工共享一种相似的飘零
在城市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异化的感觉,罗雅琳谈道,比如,很多人会把上班、写论文、做科研说成是“搬砖”,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丧失,使得这些表面上似乎很高级的活动和“搬砖”这样单调的纯体力劳动没有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打工诗歌”能引发这么广泛的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打工,都在各自的“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异化的感觉。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喜欢看李子柒。虽然她很田园牧歌,但她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于劳动分工的取消,展现了非异化劳动的可能性。马克思谈到,异化劳动之所以发生,其原因之一在于分工过细——个体是一个人,而他在劳动生产链中其实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存在的,劳动没有使他作为个体得到增长和发展,反而使被增强了的总体反过来压迫个体,这就是所谓的异化。”罗雅琳说。

李子柒的田园生活
“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李子柒这样一种非异化劳动诚然可以在审美意义上缓和我们的压力,但是她只能作为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存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那样生活。农村的问题,比如农业劳动的艰苦性虽然可以被美化,但是根本上还是需要现代工业的发展去解决。”罗雅琳也谈道。
书中的第四章《走出乡愁的乌托邦》讲城市和乡村短兵相接时,可能出现的时代现象和情绪。某种程度上,因为这种共同打工、漂泊的经历,让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相似的异化的感觉和飘零的感觉,“这进而有可能实现不同人群和阶层之间的联合,形成积极的社会变革力量。”罗雅琳在书中写道。
而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和群体的出现也并不能一概而论,第四章中,罗雅琳着重讨论了打工诗人的写作:“当下很多人倾向于将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承载某种阶级批判的功能,然后就会对打工诗人无法承担这种批判功能而失望。但我认为真正的‘群’或许不是在工人之间,而是在工人和都市新穷人之间发生的。‘群’的基础在于两点:一是普遍的乡愁,二是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异化感受。”
但是如我们所了解的,“打工诗人”这个身份在后期常常会发生变化,比如他们后来会成为专职的作家,已经脱离了打工者的状态。对此,罗雅琳认为:“我曾经为他们的作品不能有想象中的力量而遗憾。但是后来我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将关注点放在了打工诗人和都市新穷人的共鸣上。这或许是打工诗歌更有意义的方面。”
海洋必然战胜土地吗?
在《上升的大地》的第五章中,作者主要讨论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当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成为中国科幻迷的口号,其中也暗示出我们是用对海洋文明的想象去想象太空。但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他更多的是从中国人生存的土地上去寻找科幻的元素,《中国太阳》《流浪地球》皆是如此.“乡土”在刘慈欣的笔下,是即便是要去宇宙漂流时也绝对不可以放弃的故土,更孵化出水娃这种既有飞向外太空的高远志向、也始终眷念着土地的人物形象。

《流浪地球》剧照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旦提到“现代性”或“现代化”,许多人总是认为这必然意味着海洋战胜陆地、城市战胜乡村。海洋思维是否有着绝对性的优势,而乡土就一定是如鲁迅的《故乡》中呈现的那样凋敝的、毫无生气的吗?
罗雅琳将时间线调到晚清开始讲述: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常常在沿海和内陆之间不断摇摆。李鸿章在那封指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奏折中写道,清代的边疆治理重点原本在西北,但是因为当时外国势力都跑到东南海域兴风作浪,所以防御的重点应该转到东南海域。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域上的转换,即政府把重心从西北转向了东南。“当我用地域转换的线索看百年中国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中发生了多次的转换:抗战的时候,中国的重心又从沿海转向了内陆;1950—70年代,因为冷战,中国非常强调内陆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重心又转移回沿海地区;而当下的中国可能又面临新一轮的地理重心转移。”
而构成关于乡土的印象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罗雅琳认为,这本写作于40年代、在80年代被大众关注的著作无论是其创作还是影响,都要放到具体的时代中来考察。
罗雅琳认为,费孝通40年代写作《乡土中国》时,是在有意识的对当时语境下流行多年的国民性话语做一个集中的阐释和反驳。所以“缺乏公共精神”、“不识书面文字”、“没有爱情”等特点,在《乡土中国》中并不是作为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的缺点来理解的,而是被阐释为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特点,这就把之前具有贬低中国人的意味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给中性化了。在费孝通的逻辑中,不是说像西方人那样“识字的”、“讲爱情的”就是先进的,而中国人中“不识字的”、“不讲爱情的”就是落后的。他认为这是与西方不同的类型上的差异,而非等级上的差距。
“《乡土中国》这本书真正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在1980年代,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热爱进行中西比较,将中西品质上的差异理解为中西差距的重要时期。那个时候,不同的人会在《乡土中国》中读到各自想看到的东西。费孝通先生的本意其实不是这样,但是1980年代的文化气候就会对这本书进行一种刻板化的、固态化的理解。”罗雅琳说。
将费孝通先生1940年代写作的东西搬运到80年代,甚至直接搬运到现在是不完全合适的。“1940年代的农村没有过土地革命,没有过农村体制改革或是新农村建设,如果现在仍然照搬它来描述现在的乡村,就是照本宣科了。所以写书时,我也大量引用了贺雪峰先生写的《新乡土中国》,贺雪峰先生说,现在的乡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而不是《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熟人社会。对于当下的乡村而言,“熟人社会”只能概括村民小组的范围,规模是三十到五十户、两百到三百人,这是能够熟悉的极限。但是现在的一个村大概有两百到三百户,两千到三千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熟人社会的范围。此外,现在的农村青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们的行动逻辑和思维逻辑已经不再是完全受制于熟人社会了,中国的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诚然《乡土中国》中有很多经典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去套用。”罗雅琳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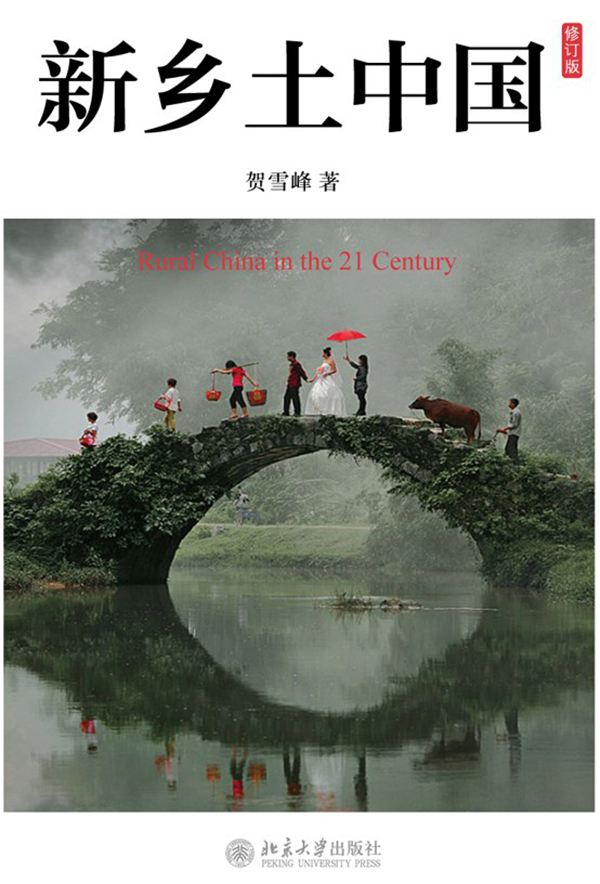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经验史:关注最为核心的时代焦虑与憧憬
《三联生活周刊》原副主编舒可文提出了“经验史”的概念,罗雅琳的《上升的大地》即是在经验史这样一个范畴下的写作。
关于“经验史”究竟指称的是什么,以及用怎样的方法研究,采访中,罗雅琳说:平常看到‘经验’这个词常常会认为它是个体的、私人的东西,存在某种小的、碎片化的经验与宏大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对抗,我们常看到的命名为‘一个人的XX史’就是如此。所以,经验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的、反宏大叙述的,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绝对独立的个人主体,这样的主体观念当然是一种想象。这种用碎片化的历史经验解构大历史的做法,是经验史所要首先反对的。”
“第二点我想引用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来说明——文学作品看起来似乎是作者个人化的创作,是自发的、私人的情感活动。但是,威廉斯认为这种看似私人化的创作实则是受到了社会性的情感结构的影响,而这个情感结构是与社会组成方式以及经济运行结构都是相关联的。第三,经验史同样也强调经验的历史向度,即每个人体会到的经验不仅是被当下的社会结构塑造的、也是被历史塑造的。比如我们使用的一些词,做出的一些动作背后都是有一系列历史脉络的。最后,这本书的立场是强调——独特的中国经验,不要套现成的框架。经验是最能打破既有的理论束缚的。”罗雅琳谈道。
“经验史”的这种写作某种程度上给了研究者们一些自由,就罗雅琳《上升的大地》一书看,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不拘泥:行文中,作者既关注了大的地域的概念如西部中国,也关注到具体的意象如黄河是怎样成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关注了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家和现象,如路遥、梁鸿、农民工诗歌、刘慈欣……“我们在学院里的生活都是被划在特定的学科之下,但是我们和舒可文老师在讨论中分享着一个共识:经验史不该有学科的限制,它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罗雅琳说。
而“经验史”要处理的“经验”究竟是怎样的?经验有经过反复验证的、已成为模式化的部分,是科学的基础和习惯的根据;同时也如我们感受到的,在这个更加瞬息万变的时代,很多现象出现、又在一夜之间消亡。罗雅琳说:“由此,我比较重视的是文学艺术本身的力量。文学艺术最为直接地把握了一个时代的核心意象,提炼出最为核心的时代的焦虑或是憧憬。这一套书系虽然强调了经验史的研究方法,但是并没有堆砌很多史料或是口述史,而是从文艺作品的角度出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