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权力的游戏与书写的祛魅——评《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
一
权力斗争、典章制度、政策得失,构成传统中国政治史叙述的三种主流脉络。近代西方史学观念的引进,又使社会结构、意识形态、阶层与集团、过程与空间等,成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史容易流为当下意识形态的阐释。这虽然是古今中外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但现代专业史家毕竟追求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探讨政治运作的构造。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已然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但在历朝的政治史研究中,宋朝是非常特殊的例外。
陈寅恪号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以传统士大夫自居的陈寅恪,治史时段涵括隋唐以前及明清之际,唯于特别推崇的两宋政治文化罕有著述,恰可以理解为现代史家对意识形态局囿的自觉规避。这一微妙的“陈寅恪现象”,昭示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困难——宋代文献相当程度上是宋儒的意识形态阐释,近现代中国学者政治观念五花八门,而人格仍多受宋儒影响,宋儒意识形态成为宋代政治史研究或有形或无形、却难以逾越的障碍。
综观现代宋史诸家:独具现代史识的张荫麟讨论宋朝开国规模、重新发明“斧声烛影”等谜案,尚未在传统权力斗争、典章制度、政策得失范畴之外开创全新局面;邓广铭在制度考证之后,重点研究民族英雄与改革家,无不具有深刻时代烙印。及至1980年代以来,重新接受海外唐宋变革、权力限制等观念的影响,宋儒精神既被神秘赋予现代政治学意味,又契合中国文人的士大夫情结,士大夫政治论遂成为宋代政治史叙述主流叙述模式,并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登峰造极之作。由此而论,近百年宋代政治史经历了由传统意识形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叙述)、传统政治史范畴(张荫麟、邓广铭)、到传统与西方意识形态神秘结合(王瑞来、余英时、邓小南等)的奇异回转。当然在此之外,也有某些更具现代史学意味的宋代政治史研究,除西方的唐宋变革论、精英地方化等学说之外,还包括阶级史观下对宋代地主阶级政治诉求的讨论,以及政治集团(何冠环、寺地遵)、政治过程(平田茂树)等相关议题,影响力远不及士大夫政治论。
意识形态阐释释历史的单调化,与专业史家所需处理史料的复杂性之间,容易形成严重的冲突或紧张。这种现象在邓小南《祖宗之法》中尤为明显,其“述而不作”(重事实呈现而轻理论阐释)的特点应该是史家意识与叙述策略双重因素导致的结果。与此相反,之前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理论阐释过度深刻而史实梳理明显粗疏,甚至被某些学者误认为“通俗”作品——这或许是《朱熹的历史世界》影响特别深远的原因之一。
《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孝宗淳熙以后,朝臣分化为道学型士大夫与官僚两大政治集团,由此形成的对孝、光之际政治史叙述呈现出“正邪不两立”的意味,给人“忠奸分明”的民间史观的印象,与宋朝政治演化的实际境况脱节比较明显。因此宋史学界一直期待更加客观、更具洞察力的政治史作品,以纠正极端“士大夫政治论”造成的理解误区。2019年,李超的《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该著指出,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道学叙事直接影响的结果”,理学叙事出自理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其可信究竟如何,非常值得怀疑。以此为切入点,李超重新梳理光宗至宁宗朝前期政治史脉络:贯穿于宁宗前期十四年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间的对抗;随着杨氏入宫直至立为皇后,主要矛盾演变为以杨皇后、韩侂胄两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开禧北伐的发动,不是出于士大夫自南宋建立以来对于恢复理想的追求,而是韩侂胄为巩固自身权位而迫不得已之举,杨皇后、史弥远等人联合发动政变以推翻韩侂胄,也是杨、韩盾难以调和的结果,属于权力斗争,与主和、主战基本无涉。李超进一步指出,依赖皇权进行政治变革,是赵汝愚发动绍熙政变的动机之一,但他试图以侵犯皇权的方式达到目的,犯下传统政治伦理的大忌;官僚集团未必一贯反道学,庆元党禁大部分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是主张调停的官员,韩侂胄的权势反而未必依附于皇权,等等。这些观点呈现的政治复杂性远非“士大夫限制皇权”这种单调的理念所能涵盖,既为还原宋代政治史的事实开创局面,也为突破狭隘的“士大夫政治”观树立研究范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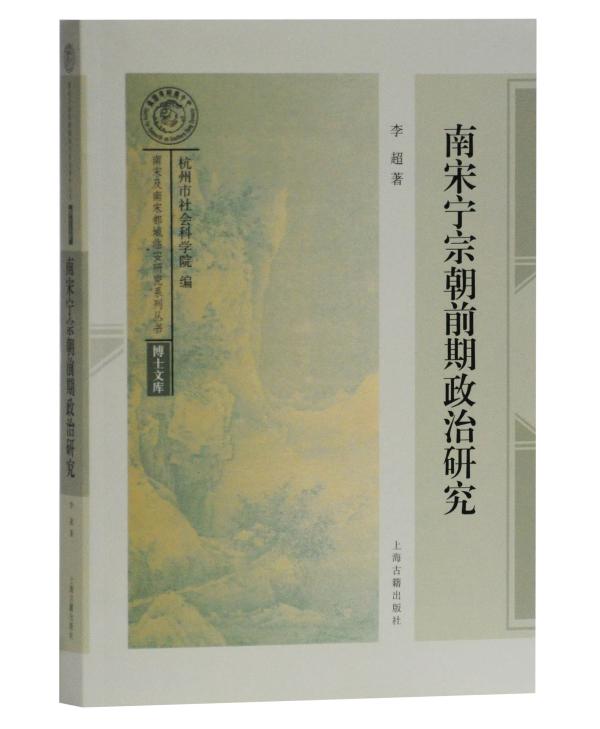
《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李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出版
二
相对于既有研究,《南宋宁宗朝前朝政治研究》各章都有明显创新:
第一章《从内禅到党禁》。关于庆元党禁的原因,以往研究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强调党禁是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权力斗争——赵汝愚在绍熙内禅后未能满足韩侂胄建节的要求,引起了韩侂胄的嫉恨,于是韩侂胄利用自身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将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加以清算;另一种是将党禁放在孝宗朝以来道学与反道学斗争的脉络下来理解。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揭示党禁形成的原因,但忽视宁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绍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光宗坚持不主持丧事的确引发严重政治危机,但化解危机的办法,宰相留正主张立嘉王(即后来的宁宗)为太子,再由太子监国代行丧事最为稳妥的。赵汝愚决意发动政变,迫使光宗退位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光宗因患病无法正常理政,导致李皇后干政;二是光宗即位后遵循孝宗晚年之政,光宗本人已成政治革新最主要的障碍。赵汝愚废父立子的做法是对皇权的严重侵犯,其大力引援道学人士入朝则授人以结党擅权之口实。宁宗对赵汝愚的猜忌日益加深,与赵汝愚有矛盾的的韩侂胄等朝臣利用这点打击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宁宗即位后的这场政争包含多种不同的矛盾,主要矛盾应是皇权与赵汝愚所掌握的外朝权力之间的冲突。
第二章《庆元党禁的“虚像”》。学界对庆元党禁对道学影响的认识上有着较大差异,有学者认为这是宋朝自崇宁党禁后的第二次“道难”,且其惨烈程度甚于第一次;有学者认为党禁的执行并不严苛,只是道学获得独尊地位后的有意夸大。其实庆元党禁中受惩处的官员依然可以聚徒讲学、往来书信,道学人士在庆元二年(1196)、庆元五年(1199)两次科举中也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所谓“伪学逆党籍”向来被视作是党禁高潮的标志,不过由于部分官员的反对,朝廷虽然在邸报公布过一份党籍名单,但没有正式颁行。李心传在这份邸报名单基础上,补充部分在党禁期间遭到贬谪的官员姓名,将其记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这份名单的结构与“元祐党籍”基本一致,李心传之所以这样做,应该是想将庆元党禁与崇宁党禁联系起来,在韩侂胄掌权的情况下委婉地表达对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的褒贬,但从未把这份名单称作是朝廷正式颁行实施的“党籍”。庆元党禁没有道学叙事描述的那样严厉,一方面斗争双方吸取崇宁党禁的教训而有所克制,另一方面与朝廷中调停势力的存在有关。
第三章《调停势力与党禁的松弛》。学界一般将庆元党禁、开禧北伐视为韩侂胄专权的两个阶段,这与南宋时人的看法有一定区别。根据魏了翁等人的论述,韩侂胄当政大致可分为“安静”“皇极”“振作”三个阶段,“皇极”即是党禁松弛阶段,以往研究对此相当忽略。其实党禁之初,赵汝愚及其追随者已被“一网打尽”,党禁时期与反道学势力互动的不是道学势力,而是朝中一批主张调停的官员。庆元初,以宰相余端礼、执政郑侨为代表的调停势力极力避免党禁升级,此后高宗吴皇后利用宁宗皇子出生的契机开启党禁松弛的进程。这种背景下,韩侂胄逐渐倾向调停,庆元三年(1197)、庆元五年(1199)朝中两次攻击道学的浪潮均被化解。
第四章《韩侂胄的困境与北伐》。对韩侂胄的研究多强调其近习身份,其实专权之初外戚是韩侂胄的重要身份。韩侂胄的地位介于内廷与外朝之间,面临宦官、后妃与外朝士大夫内外两方面的挑战。韩皇后去世后,继起的杨皇后与宁宗身边的宦官逐渐与韩侂胄处于对立状态,失去外戚身份的韩侂胄亟需由外戚专权转向宰相专权。然而外朝宰执大臣不愿看到韩侂胄的凌驾之势,韩侂胄第一次寻求出任平章军国事的努力因中枢大臣的反对而失败。于是韩侂胄打出“北伐”旗号,逐步放松党禁,以寻求新的支持者。开禧元年(1205),韩侂胄顺利出任平章军国事,并为巩固权势,伺机发动北伐。韩侂胄北伐的动力与其说是主战声浪、恢复大义,不如说是专权形态的急剧转变。
第五章《韩侂胄之死新释》。传统观点认为,韩侂胄在北伐遇挫后,一度向金求和,但金人的函首要求致使韩侂胄大怒,并促使史弥远等主和派联合杨皇后发动政变,并与金国屈辱议和。其实韩侂胄北伐受挫后立刻选择退缩,金人并未拒绝将韩侂胄作为谈判对象,并且默认宋方以苏师旦、邓友龙作为“替罪羊”的做法。开禧三年(1207)宋金和议基本达成共识。而韩侂胄的反对者聚拢在杨皇后周围,在战争结束前冒险发动政变。杨皇后主导的这场政变是她与韩侂胄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宋金和议关于函首的内容是金方得知韩侂胄死讯后临时增加的。为制造政变的合法性,杨皇后、史弥远等曲解韩侂胄的许多行为,甚至捏造某些事实,将权力斗争中的冒险政变塑造成和战之争。
第六章《“共治”理想的破灭与史弥远上台》。君臣“共治”的政治模式在南宋多数时期并未出现,但作为一种理想始终深入士大夫人心。韩侂胄专权结束后的清算、批判,最终指向其实不是韩侂胄本身,而是现实的政局走向。他们对近习干政的批评,其实更多是出于对杨皇后与史弥远联合把持朝政的的担忧。钱象祖、卫泾等宰执大臣希望太子与宰执大臣组成资善堂会议共同处理政务,宰执大臣兼任东宫官属维系对朝政的集体领导,但是景献太子对史弥远的青睐使钱象祖等人功亏一篑。史弥远专权并不是单纯的宰相专权,而是杨皇后、景献太子、史弥远三人的联合专权,杨皇后主持于内,史弥远把持于外,景献太子负责沟通内外。侂胄专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过程,韩侂胄致力于出任平章军国事意味着他在有意识地寻求由外戚、近习专权到宰相专权的转变。与韩侂胄相比,史弥远得到了皇后、太子的支持与配合,得以维持长期而稳固的专权局面。
李超最后总结:和战问题虽然时常出现在宁宗朝前期士大夫的言论中,但当时朝廷上并不存在以主和、主战为界限的阵营。宁宗朝前期政治发展的主要矛盾冲突,首先是围绕在宁宗周围的一批政治势力与以赵汝愚为代表的革新势力之间的冲突,再是分为以杨皇后、韩侂胄为中心的政治势力间的对立。后世史书中对庆元党禁的书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相当的差距,调和思想与调停势力的存在也几乎隐没不见。开禧北伐只是内部政治的外在延伸,其开始与结束都与内部政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三
李超对于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研究,容易给人故作颠覆之论的印象。不过对于一篇由博士论文改写的书稿,四平八稳或老练精深并不是合适的评判标准。李超的研究并非无可质疑、无以改进,比如庆元党禁是否真的谈不上上严厉,和战之争是否在政治变局中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这些问题应该仍有讨论的空间。但毋庸置疑,这部南宋政治史作品叙述脉络丰富清晰,史料交待充分确实,政局剖析合情合理,更重要是显示出对权力斗争与政治变幻的复杂性比较稳妥的把握能力。
从余英时到李超,绍熙政变前后政治史研究的路径看似由政治文化向更传统的权力斗争回归,其实不然。李超揭示的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史充满了宫廷政变式的阴谋,令人联想玄武门之变、斧声烛影等特殊政治事件。但玄武门之变、斧声烛影无论多么神秘,毕竟史有明载。揭示出李世民对唐朝开国的贡献不如李建成,或者赵光义弑兄篡位,即使结论可靠,也主要体现为传统考证史学的精深。而李超揭示的诸如赵汝愚为推行新政而直接侵犯皇权、和战之争与韩侂胄北伐无关、庆元党禁言过其实、调停势力与调和思想的存在等,都是传统史学叙事隐讳的议题。仅依赖传统的考证功夫不足以重新揭示这些议题,如果尚未形成全新的宋代政治史观念,就需要更新史学观念或史料处理方法才能达成类似的研究效果。李超主要运用所谓“史料批判式研究”(个人更习惯使用“文本与书写的视角”这样冗长的概念)的研究方法,指出现在所见有关庆元党禁与韩侂胄北伐的记载,是南宋后期道学家及史弥远集团有意建构的产物;力主调停的政治势力及其调和思想,是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现存宋代史书的主流叙事中隐没不见;李心传所记载的学党名单被一步步误解为由朝廷正式颁布的所谓“伪学逆党籍”,“虽然是无意造成的结果,却反映了南宋士人看待党争的固定认识模式”。虽然所谓的“史料批判”或“文本与书写的视角”早已算不得创举,但当李超指出:
庆元党禁就其严厉程度而言,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南宋士人在记录此事时,采用了同样的认知模式,且不断地将两者进行类比,就逐渐给人造成一种历史重演的印象,所谓“伪学逆党籍”便是在这种状况下一步步演变为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种特定的认知模式在无形之中形塑了宋代史籍中对相关史事的记载,甚至今天的许多研究也始终未能摆脱这种成见的束缚,对这种史实与书写的背离,当成为南宋史研究中需要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之一。
仍可以说这是宋代政治史领域内一次“古史辨”式的变革。
当然与李超的突破相比,更令人感慨或值得反思的是宋代政治史研究摆脱既有书写观念之束缚竟如何之艰难。从“积极”的方面讲,这的确显示出宋文化的超级魅力。但对此不是自觉地祛魅,而是陶醉于甚至无节制地宣扬这种文化的超级魅力,这样的宋代历史研究者恐怕是值得警惕的。
由李超的研究重视审视宋代政治史:一方面,之前数十年研究形成的诸多常识恐怕需要重新检讨,比如一般认为因儒学复兴、士大夫政治意识高涨、合理制度构建等达成的对皇权的限制,宋朝已有效地消除后宫(后妃、外戚、宦官)、武人政治弊端,实际情况可能要复复杂得多;另一方面,这不等于说否定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只是需要在复杂得多的政治史解释模式中重新理解士大夫政治。当然这是庞大的议题,超出书评的范围,在此不必展开。
(胡潮晖对本文撰写有贡献。)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