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言》:回答《使女的故事》结局之问,回应当下这个世界
在全球畅销书《使女的故事》出版35年后,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于2019年发布的新作《证言》(The Testaments),一经推出即获得了“英国每四秒售出一本,全球上市首周50万册即告售罄”的成绩,80岁的“加拿大文学女王”阿特伍德也凭借《证言》再度摘获布克奖,成为布克奖历史上获奖年龄最高的作家。
阿特伍德和她亲爱的读者说:“你们曾多次向我提问,关于基列国及其内部运作的细节。这些疑问都成了这本书的灵感来源。而另一部分的灵感来源则是我们正身处其间的这个世界。”
作为《证言》的前身,《使女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末美国在一起政变之后成了由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共和国”(简称“基列国”),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通过录音叙述自己被迫成为生育机器“使女”后的种种经历。
《证言》的故事时间线设置在《使女的故事》结局十五年后,和《使女的故事》具有同样的结构:小说主体由一个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发现的手写材料组成,材料本身是以第一人称重述二十一世纪初的基列共和国的内幕。《证言》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那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此外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丝,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对应了“前基列—基列—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在今年上海书展期间,简体中文版《证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全国首发。8月14日,翻译家袁筱一,学者毛尖、罗岗和《证言》译者于是来到上海朵云书院旗舰店,和读者一起阅读基列国和使女的故事,聊聊阿特伍德书中的世界为何能唤起我们如此强烈的共鸣。

《证言》中文版新书发布会
《证言》是一本非常伟大的答疑录
阿特伍德说,在正式落笔之前,《证言》的部分创作是在《使女的故事》的读者的脑海中进行的,大家在追问——那部小说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三十五年里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本身在改变,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答案的不断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公民现在承受的压力比三十年前更沉重。”她说。
对于小说中的基列国设定,罗岗认为很有意思:“基列国是以男性为主,却又安排女性来管理女性,通过折磨一些精英女性并使其折服,变成所谓的嬷嬷,再让她们制定怎么管理女性,某种程度上又是女性的自治。”
袁筱一强调这种压迫始终是处于循环状态的:“其实对女性的压迫往往是来自于女性。这一点,阿特伍德即使是轻描淡写地写,她的设定也还是包含着一点意味。‘男界’和‘女界’问题在《使女的故事》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尽管基列国的世界观表明男性头脑更专注等一系列优点,但《证言》最后的剧情也证明了男性没有那么伟大。”
于是强调:“基列国这样一个看似男权的国家里其实有一部分完全采用母系社会的管理方法,并且设定得相当详细,比如说女性的教育、婚配,把女性从无到有的生长过程都包含在这个母系社会里面,这是《证言》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她表示:“其实从奥芙弗雷德的视角来看,基列国的男性并没有多幸福,也没有占多大的优势。如果二元对立地来说,基列国对女性的确是反乌托邦的,但反过来它也不是男性的乌托邦。基列国中所有的人,不光女性,还有男性,包括各个阶层的男性,他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哪怕整个国家的制度设定是以延续种族的伟大目标为前提,终究还是一个失败的体制,最终要走向灭亡。”
“某种意义上,这部《证言》是为《使女的故事》读者和观众量身定制,在这层意义上它很独特。每个读者都能通过它找到看《使女的故事》时留下的那些疑问的回答。阿特伍德用一本书的结构来答疑,几乎是一种文本实验。”毛尖说,《证言》是一本非常伟大的答疑录,是游戏,也是特别把读者当上帝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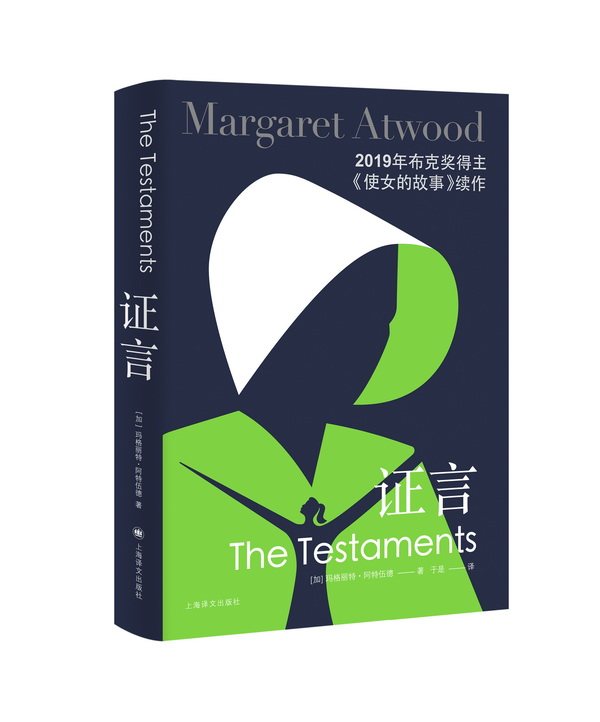
《证言》
绝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和“科幻”
虽然《使女的故事》和《证言》都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女性的生存问题,但阿特伍德始终强调她不是女性主义作家,《证言》和《使女的故事》也不是女性主义作品。她曾在英国独立报的采访中这样说:“女权主义的标签只能贴在那些蓄意将女权主义运动作为小说背景的作者身上。”
对此,袁筱一表示:“至少我读《证言》时没有把它当做女性小说来读。作为比较习惯法国小说的人,我觉得她和法国女作家相比是非常有‘立场’的,而且她非常明确地把她的立场写进小说。在1980年代就能写出《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其实非常了不起,因为当时大家都认同西方的价值观,认为民主、自由、科学技术等一定会把人类带向光明。但阿特伍德却能跳脱出这种话语体系来思考,我认为她的小说不是完全的女性主义作品。”
罗岗认为,比起女性主义作家,阿特伍德更多地吸收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成果,对现代性持反思态度。“现代女性主义赋予女性各种各样的权利,使其从各种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这些权利更多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比如西方人认为女人裹小脚是中国人愚昧的表现,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的象征,但实际上,裹小脚并非中国的普遍现象,通过将特殊现象普通化,就隐隐构成了一种文明的等级制度——西方文明是高等级,中国文明却低一等级。后现代女性主义反思这种普遍性价值,强调女性立场的时候并不需要完全接受来自西方的那一套观点,而要意识到自身历史的独特性”。
“所以回头来看阿特伍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在小说中写出了‘过程’——那些在西方看上去理所当然的女性权利是经过漫长的斗争争取到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里面女性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强调普世价值就可以解决的”。罗岗说。

《使女的故事》
除了女性主义,阿特伍德也一直拒绝把“使女”系列作为科幻作品来定义,尽管故事中的基列国是特定的架空情境,也采用了科幻文学中常见的“末日趋势”,但她认为比起“科幻”,这更是“现实”。在和朱诺·迪亚斯对谈时,她坦言:“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小说中展现的人类的种种行径并非杜撰,在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地方,它们确实发生过;而在当下世界的一些国家,它们正是现实。”
这种“去科幻性”在电视剧中或许体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剧集中始终没有提到在《使女的故事》和《证言》中出现的“2197年的研讨会”。毛尖对此分析:这个删改应该也是和阿特伍德的协商,她不会愿意把这个剧拍成一个科幻剧,如果把2197年放进去会非常明面的科幻。“阿婆也说‘我这本书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从这点来看,此剧做得非常成功。”
毛尖总结,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科幻性”都只是阿特伍德庞大叙事中的下辖主题,她所要表达的远不止这些:“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文本,也不仅是科幻文本,女性和科幻都是被镶嵌在一个更大的权利关系和广阔世界里。阿特伍德的小说中镶嵌了大量更大、更复杂的叙事,因此如果把女性主义或科幻单纯提取出来推为首要议题,就不准确。”
小说与影视改编联动,重新照亮作品的价值
影视剧推动小说续作的诞生在文学史上并不常见,但同名电视剧《使女的故事》的风靡和全球影迷的热切关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阿特伍德续写《证言》。
在《证言》全球发布的2019年,根据《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第三季上映,该剧已在近三年里横扫艾美奖、金球奖和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评论家选择奖。阿特伍德本人还在第一季中客串了一位嬷嬷,在剧中扇了奥芙弗雷德一巴掌。于是在译后记里提到,这一幕明明是阿特伍德自己写出来的场景,阿特伍德演出时却觉得特别恐怖。
“阿特伍德在写《证言》时一直跟《使女的故事》的编剧布鲁斯·米勒保持密切的沟通。米勒把剧集中出现的细节告诉阿特伍德,以保持续作与剧情一致。”对于《证言》的影视化改编,于是则透露:“很多人都在期待拍摄中的第四季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不过据我所知,第四季不会拍到《证言》。今后,《证言》有可能会另起一部新剧。”
毛尖称,一般来说,一流小说是很难被改编成剧的,相较而言,三流甚至四流的小说更适合改编成剧,但《使女的故事》作为电视剧是很成功的。不仅是编导能力,还有时间点的关心。“2017年刚好出现了女德、女权一系列焦点事件,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这类话题推上风口,《使女的故事》电视剧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话题。”
她也非常期待《证言》的影视化:“这个小说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太适合拍成剧了,尤其后半部分提速,也略简单,但很剧本,好像已经为电视剧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剧情准备。”
小说与影视的联动魅力或许正在于此。尽管阿特伍德被不少人认为是“最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她此前一直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处境。《使女的故事》在出版伊始虽有过反响,却并没有“出圈”,直到2017年电视剧的翻拍使其风靡全球,小说也频频跃上多国的畅销书榜首。
罗岗说:“阿特伍德实际上是一个很强悍的作家,我认为她是所有女作家里思想能力最强悍的。《使女的故事》在2017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对于阿特伍德来讲,是电视剧重新照亮这部沉寂多年的作品的价值。”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