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海夏天乐趣之三:好声音数金铃子和叫蝈蝈
原创 袁念琪 上海人家AB面
夏日里给我们带来乐趣的虫儿,除了“爷胡子”和“螊绩”,还有金铃子、叫蝈蝈、金乌龟、天牛……没了它们,这个夏天还真是少了不少味道。
大合唱的鸣虫,有两位角是我们孩子欢喜的,一是金铃子,二是叫蝈蝈。它俩称得上是夏日的好声音,一个如女高音,一个似男高音。长大了才知道,对金铃子和叫蝈蝈,大人才是爱得深,玩得真。

我觉得,捉金铃子比捉“螊绩”难。因为它比“螊绩”小,如它的袖珍版,像粒赤豆,发现较难。在我们的花园里,就没见过金铃子。在永嘉路小学读书时,学校组织去对面文化广场劳动。在4号门后台外的草地拔草时,有同学捉到了金铃子。听老法师讲:上海郊区的金铃子,品质要排在浙江、安徽之上。

上海人叫做“叫蝈蝈”的蝈蝈,在上海也没处可捉。在鸣虫里,要数叫蝈蝈个头最大,一个抵得上三只“螊绩”。与“螊绩”一样,会叫的是雄虫;但体量决定音量,声响是“螊绩”的几倍。这个穿着一身绿军装的大鸣虫,那两条大长腿的后腿是格外引人注目,跳跃水平肯定适合跨栏。没在野外捕捉过叫蝈蝈,想那难度是要大于捉“螊绩”的;虽然捕捉是在大白天里,可它蹦跳的速度和高度远超“螊绩”。
说叫蝈蝈是吃昆虫的食肉动物。可从田间关进笼,自农村进入城市后,它一直是吃素的,黄黄的丝瓜花,切成粒的南瓜。现在不敢养,这家伙叫得实在嘹亮,已经踩到扰民的红线了。
说叫蝈蝈按地域分北蝈蝈和南蝈蝈,无论个头还是叫声,都是北胜于南。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国人玩叫蝈蝈如“螊绩”一样,也是历史悠久,到宋成热走红,至明代普及;到清代,许多皇帝都是叫蝈蝈迷。


虽说在上海捉不到金铃子和叫蝈蝈,但能买到,就是在极左猖獗的年代,“螊绩”因涉嫌赌博而不能公开买卖。家附近南昌路一家私人剃头店隔壁,就有卖金铃子和叫蝈蝈。金铃子放在一只只玻璃盖的、如火柴盒大小的木盒里,叫蝈蝈置身于一个个澄黄色的竹编小笼里。

我在一位欢喜“螊绩”的朋友那里,欣赏他收藏的金铃子盒子,有牛角的也有象牙雕的。那天,德国一家电视台拍得津津有味。



前些年的冬天,我在办公室里听到了金铃子欢快的叫声,声音来自同事的衣内。重阳后,“螊绩”就没声音了,而金铃子仍在歌唱,它是个跨季的歌手;寿命较长的,可一路高歌猛进,唱过春节。后来换了个办公室,就没这耳福了。


金铃子和叫蝈蝈也进入作家的小说。先读到的是浩然的《大肚子蝈蝈》,我还是个小学生,羡慕那蝈蝈:“大大的肚子,长长的腿,牙齿象一把大钳子,亮亮的翅膀象玻璃片儿;还有两条长胡须,一甩一甩的;叫起来声音特别大,“蝈、蝈、蝈”,震得耳朵发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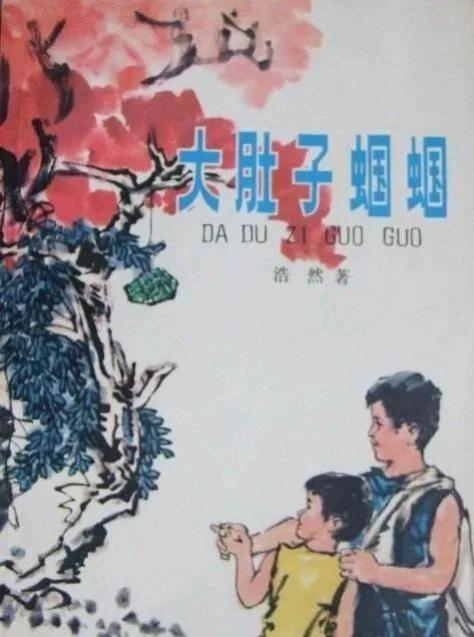
上大学,映入眼帘的是《失去的金铃子》。与日叫夜叫、越热叫得越响的蝈蝈相反,金铃子则是低吟轻唱,委婉清新。聂华苓说,“金铃子和杜鹃本身并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追寻的过程。”但是,不管是金铃子还是叫蝈蝈,失去后是再不会回来了;只有鸣叫留存心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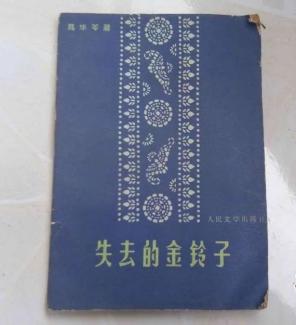
光彩,更为坚实。”(聂华苓)
在夏天带给我们乐趣的虫子里,还有上海人叫“金乌龟”的金龟子和天牛,这属于虫里屌丝。“金乌龟”乌黑,在阳光下发着铜绿色、金属般的光。天牛也是浑身黑打底,添上点点白斑,没见过花天牛;捉玩天牛,要小心被咬。大人看见我们玩“金乌龟”是嗤之以鼻,说这东西生活在粪坑旁,但我们都是在树上捉的,有时,它会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掉在你面前。
这两位卖相难看不消说,而且都是不会叫的“哑板”。但是,蚊子肉也是肉;有虫玩就行。“金乌龟”和天牛也有玩的乐子;用线扎好,让它们飞起来,一头牵在手里,像放风筝似的。
袁念琪。1978年从农场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上海电视台,高级编辑(专业技术二级),上海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等,入选王蒙主编《中国最佳散文》和《中国新闻年鉴》。著有《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上海姻缘》、《上海B面》和《零食当饭吃》等。
原标题:《上海夏天乐趣之三:好声音数金铃子和叫蝈蝈》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