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商品与女性欲望:消费社会强化了男性权威,也对其造成了威胁
在19世纪后期,消费者经常被再现成一个女人。换句话说,消费这个范畴将女性气质作为现代的核心特征,而之前生产和理性化的话语并未这样做过。因此,消费超越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而这种区分曾常常被拿来将女人贬谪到前现代的领域。不仅有百货商店专门为女性提供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而且现代工业和商业通过对家庭的商品化,越来越强烈地侵犯了私人和家庭领域的神圣性。尽管中产阶级妇女看似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因为她们只负责购买而不参与生产,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们作为消费者,非常熟悉快速变化的时尚和生活方式,而这两方面正是现代性经验的重要部分。消费文化的出现,促成了女性新的主体形式的塑造,女人私密的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被商品的公共再现及这些再现所承诺的满足感所影响。
然而,现代性的这种女性化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性的妖魔化。自19世纪中期以来,有很多激进和保守的知识分子撰文批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观念就等于一种悲观的看法,即女性气质是捉摸不定的,但又具有奇特的消极色彩,认为女性受到了日益兴起的五彩斑斓的消费文化的引诱。现代性不再代表朝向更理性社会的进步发展,而是体现了非理性主义的增长,体现了受压抑的天性以原始欲望形式的重返。如罗莎琳德·威廉姆斯(Rosalind Williams)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费概念的贬义色彩就源于女性对身体需求的屈从。”女性被描述成购物机器,她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总是想要挥霍钱财去占有更多商品。还有一种至今依然盛行的陈词滥调,认为贪得无厌的女性购物者体现了经济过剩与主流女性形象中情欲过剩的密切关联。然而,这种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可以被看作现代的,因为它是一种受管控的欲望,受控于一种计算和理性化的逻辑,所服务的是利益动机。女人容易情绪化,具有被动性,缺乏主见,这些特点使得她们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理想对象,而社会以享乐的商业化为前提,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于是无孔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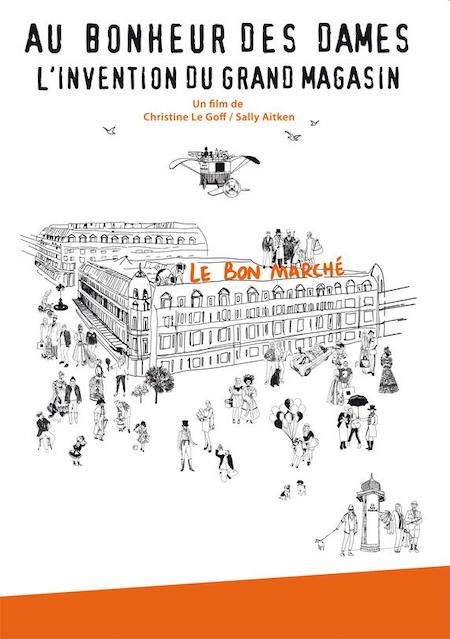
《妇女乐园(大商场的诞生)》纪录片海报,2011。
这种思潮在20世纪对现代性和大众文化的看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女人仍然是典型的消费者,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明显的焦虑,那就是随着愈发盛行的商品化所带来的阉割效应,男人也因此变得女性化。男性知识分子在描述市场营销对个体的摆布控制时,经常使用“受诱”这个字眼,该词总是让人想起被动性、共谋和享乐的混合体,他们认为这就是现代消费者的典型姿态。主体是去中心的,不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只能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图像产业所俘获。人们在控诉20世纪消费主义时,经常诉诸一种怀旧之情,追缅曾经强健的个体自我,而无处不在、光鲜动人的媒体仿像(simulations)文化已经侵蚀了这种个体自我并将之女性化。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让·鲍德里亚最近的著作,关于商品拜物教和符号暴政的理论话语揭示出了一个不断性别化的潜文本。
很长时间以来,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在采用并强化这种反乌托邦的观念,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利益在建构现代女性气质时有着系统的一致性。女人被描述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被困在物化图像的网中,她们于是与自己真实的身份相疏离。从时尚、化妆品、女性杂志,或者其他明显女性化的消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任何愉悦,都仅仅被解读为一种症候(symptom),是女性被体制化的父权控制机制所操纵。近年来,一些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拒绝这种操纵论的观点,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可能存在积极的协商和意义的再语境化。人们已经开始批评传统的左派和女性主义者对消费文化的不满,认为这种不满背后其实是过度的清教主义和禁欲主义,认为这些人陷入了对于前现代真实主体的怀旧式迷思,他们对“真正需要”(real needs)的定义是站不住脚的,也是功利主义的。
我现在不打算简单地为消费做出辩护;必须承认,有些人现在过于赞颂女性消费者具有抵抗力的能动性,将之变成新的正统观念,但这样做的危险是,他们常常忽视许多女性有限的选择,同时她们获取商品的渠道也被经济、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因素所左右。然而,女性主义理论显然需要对生产/消费的二分法保持怀疑态度,这种二分法总是将后者贬低为一种被动的、非理性的活动。我在本章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这种二分法,我希望研究消费进行隐喻化的历史,因为它塑造了我们对经济与文本交换关系的理解。我认为,对购物和阅读的再现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女性消费者的贪婪。
商品和女性欲望
在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用来描述女性地位的常见经济隐喻也许都和商品有关。正如玛丽·安·多恩(Marie Ann Doane)所言:“女人的客体化,她们对拜物、展示、盈亏、剩余价值生产的易感性,都让她们与商品形态相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女人被看作男人之间交易的对象,为了吸引男性买主的目光,她不得不尽可能增强自己的诱惑力。我已经指出,城市妓女是女性商品化在这方面最生动、最真实的体现。特别是在19世纪的法国,交际花成为情欲化的现代性的典型象征。
然而,如果女人可以被看作消费的对象,那么她们同样也可以成为消费的主体,因为随着大规模生产和现代零售战略的到来,人与物之间的日常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19世纪中叶出现的百货商店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说明新兴的经济正在日益将销售面向女性。百货商店最初不过是大一点的布料店,后来这种商店迅速增加了所售商品的种类,目的是满足女性消费者及其家庭的潜在需求,而这种需求是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创造出来的。这种从商品到景观的转变,在19世纪晚期出现的大型博览会热潮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些博览会就是消费的丰碑,向好奇的游客们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稀奇物件。这里,女性形象再次成为一种象征;比如,在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在标志性的大门上方“是一个穿着紧身裙飞起来的塞壬,她头上是巴黎市的象征之船,一件仿貂皮的晚礼服披在她身上,俨然一个巴黎贵妇”。罗莎琳德·威廉姆斯指出,这些女性化现代性的符号出现,正好顺应了万国博览会对自身功能的定位,即更强调快感和娱乐,而非道德教育。最后,广告在这个时候开始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营销技巧,刺激消费者去追求商品所倡导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因为当时的社会分工将购物视为女性的工作,所以首先是女性通过女性形象的大规模生产而以这种方式遭到了质询,尽管中产阶级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这让她们必须煞费苦心地考虑时尚着装和自我展现。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消费膨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专注于女性的享乐。消费主义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女性欲望的话语。尽管在这个世纪女性性欲一直存在争议,它要么被否定,要么被投射为“红颜祸水”的危险形象,但女性对商品的欲望能被公众视为合法的需求,哪怕这种需求常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19世纪晚期的零售商和市场营销部门总是通过饱含情欲的商品陈列和诱惑,急切地试图激发这样的欲望,而商业杂志和报纸都以赞许的口吻来谈论女人在抗拒广告诱惑上的无能,称赞女性注定无法逃脱琳琅满目的新产品的诱惑。在异性恋关系中,女人经常被描述为物,似乎只有当女性与其他客体产生联系时,她才能获得积极的主体性。欲望的回路是从男人流向女人,又从女人流向商品。
但是,假如女性对购物的快感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有害无益呢?也许,一旦被唤醒,这种消费欲就会产生令人不安、不可预见的影响,从而破坏社会结构,破坏家庭内部的父权制的权威性。因此,人们在世纪末对女性消费这个新现象常常莫衷一是。一方面,消费被再现为必要的行为,是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义务和公民责任,即便零售商也经常提到女性购物者的顺从,她们“像羊一样在软性商品标注的道路上走着”。这些话语要么将女人视为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被动受益者,要么把她们看成这个进程的受害者,究竟选择哪种立场则因视角而异。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道德革命,让下层阶级和女人的自我与嫉妒冲动得到了释放,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现有社会等级的稳定。例如,一位美国作家指出,许多女性消费者的自我放纵达到了危险程度,“(女人)目无法纪,厌恶规矩,如果不加以抵抗,她们就任由自己的性子乱来”。一种以自我满足为核心的新思潮正日益流行,很可能会对两性关系产生不良的、不可预见的影响。
因此,女性消费者的形象成了一个语义复杂的区域,关乎现代性中文化的想象和由此产生的对男女关系的影响。这一章我要讨论埃米尔·左拉的《妇女乐园》和《娜娜》,以及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女性形象的复杂多义性。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自然及大众消费重要性的关注,显然是源自19世纪末巴黎所象征的现代“消费革命”的显赫场域。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他们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关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意义,当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尽管如此,他们很多人普遍表现出了一种焦虑,担心大规模生产的奢侈品可能带来不良的社会和道德影响,而这些反应大多与主流的性别观念相关。本章将要讨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同时代人对性与资本之间关系的焦虑不安,对女性消费者的矛盾看法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被描绘成现代性的受害者,但女性也成了现代性的特权行为人;专制的资本使女人臣服,但与此同时,新兴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又推动了社会的女性化。
关于女性消费者的各种意义含混不清,这说明父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比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的更加复杂。因为,如果消费文化只是强化了女性的客体性和软弱状态,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种现象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批评,被认为威胁到了男人对女人的权威性。如盖尔·里基(Gail Reekie)所言,如果“零售商、经理人和营销专家组成了男性同盟,他们因为都是男人而团结在一起,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从女性消费者的顺从上获得利润”,那为什么其他男人会对大众文化如此忧心忡忡,将之视为一种严重的去势现象?本章所讨论的小说将女性特质问题置于现代性的核心,审视了性别政治语境下消费文化的复杂性。通过将中产阶级女性嵌入欲望和交换的回路,大众消费的增长既是对男性身份和权威结构的强化,亦是对它们的威胁。
购物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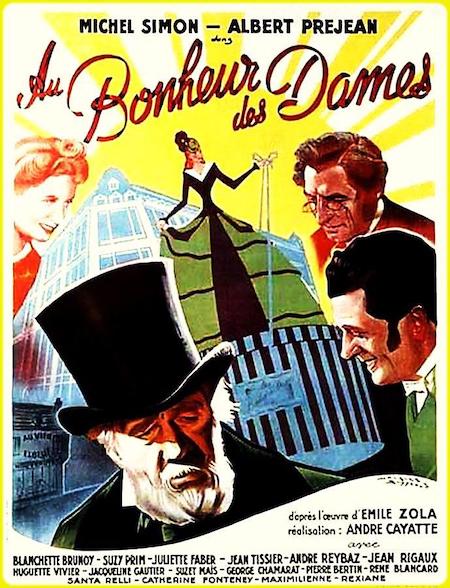
《妇女乐园》纪录片海报,1943。
在左拉的小说《妇女乐园》(Au bonbeur des dames, 1883)中, 标题就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名字,它以巴黎著名的乐蓬马歇百货商店(Le Bon Marché)为原型, 这个商店成为读者心目中最难忘的角色。这家商店有时候被描述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有时候又被描述成童话般的梦幻宫殿,它的发展构成了文本的叙事动力。这个像人一样具有破坏性和诱惑性的“现代商业大教堂”在源源不断地将女性顾客引进大门时,又毁掉了附近的小店商铺,甚至将它们逼上绝路。在左拉的描述中,百货商店是社会进步的含混象征,性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核心。争夺权力的经济斗争总是与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女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受其影响。
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都促使人们关注到百货商店在塑造文化现代性方面的重要性。大商场(grand magasin)带来了一系列重大的营销创新:固定价格,这使讨价还价变得没有必要;“免费入场”,这就让顾客在没有任何购买义务的情况下查看陈列的商品;以及同一地点在售商品范围和种类上的急剧扩大。于是,购物第一次被视为休闲活动;百货商店提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景观,以精致的商品展示,为购物者和路人提供了视觉愉悦。百货商店在商品审美化和生活方式营销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既区分又模糊了阶级差别,鼓励所有人都向往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百货商店不仅出售商品,也出售消费行为本身,将日常购物活动转变为让资产阶级大众获得感官享受的快乐体验。
正是百货商店的现代特质吸引了左拉,百货商店成为他笔下一个代表性的虚构场域,让他可以去探究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两性关系的影响。他为这本小说的写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多次长时间探访巴黎的商店,采访多位零售商和经理,仔细阅读大量关于购物、营销实践和员工工作条件的期刊及报纸文章。他为《妇女乐园》做的笔记非常详细;笔记多达数百页,内容包括购物目录的摘要、特色建筑物的草图,以及其他许多关于零售业运作机制的注释。这些丰富的记录最后变成了小说,细致刻画了商品拜物教。《妇女乐园》是消费的赞美诗,是一部以物质性为主导的小说,详尽言说了现代消费商品的多样性。就像它所描绘的百货商店一样,小说也向读者/消费者展现了商品,通过堆砌大量的商品,引诱他们或使他们变得麻木。一些段落用分类方法描述了花边类型、颜色、丝绸重量、地毯和垫子的样式,模仿了盘点存货的精确性和重复性。尽管小说批评了百货商店顾客的非理性和冲动性,但左拉的文字本身暴露出对消费文化中那些神奇物品的痴迷。
正如左拉小说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百货商店是一个被认为具有独特女性特征的公共空间,许诺为中产女性提供放纵、奢侈和幻想。这不仅是一个购物的地方,它还允许女性浏览商品、欣赏橱窗,它成为女性朋友聚会之所,还有各种设施让女性使用,如图书馆和茶室。伊丽莎白·威尔逊认为:“百货商店在真正意义上帮助中产阶级女性摆脱了家庭束缚。它成了女人可以安全舒适地会见女性朋友的地方,她们可以在这儿放松休息。”在另一个意义上,它还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现代空间模式,它原则上(如果不是实际上)向所有人敞开大门。然而,这个公共领域同时又是对私人领域的延伸,它为顾客提供亲密和愉悦的体验,目的是带来资产阶级家庭的那种舒适感(当然,这是放大版的家庭)。因此,一位作家评论道:“她(顾客)有必要把大商场当作她的第二个家,这里更宽敞,更漂亮,更豪华。正如左拉的小说所指出的,这种公共领域的女性化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和装饰风格,意在让女性消费者感到轻松自在。百货商店里陈列的女性物件——蕾丝、皮草、裙子、贴身内衣——很快就被光临的顾客们弄得凌乱不堪,这反而有助于加强那种“闺蜜式”的亲密感。因此,“妇女乐园”的顾客把百货商店既当作商业交易场所,又当作浪漫的约会场所。商店老板奥克塔夫·慕雷(Octave Mouret)苦笑地承认,她们实际上把这里当成了家。
当时的百货商店是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范例,它与政治共同体和理想辩论的理想并不相干,而是关乎感官体验和欲望的商业化。尽管很多人认为商业的发展是进步的标志,让消费者受益,也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发展存在阴暗面,它鼓励女性追求享乐、自我寻欢,这种诱惑本身就是让女性特别没有招架之力的。这时还出现了盗窃癖(kleptomania),它被认为是女性化和现代性的病症,这个惊人的例子说明,在消费文化的内核中存在与性有关的疾病。最让人不安的是,原本是无可指摘的、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性也遭到了商业的毒害,这也就打破了人们对中产阶级女性良好道德观的看法。当时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为了理解这费解的新现象,就将女性、歇斯底里症和百货商店的危险自由地联系起来。人们当时普遍认为商店扒窃是偏执的体现,扒窃犯自己也认可这种诊断,这就滋长一种观点,即将中产阶级女性盗窃视为对诱惑无能为力,她们不是罪犯,而是在无法控制的非理性冲动驱使下才去扒窃的。与此同时,消费品层出不穷、随处可买,现代社会管理松懈、道德瓦解,这些都被认为是诱发盗窃的原因。
左拉的小说还表达了对于现代化所导致的终极社会后果的不安,这种让人熟悉的不安感体现在他对生产的赞颂和对与之对立的消费的病态化。虽然小说描述了无节制的增长所带来的人力消耗,但商店老板奥克塔夫·慕雷对于经济扩张的热切信念,被视为一种值得称道的理性化理想,是资本主义发展释放的巨大辉煌的进步的体现。然而,慕雷那些同样迫不及待痴迷于消费的女顾客,却没有被赋予相同的英雄形象和世界历史的尊严。她们不是代表进步,而是代表了现代性的倒退,其特征是发泄出了一种无节制欲望的婴儿般的非理性。走上歧路的商店扒手和受人尊敬的顾客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因为她们都屈服于商品的诱惑。
情欲驱使下的女性消费天性为左拉的小说提供了主题。小说中对诱惑和引诱的描述比比皆是;书中百货商店里的顾客永远都是屏住呼吸,兴奋不已,欲望让她们满脸通红,仿佛是在迎接一个情人。她们在感官上极度兴奋,诱人的商品让她们眼花缭乱,她们完全沉溺于购物的快感,在小说中这种快感被露骨地描述为一种高涨的性激情。例如,左拉描述商店的一个常客,她和女儿站在蕾丝柜台边,“她把手深深地埋入堆积如山的蕾丝、马林网眼纱、瓦朗斯花边及尚蒂伊花边中,她的手指因为渴望而颤抖,她的脸逐渐红润,充满感官上的快感;她旁边的布兰奇也受到同一种激情的感染,脸色苍白,皮肤丰满而柔软”。消费在此卸掉了所有以满足客观需要为由的理性伪装,女顾客不成熟的情感和感官冲动被描述成消费的主要动力。消费篡夺了宗教在女人生活中的地位,促使女人盲目崇拜于一种理想的女性美,在欣欣然中迷失了自我。
尽管这些场景证明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天性崇尚直觉,渴望性爱,但这种情欲快感反过来又受零售商的营销策略的驱使。慕雷的成功秘诀是,他善于激发和控制女人的欲望。他引入一种现代的营销术——大幅削减商品选择项,承诺向不满意的顾客立刻退款——这就消除了谨慎消费者的顾虑。他重新调整了商店的布局,让他的顾客们失去方向感,这样顾客们就会徜徉于消费迷宫,受到更多迷人商品的诱惑。但最主要的是,慕雷巧妙的商品陈设能够吸引顾客。完全用手套搭建起来的瑞士小屋,敞开摆放的精致雨伞,铺满异国情调地毯的“东方风格”房间,炫目的白色窗帘,举目四望全是床单和毛巾——这些奢华的、近乎超现实的展览让顾客兴奋不已。女性日常物件因数量众多和诡异的排列方式而让人耳目一新,难以忘却。在这些华丽的展示中,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蒙太奇的美学技巧先发制人,它预示了在20世纪的消费文化中,风格化展示和美学景观将占有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视觉快感是刺激女性消费欲望的中心策略。如果“游荡者”是城市公共空间活动里自由活动的男性化象征,那么百货商店(本雅明将之描述为“游荡者”最不常去的地方)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空间,让她们可以以相似的方式漫步和观察。如果说“游荡者体现了现代性的凝视,这种凝视既贪婪又色情”,那么这种凝视绝非仅限于男性,而是女性与商品之间偷窥关系的决定性特征。然而,游荡者的超然物外则可能被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一种更亲密的关系所取代,它复杂地混杂了主动的欲望和图像、物品、生活风格对女性的成功诱惑。雷切尔·鲍尔比写道:“主体和客体、主动和被动、拥有者和被拥有者、独特和普遍之间的界限,被消费者和消费品之间无休止的反身性互动打破……引诱者和被引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女人和商品彼此炫耀,充满爱意,让年轻女孩在镜中顾影自怜这一经典画面得以延伸和强化。”
在经济上,慕雷成功地管控了女人的这种自恋式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新型资产阶级企业家的代表,他大胆的创新暴露了传统的销售模式的局限性。“妇女乐园”不断扩大,吞并了周围的建筑,最终拥有了超过三千名雇员,它成了巴黎社会的微型王国,有着自己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斗争。慕雷对企业的娴熟控制,反过来又与他对情爱的掌控联系在一起,表现为他以一人之力对一大群顺从女性的诱惑和支配。他从办公室望出去,可以俯视成群的女性购物者,他于是被刻画为一个掌控全局的主人,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女性欲望的潮起潮落。他对婚姻却有一种迷信式的恐惧,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情爱关系对象是他的女顾客,为了财源滚滚,他在对女顾客的控制和操纵中必然要投入情感。这里不是抽象理性和工具性计算占主导,反而是性权力和性统治的幻想充斥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建立这种男性资本家和女性消费者之间的独特新型关系,就必须抛弃传统的父权权威模式。因此,慕雷往往被描述为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物,“非男非女”;他富有想象力,能够预测女顾客的需求,并认同她们的欲望,他身上带有许多女性顾客的品质,反过来自己也被女性化了。现代商业的成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性,它完全有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威权的男性气质,而是一种流动的、敏感的身份,能对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快速应变。这种男性主体性的女性化,将成为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性别角色重新调整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慕雷甜言蜜语的奉承和对女人品位的直觉,都不过是他更有效地榨取女性的手段。共情是与潜在的施虐结合在一起的,殷勤有礼则伴随着对女人无法抗拒诱惑的隐秘轻视。“慕雷正是通过他的殷勤优雅,才体现出犹太人的冷酷无情,论斤出卖女人。他为女人建起一座神庙,和店员们联合起来对女人烧香膜拜,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仪式,心念顾客,别无他想,不断去寻找更强大的诱惑;而背地里,当他掏空了她们的钱包,弄得她们精神崩溃时,他就暗暗嘲笑这些女人的愚蠢。”为了满足每个女人捉摸不定的心思,商家可谓挖空心思,这也让女人的利益在公共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又掩盖了这种作为女性气质现代崇拜基础的经济关系的压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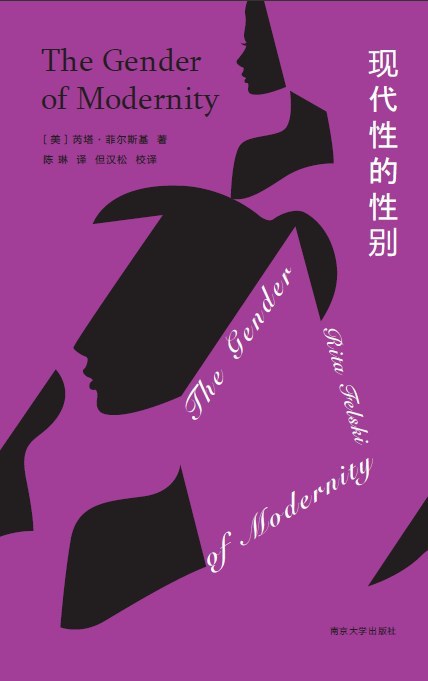
[美]芮塔·菲尔斯基 (Rita Felski) 著,陈琳 译, 但汉松 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因此,左拉的小说暗示,“资本主义的胜利”,即小说宣称的主题,最终等于父权制的胜利;经济的大踏步前进让男人对女人欲望的控制日益增强。然而,小说也提出了两性权力关系的另一种观点,它比上述概括更为复杂。女性复仇的主题打破了男性主宰的单线叙事;用左拉自己的话说,“奥克塔夫剥削女人,继而被女人征服”。小说的浪漫情节明显表达了这个主题;善于操控的慕雷最终拜倒在他的一个女雇员的石榴裙下,而这个娴静的年轻女人来自外省。黛妮丝·鲍狄(Denise Baudu)被表现为一个复仇者,她在情场征服这个男人,是为那些被他所害的姐妹报仇。根据这种原型式的罗曼司逻辑,男主人公因为爱上了女主人公而被女性化,而女主人公相对于男主人公占了上风,虽然优势有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左拉的这位女主人公虽然是商业进步的坚定拥护者,但完全没有消费的冲动,而其他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受到消费的影响。进城找工作的姑娘们往往被认为很轻易就沦落到性乱,直至最后卖淫,因为她们一旦进入城市诱人的商品世界,对奢华生活的欲望就被激发出来,只能通过出卖肉体获得经济收入。大量报刊文章都把女性店员刻画成特别容易在这方面出事的群体,因为她们经常接触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她们的阶级地位也不是非常明确,这就滋长了她们的妒忌和不满。换句话说,对商品的欲望与道德沦丧和肉体沉沦紧密相关。在这一背景下,左拉的小说将一个好女人描绘成一个前现代的女性就不足为奇了,她没有城里人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她仍然具有外省人的那种自然谦逊、勤俭持家和纯真无邪。
与之相反,沉迷消费的女性拒绝接受这种以纯洁的自我否定为模式的女性气质,她们代表的是那种未获满足的女性欲望所可能具有的威胁性和破坏性。这种威胁在左拉刻画的人群场景中暴露无遗,女性购物者蜂拥而至,呈现出一种邪恶甚至是魔鬼般的特质。慕雷的一个基本营销策略,就是制造购物人群,由此将消费者转化为景观和广告本身,从而吸引更多的购物者光顾。然而,左拉的这种描写还暗示了城市人群更为邪恶的内涵,这一点在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这些当时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那里也有所论述。正如当今一些评论家经常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中产阶级对人群的再现,往往诉诸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女性化隐喻;人群的匿名性体现了一种不稳定的、混乱的、未分化的力量,威胁到了自主的个人主义。如下文所述,一大群购物的妇女是理性失控的最典型例证。
女士们被人流挟裹,现在已无法回头。一群购物者涌入百货商店的门廊,就好像溪流将她们吸引到河谷中的隐秘水域,巴黎四周的过路者也被吸引过来。她们向前走着,速度缓慢,几乎要被挤死了,但周围紧贴的肩膀和肚子逼得她们只能直着身子;她们被满足的欲望使她们在挤进大门时既痛苦又兴奋,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好奇心。无论是穿着绫罗绸缎的上层贵妇,还是穿着普通的中产阶级妇女,或是没戴帽子的姑娘们,她们所有人都很兴奋,被同样的激情吸引。几个男人被淹没在这“波涛汹涌”中,带着焦虑的眼神看着这些女人。
在对“妇女乐园”热闹的促销日的描述中,一大群无组织的女性肉身涌入商店,驱动她们的是一种强大的、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人群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能吸引更多的女人加入,让自己被强大的人群之力推着向前。她们有着共同的购物冲动和激情,而原始的、充满欲望的女性气质又让她们联结在一起,这些都抹杀了她们之间的阶级差异。然而,如果说人群的混杂使阶级差异最小化,那么性别差异就会加剧;紧张、孤立的男性挤在兴奋的女性身体中间,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却又无法逃脱周遭那种令人窒息的狂喜。男性气质被女性的激情包围和弱化。这种对贪婪兴奋的女性人群的再现,引发了另一种可能的解读,即商业对欲望的刺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会颠覆而非鼓励两性之间的正当关系。一旦消费主义的诱惑点燃了女人的欲望,她们在兽性冲动的驱使下,就可能去狂暴地主宰男人。成群的女顾客涌进商店,就像一群复仇女神,或一群入侵的蝗虫,她们掠夺商品,迫使筋疲力尽的男店员们服从她们的每个突发奇想。“在这最后时刻,在这热火朝天的气氛中,女人至高无上。她们席卷了百货商店,像入侵了一个国家一样,在货物堆里安营扎寨。嘈杂声震耳欲聋,推销员们一败涂地,完全沦为这些女独裁者言听计从的奴隶。”百货商店是公共空间性别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个公共空间里,许多男人觉得自己渺小,无助,格格不入。
(本文摘自《现代性的性别》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