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
专访历史学家埃文斯(下)丨捍卫历史:从知识到行动

图说:埃文斯
1.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走向历史学家的道路?
埃文斯:我在战后的伦敦长大。我们家住在伦敦东区的边缘地带。我小的时候,伦敦东区被轰炸过后的可怕景象还在那儿:一排排的房子不见了,那幅画面让我印象深刻。我心想,是谁干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很好奇。当然,我的父母会告诉我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故事,我出生于1947年,属于婴儿潮一代。战时的政客们,比如丘吉尔,都还在世。我和我的同学们认为,1965年丘吉尔的去世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那是战后时代的结束。那年我们十几岁,还去参加了他的葬礼,看着送葬的队伍在面前走过。
后来我对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父母讲威尔士语,但我是在伦敦长大的,所以我讲英语。我们每年都会回去看望生活在威尔士的家人,我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很是沮丧。威尔士有很多历史遗迹,比如爱德华一世修建的城堡,废弃的板岩采石场。我从小就被各种历史包围着。
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进入牛津大学的时候,德国历史正是热门领域。有关纳粹主义在历史上的根源问题被讨论得非常多,我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尤其要说到,60年代末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英国的兴起,虽然这股潮流最后偃旗息鼓,但当时也相当令人惊恐。我那时已经学了拉丁语和法语,再学德语并不困难,我便开始学习德语,在那之后开始了对德国历史的研究。
澎湃新闻:当时对您影响很大的历史学家和作品有哪些?
埃文斯:我在学生时代涉猎非常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我影响很大,我才写了他的传记(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2019年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访者注);另外对我影响很深的历史学家还有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等。他们都是1956年以后退出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只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除外——我认为他在智识上已经脱离了共产党,虽然他一直都保留着党员身份。他们的作品都非常精彩。
法国的年鉴学派对我影响也很大。费尔南·布罗代尔,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尤其是古贝尔,这些历史学家的共同点是:他们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不同部分,经济、社会、社会结构、变革、进步、文化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这种整体性的方法正是我在撰写“纳粹德国三部曲”以及《竞逐权力》(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中试图运用的。

另外,我作为1968年的学生,婴儿潮一代,经历过60年代末的大动荡,一直对社会和政治上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动荡和革命时期非常感兴趣,纳粹夺取政权也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动荡时刻。
澎湃新闻:在您求学时期,德国国内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是怎样的?
埃文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冷战处于缓和时期。西德从战后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冷战年代转入威利·布伦特(Willy Brunt)、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t)试图与东欧和解、建立联系的时期,两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令人兴奋的时期。
在历史学领域,老一代教授大多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他们是在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接受的教育。老一代退休了,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走到前台,他们是自由派、左派,对德国历史有很多新的想法。很多年轻的历史学家非常兴奋地引入社会史,把经济史和外交史、政治史联系起来,研究纳粹主义长时段的起源。老一代历史学家认为纳粹主义是某种外来力量,否认其与德国早先的历史存在联系;年轻一代则从长时段去研究纳粹主义的兴起,认为纳粹德国与魏玛德国,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都存在着联系。
这些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里面,最活跃的一些人形成了所谓的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其中包括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 他们还有许多学生。他们运用马克斯·韦伯的方法来研究纳粹主义的起源和胜利,讨论导致纳粹主义兴起的结构性因素。我和一些受新左派影响的英国朋友对此非常感兴趣。这是历史学家对纳粹主义提出的第一个有趣的、结构性的解释,似乎能够推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但我们也在很多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属于老一代历史学家的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scher)支持他们。费舍尔是一个传统的、老式的外交史学家,他研究德国在一战中的战争目的和一战的起源。他在自己的学生影响下,也转向了结构性的解释。他的第一本大书是《德国在一战中的战争目的》(Germany’s War Aims in WWI),第二本更多的是讲起源,《幻想的战争:德国从1911年到1914年的政策》(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这本书试图对德国为什么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出结构性的解释,费舍尔非常想去寻找各种联系,虽然我不同意他给出的解释。
费舍尔和他的学生们以及比勒费尔德学派认为,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失败了,所以贵族,封建或近封建的贵族仍然在掌管着德国,他们试图以激进的外交政策来争取民主派的支持。他们的论点由一些分论点组成,比如资产阶级的封建化——资产阶级具有贵族的价值观和习惯等。
像我还有杰夫·埃利(Geoff Eley)和大卫·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以及其他一些在英国的年轻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意见。我们认为,他们把英国的历史理想化了,认为英国人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就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批驳了这个观点。我可以说,我们彻底驳倒了“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是由封建贵族统治”这个观点。你可以在阿诺·J·迈尔(Arno J. Mayer)的《持久存在的旧制度》(The Persistence of Old Regime)一书中读到这个论点,他认为欧洲在1914年仍然是由封建贵族所统治,而这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错误的,它过分简化了导致一战爆发的因素。
在纳粹主义的兴起这个问题上,比勒费尔德学派和费舍尔的观点是,这是旧精英对政治的操纵使然,但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也是一场法西斯运动。我们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把资产阶级理想化了,将其简单地等同于自由主义,是错误的。
澎湃新闻:您70年代初去德国求学,到了冷战的“最前线”,那时的政治环境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
埃文斯:造成了一些实际问题。帝国时代的档案,普鲁士的档案都在东德,所以我必须去东德做研究。但因为处于缓和时期,两边签署了一些交流协议,所以申请经费去东德的档案馆里工作一两个月还算容易。但有些我需要查阅的文件存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研究所,那里是东德政权的知识生产中心,就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了。西方历史学家在那里被划分为两类: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你得是共产党员才能被划到第一类,但我不是,所以我进不去。但后来费舍尔等人被归类为“试图保持客观立场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我让费舍尔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才得以进入。
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如果你读过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写的间谍小说,或是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你就会知道进入东柏林,被特工跟踪是什么感觉。我当时22岁,被介绍给当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研究所(Marxism–Leninism Institute)的所长,他的名字叫 Dr. Übel,直译过来是“邪恶博士”,似乎是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其实他是一位相当值得尊敬的人物,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做得很好。从西柏林过境到东柏林颇费周折,过程相当刺激。在西柏林坐地铁时,有一段路会经过东柏林的一部分,那段路的车站都是封闭的,过道上还有警卫和机枪。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让人感到非常刺激。
2.
澎湃新闻:讲讲您在大卫·欧文诉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诽谤案中的经历,那段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埃文斯: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主要写纳粹在二战中的军事行动,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希特勒的战争》(Hitler's War)。他也是一个新法西斯主义者,成立过一个不成功的新法西斯组织。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很不受英国媒体欢迎,因为他那时就已经是个彻底的大屠杀否认者。他那时开始宣称,纳粹没有蓄意杀害600万犹太人,纳粹没有制定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没有使用毒气室。美国历史学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在她的《否认大屠杀》(Denying the Holocaust)一书里称欧文是大屠杀否认者,认为欧文的作品里有很多歪曲和伪造历史的内容。这本书先是在美国出版,一年后在英国出版。大卫・欧文认为利普斯塔特严重损害了他的声誉, 于是向法院控告她和企鹅出版社诽谤。
在当时的英国,法律对诽谤案的原告非常有利。你只要对法院说,某人对外界说了有关于我的不实信息,我的名誉受到了损伤,要求对方赔偿,弥补我的损失。被告必须证明自己说的不是谎言,举证责任落在被告身上,这点真的很荒唐。欧文的诉求是将利普斯塔特的书下架,把已经印的书化浆,出版商必须保证不再出版类似的书,另外支付赔偿金。企鹅出版社决定应诉,聘请专家证人。他们说服双方律师和欧文选择仅由法官来审判,因为陪审团无法理解这些复杂的技术问题。专家证人的职责是向法庭对技术性的问题作出说明。
我和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罗伯特·简·冯·佩尔特(Robert Jan van Pelt)等历史学家被请来做专家证人。我的工作是爬梳欧文已经出版的作品,然后向法庭说明,以我作为专家的观点,利普斯塔特称欧文是大屠杀否认者的说法是否成立。要证明这一点其实很简单,但要证明他是否伪造了文献记录就比较复杂了;特别是,我们要获取的绝大部分信息都在德语文献、档案里。最后,我和两个研究助理一起,花了18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长达740页的报告。我们的结论几乎全部被法庭接受,欧文败诉,必须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共计200多万英镑。他宣布破产,没有付一分钱。但在那之后,他的名声扫地,此前他在专业历史学家当中的名声很大,大家挺重视他的。我们的报告确实证实了,他的著述中存在大量的伪造以及对原始文件、材料的歪曲的地方。这件事后来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否认》(Denial),是部制作精良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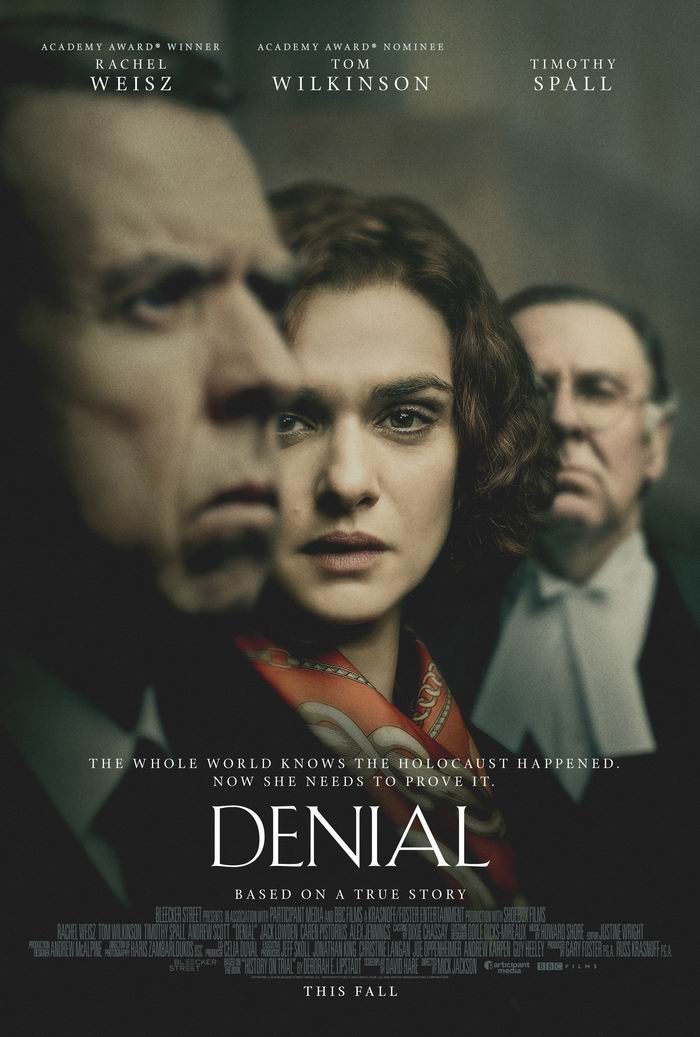
《否认》海报
在开庭初期,2000年1月到4月的时候,律师们让我推荐一本详细的纳粹德国史,他们好能快速阅读之,增加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我告诉他们没有这么一本书:好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最新的作品质量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有了“为什么不自己写一本 “的想法。这就是“纳粹德国三部曲”的真正由来。
我本来是想写一本,然后就越写越多,因为有关纳粹德国的研究作品数量惊人,当时就有大约一两万本之多。然后我的书就从一本变成了两本,最后变成了三部曲。从1982年开始,我在不同的大学里都会教一门特别课程,那是一门以史料为基础的纳粹德国的课程;我最早在东安格利亚大学开这门课,然后在伯贝克学院,再然后是在剑桥大学。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我刚离开伯贝克学院,将要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因为教授这门本科课程的缘故,我对最新的文献非常熟,所以写起来特别快。我从2001年开始写,2007年就完成了。
澎湃新闻:今年距《第三帝国的到来》原作出版已经有十七年了。您在写“纳粹德国三部曲”的时候希望达成怎样的目标,现在来看,你认为这些目标实现了吗?
埃文斯:当时的想法是写一部全面的纳粹德国史,讲述纳粹德国的兴衰。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涵盖方方面面,所以我不仅会写政治和历史人物这些传统历史作品里着重强调的内容,还会写整个历史阶段中的文化、文学、科学、艺术、教育、宗教……我想去描绘出一幅非常全面的历史图卷。
在当时具有通史性质的作品里,威廉·L·夏依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是最有名的。夏依勒是位杰出的记者,书写得很好看,但书里的内容已经过时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美国,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对纳粹德国历史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我想写一本能够总结、展示这些成果的作品。我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作品是跟得上时代的。我想在我的作品里把夏依勒那些诸如“所有德国人都是积极的纳粹分子”的陈词滥调统统抛弃掉,去展示这幅历史图景的复杂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需要我们去辨识的差异:纳粹德国时期的德国社会远非铁板一块。
我还想让它变得更有可读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所使用的一个方法是:在书里向读者介绍一些个体,他(她)们是生活在当时德国社会的各色人物:纳粹分子、非纳粹分子,犹太日记作家、一个保守的德国女人;从头到尾,跟随他们的日记、信件和生活,希望借由他们的个体经验,能让我所描绘的宏大图景变得具体化,去展现这个宏大图景怎样影响着普通人,他们在其中是如何生活的。
我想我做到了我当初想要实现的目标。这三本书所受到的认可令我相当惊讶,“三部曲”的英文版在英国和美国的累计销量共约27.5万册;几十种其他语言的版本陆续问世: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德语,甚至还有法语版——法国人很少翻译书。现在又有了中文版,我非常高兴。各种语言版本的总销量至少近50万册。它在德国出版尤其让我高兴,因为德语世界至今还没有关于纳粹德国的通史作品——从时间跨度和覆盖的内容广度的意义上,德语世界还没有“纳粹德国三部曲”这样的同类作品——德国人往往写的是短教材和长专著。
澎湃新闻:我想您的作品的可读性很多是来自于英国历史写作特有的传统,比如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作品,请您谈谈这种历史写作的传统。
埃文斯:英国的历史写作,特别是英格兰的历史写作有一种文学风格的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和19世纪的托马斯·麦考莱,再到20世纪的霍布斯鲍姆,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活跃。我之前讲了几点我对德国历史感兴趣的原因,除了那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老师当中有一些人是纳粹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移民,都上过战场。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历史学家,至少我这一代英国历史学家在战后对欧洲大陆的历史会那么投入。
可以数出很多位对不同的欧洲国家各有专攻的英国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很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认识自己的方式。写意大利的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写德国的伊恩·克肖(Ian Kershaw),写法国的西奥多·泽德林( Theodore Zedlin),写芬兰的大卫·柯比(David Kirby),写西班牙的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和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等等。我们的作品在不牺牲学术品质的前提下,可读性也好。
3.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写《捍卫历史》是为了回应9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在知识论上的挑战,想问您这场历史学家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辩论留下了什么遗产?
埃文斯:人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将文化和语言作为解释和理解历史的方式。我们摆脱了70、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模式。90年代之后,历史学家对思想、语言和文化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又开始忽视社会和经济因素,转而推行一种粗糙的文化甚至语言决定论,这和老的经济决定论一样是片面的。
另一个影响是,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在研究中增强了。从消极意义上说,它可能导致历史写作变得自娱自乐,历史写作变成了个人观点的表达,成为一种非常自我中心、自恋的行为。积极的一面则是,它使我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变得更加诚实。我们现在有了像西蒙·沙马(Simon Shama)、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这样的历史学家,作为主持人出现在广播、电视、纪录片之中,他们给出的显然是个人对过去的认识,但大多是建立在权威知识基础之上的见解。历史学家接受了自己研究中的主观性,开始更多地面向公众,将历史学的解释与研究传播出去。
澎湃新闻:您做欧文案的专家证人,写“纳粹德国三部曲”,都是您“捍卫历史”的具体行动,您现在在做哪些旨在“捍卫历史”的工作?
埃文斯:我还是做我最擅长的事情:再写一本书。我刚刚写完一本书,书名叫《希特勒阴谋论:第三帝国和偏执的想象力》(The Hitler Conpiracies: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ranoid Imagination),从结构、性质和起源的角度去处理与希特勒、纳粹德国有关的阴谋论,对每一种阴谋论都作出澄清,探讨其经久不衰的原因。
这本书分五个章节,每个章节分别去处理流传广、存在时间久的五个阴谋论:第一章是关于反犹主义的小册子《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据说这个小册子影响了希特勒;“背后捅刀子”的传说,即认为德国军队在一战中不是在军事上被打败,而是因为被国内的革命者在背后捅了一刀;围绕着国会纵火案,从左、右翼阵营都传出了阴谋论,左翼阵营认为那是纳粹为了夺取权力,故意制造的;1941年纳粹党领袖鲁道夫·赫斯带着所谓的和平使命飞往苏格兰,围绕这件事也有很多阴谋论;最后,有阴谋论认为,希特勒1945年逃出了总理府地堡,之后一直生活在阿根廷。很多人之所以会传播这个阴谋论,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希特勒的下场真的有这么惨:1945年4月13日,希特勒在地堡里开枪自杀。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最近在英国、美国等地开展的“推倒雕像”运动?一个国家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过去?
埃文斯:推倒雕像由来已久。它往往发生在公众记忆和舆论经历重大转变的时候,比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又比如纳粹德国倒台之后。

1792年8月,在法国大革命中,民众用绳子和杆子推倒路易十四的雕像。
文化记忆通过公共雕像、纪念碑和纪念馆得到外在的、物理性的表达。它们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更好地说,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英国在其处于帝国巅峰时期的维多利亚晚期的文化记忆,并不适合21世纪的英国,现在受到关注的很多雕像就是在那个时期制作的。我们也已经成为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社会,这点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让我真正感到作为英国人的骄傲。
过去几周在英国(注:这里的谈话时间是6月23日),针对拆除雕像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有历史学家质疑,简单地将它们从公共空间中除去不妥当,还有人会说,拆掉雕像就是“隐藏我们的历史”。但历史书里并没有多少雕像的存在。推倒雕像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就意味着是在抹去历史。将它们放进博物馆里也不会让公众失去审视它们的机会,恰恰相反。推倒雕像与历史无关,而与记忆有关。
政治家往往认识不到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区别。迈克尔·戈夫2010年至2014年担任教育部长时,希望在学校里开设新的,强调英国历史积极面的历史课程,增强学生的国族意识。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在民主、热爱自由的英国人与邪恶的德皇暴政之间发生的斗争——尽管参战的英军有40%没有投票权,而且英国的主要盟友之一是沙皇俄国。
历史与记忆不同——不是个人记忆,而是国家的、集体的或者文化的记忆。历史也不是给过去的人分出忠奸,把一些人封为英雄,把另一些人打成恶棍。大英帝国是好还是坏的争论是很幼稚的,与严肃的历史研究毫无关系。
真正的问题是,雕像纪念的是谁的历史?那些参与到这次推倒雕像运动里的人并不恨英国,他们只是希望英国能有一种不同的国民记忆。比如,德国人为1933年至1945年纳粹当政时期的受害者竖立了纪念碑,这不意味着他们恨德国,他们只是想以这种方式宣告世人,自己对德国的看法与希特勒及其同伙不一样。
澎湃新闻:对于一些雕像,除了推倒、移入博物馆,您有什么别的建议?
埃文斯:我们可以向德国的做法学习。比如在德国北部港口城市不来梅,1932年,一个公园里竖起了一坐巨大的用红砖制作的大象,以此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协约国抢走的海外殖民地。后来德国人没有将这座雕像推倒,而是在1989年将其重新确立为一座“反殖民主义雕像”,一旁立了一块铜牌,讲述德军曾经在海外殖民地的暴行以及这座雕像的历史。由于这座红砖大象本身并不会令人反感,甚至还有一定魅力,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推倒雕像,可以重新校准公众记忆,宣告一种新的国民身份,但从长远来看,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塞西尔·罗德(Cecil Rhodes)等人的雕像可能会被推倒,但在我们社会的种族歧视、不平等和偏见等真正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推倒雕像仍将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我们希望目前的抗议浪潮能够产生一些实际影响,让格伦费尔塔火灾和“疾风号世代”遣返事件的受害者所遭受的可耻对待和忽视不再发生。

- 乌克兰同意停火30天
- 文旅部将对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治理
- 银行加大力度转让个人不良贷款

- 日经225指数午盘涨0.29%,报36898.83点
- AI智能体概念集体走强,立方控股涨超20%

- 化学反应中,能改变化学反应速率,但其本身在反应前后都不发生变化的物质被称为
- 建筑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2025年3月,授予中国建筑师刘家琨

- 17颜宁,有新任职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