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陈丹青笔下的霍洛维茨

画家出身的陈丹青谈起音乐,与村上春树和小泽征尔的对谈类似,都是一个在艺术中,却又异于音乐领域的人,从外往里看,常常有通感的趣味。
文章来源: 美在高处 / 作者:陈丹青
转载编辑:田艺苗的田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不仅有行云流水的文字,更让人感动的是,陈丹青对音乐带有时代和生活烙印的理解,隔着时空,这种理解又像重重发酵,带出厚重之感。

霍罗维茨!国中的爱乐者想必知道他。此间说起这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唱片行每年推出他的新磁碟,我也藏有好几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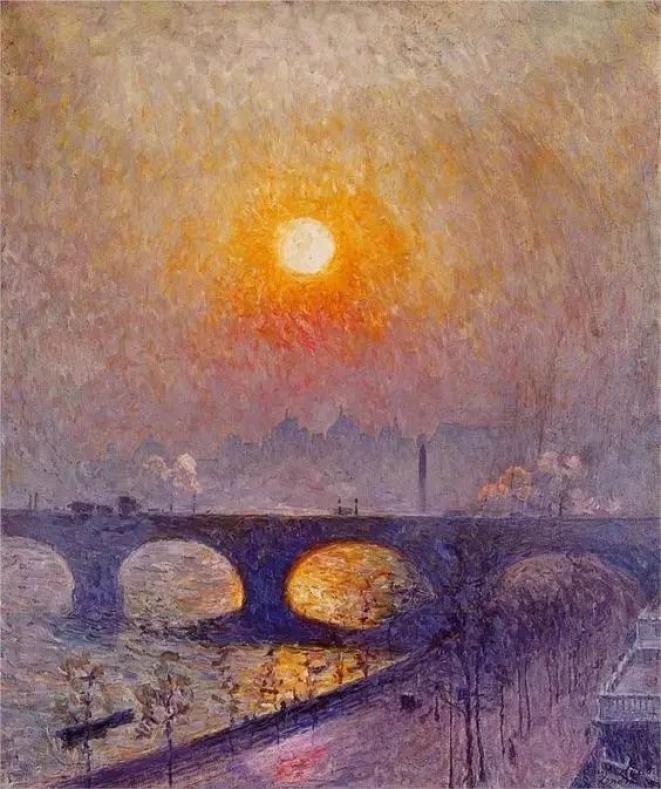
我一向自以为认识老霍。记录他演奏生活的四部电影,我都看过。在荧幕上,他又是另一番风采。

一位大师,得活到这份岁数,上帝才会给他如此生动的老脸。看他早岁的照片,头发紧紧向后梳拢,斯拉夫人的修长鼻梁,顶光照下来,风流倜傥。如今老了,嘴唇象老太太那样抿着,似笑非笑。

制片人去他家拍片,老头就像个孩子,听任摄影师摆布。然后开始弹奏,渐渐忘记正在拍摄:“下一支么?”他自言自语,“我还会弹舒伯特!”于是舒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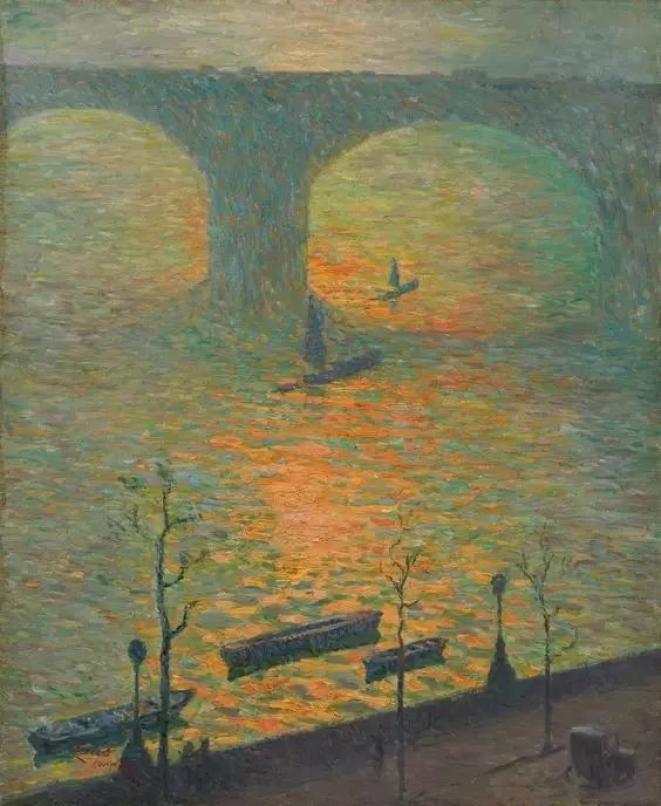
片尾是他长时间在台前傻站着,等候掌声平息。终于,他用双手移到耳边——因掌声使他说不成话——作出要去躺下休息的姿势。

奇怪,他的著名的左手的力度,那排雷轰鸣般的低音,即处于如此这般。镜头移近了,移向他皮肉垂挂的老脸——一滴鼻涕,正凝在他巨大的、西方人才有的鼻孔边缘。

那是他 60 年前出亡苏俄,头一次重归故园。60 年前,他说他绝不再回这个国家。

忽然,老头子本人在收音机里唠叨起来,结巴、咳嗽、夹着老人的干笑,谈起他年轻时,怎样被引见斯克里亚宾,又说拉赫玛尼诺夫待他怎么好:“是的,我想,他就是我的爸爸。”

“曼哈顿,上东城麦迪逊大道,81 街街口,某号,小教堂,周五周六,下午四至八时,霍罗维茨告别仪式向公众开放。”

国中现在的规矩不知怎样了,在我出国前,一位文化名人的殡仪,卑贱如我,可有幸前往?票是断乎少不了的,且非有十二分背景的熟人。但周五午后我径自去到上东城:我确知自己属于“公众”之一,除非演出,票一概无须。

入口处人不多,内厅亮堂。我移步进入,猛听得老霍在弹琴。他不是死了么?我诧异,随即一眼望见厅堂尽头,围满玫瑰花的他的棺木。棺的两侧,是一对扬声器,叮咚琴声就从那儿送出来。

琴声。人们排成一线,依次缓缓移向棺木。一对老夫妇正从花丛前退下,在队伍两边的长椅阵中,与先前到来,拜谒遗容后,未曾离去的人们坐在一起。我环顾来者,这是每天在地铁中见到的平民百姓。

在我面前是一位肥胖的黑人妇女,她蹑手蹑脚走上前去,划了十字,伫立着,背影象是俯看摇篮的母亲。转过身来,她神色平和,满面泪水。巧呢,这时响起的曲子,又是那首斯卡拉蒂。其时花丛棺木距离我三两步的样子,琴声近切而响亮,轮到我了。

下雨了,两位警察在雨中,为络绎赶来的车辆与人群安排秩序。下到地铁车厢,起动后的轰响,便不容我专心回想灵堂里的琴声。那一对扬声器想必价格昂贵,我从未听过如此纯净良好的音质。


2020疫情蔓延,很多人面临失业、转行、转型,学校延迟开学,学生荒废学业,整个社会被焦虑、失眠、抑郁的气氛包围。到了下半年,大家一边观望,一边为后面的生计打算。其实在全球疫情失控的时候,我们活着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
在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锻炼身体,好好吃饭,多读书。
你要学会战斗,也要擅长等待。
原标题:《陈丹青笔下的霍洛维茨》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