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姚崇新:考古学家做图像研究的基本原则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受海外的影响,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我国艺术史研究逐渐趋热,除了传统的美术史界外,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图像资料的兴趣越来越浓,《美术史研究集刊》《艺术史研究》《艺术学》《艺术考古》《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形象史学研究》(现已改为《形象史学》)等相关刊物的相继问世即是明证,而且前两种刊物已成为海峡两岸公认的有关艺术史研究的权威期刊。的确,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艺术史研究取得了较多进步,但过热未必是好事。时下,谈论图像甚至已成为一种时尚,但部分学者缺乏必要的图像知识储备和图像研究方法的掌握,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目前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图像资料进行跨时空的勾连,从而达成图像跨时空交流的宏大叙事的预设,但研究者又往往拿不出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图像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探讨西王母图像与娜娜女神图像之间的联系、在汉画像石中过度搜求贵霜艺术因素等即属此种情况,这样的做法令人堪忧。是到了应该注意图像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了,但以下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思考。

北凉壁画:月亮与西王母
一、要避免天马行空式的解读
在图像解读中不能没有发散思维,不能没有想象力,但应该有个度,发散过头了、想象过头了就会出现谬误。
比如对史前图像的解读有时容易天马行空。由于史前研究无法用文献进行佐证,我们允许史前研究提出不同的假说,假说一般是指在逻辑上似乎可以成立但难以有效验证的观点,既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但也不能因此对史前图像的解读过于随意,不能因为别人拿不出反驳你的证据,就将自己的观点视为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部分学者对史前图像(包括岩画)的解读过于随意。史前研究难以验证是客观事实,但研究者应该明白,考古材料自身还是有一定的自我验证能力的。比如,同一图像母题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载体上、不同性质的遗存中、不同的考古环境中,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对这一图像母题进行的内容、性质或功能预判,纳入不同载体中、不同性质的遗存中以及不同的考古环境中,分别进行验证。
贡布里希在《象征的图像》中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套标准的防范措施,以校正对图像阐释天马行空、言说过头的习惯,正是这种习惯败坏了图像学的名声。看来天马行空不仅仅是史前图像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实际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只在乎自己提出的解读方案是否“有创意”,是否“有新意”,已经不怎么在乎有效证据链的建立了,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如何避免天马行空式的解读呢?我以为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证据。什么是切实有效的证据呢?以图像的跨时空交流研究为例,我以为,首先要寻找图像在时空位移中的轨迹证据,即不仅要考虑图像从哪里来,也要考虑图像是怎么来的,路径是什么?沿此条路径传播的可能性是否具备?其次,要从微观层面观察,图像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比如,两地图像之间是否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图像元素?最后,从宏观历史背景看,交流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例如,如果你认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环主室形成的马蹄形回廊结构受到了印度佛教支提窟结构影响的话,那么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提供证据:1)印度佛教支提窟东传的轨迹;2)从细部列举刘胜墓结构与印度佛教支提窟结构的相同或相似之处;3)佛教入华的宏观历史背景。事实上,从以上三方面都不能提供切实有效的证据,相反,第三点可以提供有效的反证,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佛教初传中国能早到刘胜的时代。仅由第三点提供的反证,就足以否定刘胜墓结构受到印度支提窟结构影响的说法,那么这一说法就是“天马行空”。此例的内容虽然不是图像,但在文化交流范畴,物、像同理。
二、要避免过度阐释
按照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图像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解释作品的内在意义或内容,即对图像背后信息的进一步挖掘与解释——这就是真正的图像学研究(除此之外的研究属于图像志的范畴)。内在意义或内容究竟可能是什么?潘诺夫斯基认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哲学、宗教等等往往可以通过艺术家的手笔凝聚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而凝聚在艺术品中的具体内容就构成了作品的内在及本质意义,是艺术家真正想表达的思想,也就是作品的“象征意义”。这一理论能够成立的社会逻辑是:任何艺术作品的创作都或多或少的包含着一定的时代烙印。艺术家的艺术创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而且还可以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空,所以社会历史的烙印在作品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艺术作品与其所生成的社会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的差异在于,一类作品所对应的具体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作为一种单个的艺术品,它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可能存在个性差异。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对其背后隐藏的内在意义和内容有一个导向性思考。
近年来,已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图像资料隐含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信息(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关于图像文献研究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邓小南《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的确,从历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图像资料显然不仅仅是美术史的“专材”,上述学者的意识可能意味着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图像资料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这样看来,阐释图像的所谓“象征意义”成为图像学研究的“王道”,是图像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但在实际研究中,有些学者往往存在“过度阐释”的倾向,对图像所谓的“象征意义”求之过深。有的研究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有假设有求证,貌似也有证据链,因此很容易迷惑读者,但是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这提示我们,在阅读有关图像研究成果时,要注意其证据资料是不是经得起严格的逻辑推敲。“过度阐释”的后果是,往往使本来可以成为正确的结论变成了谬误。因此,在进行图像学研究时,我们还必须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图像作品或其他艺术品固然有人类情感因素的寄托,固然隐含着一定的社会历史信息,但从理论上说,如果试图把所有人类的情感经验都附加在图像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图像本身并没有那么高的“附加值”,特定的图像资料所附带的信息是有限的,因而对这些信息的“发掘”也并不是无止境的,当把这些信息“发掘”到极致之后就应当停止了,如果再继续的话就是过度阐释,就是谬误。有时候,真理与谬误之间就是“进一步”和“退一步”的差别。
三、不能将不同时空中貌似相似的图像随意勾连
我们应该承认,图像在一定的时空中的确存在交流与互动。但是我们在研究这种联系时一定要注意寻找有效证据,如果没有有效证据时不能做判断,否则很危险。如果认为二者确有关系,那就必须提供流传与传播过程的证据。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时空下独立发展起来的造型艺术从外形看,也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娜娜女神图像与西王母图像,在构图形式上的确有一些相似性:都是女神,都以兽为坐骑,但不能因此得出二者有关系的结论,因为事实非常清楚,这两位女神完全是在两个不同时空下发展起来的造型艺术,二者从未有过交集。西王母出自中国本土创造,战国时期其信仰开始流行,汉代开始出现其图像;娜娜女神出自西亚两河流域,是古代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神祇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可见,西王母与娜娜女神二者可谓风牛马不相及。

卡斯特文明:描绘国王将女儿献给娜娜女神
四、要注意图像形式与内容的不变与变
在不同的语境中,相同的图像可能内涵相异,因为图像的形式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借鉴的结果往往可能意味着内涵的差异。例如,佛教密教的神祇及其图像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婆罗门—印度教的神祇及其图像,造成密教万神殿中的神祇及其图像与婆罗门—印度教万神殿中的神祇及其图像有很多是相似的,有的在造型上甚至完全相同。但进入密教万神殿的婆罗门—印度教神祇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大自在天为婆罗门—印度教地位最高的三大神之一(坐骑是公牛,多头多臂),被佛教吸收后称摩醯首罗天,地位明显下降,只是一种护法神,相应地,其图像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饶有趣味的是,中亚粟特地区的拜火教也吸收了若干婆罗门—印度教的神祇及其图像,同样包括大自在天,在粟特版拜火教中,大自在天的身份变成了风神维施帕卡,相应地,其图像的内涵再次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是图像形式的不变与内涵的变。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不备举。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图像母题在不同语义场中可能存在的性质与功能差异。
五、要正确看待图像的程式化和滞后性问题
图像创作有一定的程式化倾向和图像内容有一定的滞后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否认。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为何会出现这种程式化的倾向。程式化与滞后性存在着内在联系,只要存在程式化就必然存在滞后性。程式化与滞后性的产生,归根结底,与艺术品的商品化有关——与之相联系的是作坊式生产、规模化生产。从商业的角度看,作坊式、规模化生产显然更能显现经济效益,同时,创造新样式显然要比复制旧样式成本要高得多。艺术品要求变求新,是比较难的,比较容易的做法就是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根据现有粉本来制作速度更快,因此,艺匠们缺乏创新的动力。因此,作坊生产、规模化生产的后果是一定时期内图像从形式到内容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图像的程式化倾向因此产生,进而产生滞后性问题。事实上,画像石、画像砖、佛教造像甚至墓葬壁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程式化和滞后性这样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认为也不能绝对化地看待图像的程式化和滞后性问题。比如,如果我们绝对化地理解程式化问题的话,就无法解释佛教艺术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风格变化,更无法理解中国佛教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一言以蔽之,在我看来,不存在绝对一成不变的“程式”。“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关于滞后性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对具体对象做具体分析,有的图像内容反映的时代气息其实是很浓的,丝毫看不出“滞后性”,安伽墓石葬具浮雕图像中表现墓主人生前与突厥人交往的图景就是最好的例证,因为这些图像内容可以与墓志文字相互呼应。荣新江先生对粟特石葬具图像的研究正好说明这些图像资料具有时效性,是“与时俱进”的(荣新江《粟特与突厥——粟特石棺图像的新印证》,载周伟洲编《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不能简单贴上“程式化”和“滞后性”的标签,否则势必忽视这些图像资料潜在的史料价值。
六、要重视图像自身的创作传统与脉络
某些图像母题在一定时期之内,有其自身的创作习惯、传统、演进脉络,因此,在做具体分析时要注意这个传统,否则解释会出现偏颇。
兹以《历代帝王图》的研究为例。《历代帝王图》又名《列帝图》、《十三帝图》、《古列帝图卷》、《古帝王图》,传为唐阎立本所作,现仅存摹本,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画面从右至左画有十三位帝王形象:西汉昭帝刘弗陵、东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蜀主刘备、晋武帝司马炎、陈宣帝陈顼、陈文帝陈蒨、陈废帝陈伯宗、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各帝王图前均有榜题,且均有随侍,人数不等,形成全画卷相对独立的十三组人物,共计四十六人。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十三位帝王的着装并不一致,有的着帝王的“正装”,即着衮服戴冕旒,有的却着“便装”,即普通士人装扮,着便服戴白纱帽。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画家有意为之,寓示褒贬:身着便服者暗示他们非正统君主,身着衮冕者则暗示他们在法统上具有优势,属于正统君主,这可能与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初君臣对南北朝正统所在的历史认识相关——着衮冕者为正统,着便服者为非正统(陈葆真《图画如历史:传阎立本〈十三帝王图〉研究》,颜娟英主编《美术与考古(上)》,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这一观点似乎可以归纳为“政治隐喻说”。但这一观点与作品的实际呈现存在一定的矛盾,如正统性无可置疑的汉昭帝未穿冕服,而不具正统的蜀、吴二主却着冕服。
孙正军认为,从图像自身的语言看,“冕服即正统”、“便服即非正统”的对应关系恐难以成立。他检讨了汉代以来帝王图像创作的传统和习惯,认为汉代以来对于帝王类的肖像的创作,并不完全恪守帝王本身的着装传统。具体而言,绘制上古帝王时多用冕,绘制秦始皇及春秋战国诸王时则多用通天冠。及至魏晋南北朝,东晋南朝和北朝实际都存在两种绘制皇帝形象的模式。其中,自汉代而来的着通天冠皇帝像传统在南北双方均有继承,且各自又发展出新的皇帝像绘制模式(孙正军《重视图像自身的脉络:以〈历代帝王图〉皇帝异服为线索》,《唐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这一观点似乎可以归纳为“自身传统说”。这样看来,“政治隐喻说”似乎不能成立。
孙正军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致力发掘图像的“象征意义”时,也要千万注意图像自身的创作传统与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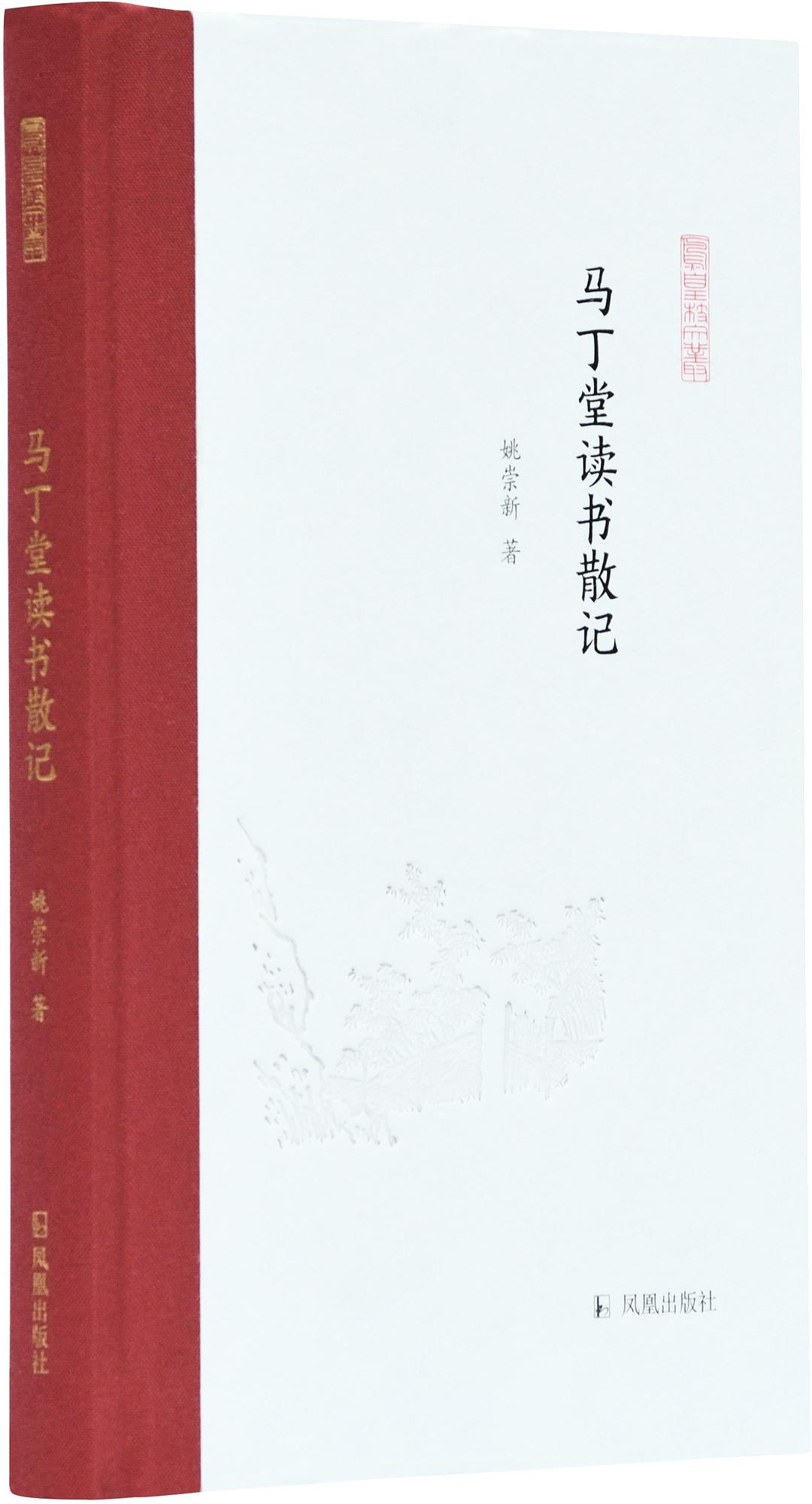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