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从《金枝》到《黑色雅典娜》——20世纪西方文化寻根札记
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希腊文明真的是雅利安人征服土著的结果吗?马丁·贝尔纳,这位古典研究领域异乎寻常的闯入者,以《黑色雅典娜》这部极为大胆的学术著作挑战了人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的全部基础。他认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亚非语文化,但自18世纪以来,主要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这些亚非语影响被系统地忽视、否认或压制了。在他看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
这本足以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相提并论的作品,1987年出版后在学界激起轩然大波,此后多次再版,而针对这部著作的争论也持续了三十多年。
本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叶舒宪2000年所写,以三部里程碑式著作——弗雷泽的《金枝》、施瓦布的《东方文艺复兴》和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浪潮的进程。值《黑色雅典娜》在中文世界首次完整出版之机,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特别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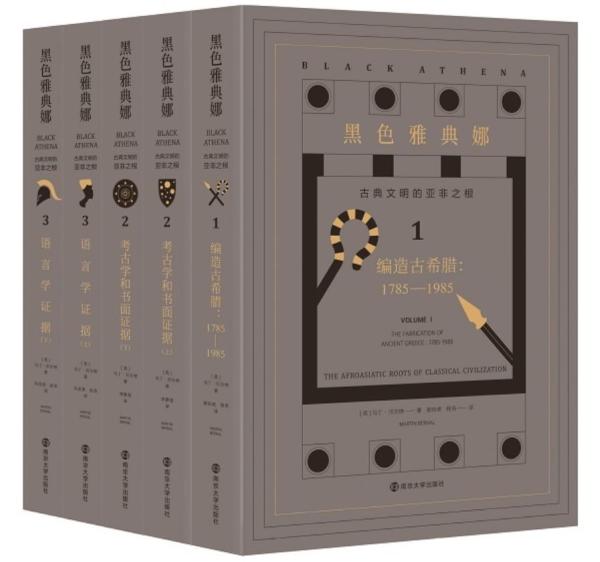
回首20世纪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浪潮,有几部书可以作为学术思想进程中的里程碑式著作。如果把过去的这100年大致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那么弗雷泽的《金枝》、施瓦布(R.Schwab)的《东方文艺复兴》(Laenaissance Orientale,Paris: Bibliotheque Historique 1950)和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Free Association Books, London 1987),这三大巨著可视为每时期的代表。
《金枝》被称为古典人类学的“圣经”,或人类早期巫术、宗教、神话、仪式和习俗的百科全书;它在激发西方人的远方异国情调想象,建构关于“原始社会”的图景,催生现代主义的原始情结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学界早有公论。光是集中研究《金枝》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专书就已有维克里《<金枝>的文学影响》(J.B.Vickery,The Literary Impact of The Goldern Bough,1973)、罗伯特·弗雷泽等编的《詹姆士·弗雷泽爵士与文学想象》(R.Frazer ed., Sir James Frazer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Macmillan,1990)等多种,国内也有相当的专文介绍。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1957年的《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干脆把《金枝》奉为文学批评的杰作。当年郑振铎先生读到《金枝》后大受启发,写出《汤祷篇》等,被周予同先生称赞为在信古派与疑古派的斗争夹缝中另辟出一条古史研究道路。
施瓦布的法文著作《东方文艺复兴》问世之际,中国学界全面倒向苏联模式,与西方学术开始隔离,所以整整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书尚不为国人所知。这是一部学术思想史或专题学术史类的著作,其讨论的范围要比《金枝》那种包举宇内、纵横四海的气势小得多,集中探讨西方知识界对印度文化与伊朗文化的兴趣由来,英、法势力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渗透如何诱发了人们对东方异国的再想象,对古老的梵语的再发现,以及由此而催生的专门学科“东方学”如何在18-19世纪的欧洲学界获得建制。施瓦布的书名得自于一个多世纪前埃得加·奎耐特(Edgar Quinet)著作中一章的标题,他们两人有一个共识:新兴的东方学已经压倒了新古典主义,关于古代印度语言文化的知识,其重要性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并不亚于传统的古典学——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化研究。施瓦布认为,第一位提出一种“东方文艺复兴”思想的人是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施雷格尔。他在19世纪初的《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一文中声称,研究印度文学需要巨大的热情和虔诚,一旦这座古老的智慧宝库被打开,世界将会随之而改变。这种对东方文化的热切期待心理使我们想到德国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初读梵剧《沙恭达罗》后的强烈反应,后者甚至认为这一部印度剧的价值超过古希腊全部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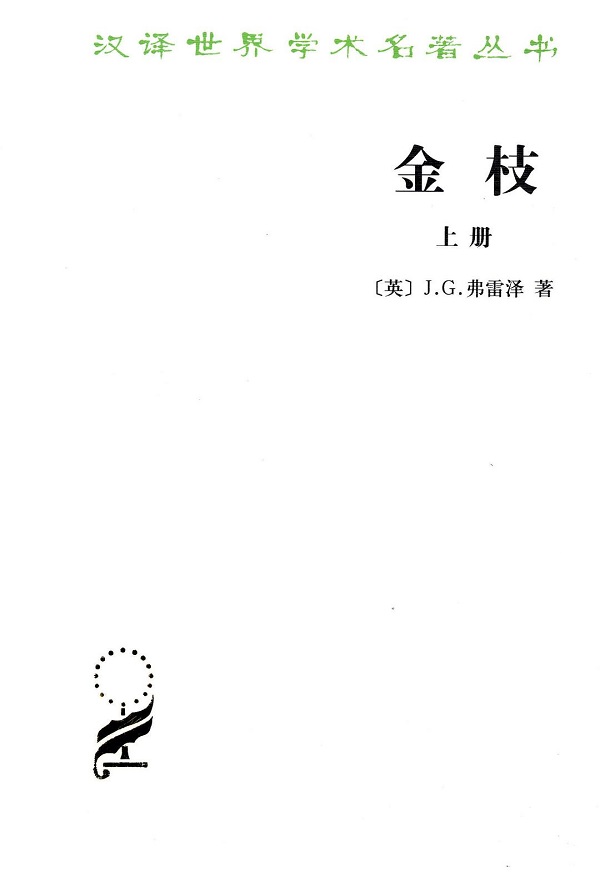
从今天的全球一体化大视野上看,过去的两个世纪正是东西方文化打破隔绝,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对话的两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外向型的西方强势文化对于内向型的东方弱势文化总是充当探险家,探宝者的探求角色。中世纪寻找圣杯的传奇故事伴随着近代殖民化历史的展开而兑现为寻找财富与新知的现实冲动。西方知识人眼中的东方异族也只有随着文化误读的节奏效应而在乌托邦化与妖魔化之间往复运动:文化期待心理的投射作用总是把文化他者加以美化、理想化;而真实的接触和霸权话语中的偏见又总是将乌托邦化的他者打翻在地,使之呈现出丑陋的“妖怪”面目。
由于施瓦布的书早出萨伊德的《东方学》20多年,所以书中并没有突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的后殖民理论倾向,而是专注于史实的勾稽和文献的疏理,特别是有关古印度和古伊朗语言的研究如何在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达成“印欧语”假说,这一假说派生的文化寻根热情如何成为19世纪后期欧洲知识界的持久兴奋点。由于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得到空前的揭示,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就顺理成章了。20世纪末期的欧洲一体化也许只有放置在19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各国族在语言文化上的认同背景中加以审视,才会看得更清楚吧。而印欧母语假说对于印度文化而言,使欧洲知识人的想象空间得到调整,喜马拉雅山那边的深肤色古老人种,现在变得既遥远又亲近:远的是地理上的距离,近的是人种和血缘。试想一个家族中丢失已久的一位成员突然又回归到家中来了,对于双方来说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充满着白人优越感与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第一次看中的东方作者便是印度的泰戈尔?即使不论泰戈尔所受的英语教育和英国留学经历,如果不是走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后门”获得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垂青东方人的时间也许会推迟数十年。
一位研究英语文学与印度之关系的印度学者崔维迪(Harish Trivedi)在《殖民的交换》(Colonial Transactions,Manchester University,Press, 1995,p.vii)一书中无奈地说:“从我们全部殖民经验中构建的现代印度历史中,印度和英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才是最重要的方面。它们仍然在建构我们的感觉和身份,即使今日的后殖民时代也不亚于昔日的殖民时代。直言之,是英语的征服与统治;美言之,则是东西方的相遇。”印度人借助于欧洲人的再发现才开始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根脉,而欧洲人也在比较语言学和新兴的东方考古学的双重刺激之下,将对西方文明根脉的把握转向古希腊之外,在西亚、南亚和北非去探求更为久远的文明传统。
施瓦布确信,西方人对“东方”的发现是近代以来“全球”观念形成的基础,这一发现的思想背景与浪漫主义运动密不可分,时间在18世纪后期开始。他指出,在浪漫主义时代之前,欧洲的男男女女并不知道,也不会关心“东方”的存在及其价值。就在启蒙运动时期,埃及还被看作属于西方文明,而不是东方文明。这一时空错置直到19世纪东方学大盛时才纠正过来。德国浪漫主义者曾认为,人类和白种人(the Caucasians)均起源于中亚的高原山区。而古代印度的书面语言——梵语及其使用者雅利安人也被看作是起源于中亚高原的游牧者群落。这一巧合使自认为是雅利安族后代的欧洲人极度兴奋,由此诱发的文化寻根的激情弥漫在诗人和学者,政治家的言行之中。英国湖畔派诗人几乎全体拜倒在新翻译过来的印度古诗之下;德国的哥德撰写出《东西合集》;连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时还随身带着一本《吠陀》。在德国的大学里,梵语一度成为人所仰望的显学,梵文教授的职位之荣耀盖过希腊文、拉丁文教授们。中国学界当然不会忘记本族的印度语言文化专家季羡林先生也是在德国面壁十载才学成梵文归国的。倘若大唐和尚玄奖活到今日,恐怕要去取真经的地方不是印度而是德国吧?季先生近年有一个颇惹争议的命题“21世纪是东方人的世纪”,其实若从学统渊源上看,这种表达方式直承欧洲学界的“东方文艺复兴”传统。只要随手举出两个例子,就不难发现当今中国学人的“东方复兴”期待其实要比100年前的法国人和200年前的德国人委婉得多。
1915年,罗曼·罗兰,这位为法国赢得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宣称:被世界大战所损伤手脚的欧洲,将从亚洲的文化精神中获得治疗的希望,未来就在于认识和发扬东方的传统。
1803年,第一个在波恩大学获得梵文教授席位的施雷格尔在一封信中写道:“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印度。”
看来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东方注定是被“发现”的一方。不论怎样呼唤“复兴”,其被动性已然成为宿命。难怪萨伊德在其《东方学》卷首题辞要引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的话来为自己点题:“他们不能表现自己,他们必须被人表现。”同样的话语从东方人口中说出和从西方人口中说出,效果截然不同。文化身分的悬殊使同一种措辞要么成为赞誉,要么成为自大。
萨伊德以一个旅居美国的东方学者的身份面对和施瓦布同样的东方学史课题,尽管他在书中10多次提到施瓦布的著作和观点,间或还有大段的引述,但是他的兴趣和意图却截然不同。简言之,施瓦布是欧洲的东方学的生动讲述者,而萨伊德则是东方学的批判者和颠复者。如美国人类学者詹姆士·克里福德所说:萨伊德的话题常被认为是同19世纪的语言学、东方语言文本的收集和整理相关的一门相当陈旧的学科。雷蒙德·施瓦布的百科全书式的《东方文艺复兴》(1950)当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性历史,其中包括了汉学家、伊斯兰学者、印欧学家、文人、旅行者,等等。萨伊德无意去修订或增补施瓦布的书,因为他的方法不是历史学的或经验式研究,而是演绎的和建构式的。他的研究在拓展该领域的同时还使之形式化,把东方学转化成为一种复杂多样之总体的举隅修辞术(synecdoche)。萨伊德效法福柯把这个整体称为“话语”。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的是,自尼采到福柯的学术叛逆性格和系谱学方法使萨伊德的《东方学》实际上解构了西方人的东方学,并将尖锐批判的矛头直指向西方所谓“知识”、“科学”的虚构性,以及学术话语背后的殖民主义价值观。也正因为这样,《东方学》比法国人施瓦布的《东方文艺复兴》更加具有超学科的影响和冲击力,现在几乎成为文化研究方面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典之一。
等到英国人伯纳尔着手撰写《黑色雅典娜》这部为整个西方文明重新寻根的上千页大书时,他一定费心权衡过如何在施瓦布和萨伊德所代表的两种写作方式之间找到后来居上的途径。该书首卷575页的巨大篇幅仅有4次提到萨伊德,提到施瓦布稍多,加上引用和介绍共有10余次。卷首的谢辞中列举的数十个人名中,萨伊德的名字被排在第七十位。书的副题叫“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此处的“古典”同英语中的惯用法一致,专指古希腊罗马文化,作者显然是要告诉世人,西方文明之根并不在西方自身,而在东方。而且,这种“根”(roots)是复数的,是一种复杂的盘根错节,而不是一目了然的单一根脉。而30年前美国近东考古学专家,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克拉莫尔(S.N.Kramer,又译克雷默)发表《历史始于苏美尔》(History Begins at Sumer,1958)一书,似乎重演了当年泛埃及主义或泛巴比伦主义的文明单一根源论。伯纳尔用一个言简义赅的合成新词“非亚”来替代形形色色含混的“东方”(east,oriental),似乎要把北部非洲和西部亚洲看成与欧洲不可分割的文化传播区。这就从眼界上和研究范围上超过了以印欧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为主线的施瓦布和萨伊德。伯纳尔不是在陈述或者颠复欧洲人的东方学,他是在重构东方学,使它成为与西方学不可分割的知识,成为西方文明史的基础。

《黑色雅典娜》首卷题为《编造的古希腊1785-1985》(The 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全书共10章,从古典学的诞生讲起,追溯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埃及和古希腊文化关系的认识,17、18世纪以来埃及学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几经兴衰的情况,乃至19、20世纪西方公众心目中的埃及形象,种族主义时期对埃及人是否黑肤色的疑问,菲尼基学与亚述学的兴衰,闪族人种的由来与流布、雅利安模式的产生与演化,以色列的现代兴起和犹太学中的泛闪族主义,末章讲述二战后东方学阵容的新变化与埃及学的再造,尤其是黑人学者中间关于黑人构成古埃及文明的主体的观点。全书的叙述主线是有关希腊文明起源的两种理论假说模型之间的对立消长,即埃及模型与雅利安(印欧)模型。作者的倾向性在《黑色雅典娜》这个惊人耳目的书名中已体现出来,在结论部分更明确地将自己划入黑人学者的观点一边,提出修改后的埃及模型:确认以黑肤色人种为主体的古埃及文明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适当吸收亚述、菲尼基学方面的观点,在埃及之外追索希腊文明的又一条根脉西亚闪族文化;甚至也接受雅利安模型的某些成分,包括其核心假说:在某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讲印欧语的人群从北方进入希腊。
伯纳尔这部书的精彩之处当然不在于他调合各种观点的能力,而在于他成功地引入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在清晰地陈述学术史的复杂多变的脉络的同时,透过“学术”和“科学性”的表象去揭示背后发挥作用的文化因素和种族偏见,从所以然的层面上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会产生某种貌似真理的知识编造。现代知识社会学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最重要贡献就在于揭示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信仰和观念均可视为象征性的商品,其产生与价值取决于象征商品的市场(the Market of Symbolic Goods)。伯纳尔虽然没有象福柯、萨伊德那样喜欢使用“话语”或“系谱学”一类批判性的字汇,但是他对知识社会学方法的自觉贯穿在这部经营十年的大著始终,使这位治汉学(中国历史)出身的“东方学家”在自己较陌生的广大领域里驰骋古今,使一个学术史课题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批判倾向,他指出:“埃及人和菲尼基的殖民使他们(古希腊人)的祖先文明化。”“随着19世纪种族主义的强化,对埃及人的厌恶日渐增长,不再把他们看成希腊的文化先祖,而基本上视为异族。”一整套新的埃及学学科的就这样发育起来,以便去研究这一异族文化,同时强调埃及同希腊罗马“真”文明之间的距离。
埃及学术地位的衰落对应着1820年代种族主义的兴起;菲尼基学地位的衰落对应1880年代反闪族(anti-Semitism)运动的兴起,并在该运动的高峰期(1917-1939)而归于沉寂。这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如下信念已坚定地确立起来:希腊并没有从埃及和菲尼基获得有意义的文化借用;关于埃及、菲尼基殖民的传说完全出于荒谬;关于希腊智者到埃及学习的故事同样是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些信念在1945-1960年间依然存在,即使其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学术界中已被普遍地质疑。
从60年代后期开始,极端的雅利安模型遭到犹太人和闪族学人的沉重打击。迦南人和菲尼基人在古希腊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然而,把希腊文明多半溯源于埃及的传统观点仍然被否认。在希腊语言研究——浪漫主义和极端雅利安模型的最后阵营——中,任何关于非洲亚洲对希腊影响的见解均被斥为荒诞。
在伯纳尔看来,埃及模式之所以会被雅利安模式摧毁并且取代,并不是学术本身的因素在起作用,并非雅利安模式能更有效地解释相关现象,而是要使希腊历史及其同埃及和利凡特地区的关系适应19世纪的世界观,特别是其系统的种族主义观点。20世纪的学者已经揭示出“种族”(race)这个概念,是虚构的神话,欧洲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历史观均遭到空前的怀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回顾雅利安模式的炮制,有理由说它是在“罪恶”和“错误”中产生的。不过,在同一个时期产生的、带有同样不光彩动因的达尔文主义,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理论图式,所以雅利安模式的概念尽管沾染着罪恶,并不一定要废弃它。这又显出伯纳尔较为开明通达的一面。
综观《黑色雅典娜》第一卷,除了尖锐地质疑西方理性与科学招牌背后的种族主义罪恶之外,作者还对18世纪以来流行的“进步”(progress)观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偏见做出分析批判。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进步’针对埃及”、“进步”和“欧洲是‘进步’的大陆”这样三个小节标题,便是集中探讨这个问题的所在。作者认为,1680年土尔其被打败和牛顿物理学的普及流行,改变了欧洲人的自我形象。在后牛顿世界中写作的知识分子,如孟德斯鸠,从前曾把埃及人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现在却开始把东方“智慧”同欧洲的“自然哲学”相对照。伴随着欧洲经济和工业进步以及向其它大陆的扩张,欧洲优越的观念在18世纪逐渐增强。由于和“进步的欧洲”形成对比,原来受到尊崇的古老文明之偶像,如埃及和中国,都似乎现出了停滞不前的本相。埃及的古代,“以前被视为主要的可贵之处,观在却变成了一种缺陷(liability)”。进步的图式把欧洲列强摆在历史前行的先锋地位,殖民和扩张也就自然成为合理的、合法的事情。历史偏见一旦形成并且蔓延开来,便会假借“理性”和“科学”之名去生产罪恶,并在知识生产领域不断地为谬误和歪理开拓买方市场。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第五章中有一节题为“中国的败落”(The Fall of China),所讲的不是中国国运的实际衰落,而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如何伴随着欧洲人的自我感觉由卑到尊的转化而一落千丈,从乌托邦化的理想道德之邦,变成贫穷、迷信、愚昧、腐败的异已国度。尤其是在1839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以保护其鸦片贸易以来,直到19世纪结束,英法和其它列强,对中国的进犯,是中国形象转变的关键因素。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因为消费鸦片而备受责备。德·托克威尔(De Tocqueville)写于1850年代的著述表示,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这样赞赏中国实在不可思议。
中国形象的败落反映在语言学上,德国的洪堡德将汉语作为与世隔绝的语言,等同为婴儿语,列入人类语言进化序列的最初级阶段。19世纪中期的印欧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雷彻(August Schleicher)建立的语言进化三阶段模型中,孤立语型的中国语位于最早阶段,随后是胶着语型的乌拉阿尔泰语(土尔其与蒙古),最高阶段是屈折语型的闪米特语和印欧语。如果把语言发展水平看作文化高低的标志,那么中国人自然被看成世界历史的最原始阶段。这样,在历史语言学的“科学的”基础上,埃及与中国同样被踢出了历史,变成了挪亚洪水之前的遥远古昔。我们在19世纪号称最博学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看到的世界精神之行程,之所以从中国开始,至基督教的欧洲而到达终点,看来并不是个人幻想中的虚构。而马克思构思人类社会发展诸阶段模式时,特别标出与西方历史迥异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现在看来自然也难免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从20世纪初的《金枝》到这个世纪末的《黑色雅典娜》,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之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认识上的启蒙,终于站到了全面清算西方中心历史观和白种人优越论偏见的自我解构立场之上。这一历程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学术思想的巨大变迁和批判理论的日益深化。西方“理性”自大的一统天下终于宣告结束,人们已经能够识别权力和利益如何驱使“理性”作伪,往昔信奉为“科学”和“真理”的东西,如今接连二三地暴露出“建构”和“虚设”的马脚。象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的《社会建构的现实》(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nchor Book,New 1957),历史学家霍布斯包恩(Eric J. Hobsbawin)等的《被发明出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人类学家库柏(Adam Kuper)的《发明原始社会》(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1988,Routledge),考古学家乔治·邦得(George C.Bond)等编的《社会建构出的过去》(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等一大批新近问世的著作或文集,仅仅从书名的措辞就不难看出“打假”的激进要求已经变成知识界相当普遍的共识。
在库柏的《发明原始社会》一书中,文化寻根的早期杰作弗雷泽《金枝》也被列入“发明”原始社会的古典进化论派学者群的行列:“《金枝》出版大获成功,为众多读者提供了古典学、外域风俗和勇敢的理性主义的难以抗拒的结合物。”弗雷泽在他的书房里旁搜博采一切可能到手的人种志资料时,他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所醉心研究的“原始社会”不过是一种虚设,是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服务的工具。如萨伊德在《东方学》1994年版后记中所说,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要重新的创造它自己的“他者”。人类的身分不仅是不自然的和不确定的,干脆就是建构出来的,甚至是发明出来的。自我身分的确认需要有“他者”作为条件,所以“建构”和“发明”是不可避免的。
唯其如此,为了在符号生产的领域里明辨真伪,解构和打假的本领也就成了未来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一种基本素质。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