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只有发自内心的利他行为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
【编者按】
乔治·普莱斯出生于纽约,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一生颠沛流离,曾被哈佛大学录取,晚年却流落街头。他追求利他主义的根源,身体力行,广善布施,临终却被世人遗弃,长眠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进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普莱斯可以用很多标签来概括,他似乎在他关注的每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他从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在生命的末期,普莱斯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和爱都给了街头的流浪者,后来自己也沦落成和他们一样。从曼哈顿计划到发现解释利他主义的公式,从无家可归到绝望,普莱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达尔文谜团的悖论。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本文摘编自《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乔治·普莱斯传》,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寻找“利他密码”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舞台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演员。可是,这场为了解利他行为的谜题而进行的探寻,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呢?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科学的历史,我们常常会得出一条有益的结论,那就是创造科学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如果我们细加思索,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在这个关于利他行为的故事中,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寓意是不太容易领会的。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用科学进行有意义的研究的问题,另一类是在科学范畴之外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划清两者的界限。目前,两群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一群人相信科学可以给出一切问题的答案,另一群人把科学看作威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尖锐的矛盾,正是因为我们没能完成上述任务。比如,鄙视宗教的唯物主义者和怒斥进化论的神造论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而造成这些争论常常是因为缺失一种基本能力,也就是划清上述两类问题之间的界限的能力。宗教诉求和科学追求本应各司其职,但人们对两者之间的界限却深感迷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理解,因此他写道:“虽然科学能够回答很多问题,但关于生命的问题仍然从未被触及。当然到那时,将不会留存任何问题,而只剩下答案。”在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中,维特根斯坦写下了一句话:“对于我们不能谈论的事情,我们必须沉默以对。”
在这里,人类试图用科学的方法破解利他行为的谜题,科学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在寻找生物学上的“利他密码”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将个体和群体对立起来,将基因和个体对立起来,将真正的善意与经过伪装的利己主义对立起来,也将冷酷的生物学规律和灵魂的超然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混乱与秩序对抗的故事,是一个文化与本能对抗的故事,是一个人类与动物对抗的故事。因此,在这个故事中,科学的事实和道德的伦理不期而遇。在这个故事中,自然与试图理解自然的物种互相对视。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
在故事的开始,两位来自19世纪的角斗士提出了它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可以用生物学的方式解释道德,那么这种解释在我们的心灵中究竟占了多大分量?克鲁泡特金认为这个因素占了很大的分量,而赫胥黎认为人类不仅完全不可能从自然中找到任何道德启示,也不可能从自然中获得任何安慰。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俄国的那位无政府主义大公太温和了,他认为人类的所有善意都是一种“自然特征”;而英国的那位斗犬又太严格了,他誓要将人性和人的动物本源划清界限。在自然界中寻找互惠的关系,再把这种关系强加于人类文明,这可能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互惠的关系定义了人类的境况,而真正的善良事实上可能是人类的一种独特发明。也许,霍布斯是对的,我们确实会为了私利而互相斗争;与此同时,卢梭也是对的,他相信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社会也可以实现和谐和进步。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可以创造出真正善良的行为,并且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始于自然。因此,克鲁泡特金和赫胥黎各自掌握了一部分真理。
但是,如果在人类诞生之前,选择的逻辑就已孕育了道德的种子,之后人类文明才把这颗种子培养成我们所谓的“道德感”,那么对于这项弥足珍贵的发明,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换句话说,当人类的道德跨过了历史的长河,进化为一种与其起源截然不同的东西时,道德的起源究竟会对我们的道德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认为,“一个可行的道德系统不会脱离生物追求生存和繁殖的必要规则”,这种亲缘选择和互惠回报的必要规则最早出现在哺乳动物中。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有了这种说法后,汉密尔顿式或者特里弗斯式的逻辑有时会被攻击为遗传决定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大部分人都讨厌这样的理念:人性中的优点与缺点都是通过某种机制印刻在我们的基因之中的,因此从本质上说,这些优点和缺点不由我们决定,也不受我们控制。如果现实确实如此,那么生命便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愤世嫉俗的生物决定论者认为,感情只是我们妄自尊大的情绪的产物。人性具有自我欺骗、盲目的特点,因此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构成上有局限,这是一种我们难以接受的心理鸿沟。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是对的,但这种理论仅对了一半。毕竟,除了虚荣心以外,人类还有非常健康的关于现实的直觉,我们认为基因不是这出戏剧的唯一主宰者,这种想法既符合我们的虚荣心,也符合我们的直觉。此外,科学也证实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当然,霍尔丹、梅纳德·史密斯、汉密尔顿和普莱斯都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当这些学者谈论利他基因时,他们指的事实上是“能提高基因携带者采取利他行为的概率的基因”。只要这种利他基因具有可遗传性,进化的逻辑就适用于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是预先决定的,虽然不够谨慎的科学家有时会发表这种误导性的言论。即使承认利他基因的存在,文化和教育仍然在利他行为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严格来说,也许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具有遗传的成分,但这不等于说“基因决定了我们是谁和我们的行为”。今天,研究这个问题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基于文化区别的自然选择塑造出与基因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人类行为显然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狭义的自然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对生物学家而言,决定一种影响繁殖适应性的行为是不是利他行为的标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机。人类事务中的自利主义和利他主义,跟蝌蚪吐出同类、鼹鼠挖土、布谷鸟悄悄地将蛋下在陌生鸟类的巢中没有一点儿关系。在人类世界中,只有发自内心的利他行为才是真正的利他行为。当然,人类的大脑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器官。但是,心理学上的利他主义与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心理学上的利他行为与生物学上的提高受惠者适应性的行为并不相同。
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亚当·斯密的观点缓和了一些。在这本著作中他写道:“人类具备了这种能力,我们对别人的幸福感兴趣,并能从中得到必要的快乐,虽然我们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实利,除了见证这种幸福的乐趣以外。”不管是生物决定论者,还是那些认为我们的进化天性与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的人,都应该好好读读这句话。这位17世纪的爱丁堡经济学家的文字对他们大有好处,在我们的天性中有许多不同的馈赠。究竟应该怎样利用它们是我们面对的挑战,因为除了善意以外,我们也具有残忍的能力、恶意、荒谬愚蠢的能力和感到无聊的能力。显然,如果我们的遗传天性同时为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提供了基础, 那么我们道德生活的控制权就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
毫无疑问,社会生活为我们打下了某种基础,有一天它会在人类中孕育出“道德感”,防御欺骗的机制、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共情的能力、羞耻、嫉妒、同情、愤怒都是美妙的进化之旅上的不同阶段。同样,在进化之旅中,人类也产生了基本的需求和冲动:幼儿依靠别人照料的本能,群体成员互相依存的需求,对地位的追求,性的需求,母性的本能,还有求生的本能。这些基本的冲动和必要的需求非常容易受各种因素影响,我们的道德感也不应该忽视这些冲动和需求。达尔文曾经写道:“所谓的道德感最初来自社会本能。”人类的善意也许有其自然的起源,这可能会产生令人迷惑和不快的结果。这种信念若被错误的人利用,就会让人忽视生物学意义上的非功利行为的思想。
是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天性都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类的大脑确实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器官。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学上的利他主义和心理学上的利他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两者都可以从进化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我们的大脑是进化的产物,但这并不是人脑最有趣的特点,也不是人脑最独特的特点。进化赐予我们的天赋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塑造我们生活的道德冲动,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事实,它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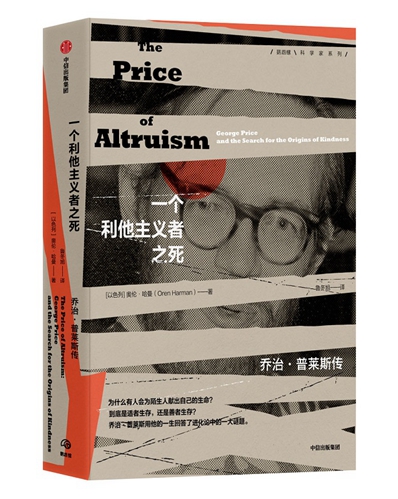
《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乔治·普莱斯传》,[以]奥伦·哈曼著,鲁冬旭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