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失乐园:中晚唐诗人对玄宗朝盛世的叹惋与怀慕
【编者按】
“乐园追寻”是自远古神话、宗教信仰以迄诗歌小说等文学艺术中一个普遍而重要的课题,反映了人类对现实环境的认知与超越,对理想世界的探索与构设,以及对自我心灵的安顿与开显。台湾大学教授欧丽娟在《唐诗的乐园意识》一书中从回顾先唐种种的乐园形态开始,细腻地抉发唐诗中形形色色的乐园,从初盛中晚唐一路往下,意图建立一个历时性的乐园意涵流变史,本文摘编自该书《中晚唐时代的乐园回溯》一节,由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对历经丧乱之后的中晚唐诗人而言,于玄宗朝时臻于顶峰的大唐盛世,是一个熟悉得近在昨日、却又遥远得无处寻访,既令人骄傲依恋、复心生欷歔惆怅的真正“失乐园”,因此在与现实对照的同时,总不免成为今昔相较的终极坐标;而一旦有机会碰触到从昔日乐园中残存下来的“人物碎片”或景物遗迹时,这些在失落乐园之后才开始参与唐朝历史的诗人们,除了出于政治目的而刻意选择借古讽今的摹写角度之外,多是以一种怜惜叹惋之心与爱羡怀慕之情交织杂糅的感受,来看待眼前的乐园见证者。由于距离开元、天宝之盛世犹时未远,其间虽已有数十年,但至晚到中唐时,诗人仍有机会亲身目睹在盛唐繁华核心中度过青春时期的前朝人士,这些在乐园一夕之间土崩瓦解之后依然尚存的遗民,具备了宇文所安所说的“断片”的意义:“在我们同过去相逢时,通常有某些断片于其间,它们是过去同现在之间的媒介。”但这些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断片”身经的历史转折落差实在过于巨大,于是在观者心中引发的惊诧悲悯之感也就更为强烈,因此清李锳《诗法易简录》评元稹的《行宫》诗时即云:“明皇已往,遗宫寥落,却借白头宫女写出无限感慨。凡盛时既过,当时之人无一存者,其感人犹浅;当时之人尚有存者,则感人更深。白头宫女闲说玄宗,不必写出如何感伤,而哀情弥至。”这正是中唐诗人将遗民特别标举出来的原因。同时,这些遗民既是乐园的见证者,因而无论当下是如何的穷愁潦倒,他们身上所依稀残留的盛世光辉,却足以诱发一种来自已逝岁月的奇异魅力,因为不但从其言谈举止(尤其是从其口述的回忆)之中能够再现一去不返的黄金岁月,甚至他们本身即是乐园曾经存在的最终的、真实的证明,故而“断片最有效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价值集聚性。因为断片所涉及的东西超出于它自身之外,因此,它常常拥有一定的满度和强度”。我们可以说,这些“断片”的满度和强度主要便是来自于过去所拥有的全部价值,而无缘躬逢其盛的中唐诗人便可借之获得一窥乐园宫墙的机会,并可在稍事追抚之后,进一步满足潜藏于内心中一种回归乐园的情感需要。
如元稹《行宫》诗便是一例,诗云: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诗中在寥落寂寞的行宫里“说玄宗”的,固然是年华老去的白头宫女,出发点主要亦是基于缅怀个人之青春往事的心理,但作为倾听者而将其所说笔之于诗的诗人,其欲参与乐园而已然时不我予的命定,岂非也获得了突破的机会?随着白头宫女的叙述纵身于回忆的线索之中溯游而上,玄宗朝的乐园大门又再度向他们开启。
同样地,元稹的另一首长篇作品《连昌宫词》(元和十三年,818)与其十六岁时所作《代曲江老人百韵》(贞元十年,794)同一旨趣,虽然都主要是借玄宗朝治乱盛衰之事迹,以传达谏戒规讽之理为宗旨,但两诗亦分别透过“曲江老人”“宫边老翁”的泣诉之语,将天宝时期的辉煌气象自遗民追忆的口述历史中源源再现。
即使最终存在的乃是讽谕的宗旨,但从这首长诗的相关内容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元稹视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变之后的历史为“乱”,而视玄宗朝(此诗主要是指添加了贵妃在内的天宝年间)为“太平”时代,故在历数今昔之间的巨大落差之后悲痛地质问“太平谁致乱者谁”,由此亦使开天盛世展现出乐园的意义;而失落了乐园之后,身当“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如此颓败之时代环境中的诗人,也只能借助于宫边老翁之口,才得以遥想当时“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之类春情洋溢、歌舞升平的乐园内部之景观,并由此获得界定盛衰得失的比较基础。诗人自身虽无由亲炙昔日之盛世,却在一生绾结时代两端的遗民身上取得一条导向过去的记忆通路,而在沿途指针所显示的种种具体内容中展开想象乐园之美的追拟体验。
另外,白居易所遇见的被永远逐出乐园之残存遗民更多,如梨园弟子、宫廷乐师、大内宫女,和得到过不少盛唐诗人赠诗的康洽等,都纷纷在他的诗里留下了记录,其笔调则是濡满今昔对比之下所产生的欷歔凄凉之情。如《江南遇天宝乐叟》《赠康叟》《梨园弟子》《上阳白发人》等篇。
在以“绿苔重重封坏垣”的长生殿和“满山红叶锁宫门”的华清宫所构成的背景中,白头老病的宫廷乐师和梨园弟子在诗人的询问下“泣且言”“话梨园”,遂源源流出昔日繁华盛况的图景。可见,白居易对这些人产生了“再三怜汝”的加意珍惜之情,乃是因为他们不但曾参与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成为乐园中的居民与见证者;又在袭卷一切的浩劫之后幸存下来,成为少数能够提供记忆来联系过去的媒介。但是遗民的日渐凋零同时伴随着乐园的渐行渐远,一旦终至于无一人可口述其身经目睹的证词之时,乐园便将完全从人们的生命感中消失,只剩下白纸黑字所勉强留住的冰冷记录,而沦为与现在毫无联系的过去历史,这就真正进入了彻底的封闭与永远的放逐。诗中所谓“万人死尽一身存”“天宝遗民日渐稀”和“零落年深残此身”,正说明其人所具备的珍稀之处。
同样地,以宫词百首闻名的王建,也大量运用其所擅长的宫词的形式和表现手法来歌咏此一题材,除了以《霓裳词十首》追忆贵妃与玄宗以音声歌舞相欢为伴的宫中繁华之外,透过遗民的触发而依稀流露追悼之情者,亦不乏其例,诸如:
先帝旧宫宫女在,乱丝犹挂凤皇钗。霓裳法曲浑抛却,独自花间扫玉阶。(《旧宫人》)
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着音声总举头。(《楼前》)
象征昔日风华的“凤皇钗”与“霓裳法曲”,如今在旧宫人身上或者只是聊备一格地“乱丝犹挂”,其发乱钗斜、衰容黯淡之状堪叫人不忍卒睹,或者竟至于“浑抛却”的境地,完全进入了彻底遗忘的深渊,而眼前唯一真实的,只是孤独地扫除玉阶上层层堆积的落花而已;至于在杜甫笔下极热闹的玄宗生日“千秋节”,至此也只剩余当时似曾相识的音乐片段,吸引了曾经教舞以助举国欢腾的“飞龙老马”听声举头,而据此抓住已渺茫如空中之音的过去的残留。至于顾况的《八月五日歌》一诗,由前半的“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开元九年燕公说,奉诏听置千秋节。丹青庙里贮姚宋,花萼楼中宴岐薛。清乐灵香几处闻,鸾歌凤吹动祥云。已于武库见灵鸟,仍向晋山逢老君。率土普天无不乐,河清海晏穷寥廓。梨园弟子传法曲,张果先生进仙药”一转而到后半的“玉座凄凉游帝京,悲翁回首望承明。云韶九奏杳然远,唯有五陵松柏声”,此中依依回首的“悲翁”却只能听取五陵松柏的萧瑟之声,可见这些遗民所牵带而出的乐园连线,总是柔肠寸断又尘灰满布的惨淡轨迹,这也正说明了元稹《何满子歌》《望云骓》,以及刘禹锡《赠歌者何戡》诸作的书写特质。
此外,中唐还有从另一方面来展现开元、天宝时期乐园意象的诗人,此即韩愈的《和李司勋过连昌宫》诗。诗中最特别的地方是以开元为历史坐标,来作为当今帝王世系传承定位的基准: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第几孙?
对“宫前遗老”而言,历史在安史乱时便已停止前进,沉眠并封闭于乱发之前的时刻里,以至于停格的开元盛世变成了永恒的“现在”,而此后在时间发展中犹然不断进行的王位兴替和人事变迁,都必须回归于此才能获得理解的基础。所谓“今是开元第几孙”的询问,犹如《桃花源记》中“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一段话的翻版,它们意味着纵使外界风风雨雨,几经沧桑兴亡,对执意将记忆和生命停顿于过去某一时刻(如秦朝或开元时代)的人们而言,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过去,只有已然封存静止的那一刻才是可以持续却又不受侵扰的永恒。而陶渊明所塑造的一个永恒乐土竟然在中唐时代发出了音质清晰、内容近似的回声,更显示出玄宗时代在中唐人的心目中所深具的乐园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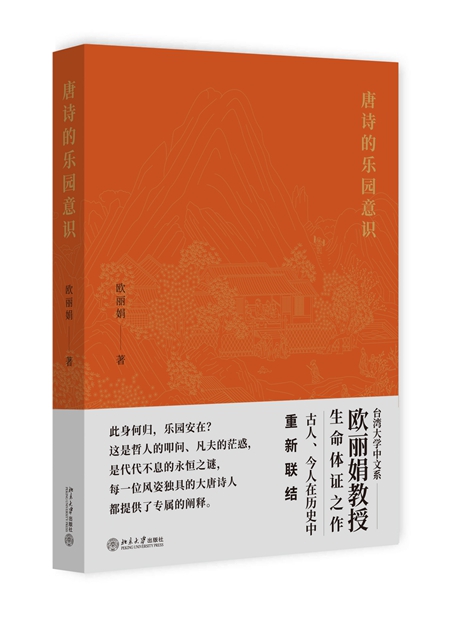
《唐诗的乐园意识》,欧丽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