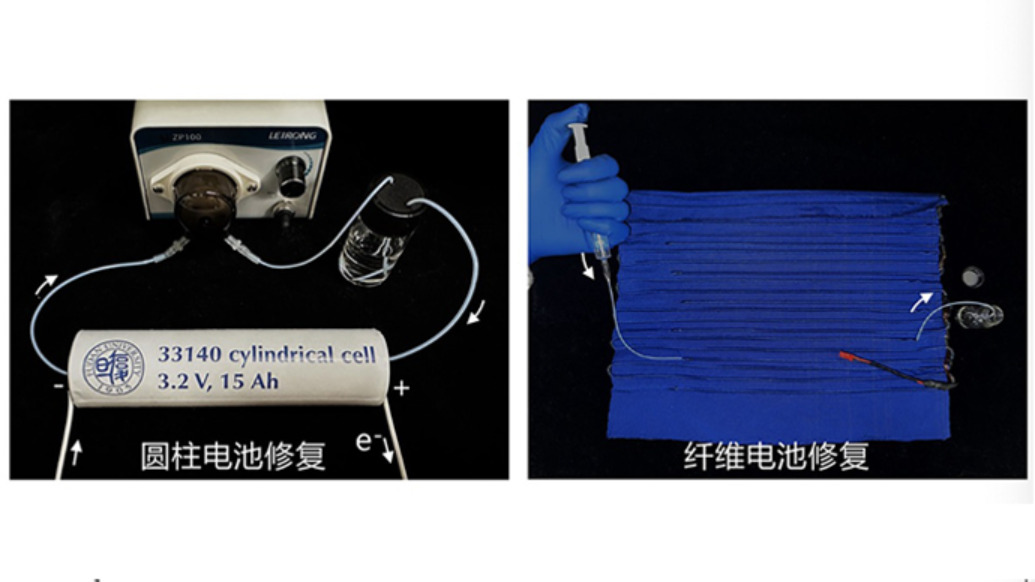- 9
- +1183
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琐记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

复旦校园
文 | 南焱
一
张新颖老师是山东人,但并非是膀阔腰圆的山东大汉,而是北人南相,个头不高,温润如玉,更像是江南文人。我们曾私下觉得,他跟山西人贾樟柯外形近似,满腹才华而为人谦和,只是他不像贾樟柯那般舌吐莲花、侃侃而谈。
初识张老师,应是2000年前后,未见其人,先闻其名。当时我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大二,系里的李振声老师给我们教授现代文学史课。李老师则是典型的江南文人,学问很好,气度儒雅,这一点备受女生好评。但他极低调,讲课慢条斯理,声音也不高,加之讲解偏深奥,大一时并不受我们这些生瓜蛋子的理解和欢迎。
但进入大二后,讲课、听课者均渐入佳境,尤其是李老师讲柔石、卞之琳等人的作品,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学期结束时,李老师在最后一堂课上说,下学期他不接着上当代文学史了,另有年轻老师来任教。教室里立时一片喧哗,大家都舍不得他,也担心接棒的老师水准平庸。李老师接着恳切地说,这位老师要比他学问好,这绝非自己谦辞。
李老师所说的年轻老师便是张老师。其时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不久,但在学界已经声名鹊起。李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写道:“与他的同代人比起来,新颖可以说是很幸运的,读研究生及出道伊始,即得以跻身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教授的门墙,他不仅由此获得精湛的学术指点、训练和扶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道义承当和精神人格气象,都有相当完整的呈现,耳濡目染其间,对新颖精神生命和学术生涯的立足基点的建构,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张老师的名字,其时我们已有耳闻,他写的《栖居与游牧之地》、《歧路荒草》,我在学校图书馆也已读过。由他来教当代文学史,应该很不错。等到在五教开课时,张老师走进教室,穿着浅棕色外套、浅蓝牛仔裤,拎着一个大黑电脑包,看起来挺清爽,但并无特殊之处。说了几句闲话,便正式讲课。张老师讲课,语速也慢,音调不也高,但很清晰,不扯生涩学术词汇,不故弄玄虚,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一堂课下来,我们觉得这位年轻老师教得蛮好,李老师诚不我欺。还有一个优点是不点名,个别旷课者更是窃喜。
说实话,当代文学史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一段,所谓的文学代表作居多是政治传声筒,无聊且无趣。期间不能公发表的地下文学,倒有些不错的作品。对于那些高大上的无聊之作,张老师则是快速掠过去,更侧重讲潜在文学写作。1978年后的文学作品,则讲得比较细致了。对于自己喜欢的小说、诗歌,他会细细讲解,乃至在课堂上直接朗读,语气舒缓而平实,真诚投入,也很有感染力。
张老师一直保持着在课堂上朗读的习惯,不管是当代文学史课、当代新诗课,还是后来上沈从文精读,喜欢读那些精彩的段落、章节。比如穆旦的《诗八章》、孟京辉的戏剧《恋爱的犀牛》、许辉的小说《碑》,都是他在课堂上单独讲过的作品,每每都会读全诗或部分段落。其实,一边诵读一边讲解,更能让学生集中精力,直接感受原作的魅力,远比通常讲课流行的泛泛而谈更有效。
我没听过张老师的沈从文精读课,但有一位学生这样记载:“他讲沈从文的《湘行书简》,确切地说,是读。读的是题为《夜泊鸭窠围》的信。他这样读,‘想起那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因这曲子我还记得了我独自到锦州,住在一个旅馆中的情形,在那旅馆中我听到一个女人唱大鼓书,给赶骡车的客人过夜,唱了半夜。我一个人便躺在一个大炕上听窗外唱曲子的声音,同别人笑语声。这也是二哥!那时节你大概在暨南读书,每天早上还得起床来做晨操!命运真使人惘然。’读到这里,他便止住,而我们期待下文,于是静默,真是足够沉默,整个宇宙的静默,可他只利索地合上书,台下顿时哇啦哇啦地响起来。”
记得当代文学史课的期末考试,最后一道题是谈论诗人曾卓的《悬崖边上的树》、穆旦的《智慧之歌》,这两首诗里都写到了树,比较两者的异同。有同学考完后,觉得这道题出得太没意思,树有什么好谈的,无非是作者心中寄予的一点精神象征罢了。后来,张老师不止一次地说,他喜欢所有的树,不只是文学作品中有象征意义的树,更喜欢日常生活中真实生长的树。

2005年毕业前夕同门合影。
二
那时我已开始写诗,偶尔课后会拿些习作请张老师斧正,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倒也彼此熟悉了。2002年夏天,我保送在本校继续攻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系里有规定,凡是保送读研,学生可以自由挑选导师。由于课讲得好,张老师很受学生欢迎,想跟他读研的学生自然也不少,我也有此心愿。
当时,他刚评上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届研究生有黄德海、苏鸣。黄德海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载着我去张老师家登门拜访,我表达了跟他读研的意愿,张老师爽快地答应了。临别还送我们每人一本新出的著作,嘱咐说外面马路上大卡车很多,骑车要小心一点。没想到开学后出了一点小差池,经过一番小波折,我总算成了张老师带的第二届研究生。
按照系里的规定,每个导师都要给自己带的研究生开小课。当时张老师门下弟子不多,总共也就区区几人,上小课就在教研办公室里,每两个星期上一次,一次不短于两个小时。提前一周布置好必读书目,上小课时每人围绕书目发言讨论,一般是师兄黄德海打头阵,我发言比较靠后。那时我年少轻狂,喜欢故作惊人之语,立论追求标新立异。张老师则是边喝茶边听我们发言,一般也不打断,只是最后做点评式发言,每每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使我们茅塞顿开,冷汗浃背。
这样的小课上得开心而充实,每次两个小时总嫌太短。除了讨论文学专业的书目,中间也会插入观影讨论,像当时上映的《十七岁的单车》、《无间道》,也都进行了热烈讨论。每次小课结束后,就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餐厅吃饭,大家聊得很欢乐,但张老师的话则不多。他也曾经在文中直言,自己的性子比较闷,给学生的印象并不亲切,不会打成一片,坐在一起说话常出现间隙过长的沉默,令学生颇感压力和不自在。
不过,在给我们上小课的那三年,我们倒没有感到压力和不自在,反而觉得氛围挺亲切、随意。研一时,我把自己在本科期间写的诗作,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带给张老师点评,但他没有说什么。其实,那本册子大多是习作,当时我看过很多中西方现代派作品,囫囵吞枣,消化不良,写作时难免邯郸学步。研二时,我慢慢摆脱了这种摹仿的习气,开始写自身的切身经验,又打印了一册新作,带给张老师看。这次,他马上给出了好评,尤其提到其中写家乡和亲邻的几首诗很好,也让我倍感鼓舞。
同门之中,德海师兄读书最勤快,也读得最多,寝室里床上床下全是书。我也看得很凶猛,有空基本都泡在图书馆里。等我读研三时,张老师又带了两届新的研究生,其中有两位才女徐敏霞、周嘉宁。她们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刚进大学就已经出道,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徐敏霞本科毕业后,去西部支教一年,对她这样小有名气的上海女孩,实在是难能可贵。而她说自己最尊敬的人就是张老师。对于热衷创作的周嘉宁,张老师则基本放养,她不想来听课也可以。
张老师带研究生,一方面很宽松,另一方面也很严格。写论文自然不消说了,没有新的观点和角度就不能轻易动笔。当时他准备出一本新著《双重见证》,收录了他的大部分重要批评文章,就叫我负责校对这本书,没有什么具体要求,说只是锻炼一下认真和细心的态度。我逐字逐句校对了全书,足足看了三遍,虽然略嫌枯燥,但也受益匪浅。硕士论文写的是穆旦,张老师让我放开写,改了两稿,最后我写了七万多字。现在看来,这篇论文不乏粗陋之处,但其中洋溢的蓬勃激情,却也是弥足珍贵。
研究生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毕业时我没有选择读博而是工作。当时觉得在大学校园待了七年,委实有点腻了,况且张老师也还不能带博士生。另外,经济窘迫也是客观原因。在复旦七年,家里总共只给了我七千元,这点钱只够交两年学费,其他一切生活开支就全靠自己解决了。拿奖学金、做家教、干兼职,没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就这样度过了七年,还买了十几箱书。再接着读博,也难以为继了。待到毕业时,我已经山穷水尽、身无分文,前往北京时跟本科同学借了三千元,权当第一季度的房租、生活费。
我的性格跟张老师比较接近,也偏内敛、沉闷,每每聚会时充当听众,极少滔滔不绝。事实上,我们平时私下交流也不多。临近毕业前夕,找工作很纠结,自己也缺乏一点主见,有一次就去他家长聊了一通。其时我发泄了一些心中的郁闷之情,张老师认真地倾听,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后来听说我要去北京的报社做记者,他惊讶地问,你这性子适合吗?其实,他自己曾经也干过四年记者。随后,张老师笑道,在社会上打两年滚,再回学校读书,也挺好的。
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些感动,张老师对我素来宽容,从不施加任何责怪,更多的是一份理解和包涵。我来北京的前夕,他专门预定了一个包房,请我们同门吃饭,大约也有惜别的意思。饭桌上的气氛不太轻松,只有德海师兄挑一些有趣的话题,大家喝了不少啤酒。吃晚饭各自取道回去,张老师走路的姿势一贯就是这样的,身体有些往前倾,步子有些缓慢,他的身影慢慢地在路灯下消失了。
那时我的内心颇有些伤感,毕竟要离开学习和生活了七年的复旦校园,要离开熟悉密切的师友,而前途并不明朗。只记得在饭桌上我大约说过,只要有张老师在,走到哪里我在精神上也不会孤独。
次日匆匆收拾了一番行李,傍晚时分登上了上海至北京的列车,在车上坐了一宿,疲困得睡了过去,醒来已是次日黎明,胳膊枕得发麻,车厢内乘客还都在熟睡中,周围显得格外安静,只有车轮的声声撞击,车窗外已是晨曦中辽阔的河北平原,闪过一片片玉米地、杨树林,望着窗外,黯然神伤,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封面。
三
到北京后第一年,除了工作之外少有交际活动,而以前的朋友各奔东西,渐渐疏于联系。新生活使我骤然被抛入孤立的处境,四顾便觉得异常的茫然和无聊,伴随着的是日益滋长的寂寞情绪。就在这种并不良好的状态中,收到了张老师寄来的新著《沈从文精读》。可以说,当时我以一口气的劲儿读完了全书,并自以为有所触动,写了一篇小书评,谈了一些浅薄的感想,发给了张老师。
之后这几年,我陆陆续续了解到,张老师一直想写一本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已有好几种,且质量非常高,而其后半生的经历,尤其是精神历程,却极少有人深入关注,也缺少有分量的传记。张老师并不自认为是沈从文研究专家,但他正式写论文研究沈从文,至今起码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心浮气躁的时代,还有学者长年专注研究一个作家,多少有些罕见吧。前几年,张老师的心血之作《沈从文的后半生》问世后,在学界可谓轰动一时,得了许多年度好书奖。之后,他又推出了《沈从文的前半生》,双书合璧,堪称完美。
张老师还写过一篇论文,谈沈从文对当代作家、导演的影响,并以此文获得鲁迅文学奖。他认为沈从文对侯孝贤、贾樟柯的影响很大,两者的电影里都有传承沈从文的气息。2009年,有一次我去贾樟柯工作室做专访,问哪个作家对他的影响最大,老贾坦然回答:“我最喜欢沈从文,他的生命成长经历跟我有相似之处,特别亲近。他的语言里面的声音、色彩是其他中国作家不能企及的,最让我激动。”
老贾还提及,自己特别喜欢沈从文的短篇《连长》,小说里写到在冬天里吹响的军营喇叭声,在下雪天里像棉絮一样飘荡,令人听了觉得格外寂寞,也让自己很感动。《连长》写的是一位连长在部队开拔前夕,到情人家里小聚,相对无言,心里十分忧愁,外面下起了雪。里面有这样几段,其情其景,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片,从窗口望去,象正有人在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象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是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的大校若不是落雪,天气已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不见得天气和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中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全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
两人不说话,两人便都听到外面的雪落地作极微极匀声音,又可听到屋后竹园大堆的雪下坍以后竹子弹起的声音。此外可是全无响动了。全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人声,也没有锣鼓唢呐,一个村子里面的一切全象睡着,又象全死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屋子中慢慢颜色暗默,火塘内的炽着的炭却益发加熊明了。”
工作两年后,我一度想考博回复旦读书,此时张老师也评上了博导,但结果我错失了机会,大概也让他有些失望吧。之后,我再无读博的打算,也就一直在报社干着媒体工作了。曾经先后有两次去上海出差,由古道热肠的德海师兄相约,跟张老师一起聚会吃饭。聚会跟在校时差不多,还是在路边小餐馆,点几个家常小菜,喝几杯啤酒,聊的全是新书、学术话题,气氛依旧浓烈。
我的性子原本比较孤冷,不太热衷于联络感情,毕业之后的这些年,我跟张老师的联系也并不算多,只是偶尔来往邮件而已。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整理一些自己的诗作,发给他看一下,而张老师也总是给予勉励的回复。张老师早年也写过诗,后来一度中断了。2011年,他在学术工作之外,又捡起了诗,用纸和笔写起诗来,还渐渐成了习惯。
用张老师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拘谨的人,也是很害羞的人,所以特别渴望自由,其实写诗是非常自由的状态。“虽然我写的数量很少,但是对这个东西会有一个依赖,这个依赖说的轻一点就像人对烟的依赖,说的重一点就是对毒的依赖,你自由地运用字、词、句,自由地表达状态,对这个状态有所迷恋,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年来,张老师一直勤于著作,得过很多大奖,还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如今门下更是桃李累累,在学界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大概在世俗的眼光中,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但他似乎一如既往,保持温和低调的秉性,宽厚待人,也从不参与公开的争论,即便在微信朋友圈,他也极少发言,只是偶尔点赞而已。当然,不对那些热闹的公共话题发言,与时代的喧嚣保持适当的距离,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在《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中,他这样写道:“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
我想,这大概也是张老师的自我期许吧,甘愿居于时代的洪流之外,并非个人逃避,而是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确立个人的根基。他还就沈从文写道,现代以来的中国,也许时代和社会太强大了,个人的力量与之相比过于悬殊,但个人弱小的力量也是力量,而且隔了一段距离再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强大的潮流已经消退,而弱小的个人反而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
这种安心于时代边缘的独立姿态,跟一棵树的姿态也比较相似。张老师非常喜欢树,写过多首有关树的诗,其中有一句诗是这样的:冬天的树和春天的树是同一棵树。冬去春来,迎来送往,无论严寒酷暑,伫立在那里,不惊不乍,不急不躁,攫住脚下的一方泥土,伸展自身的枝叶,这就是一棵树的姿态,也许可以用来形容张老师吧。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 台湾商场突发爆炸
- 外交部回应美俄元首通话
- 央行:择机调整优化政策力度和节奏

- 国内期货夜盘开盘,原油跌超2%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实验室聚焦中医药原创性研究

- 中国内地动画导演、编剧、制作人,凭借哪吒1和2成为百亿票房导演
- 李白的诗《题峰顶寺》中“恐惊天上人”的上一句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