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 +153
家庭的解体与重生:历史视野下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其对于震区社会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未消除。但是,与建国以来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和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其在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究其因,一方面是地震发生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对灾情信息的封锁以及意识形态的抑制,使得正常的学术研究难以产生;一方面则是因为对此次灾难的救援及灾后重建更多地被当成弘扬的典范,使很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特别是海外学者不愿意接触这一事件。汶川地震爆发后,唐山地震及其救灾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又变成了印证中国社会进步的反例,但却少有人对此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与探研。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对唐山地震没有任何的研究。事实上,就在地震爆发之后,中国科学界就已经对唐山地震的发生原因感到迷惑不解,进而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研究与唐山地震有关的一系列自然现象,并在理论上形成一定的突破。主要成果有《唐山地震考察与研究》《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唐山大地震震害》《唐山地震孕育模式研究》《唐山强震区地震工程地质研究》等。
与此同时,一批从唐山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在唐山地震十余年之后,主动运用其时复兴于中国的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大量社会调查,对唐山地震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灾区社会恢复和社会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地震前后唐山地区人口、家庭、婚姻、生育以及社会心理、社会习俗方面的巨大变动及其重新整合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此为契机,地震社会学在中国应运而生,成为中国灾害学领域的重要生力军。其代表作品有:《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1986年)、《地震社会学研究》(1988年)、《地震社会学初探》(1989年)、《唐山地震的社会经济影响》(1990年)、《河北省震灾社会调查》(1994年)、《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与人们的启示》(1996年)以及《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对策》(1997年)。
一部分来自医学界的相关学者,也以大量临床实践作为案例,侧重探讨地震对不同个体的心理、精神所造成的短期及中长期影响,将人文关怀渗透到医学研究之中,是为中国灾害心理学的先声。
另一方面,唐山地震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曾参与地震救灾的钱钢,以十年时间坚持不懈地追踪访谈,全景式地记录了地震当时唐山人民的种种表现。其作品《唐山大地震》被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没有灾难书写的历史”。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积累,以唐山作家为创作主体,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唐山大地震文学”已在中国文坛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们运用不同的文学体裁,真情地再现了地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强大冲击,以及灾后社会重构与整合的各个层面,为深化唐山地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
但是上述研究与反思,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大体说来,这些研究仅仅局限于唐山地区和此次唐山地震,很少与此前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地震或其他灾害事件联接起来,进而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探讨唐山地震对于人口变迁和人口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迁移,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变化,此种变化是如何与唐山地震纠结在一起共同影响着曾经是灾区的社会,影响着灾区的社会恢复和重生的进程,更是少有人问津。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发挥历史学家的优势,充分发掘和利用迄今尚未受到重视的官方档案、新编方志以及文学作品、口述史料等,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家庭作为考察对象,从人口的迁徙、婚姻、生育、抚养、丧葬等诸多方面,对家庭在灾前、灾时、灾后以至今天等不同时期的形态及其变化进行系统的考察,以期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探讨地震灾害的社会影响及其漫长的修复过程,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震害中被夺走了生命?
尽管这场地震距今已近40年,但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由于唐山地震伤亡人数是在地震三年后方才得以公布,此后官方陆续公布的数据多有歧异,致使国内外学者与社会舆论对此长期抱持怀疑的态度,而且众说纷纭,唐山当地民众也有不同的说法。
事实上,从目前掌握的档案与数据来看,官方之“死亡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的结论虽然不尽可信,但显然并不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与事实相距甚远。因震后各个时期所做统计数据的不完善性,以及调查地域的不一致性,目前已很难对地震当时的伤亡做出极为准确的数字重建。但是通过各类文献的比对,较为明确的答案可能是,地震中至少应有近26万人死亡、50余万人受伤;唐山市区7218个家庭灭门绝户,出现12869名丧偶者、2652名孤儿、895名孤老、1814名截瘫者。如加上天津、北京等地的统计数字,则死亡人数当在30万人左右。2008年,随着唐山市内地震纪念墙的落建,多达24万余名死难者的信息也逐渐清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可视为一种旁证。至于1976年8月唐山地委会的人口死亡调查,则是目前最可信赖的统计数据。从当时的文件来看,地震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基本上掌握了死亡人口总数,只是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不愿意对外公布而已。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一原本及时发布的数据,直至几十年之后才大体上被公众接受,其对于政府公信力所造成的损害无可估量,也给人们对此次地震进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人为设置了诸多障碍,可谓适得其反。2005年之后,中国政府颁布条例,决定及时公布灾害死亡信息,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对唐山震区的人口增长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邹其嘉、王子平等学者在探讨唐山市地震前后人口变动过程时指出,人口生育补偿规律是唐山市震后人口自然变动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大体上经历了负向增长期、生育补偿期、向常态自然人口规律复归期等三个阶段;其中的1978年和1982年是人口生育补偿期的两个生育高峰,主要原因在于震后唐山年轻人口比重增加,并迅速进入初婚年龄,大量破损家庭短期内完成重组。但是作者并没有考虑到震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生育的影响,也没有与此前的“三年自然灾害”对人口的影响进行比较,以致对灾后人口增长机制的描述未尽准确,尚有诸多进一步商榷之处。
对于第一个阶段,当然没有疑问,而且需要补充的是,仅仅计入人口的绝对损失,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还应将由此造成的相对损失包括在内,如此,其造成的破坏性更为突出。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则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使此前中国历史时期常见的灾后人口反馈机制发生明显的变动。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唐山市区人口出生率下降,并达到该时段的最低值,仅为13.8‰。此后,1962年到1967年间,人口开始出现补偿性增长高峰,其中1963年,出生率达到50.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唐山大地震虽然使唐山市区的死亡率达到前所未有的134.7‰,但此后人口并未出现更大的补偿性增长高峰,仅在1981—1983年间略有回升。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唐山市区人口的增长形态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调解作用。除此之外,1981年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法》将结婚年龄由原来的“男二十、女十八”提高至“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结果使河北省当年结婚人数激增。这也很可能是1981—1983年唐山市区出生人口小高峰出现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却不是地震人口损失引发的。
即便如此,马尔萨斯揭示的灾后人口补偿机制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发挥作用。震后一段时期,在不影响计划生育的大前提下,国家对地震重组家庭夫妇的生育给予了政策上的特别调整。所谓的“地震孩”“团结孩”就是这一政策的结晶。1977—1982年间的具体的措施是:震后初期,重组家庭中,夫妇一方不足两个孩子,均可再生育一个;1978年间,生育政策宽松到,不论一方有几个孩子,只要一方没有孩子,都让生一个“团结孩”。但时间不长,这种政策就停止了。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证城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1983年到1984年,重组家庭只要一方有一个孩子,即不能再安排生育。但新的政策出台后,再婚夫妇一方有两个孩子的丧偶者,另一方系初婚或未生育过的,可以照顾生育一个孩子。这样的解决方式,解决了一大批重组家庭的生育问题。而1986年,唐山市区仍有178户地震重组家庭,其中一般是男方有三个以上孩子,女方年龄较小系初婚,孩子的年龄较大,家庭关系因此不和谐,有的夫妻关系已经到破裂的边缘。对于这样的家庭,唐山市计生委认为,可以予以照顾生育一个孩子。市计生委(1986)10号《关于解决震后重组家庭照顾生育问题的请示》,唐山市国家档案馆,105-01-0239。此举反映了政府在震后社会恢复阶段中为维护家庭稳定做出了努力,但实际执行中的细节尚待商榷。

第三个方面涉及震区家庭生活的解体与重构。
地震的冲击使唐山市区每家每户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员,由此造成的家庭构成的诸多巨大变化,对震区家庭形态、婚姻观念和家庭生活均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地震重组家庭(patchfamily)、截瘫患者家庭以及地震孤儿的抚育与孤老赡养成为震区突出的社会问题。地震社会学家震后所做的一系列调查与研究,对分析震后家庭表现出来的种种变化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档案显示,在接近26万人死亡、50余万人成为伤患的巨大人口变动中,仅唐山市区,至少有25448个家庭受到最沉痛的打击,其中全家震亡7218户,震后一方丧偶者达12869人,孤儿2652名,孤老895名,截瘫人员1814名,可谓支离破碎。家庭平均人口,也从1975年的4.37猛减到3.55,每户减员1人,直到1982年,才有所恢复,达到4.12。此后由于核心家庭户数逐渐增多,唐山市家庭平均人口数有减少的趋势。
地震的来临,使灾区人民赖以生存的一切生活物质基础被摧毁殆尽,也使正常的家庭生活陷入种种突如其来的改变之中。半数以上的家庭,纷纷以亲缘、血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组成“共产主义大家庭”,过着一种群居式的生活。还有三四成的家庭选择在空旷的场地搭起一家一户的“防震窝棚”,依靠组合成的新居住区实现共同生活。待震区简易住房大批建成之后,这种应急式的生活方式迅速消失,灾民开始向小家庭模式回归。
此时,地震的影响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在家庭的层面显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震后重组家庭大量涌现。震前唐山市因离婚、丧偶而再婚的家庭比例极小,仅有1%左右,震后到1979年底,重组家庭占地震中丧偶家庭的半数以上。至1982年,重组家庭在市区达7515户。当时唐山的社会舆论一反传统婚姻观念中排斥再婚的思想,对这样的重组家庭普遍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其中有不少是叔嫂婚、两代联姻,两者在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仅并不常见,而且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政府也采取特殊的生育和就业政策,如重组后一方无子女可再生一胎,农业户口可转为非农户口,继子女可以顶替接任继父母的工作岗位等,鼓励灾民重组家庭。但是绝大多数重组家庭都是建立在同病相怜的相互安慰与理解之上,并没有深厚的爱情基础,实际上很不稳定,离婚率远高于普通家庭。其后经过长期的磨合,这种家庭模式终于渐趋稳定。
那些身体上重度残缺,无法生育的截瘫患者,也被特别批准结婚。其中很多病人,在外地养病期间相识、相爱,他们于1979年11月至1980年6月陆续返唐后,纷纷要求结婚。对此,基层民政部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依据当时婚姻法规定,即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禁止结婚,坚持认为应依法办事;一是认为准许结婚有利于双方的精神恢复,应作为特殊情况对待。经过省政府的慎重考虑,后一种建议被采纳。1990年代以降,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截瘫伤患的婚姻开始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市政府和民政部门还专门拨款,于唐山市路南区筹建了“康复村”,并为入住的25对截瘫情侣举行集体婚礼。此外尚有只同居不结婚的现象,体现了现代家庭模式的多元化。
也有一部分地震中的丧偶者和截瘫者,此后再没有重新组建家庭,而是选择独身一人,孤独终老。对此唐山市政府采取依靠集体、国家补助、分散管理、尽量就地安置的原则,予以赡养。对于地震孤儿,则允许亲属、父母生前所在单位或社、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收养。在3000多名被收养的孤儿中,少数走入了国际家庭。至于无亲属抚养,或未被收养的孤儿,则进入国家在石家庄、邢台、唐山三地建立的五所孤儿学校。这些孩子,享受了来自社会大家庭无微不至的爱护,但是国家的抚养只能保证其生活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线上,且标准一致,与孤儿多样性的发展诉求之间往往发生冲突,不少孤儿在长大成人后出现了自卑、焦躁、敌对、依赖等种种变异心理。还有一些年纪幼小的地震孤儿,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孤儿院便统一为这群孩子改姓“党”。但是据知情者透露,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自己祖先的追索之愿也愈加强烈。

第四个问题涉及对死者的殡葬与追念。
其中隐藏着的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个体与国家之间在纪念仪式上的较量与博弈,以及国家在此一过程中的适应与调整。
“入土为安”曾是中国城乡各地最普遍的信仰与风俗,唐山亦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铲除所谓的封建迷信,唐山地区开始推行大规模的殡葬制度改革,要求实行火葬,废除土葬。地震前,市郊的火化率高达80%,各县平均45%。但是始料未及的灾难,打破了常态下的丧葬行为。短时间内土葬数以万计的尸体,迫切需要大量的荒地,家属们为此开始激烈的争夺,甚至发生口角与暴力冲突。此后,为防止疫病,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和防疫部门开始组织清尸队,对浅埋和裸露的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在指定的地点集中埋葬。
这样一种应急性的丧葬形式,对政府此前大张旗鼓推行的文明化殡葬改革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以致在震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形成被当地政府官员称为“土葬回潮”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唐山全市火化率下降到16.5%,迁安、滦南、乐亭、迁西、玉田等五县火化率不足5%。随之而来的还有“看风水、选坟地、搭灵棚、雇棺罩、扎纸人纸马、披麻戴孝、停尸跪拜、焚纸烧香、扬幡招魂”等形形色色被认为“封建迷信”的丧礼程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至此展开了一番新的较量。
对于逝者的追念同样体现了文明与文化及其背后隐藏着的国家与民众复杂的博弈态势。地震那一年的阴历十月初一夜,到处散布亲人焚纸拜祭的点点火光。但是随着唐山十年重建运动的兴起,废墟逐渐被清理干净。唐山人于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十字路口,选好地点,燃一把火,再为亲人送去纸钱,愿亡灵得以安息。年复一年,这种来自不同家庭约定成俗的自发性行为逐渐演变为唐山的公祭日,政府要求每年的这一天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有意义的纪念活动。震区家庭对亲人的追念,在政府的官方塑造下转变为对国家抗震精神的颂扬。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数十万被集体埋葬的死难者家属,越来越不知应在何处祭奠和告慰自己的亲人。为死难者立碑,成为唐山所有幸存者共同的心愿。于是在政府的组织和规划之下,诸如抗震纪念碑、抗震纪念馆、抗震纪念广场等建筑纷纷建立起来,以政府为主导的纪念活动也周期性地举办,以“弘扬抗震精神、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宣传、树立唐山形象”。政府的动员、组织、宣传工作扩大和加强了地震纪念的社会影响力,使地域性活动演变成为受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关心、瞩目的事件。而另一方面,作为平凡个体的“家庭”,在纪念过程中的行为与感受也被官方的“盛大”活动轻易地忽略与隐去。
进入21世纪,官方集体的周年纪念形式再不能够满足普通民众追求尊重个体、回归自我的更高精神追求,很少有人会在纪念日里前往抗震纪念碑前祭扫,人们更加需要的是“真正能走入震亡者亲人的内心”,“与他们的心灵产生共鸣”的空间。2008年7月,镌刻着几乎所有遇难者姓名的“地震哭墙”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初步建成,历史终于还原了每一个二十四万分之一。此时恰好处在汶川大震、举国悲痛之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中国政府的举国救灾体制在唐山地震中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在灾时,在唐山市区夷为平地,社会功能几近崩溃的情形下,使近百万受灾民众得到了快速的人力、物资救援与医疗急救;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承担着“家长式”的义务,持续不断地哺育和关怀着这里的地震孤老与截瘫患者,并且因应民众的要求,对灾后救援与恢复模式不断地进行反思与调试。从最初对生者的救援到今日对死者的追忆,唐山大地震的灾后恢复总算画上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如此长期的社会善后,不仅是中国地震救灾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世所罕见的。
(本文摘自夏明方著《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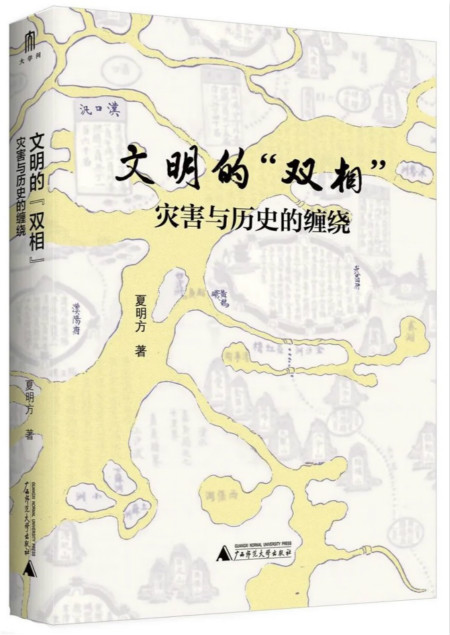



- 谁在把水搅浑
- 服务业扩大开放,多领域明确试点任务
- 中汽协倡议规范驾驶辅助宣传

- vivo新一代旗舰机vivo X200 Ultra发布,6499元起售
- 科大讯飞一季度净亏收窄超三成,2024全年营收重回双位数增长

- 国际东方学大师,精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
- 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有名句“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