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感伤主义的失败:“自我塑造”的努力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崩塌了
【编者按】
一个人内心的情感体验,是某种关系的体现。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阶层的情感表达,都无法忽视社会情感准则的教化训练。《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作为情感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提出了情感表达、情感体制、情感导航、情感自由、情感痛苦等理论,并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研究启蒙时代及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情感表达方式的变化及其意义。本文摘编自该书《现代性诞生中的情感:法国(1680年—1848年)》一节,由澎湃新闻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近年来,出现了颇多关于欧洲早期现代化中的礼仪或礼节的研究。大家虽然对很多问题仍存争议,但已经有一个足够清晰的发展演变表。新“礼仪”规范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王宫,是作为城市公民(或者封建诸侯)的自由同文艺复兴时期暴君的新权力之间的情感妥协的结果。统治者们在王宫中要求他们的贴身仆人所具有的技能多样性与随时服从性,在这礼仪规范中则表现为意味着自由和自我决断的冷漠、放松、优雅,而究其实质,仍是要求顺从的朝臣。事实上,很多人,包括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都视冷漠为一种令人振奋的标准,展示着冷漠精致的宫廷礼仪,肩负着高级官员或外交使馆分派的复杂任务,这构成了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一种道德理想。朝臣们的技艺及顺从看起来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自我塑造”(self fashioning),一个可能使人为之殉难的理想,如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例子一般。
在凡尔赛王宫及那些所谓的君主专制的王宫里,这些局限被尽可能地推演至了极限——或者甚至更离谱。这些君主专制王宫直到17世纪晚期,都视凡尔赛宫为他们的模仿对象。未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英国君主制及1660年以后法国出现的新的情感庇护所,为阐述感伤主义的新情感风格奠定了基础。
到18世纪80年代,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感伤主义都已成为普遍的常识。新的情感观念同新的情感行为同时形成。平等主义口号、共济会团体、深厚的友谊及“书信和国”的通信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从等级森严的宫廷礼仪和公共礼仪中解脱出来的、直接实际的方式。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批评洛克,坚持认为道德感是与生俱来的,并认为道德感是高尚的情感冲动。他对洛克的批评很快被英国与法国的不同的思想家所接受,包括哈奇森(Hutcheson)、马里沃(Marivaux)和狄德罗(Diderot)。随着理查逊(Richardson)及卢梭的小说在18世纪中期出版发行,精心制作的新“市民剧”上映,以及由格勒埃(Greuze)和格鲁克(Gluck)推动的绘画和歌剧的新风格风行,感伤主义理念和实践获得了空前的流行和知名度。如同数以百计的小说所描述的一般——比如《帕梅拉》(Pamela)、《新爱洛依丝》(La nouvelle Heloise)、《保罗与弗吉尼亚》(Paul et Virginie)、《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等,在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中,感伤主义构成了解放的政治和情感意识形态。包办婚姻中配偶的情感痛苦,遭受主人强奸而主人却不受惩罚给家仆带来的情感折磨,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女因财产匮乏而产生的情感痛苦,因财富或出身差异而被迫分离的相爱的人的情感折磨,被父母送到修道院的年轻女性的情感痛苦,孤儿、寡妇及年老的未婚女性的情感痛苦——所有这些政治罪恶都被呈现在热情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读者面前,并由他们探讨和批判。与此同时,绘画、歌曲、戏剧也表达了类似的理念。感伤主义开始改变狭隘的精英内部人士的私人关系,比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Phlipon)和罗兰(Jean Marie Roland)的关系,并开始对更广泛的公众产生影响。
而且,在君主专制国家,感伤主义传达着清晰的政治解放的讯息。在法国,国王的法外权力,比如国王签署的拘禁令、国王的偏袒、奢靡及放荡堕落所体现出的——符合传统贵族礼仪的种种行为——现在则在小说、戏剧、诽谤性的小册子以及律师辩护词中遭到各种批判和谴责。简单、真诚和平等主义同理心的感伤主义理想,是评价君主专制政体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据此,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数年内,人们发现了君主制的不足。到这个时期,卢梭已经告诉了人们如何把感性的情感主义和公民道德相结合,即使是路易十六和他的臣子们也已把自己表现为既对公共负责,又慈悲为怀的人。
感伤主义最大的不足是它的自然主义,即认为情感敏感性构成了与生俱来的道德感。拥护上述学说的人常常用衔情话语来训练自己对强烈的、“自然的”、合乎道德的情绪的感受。他们的成功似乎证实了这种新学说。同情的眼泪、友谊和爱的传递、刻意的朴素衣着和举止,成为有道德的象征。小说、演奏作品、戏剧及朋友间的来往信件,都成为自然敏感性抛洒盈盈泪光的场所。当然,这个学说的一些拥护者比其他人更善于遵守它的规范;而那些不那么信服该学说的人则被轻视或怀疑。结果,18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接纳了这类情感管理模式的人,还是鄙视这种模式、认为该模式带来虚伪的人,数量都有所增加。对美好情感的自然起源的信仰,导致感伤主义者对政治改革有着过分简单化和乐观化的希望。淳朴的农民被认为天然具有形成公民美德的能力。总而言之,改革看起来是为了扫除一切通向自然情绪的障碍,而不是为了建立保护性规范。与此同时,对虚伪的质疑给当时的政治思想蒙上了一层摩尼教的色彩,带来了一种认为善与恶纠缠在一起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启动并着力建立自然情感规则后,在如何区分合理的异议与伪装的邪恶敌意这一问题上,革命领导人面临着巨大困难。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已经随处可见的摩尼教倾向,现如今数百倍地增长着。毕竟,自然的情感应该在好公民之间产生完美的共识。在一个政府和民事立法全面变革的时代,不满的声音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感伤主义的幻象,人们只能以内战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就像战争被某些人宣传为能促进公民天然的爱国心一样。置身于这种阴郁的环境中,即便是那些接受了基本原则、有着值得被称赞的政治英雄主义过往的大革命的领导者们,也不可抑制地因为一些利益或政见上的细微分歧而陷入倾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恐怖统治更像是感伤主义的一种表达,如同格鲁克(Gluck)的眼泪汪汪的戏剧,以及朱莉·德·莱斯皮纳斯(Julie de Lespinasse)或者罗兰的泪痕斑斑的信件。无论如何,到1792年,由对断头台的恐惧而诱发的情感痛苦及一浪胜过一浪的国内冲突,开始逐渐破坏感伤主义者对自我的信心。恐怖统治走到尽头,既是对这个失败的回应,也是对迅速蔓延的对不真诚、不确定和摇摆心理的认识的反应。1794年至1795年间,转化的失败得到了广泛承认。某些感伤主义“话语”开始被视为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这些话语在政治中的使用突然遭到禁止。这是一个无法构建自己世界的话语,“自我塑造”的努力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崩塌了。
伴随着恐怖统治的结束和拿破仑统治的开始,一种人们不曾预料到的新情感政体诞生了。感伤主义学说遭到禁止。人们以毫不掩饰的厌恶态度对待斯塔尔(Stael)、贝尔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 Pierre)及其他人为感伤主义所作的辩护。在先前感伤主义的位置上,很快生长出新的、民主的荣誉法则——并且匆忙同亚当·斯密的自私的、看不见的手达成和解——从而勾勒出一幅新的男性统治公共事务和私人财富领域的蓝图。事实上,情感主义的迅速消失也反映了心理调控的努力,即极力把令人失望的信念和因太痛苦而使人不愿意记住的情感从注意中抹去。如若是这样的话,这些努力的成功在历史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将一直延续到今天。
1804年的《民法通则》为这个新的男性活动的王国提供了法律框架。但是,几乎在书写法律条文的墨迹尚未干时,曼·德·布朗及其他人已经开始对《民法通则》珍视的狭隘利己主义提出质疑,他们推崇一种精神意义上的但又世俗化的人类理性概念。他们相信,如果理性是人性中振奋人心的因素,那么它对人类历史相当有限的影响反映了生理、环境、食欲、想象和激情的巨大的反作用力。理性是微弱的,人类体质是脆弱的。谨慎的“心理”反省揭示了一个包括冲动、情绪、身体影响、恐惧和幻觉的混乱地带。艺术家可以描摹刻画这个地带,可以在私人生活中(谨慎地)追求幸福。但对于涉及财产、商业、政治和荣誉的事物来说,如果理性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运用(而不是辅助性地使用)一定的共鸣式道德感,可以确保其更好地运转。到19世纪20年代,大学开始讲授这类思考方式,类似于《环球报》的这类报纸开始传播这类思考方式,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开始使用这种方式进行辩护,传记及日记撰写者开始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反思和自我反思。由此(无意地)实施的衔情话语训练鼓励了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脆弱的、易变的。然而一旦确认了自己是脆弱的,就很容易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及对屈辱的害怕。在剔除感伤主义后,人们重新认识了启蒙运动及大革命的历史。那些在公共场所展示情感灵活性的男性——尤其是辩护律师和政治家——获得了声望和权威,同时也招致一些人的冷眼旁观,即那些对人类可能性充满新的悲观看法的人。在私人领域,感伤主义理念仍然存在着,尤其在那些有文化的、继续阅读上个时代的著名文学作品的女性那里。虽然被剥夺了知识基础,感伤主义的衔情话语仍然模塑着很多人。乔治·桑试图提出现代感伤主义,以挑战关于人类脆弱性的新观念。她的这一举动得到诸多称赞,但追随者甚少。毫无疑问,对于很多男性来说,要他们承认他们对某些特权的要求是毫无依据的,只会加剧他们个人的脆弱感以及对羞辱的挥之不去的恐惧。
悲观的好处在于降低了期待,提高了对偏离规范行为的容忍度。新的民主荣誉法则的优点在于,它在支持这种宽容的同时,允许任何被妥当掩盖起来的偏差行为。至少,新秩序在这方面更符合我们真实的、伟大的自然遗产——也就是我们的可塑性——这是智慧本身的标志,而不是软弱的标志。对于历史的曲折,衔情话语理论给出了一种逻辑和连贯性,部分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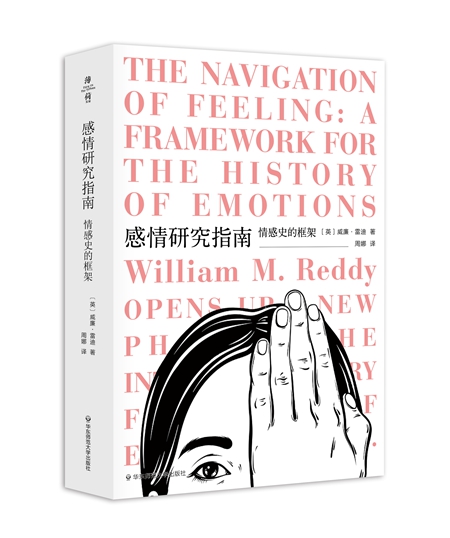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