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刘道玉口述: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口述改革历史》——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这标志着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恢复了大学的教学秩序,也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给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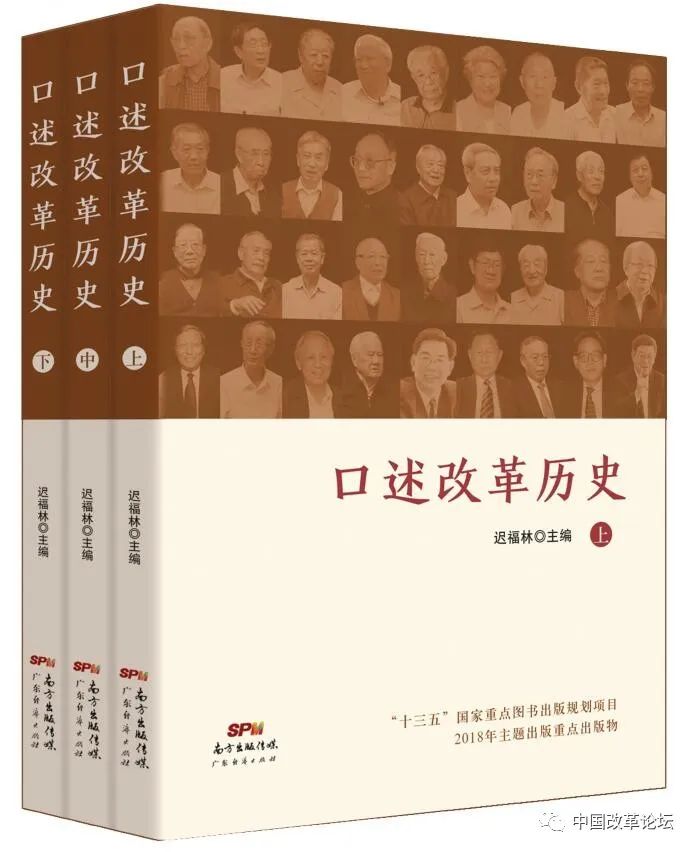
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
2020年高考已启幕。中改院“口述改革历史”人物访谈曾有幸访问亲历恢复高考决策的见证人。下面,我们一同回顾这段历史。
口述者:刘道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

借调教育部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当时拨乱反正的任务有多么艰巨。教育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同时担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刻地感受到基层广大教师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情。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被借调到教育部,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1977年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由于当时我觉得是临时借调,待不了多久,于是就在教育部办公大楼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住了下来。它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室内放置了一张木板床、一副卧具、一张木制的办公桌、两个开水瓶和一个洗脸架。我没料到,一个月以后,中央组织部正式任命我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虽然我极不情愿当京官,但身不由己呀,于是我这一住就住了两年,当了两年的“临时工”。
当时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办公司6个司局单位都由我领导,我负责的范围相当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时候教育部党组11个成员中,只有我是从大学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况。
会议背景和筹备工作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遵循的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各省市和大学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提出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也没有被推翻,这“两个估计”把我们这些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
那时,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打倒的对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决心从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让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他打算召开一个会议,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来在会上他也说了:“请你们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邓小平办公室通知教育部,这个会议要从教育部和科学部各选15个知名专家参会,会议时间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我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高教司司长,受教育部的指派,负责选定名单,初步选拔了16人,最后科学院也选派了17人,总共33人,加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和新闻记者,总共70多人参加座谈会。
当时确定名单的时候有两点考虑:第一,必须要是知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而且要敢于说真话。比如说杨石先是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苏步青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知名数学家,等等。第二,当时我也考虑到名单上还得有一些中青年,遵从老中青三结合嘛,所以一些中青年像温元凯,他当时还是30出头的小青年吧,还有中山医学院的宗庆生等参加了会议。
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秘书组,负责会议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与会代表都是我们两个人通知的,也是我亲自到机场接送的,当然,大部分代表都来自北京,所以我的接送任务也不是很重。
决定恢复高考
座谈会是在8月4日上午9时开始的。邓小平同志作了一段开场白。说实在的,当时这个会议,刚开始大家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心有余悸,刚开始还不一定就敢讲。于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启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他说:“‘四人帮’粉碎了,不会再‘抓辫子’‘戴帽子’和‘打棍子’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经过小平同志的反复动员,大家开始讲话,并逐步活跃了起来。
我记得,首先讲话的是复旦大学的苏步青。他说:“我想不通高教战线17年是资产阶级专政,那我们过去做的工作都是为谁服务的?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做的工作吗?但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他问得很有道理,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怎么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呢?邓小平同志就插话说:“17年是黑线专政讲不通,17年是共产党领导的嘛。”对于这个问题,他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样慢慢地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大家思想都放开了。
北京大学的沈克琦说:“我们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聂元梓在北大挑动群众搞批斗,我们受尽了苦。‘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非正常死亡几十个人,像翦伯赞、俞大絪等,都是知名教授。而且‘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教授都被反复抄家,他们收藏的文物、著作手稿都被抄走了,希望中央能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帮他们找回他们最珍贵的书稿、字画等。”
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研究农药的泰斗,他说:“国家科委的大楼被军队占了,科委都解散了,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科研、没有科委、没了科学,怎么行呢?”他要求尽快把被占的国家科委大楼归还给国家科委,并且要恢复国家科委。讲到这里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插话说,应该收回,国家科委应该恢复。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会上慢慢地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发言也踊跃了。
我作为高教司司长,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有人提到恢复高考问题。在会前我做了调查: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该如何入手?那时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那个时候工农兵学员进校以后都以改造者自居,以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当时的大学招生就是从工农兵里招,有一个“十六字”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说是自愿报名,你报了,领导不批准,有什么用?所以这“十六个字”就变成四个字:领导批准。领导决定一切,导致当时走后门之风猖獗,领导要谁上谁就上,不让谁上谁就不能上。举个例子,有个著名作家熊召政,1976年时他是湖北英山县的一个知识青年,群众已推荐他上大学,但是到了县里,县委书记不同意:“你明年去,今年我儿子要上。”当时就是这种情况。会前我到沈阳、天津做调查,后来到了顺义县,该县革委会姜副主任对我说:“现在大学虽然恢复了招生,但我们工农子弟仍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十六字’招生方针,就是开后门的方针,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恢复高考,我们工农兵子弟不怕考,不信你查一查‘文革’以前,上大学比例多的还是我们工农兵子弟。”
是的,我上大学那会儿,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要占70%左右。当时大学招的工农子弟文化程度严重参差不齐,大多是初中毕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高中生极少极少,因为高中生都下乡了。当时说“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所以大学教学就没办法教了,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培养出合格人才的。所以我一直记住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一定要恢复高考。
但会议开了两天了,没有人讲到这个问题。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副教授晚上来找我,他说:“我坐了两天了没有发言,一直在听,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讲什么好。”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因为我们都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师,我又是会议秘书长。我说:“虽然大家都讲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没讲到,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针,恢复高考的问题。”其实当时提这个问题是非常冒险的,弄不好就要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因为“两个估计”还没被推翻。但是我这个人历来胆子很大,我敢说。我说你就讲这个问题,他同意了。
当晚,查全性副教授做了认真的准备。他发言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大学是靠钱,“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说“学会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大家纷纷发言,像吴文俊、汪猷、唐敖庆等都表示附议。
当时刘西尧是教育部部长。邓小平同志问他:今年恢复高考怎么样?刘西尧说,要改就得推迟,现在是8月6日,当年6月29日到7月15日的招生会已经在太原开过了,还是按照“十六字”方针布置的,招生报告已经给国务院送去了。邓小平同志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教育部说那我们今年就改。
全国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
8月13日,当年全国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到9月25日结束,开了44天。在会议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邓小平于9月19日再次找刘西尧等人谈话,要求教育部争取主动,尽快结束招生会议。这是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第二次拍板,说明当时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1977年,我们是恢复“文革”以前的高考,完全按照“文革”前的做法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录取分数线。恢复高考,重新招生,但当时我们的教学计划还是针对工农兵的,教材都是为工农兵大学生配备的,统一高考招进来的学生不能再用一样的教材了,怎么办?我就给党组织提出建议,说必须马上召开一个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重新研究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不然统一招进来的学生我们没办法授课。当时时间很紧,我提议马上向国务院报告。国务院也很重视,说这个会很重要,安排我们到北戴河国务院招待所开会,这个招待所在“文革”中被当作“封资修”的安乐窝封存了,我们亲自启封,打扫卫生。
这次会议要形成恢复高考以后的招生工作计划和教学大纲,当时我们怕控制不住,意见不能统一,就只通知了15所学校参加,再加上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两个教育研究所,一共35个人参加。8月12日至18日正式开会,恰好与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一天开始和结束。
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思想。制定新的教学大纲必须肃清“左倾”思想流毒,坚持“三基”和“四性”,最后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满意的《会议纪要》。座谈会结束当天,我们与北戴河镇的居民一起上街庆祝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最后通过的那个教学大纲,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意义和感触
据统计,1977级、1978级总共招了60多万名学生。当时在农村还有860万名知青,很少数的幸运者才能够被录取上大学,这些都是真正的佼佼者。20世纪80年代学校的风气好得很,不是“你要我学习”,是“我自己要学习”,没有考试作弊的人,都是自觉地考试,自觉地要学习,因为上大学是很艰难才得到的权利,他们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觉得恢复统一高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一个意义,虽然它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在“两个凡是”“两个估计”没有被推翻的情况下,能够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那是了不起的。
第二个意义就是拯救了一大批知识青年,他们现在绝大部分都成了国家栋梁,成为学术界、政界、经济界、企业界的骨干。我们武大有位一级教授、著名数学家叫李国平,他的儿子是知青,招工到武汉市当理发员都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在农村没饭吃、吃不饱啊,回来就是当理发员,他还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参加了1978年高考,被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现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有个学生叫谢湘,后来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部主任、副社长,也是1977级的学生。她返城后是襄樊市纺织女工,当个女工都高兴啊,她妈妈要她参加高考,她坚决不参加:“我不参加,我做女工很好,我是工人阶级。”而且她当时准备提车间主任,她都不想高考。她妈妈亲自跑到襄樊棉织厂,说:“你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不考就不是我女儿。”强迫她考,最后她考取了,考到了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青年报》,一直升到副社长。要是没有高考,这一批人就被埋没啦。所以我开玩笑说:恢复高考招收了1977级、1978级、1979级的学生,他们就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将来一定能够担当大任。
第三个意义,恢复高考使社会风气、学习风气焕然一新,这是无法衡量的重大意义,把过去的“读书无用论”“教书倒霉论”一扫而光。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很多教授,都把书当废纸卖掉了,认为这一生不可能再教书了。虽然我的书没卖也没烧,但是我也准备改行学木工手艺了。恢复高考以后,大学里进了一批高中、初中文化的学生,教师不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是不能教他们的。所以,教风学风焕然一新,老师们上下班都是跑步前进的,实验室的灯光昼夜通明,大家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甩开膀子大干,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全部抢回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所以说,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教育受灾多么严重;没有经过拨乱反正,就不知道拨乱反正多么重要。我对改革的情结这么浓厚,原因就在这里。
(本文原题为《口述改革历史|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作者刘道玉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选自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编的《口述改革历史》一书,微信首发于公众号“中国改革论坛”,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