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考古学家柴尔德:谜一般的人物
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于1957年逝世,享年65岁。然而,对于他的遗产,仍不能如考古学教科书对已经作古的学者所做的评价一般,用习见的方式加以总结。许多认识他的同僚,仍然和以前一样,要么把他看作一个充满灵感的人物,要么认为他走火入魔,中邪太深。在年轻一代的英国考古学家眼里,他既是一位想要叛逆的严父式人物,又被尊为羽翼丰满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权威。他浩瀚渊博的著作,以重点和方向的多变著称,而由于不同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被同时代的考古学家所充分理解或接受。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对于他的著作意义所持的争议,愈加热烈。虽然,就时间上说,我们离柴尔德还是太近,而无法全然不带感情色彩地评价他的著作,但是,我们能够开始对其具有世界意义与持久影响的理论基础做一番审视。
柴尔德于1892年4月14日出生于澳洲悉尼。1914年自悉尼大学毕业后,转赴牛津大学求学。因为受到亚瑟·伊文思爵士(Sir Arthur Evans)和约翰·迈尔斯爵士(Sir John Myres)的影响,他的兴趣由古典哲学转向史前考古学。两年之后,他回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参与了左翼政治活动,并一度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的私人秘书。1922年,他对自己祖国的政治感到幻灭而回到英国,并靠翻译、兼任教职以及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工作为生。但是,他的大部分心血都投入东南欧的史前研究上。1925年,他出版了《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翌年,它的姐妹篇《雅利安人》(The Aryans)问世。
1927年,柴尔德就任爱丁堡大学新设立的考古学阿伯克龙比教职(Abercromby Chair)。于是,他成为当时英国仅有的几位专业考古学家之一。紧接着,他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奠定了他在欧洲和近东史前史的专家地位。
这些著作包括1928年出版的《最古老的东方》(The Most Ancient East),1929年出版的《史前期的多瑙河》(The Danube in Prehistory),1930年出版的《青铜时代》(The Bronze Age),1934年出版的根据《最古老的东方》修订并多次再版的《最古老东方的新认识》(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1927年以后,为了对他第二故乡的史前史有更好的了解,他也参加了苏格兰许多地点的发掘,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Scotland)。
1930年代,柴尔德对文化进化论的研究兴趣日增。这种兴趣在他最畅销的两本书《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1936)和《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2),还有两本比较专门的著作《进步与考古学》(Progress and Archaeology,1944)和《苏格兰人以前的苏格兰》(Scotland Before the Scots,1946)中体现出来。在这些著作中,他试图从文化发展中描述各种规律。他希望借此有助于对欧洲过去的一个空白阶段提供一种较为均衡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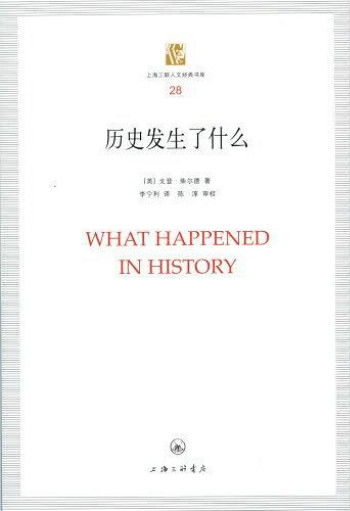
1956年,柴尔德从考古研究所退休,并于次年春天,在离家35年之后回到澳大利亚。同年10月,在攀登悉尼附近的蓝山(Blue Mountains)时坠崖身亡。
柴尔德的声望
在1920年代,柴尔德根据他对欧洲史前史,特别是公元前第二和第三千年的系统研究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他对这些材料的综述为一代乃至几代欧洲考古学家开启了如何对其进行研究的先河。在《人类创造了自身》出版之前,对柴尔德著作的了解主要限于欧洲考古学家。之后,他从一种唯物主义或理性-实用主义观点为近东文明发展提出进化论阐释,从而赢得了一种颇有争议的和世界性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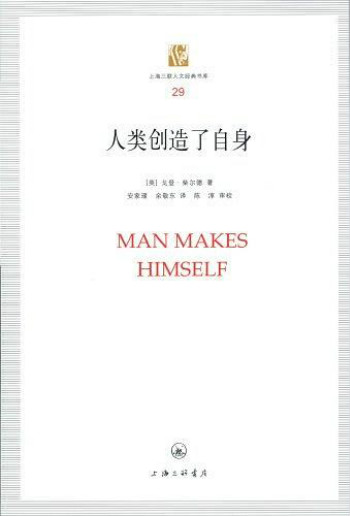
同辈考古学家尤其折服于柴尔德对欧洲和近东考古材料的详细了解。为了获得这方面信息,柴尔德经常周游欧洲,造访博物馆和发掘工地,借以积累专业知识和心得。他具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敏锐记忆力,这使得他能够从相隔遥远的区域器物中发现共性,而这种共性为那些地方专家所茫然不知。他有阅读多种欧洲语言的能力,以在各种无名杂志里辛勤寻找材料,并在他《欧洲文明的曙光》的各修订版中引用而著称。欧洲考古学家对此也十分了解,把自己的著作寄赠给他。斯图尔特·皮戈特教授声称,柴尔德最终将此视为不只是一种尊重更是一种权益,是对一名学者卓越成就的应得回报。
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柴尔德为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提供了他所发现的对他们自己材料分析有用的想法。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离世引发了考古学界前所未有的悼念和追思浪潮。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称赞他是“我们时代顶尖的史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界极少数最伟大的综述者之一”。在英国,皮戈特克服了英国人的谦逊,形容柴尔德是“英国也可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前学家”,而一位顽固的人文主义者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声称,柴尔德使得“对人类的研究几乎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被这刚愎自用的科学所承认”。在其故乡澳大利亚,柴尔德被形容为“可能是最高产和被翻译著作最多的澳大利亚作家”。他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捷克文、丹麦文、法文、德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
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从一种历史视角观察柴尔德工作各个方面的研究。这就使对他的了解变得很有必要,因为自他去世以来的时间流逝,已经能使今天大多数考古学家自动排除从其原始背景来看待他的这些著作。反而他的观点因为与当时的争议有关而有一种被断章取义地引用或加以谴责的倾向。彼得·盖瑟科尔提醒我们,这样一种做法“有将历史仅当作虚构来处理的危险或予以认可或加以嘲弄……以便证明时尚态度的正当性”。
本研究并不关注柴尔德对特定考古材料的阐释,而是聚焦造就了这些阐释的思想。其各个时期的思想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过,柴尔德思想的发展有足够的连续性,而为了便于人们了解他一生的工作,任何将其归于刻板阶段序列的做法是高度主观性的。我们无法将其思想以一系列范式的彼此取代来进行解释,一如托马斯·库恩(T.S.Kuhn)描绘的一种科学学科发展的特点。
塑造一位社会科学家思想的那些影响的复杂性确保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是一种线性的过程。在某特定时段看似重要或有吸引力的许多思想,从长远来看会证明是错误的或毫无价值的。然而,思想的发生从塑造考古学理论的长远发展而言,只不过像突变单独对某生物物种发展所起的作用。考古学家最终会根据他们解释体量不断扩增的考古材料的功效来判断这些思想。这个选择过程有助于他们克服一时的错误和时尚,并发展一种累加的理论实体,以便增进和扩大对过去的了解。在不同考古学传统中常见的理论趋同,见证了这一过程的力量和必然。任何对柴尔德思想的评价必须考虑,在何种程度上,他改善和扩展对考古材料理解的能力,与其时代的总体发展同步或比其超前。这一分析必须考虑当时他所能获得的不断增加的材料,以及他所掌握的发现和分析这些材料的方法。
我们将从观察柴尔德思想的缘起,以及这些思想如何被他所修改,并形成较宏大的理论性系统陈述,并具有令同时代考古学家信服并获得启发的能力开始。那时,最重要的源头,特别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是高度成熟的西欧考古学传统。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它已经作为一门科学学科而确立。他的研究和著作主要采取的形式就是为这个传统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来自苏联考古学、美国人类学,以及其他关系较为疏远学科思想的影响。他对哲学和政治学有一种附带的兴趣,并比他同时代考古学家更加关注证明考古学的社会价值。他的思想过程也明显受到他对当时社会和经济问题所做出的个人反应的影响。
争议
考古学家对柴尔德工作不同方面的相对重要性一直有不同意见。许多英国考古学家视其理论除了为其解释欧洲史前史的主要工作构建了主要框架之外没有什么意义。皮戈特把他形容为“一位伟大的综述者和系统分类者,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将整个欧洲史前史领域掌握在一个学者脑子里的人”。在其他地方,皮戈特谈道,“对于专业考古学家来说,柴尔德首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年代学框架构建者,他能够以学者的条分缕析来俯瞰欧洲全景,并总是能从考古学细目的史前密林中分辨出树木”。这种观点与传统历史学家如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相一致,后者认为事实是构建他们这门学科的坚实核心,而阐释被认为与个人观点无异。其他评论者如埃莉森·拉弗茨(Alison Ravetz)和彼得·盖瑟科尔同意柴尔德在自己学术生涯之末所下的结论,即他对史前学最有用的贡献是“阐释的概念和解释的方法”。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持中间立场。他称赞柴尔德“根据对具体文化组合的详细研究和非常清晰的方法论,用一种宏观调查取代了民族主义有限研究争论不休的矛盾”。伦福儒以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对柴尔德的成果进行再阐释,其本身就是对柴尔德工作持久意义的证明。
与他们的观点相同,柴尔德对区域史前史的综述构成了他一生工作的核心,有些英国考古学家对其著作做了区分:技术性著作,主要针对学界同行;其他不太重要的推理性著作,主要针对大众。大部分技术性著作被等同于他的区域性综述,《欧洲文明的曙光》就是这类综述的祖型(archetyp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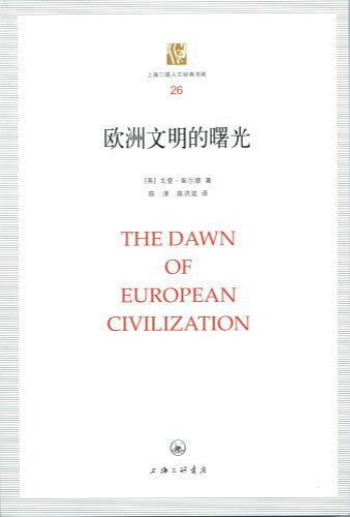
对于哪些书属于通俗一类也存在分歧。大部分考古学家同意,《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属于这类;格林·丹尼尔添加了《社会进化》,而皮戈特添加了《进步与考古学》、《历史》与《欧洲社会的史前史》。拉弗茨十分正确地声称,柴尔德的“小册子”不是对他区域性综述的普及,而是他另一种学术性的表现。丹尼尔承认这点,他把《人类创造了自身》、《历史发生了什么》和《社会进化》形容为“本世纪迄今为止史前史宏大综述最重要的著作”。柴尔德的著作如不考虑这两种题材就无法予以了解。
美国考古学家对柴尔德的思想做了一种相关的二分。罗伯特·布雷德伍德声称,“如要了解这个人,就有必要强调柴尔德在人文学科的早期训练,以及他早年对历史唯物论的期许”。欧文·劳斯(Irving Rouse)说,“在柴尔德的兴趣与学术方法中有种尖锐而冲突的二分,这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他认为,一方面柴尔德是一位人文学者,比他同辈的其他学者更好地利用了归纳法,从历史学观点来对考古材料做出综述;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进化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令他在撰写理论著作时,从辩证唯物论的立场来解释这些材料。劳斯认为,在后来的研究中,柴尔德采取了演绎法,这包括假设某些理论是真实的,并选择考古材料来加以说明。他有这样的看法,即柴尔德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无视与他理论相悖的事实。
对他英国的考古学同人而言,“柴尔德最大的谜团是,在何种程度上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苏联,对他的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看法。《苏联大百科全书》称赞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考古学家” ,而考古学家亚历山大·蒙盖特(Alexander Mongait)在他题为《资产阶级考古学的危机》的演讲中,坚称柴尔德没有成功“克服资产阶级科学的许多错误”,即便“他了解科学的真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并恬不知耻地自称为苏联考古学家的学生”。实际上,蒙盖特将柴尔德归入受人鄙视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者之列。拉弗茨认为,当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古典主义学者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批评柴尔德没有把阶级冲突看作社会革命的一个基本要素时,他表达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柴尔德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因为他偏离正道,努力不够” 。但是,《古与今》(Past and Present)的主编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断言,柴尔德在他的考古学著作中曾设法“塑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力也许没有白花。柴尔德在牛津时的好友帕姆·达特(R.Palme Dutt)说,柴尔德一直“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心系魂牵”,并声称正是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得他成为他的时代顶尖的考古学家。
盖瑟科尔同意达特的意见,即马克思主义是柴尔德第一本书中“贯穿始终的学术力量”,这使其著作成为一个逻辑整体。不过他认为,当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完善时,他以一种令人失望的有限方式,就用这种理解作为解释欧洲史前史的一种工具。盖瑟科尔特别指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强调科学知识的客观作用,柴尔德开始偏离了较为灵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种辩证互动。马克思本人从未厘清技术和社会互动形态之间的关系,而任何社会都是以这种关系来生产社会成员生存所需的东西。然而,他视“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了每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在政治、法律和宗教上的表现形式。拉弗茨在柴尔德19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较晚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区分,她认为前者以一种天真、乐观和机械的理解为特点,而后者较为巧妙和原创。她说,在该时期的著作中,柴尔德意识到不大可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现成地用于考古材料,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考古学事实之间开启一种较有成效的对话。拉弗茨将此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其意义并未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拉弗茨似乎将柴尔德的著作视为当时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较为自由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表现。
大部分认识柴尔德的英国考古学家,倾向于降低马克思主义在其著作中的重要性。惠勒说,马克思主义为柴尔德的阐释增色而非造就了这种阐释。皮戈特认为,柴尔德不时地尝试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看作是或许能证明对了解过去十分有用的模型。他也认为,“这位腼腆、理想主义和别扭的”澳大利亚年轻人很可能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的蓝图,其中知识分子享有一种光荣的地位,而里面的一位“外来者”会比较容易地承认其权威。尽管如此,皮戈特还是将柴尔德的大部分专业兴趣说成是一种“复杂的智力笑话” 。格林·丹尼尔承认,柴尔德充满情感和严肃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探索,以寻求考古学问题的答案。但是丹尼尔也指出,在他生命的终点,柴尔德对苏联考古学的学术性变得更具批判性,并认为这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厌倦。丹尼尔告诫说,因为柴尔德在政治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推测他在考古学上必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错误的。
格拉厄姆·克拉克对柴尔德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看法不以为然,并就这种立场对他著作的影响提出了有力的否定意见。他声称,马克思主义被柴尔德用于考古学后,在他中年严重影响到他的学术工作。只是到他生命的终点,柴尔德才意识到“他的主张欺骗了他”,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文化过程。然而,克拉克所说的表明柴尔德对马克思主义的幻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指苏联语言学家和史前学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cholai Yakovlevich Marr)的学说,1950年斯大林对马尔进行了公开的批判。
当柴尔德的工作成果斐然时,就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意见。劳斯显然认为,他的功力在去世的时候达到了巅峰,而拉弗茨认为他最后几年的工作是极具创造力的,如果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十分成功的话。克拉克说,柴尔德的创造性阶段在1930年已经结束,他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深陷马克思主义而日趋衰微。马尔瓦尼(D.J.Mulvaney)否认,柴尔德1936年之后的文章大体上都是对老的论题进行修改或完善。而盖瑟科尔则认为,他1950年以后的著作因为拒绝考虑大量的考古学和民族志信息而存在瑕疵,他本应该用这些信息来检验他的假设。
其人其事
虽然柴尔德是一位高产作家,但是对于传记研究而言,他是一个棘手的话题。他显著的深藏不露、不愿透露其个人意见和反应,以至于在传记问题中进而对他学术生涯评估的关注甚至都产生了问题。柴尔德对他工作仅发表过两篇很短的评价如盖瑟科尔所见,“过于约略,无法给予读者有关他想法比惊鸿一瞥更多的线索,而这已经快接近他生命的终点”。其论著及大部分考古通信的非个人性质,赋予了蕴含其个人观点的罕见表达以特别的重要性,就像他专著中的引人注目——常常是暧昧的点睛之笔。这表明,不管我们对其个人信仰和感情知道得如何之少,但是将柴尔德简单看作其工作的具体表现是不对的。
对于柴尔德所谓的腼腆、社交上的笨拙以及缺乏亲密朋友的传闻很多。斯图尔特·皮戈特对他的外貌着墨尤多,柴尔德本人对此否认。而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很不友好地形容他是如此丑陋,以至令他看一眼就感到痛苦。澳大利亚作家杰克·林赛(Jack Lindsay)觉得他的外貌“古怪而讨人喜欢”,并同时认为这可以说明他的含蓄。但是,格拉厄姆·克拉克对这种推测表示怀疑,指出柴尔德“就像其他男人一样喜欢照相”。皮戈特认为,柴尔德个人和学术关系被这样的事实而弄得有点复杂: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在英国是外来者。克拉克和盖瑟科尔将他与欧洲的学术及感情牵连说成是对他澳大利亚籍贯的一种逆反。然而,林赛对柴尔德的描述认为,他的个性早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就已形成,他是在1921年认识柴尔德的。
最近,格林·丹尼尔对柴尔德是一个怪人和没有朋友的看法做了及时的纠正,他说“柴尔德是极为友善的人,很好相处,很会享受美好的生活以及许多认识和喜欢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友谊” 。莫蒂默·惠勒也同样提到了他一贯和友善的热情好客。虽然柴尔德常常被看作是一位特别不善演讲的人,但是当研究生来找他时,他在时间上十分慷慨,在考古所的研究生中深受爱戴。在苏格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他和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在国外旅行中,他求助外国同行,并和他们交朋友。他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柴尔德都能使自己融入各种场合,并为他的雅典娜俱乐部会员身份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听戏剧、参加音乐会和打桥牌,并在朋友和学生陪同下远足和开车。虽然柴尔德远离政治,但是他小心谨慎地服务于各种杂志和协会的委员会。尽管他避免个人关系过近的纠缠,但是他显然不是愤世嫉俗,对社会的热情和责任也并非无动于衷。
虽然柴尔德十分明白他作为一位学者所取得的声望,但大部分认识他的人都因为他的低调谦虚而对其印象深刻。这种性格也许可以解释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还有就是他深受诟病的不修边幅。然而,柴尔德的谦虚被他无处不在的幽默感所补偿,从狡黠到滑稽模仿。他看来十分欣赏自己所穿的破旧而古怪的衣服。他曾穿着短裤冒犯过苏格兰人,并因身着澳大利亚宽檐礼帽和飘逸斗篷而让芝加哥公交司机大吃一惊。有一次他告知布雷德伍德,他所穿的破裤子是他二十年前在访问贝尔格莱德时所买,并想知道式样是否还行。
他对自己的寓所也毫不在意。因为与他同名,他明显对爱丁堡那家阴暗的“维尔旅馆”(Hotel de Vere)十分心仪。在伦敦,他挑选了一处名叫“莫斯科大厦”(Moscow Mansion)的公寓楼居住了一段时间。从1927年到1946年在苏格兰工作期间,柴尔德把自己当作一个本地苏格兰人那样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惹恼了那些反对任命一个外国人当爱丁堡大学考古学主任的人。他也喜欢炫耀自己的左翼兴趣,在信件上用西里尔字体签名,在漂亮的旅馆里索取《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并在他办公室里展示这份报纸,在公开演讲里引用斯大林语录。这些做法大体被说成是用一种顽皮的方式来吓唬中产阶级的朋友和听众,但也有人认为,这也很可能是故意所为,企图来掩饰自己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严肃性,并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社会影响。更有可能的是,这种举动只不过是他学术上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真实反映,基本上并不带什么政治(因此无害)性质。
柴尔德的同时代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是如何将这种玩世不恭延伸到考古学写作中去的。有人认为,《苏格兰人以前的苏格兰》中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是被设计来诋毁苏格兰古物学会的听众,并在苏格兰人中制造分裂。皮戈特说柴尔德把这样做看作是一种刺激的智力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容易让那些并不认为这是游戏的人感到困惑。
柴尔德对他的观点显然并非采取同等严肃的态度。他为某些人献身,对某些人试试分寸,并很可能仍然拿某些人开玩笑或认为他们有点古怪。然而,甚至今天的考古学家仍无法对他的各种观点归入哪种范畴而达成一致。虽然以比他对待自己更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是不对的,但是猜测他对我们所不赞同的观点不够严肃也是危险的。一个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确定他的哪些观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受到青睐,而哪些观点在他的著作中意义短暂。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将努力追踪柴尔德较为重要的观点在他学术生涯中是如何发展的,并依此来确定这些观点的长远意义,以及它们在不同时期里的相互关系。
最后,我试图对柴尔德著作仍能对考古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做一评价。这需要仔细厘清影响柴尔德最后思想的那些原则,以及我认为是最成熟的状态。他的后期思想没有详细地应用于欧洲史前史的特定问题,这掩盖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在此时,柴尔德发展出一套十分完整的概念,从许多重要方面预见了1960年代初以来在美国兴起的新考古学的一些原理。但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应与盲目信奉政治教条相混淆),令他采取了与新考古学直接相悖的立场。而这对于什么是考古学或它应该怎么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点仍然是柴尔德思想争议尚未探究的领域,并仍然是对考古学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本文摘自布鲁斯·G.特里格著《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何传坤 、 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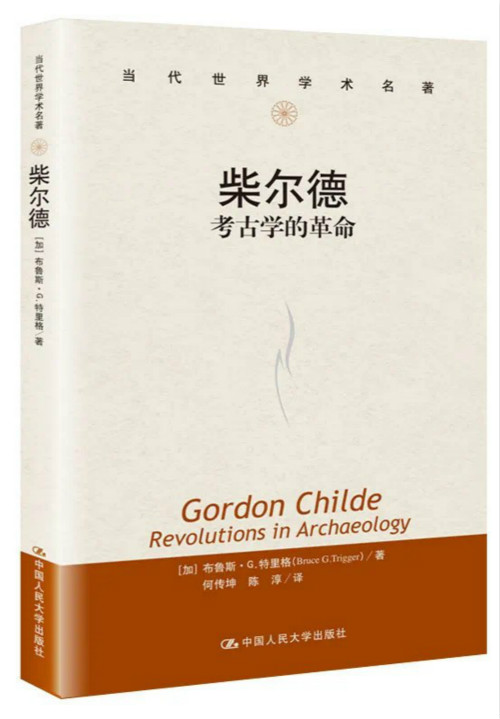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