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修志评《皇帝的四库》︱十八世纪中国的皇权与“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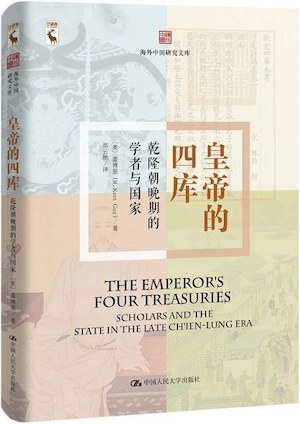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呈现出“溯流而上”和“由外而内”的变化。受“教父”费正清的影响,学者们从关注近现代中国到关注清代中国,六七十年代主要关注十九世纪,侧重清朝与西方相遇后的历史,确立了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解释模式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二分法。但到八十年代,受亚洲崛起和西方学术风气变化的刺激,学者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野有所转变:一是延伸触角,开始关注十九世纪之前的历史,即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前的历史,以更好地衡量清朝面对西方的实力和现代转变,如美国权威杂志《清史问题》1965年创刊,英文原名为“Ch’ing-shih wen-t’i”,1985年开始更名为“Late Imperial China”;二是转变视角,开始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来阐释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且受欧洲“年鉴学派”的影响出现社会史的转向,从关注中西交流转为研究中国的内部结构,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1984)、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80)。由此,十八世纪的康雍乾时期成为美国清史研究的热门时段。
正是在如此学术激荡之中,1981年,哈佛大学博士生盖博坚(R. Kent Guy)写完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学术:〈四库全书〉编纂的政治意义》,1987年改名为《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出版,1989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二十世纪前“佳作奖”(Honorable Mention),可见其受评价之高。根据笔者的阅读印象,此书屡被北美学者如艾尔曼、韩书瑞、罗友枝、柯娇燕、罗威廉、卜正民、欧立德、张勉治、梅尔清、周绍明、何伟亚、白彬菊、包筠雅等在各自代表作中重点引用(梅尔清称此书是“对《四库全书》编纂的里程碑式研究”),俨然已成为欧美研究十八世纪和清代中国的必读书。2019年,此书由郑云艳翻译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盖博坚的“知识分子之问”
《四库全书》是古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从开馆编修到七馆校勘完成共耗时二十多年。但从晚清到当代,后人对《四库全书》毁誉参半,在认同其价值的同时,也批判其作为清廷实施高压统治和思想控制的工具,因为《四库全书》在征书和纂修过程中,伴随着因满汉矛盾而起的禁书毁书和文字狱运动,充斥着对“违碍书籍”的审查销毁、对“反动言论”的钳制惩罚和对士人的威胁迫害,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乾隆帝修四库是为了发起“文字狱”。应该看到,晚清以来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与不同时代的现实情境和革命话语紧密相关,承担着反满运动和反封建任务。从晚清俞樾、章炳麟到近代萧一山、鲁迅、吴晗、郭伯恭、钱穆等皆激烈批评《四库全书》而导致的“总检查”“古书亡”“愚天下”“寓禁于征”等后果。到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学界开始反思以往评价,认为不能简单从政治压制和思想控制分析《四库全书》,最近宁侠澄清了以往“寓禁于征”的观点不切于实情。但中国学者多从文献学角度研究,限于主题和方法,在具体论述上仍不免乏力。
为何选择《四库全书》作为研究对象?怎样破除以往学界观点的笼罩?盖博坚在《皇帝的四库》开头自云此书选题受到俄国历史的影响,因为“知识分子”一词,是在俄国历史上被创造出来描述那些反对国家和批判现实的学者的,他们与国家之间有种疏离感,但是清代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吗?他们对清朝的态度如何?《四库全书》是一个考察学者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窗口,因为在此工程中,乾隆帝、皇室成员、军机大臣、地方督抚学政、三百多位优秀学者、不计其数的藏书家、三千多抄写人员通力合作,为考察学者与政府关系提供了充足而有效的样本。可以说,《四库全书》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乾隆帝作为主持人,以皇权和国家的名义将当时代表性的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联合起来。
盖博坚《皇帝的四库》在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上对以往研究发起挑战,聚焦于清修《四库全书》体现的学者与国家的关系,强调清代权力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多维性,试图纠正以往学界认为《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体现皇权专制和思想控制的刻板印象,可谓翻案之作。笔者认为该书触及的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尤为引人深思。
清代学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四库全书》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活力,满足了各种不同的关注点,体现了皇帝、官僚和各种学者的利益诉求。纂修四库由朱筠倡议,为清代学者文人提供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空前文本资源和学术评价平台。朱筠建立了一个包括官僚和学者在内的网络,大批汉学家出自其门下和幕府,盖博坚认为朱筠建议修书也是为这些人才寻找出路,“朱筠和他的朋友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四库全书》项目,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希望利用该人际网络关系”。当时最杰出的一批学者担任了四库馆臣,如纪昀、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王念孙、任大椿、程晋芳、姚鼐、翁方纲等。而针对与《四库全书》关系密切的文字狱,盖博坚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学者文人也主动助澜了文字狱。因为文字狱早期多是由知识分子内讧引起而由朝廷最后裁决,受到地方士绅官僚报复、官员仕途升迁、督抚应付中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该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且乾隆帝更为关注的是反满文献对清代初期的历史书写问题。这与乾隆在后期担心满汉党争、满族被汉化、维护满族主体性等情势有一定关联,关于这一点,美国“新清史”学者如柯娇燕、欧立德在其作品中多次强调乾隆对满族主体性的重视。从这一角度来说,在利用文字、图书来探求获取思想合法性来源上,乾隆帝和清代汉学家颇多暗合。因此,作者更强调学者文人在《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中的主动性角色而非受害者角色。

无论是《四库全书》还是文字狱,其实都延续了传统中国皇权与学者的合作关系,盖博坚认为:“中国国家在学术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事实上,这种角色是中国传统国家的本质。”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指出,只有地方精英将国家制度与精英们的自身网络结合起来,国家目标才更可能得以实现,国家也必须与地方精英合作,其实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的默契合作在清代也是如此。从这一点来说,乾隆帝通过修四库和文字狱,是在利用文字来凸显合法性及加强与学者文人的合作,更多地继承了以往各朝的统治手法并加以强化成为集大成者,而非凸显了“新清史”所谓的满族特性。魏斐德《洪业》和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阐释了顺康雍时期政府与学者的紧张磨合关系,而到了乾隆时期,无论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揭示士林精神世界在皇权设计下出现变异,还是罗威廉《救世》分析以陈宏谋为代表的汉族知识精英已积极经世,总体来说学者文人与政府已自然达成合作关系,十八世纪的治理制度已经成熟并走向倦怠。
皇权在清代汉学中的角色
如何认识皇权在清代汉学中的角色?或具体言之,乾隆帝在“汉宋之争”中的角色是怎样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四库馆就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因此,乾隆帝主导的《四库全书》既是汉学(考证学)推动的结果,也是汉学进一步繁荣的原因,这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余英时所言从“智识主义”到“文本主义”及艾尔曼所言“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但清廷崇奉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却在官修《四库全书》中遭遇挫败,这肯定是朝廷和学者共同合作的结果。学界常聚讼的两个问题是:清代汉学的兴起是基于“内在理路”还是“外缘影响”?乾隆帝是否怀着帝王心术而有意利用《四库全书》怂恿“汉宋之争”?
应该看到,一方面,清代汉学兴起有一个自然演进过程。清初学者反思明亡教训,出现了经世思潮和余英时所谓“清代儒家知识主义的复兴”,刺激了重构古典儒学的考证学的兴起。艾尔曼指出,十八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江南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到了十八世纪晚期,考据学家基本接受惠栋提出五经比四书更具权威性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没有官方的默许和鼓动,清代汉学不可能公开怀疑宋儒。钱穆指出清廷“利用了元明以来做八股应举的程朱招牌,他们绝不愿学者认真效法程朱,来与闻他们的政权”。因为真正的程朱理学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君臣共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这恰是乾隆公开批判的:“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据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统计,乾隆在三十二次经筵讲学中,有十七次质疑朱子。夏长朴指出,乾隆帝认为南宋以来宋学的讲学、结党的流弊影响政治安定。既然庙堂之上的皇帝质疑朱子,那台阁之中和江湖之远的官僚和学者也会效仿了。显而易见,虽然《四库全书总目》声称“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但对宋学颇多批评。杨念群认为考据学的兴盛是乾隆有意设计的结果,体现了清廷严酷而高超的政治控制。张循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和颁行这一事件就像是一座桥,把官方统治学说的调整和士林学风的变化连接起来了”。但正如盖博坚不断揭示十八世纪的复杂特征,我们更应采用多元交融而非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即皇权确实在学术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仍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盖博坚认为,与其关注清代皇权对学术的约束,不如研究和评价清代学者如何在政府约束中取得的成就更为切实。
清代皇权的本质和限度
作者通过《四库全书》和文字狱着力考察皇权的本质和限度,一方面,政府和学者的合作共同烘托了皇权,历来“统治艺术和著述艺术是同步发展的”,另一方面,皇权虽是合法性的中心,但朝廷威望是通过官僚实践达成的。乾隆帝通过军机处选拔馆臣和编修人员,通过地方督抚采集和审查图书,必然在十八世纪多元化的社会中遭遇阻力。我们应该看到,除皇帝外,参与纂修《四库全书》的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结成一个包括军机大臣、满汉官员、地方官僚、学者文人、地方士绅等在内的诉求网络,每种角色既多元又不断变化。在修四库和文字狱的过程中,监督和奖惩体现了清朝行政管理的特点,乾隆帝看重的不仅是完成工程和处理案件的结果,更是官僚和督抚在执行命令的态度和效率,所以修四库和文字狱恰成了乾隆考评和支配官员的一个契机,证明了清代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皇权的局限性。
孔飞力在经典著作《叫魂》中指出,清代“官僚君主制”的内在机制要对叫魂危机此类“事件”进行加工,转换为权力和地位,对君主来说,他可以塑造、界定甚至制造“事件”,需要具体的机会强调对官僚的支配,增进自己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修四库和文字狱也是一种“事件”和“机会”,既考验着士人的忠诚,又考核着官僚的效率,体现出清朝行政管理的特点。盖博坚着重探索了军机大臣如刘统勋、于敏中、和珅在修书中的角色,一方面,军机大臣对修书的态度不一,曾抗争和限制乾隆帝的修书决策,如刘统勋反对扩大修书规模,于敏中则赞成,而和珅倒台的重要原因是四库馆臣普遍反对他,包括朱筠的密友洪亮吉;另一方面,军机处在修书的顶层设计和人事调配上起到直接作用,军机大臣可以影响皇帝的决定。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指出,十八世纪的军机处作为内廷机构,通过“法外活力”复制了外朝具备的行政、通信、档案、出版等功能,激励大臣对君主和政府施加影响,反而成为一个反对皇帝特权的组织。无论是乾隆帝对官僚的整饬、军机处对修书的影响还是学者嵌入官僚体系,都说明皇权并非所向无敌、一插到底。这注定皇权虽是合法性和权力的中心,但毕竟有限度。

多元化的十八世纪
如何看待十八世纪对清代政治和学术的影响?盖博坚认为乾隆晚期修四库、发起文字狱应当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变化来理解,涉及满汉关系、官僚党争、学术斗争、学者与政府关系等。他在全书中不断提醒读者:这是在十八世纪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作者认为《四库全书》反映了十八世纪的社会特征,如学者对采集、整理和校正古代文本的兴趣日益提高,经济蓬勃发展使贫穷学者可能找到赞助者进行相对专业化的研究,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逐渐融合,如不少汉学家和藏书家出身于江南富商阶层,社会财富和学术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在十八世纪,虽然社会相对安定,但各个阶层之间存在各种合作或冲突的可能性,关键在于朝廷和社会之间形成某种共同利益,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地方士绅与朝廷政府的合作。就《四库全书》得以顺利编纂来说,由于许多巡抚在其州府设立书局,成为沟通中央政府和地方藏书家的桥梁,而江南士绅多为藏书家,他们不仅提供书籍,也评估书籍,且不少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也在幕府中招揽不少学人,建立学府精舍,编纂书籍。就文字狱来说,十八世纪的士绅冲突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十八世纪这个复杂的、多中心的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也可能存在重叠之处。因为士绅的交流、官僚和朝廷利益的相互作用,这场运动发展了起来。”
另外,十八世纪满汉之间的分工合作也使《四库全书》顺利编纂,而官僚系统过度扩张则使乾隆帝明显对官僚阶层的迟滞感到不耐烦,促成了他通过图书审查来整顿官僚秩序。由此观之,即使是乾隆帝也是身在十八世纪这个巨大的权力网络之中。盖博坚指出:“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太大、太复杂、太多元化,以至无法由一人来主宰。这个时代的狂热和过激行为见证了这种复杂性……在十八世纪中国,帝国意志的执行也常常受到当时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
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十八世纪?
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盖博坚《皇帝的四库》的观点仍有可商榷之处,毕竟此书在资料使用和问题意识上受到八十年代的限制。盖氏此书出版后,中外学界又出现几部著作可弥补其不足,如黄爱平、吴哲夫在郭伯恭基础上相继出版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著作(1989、1990),Cary Y. Liu、Cheryl Boettcher Tarsala分别研究文渊阁建筑和《四库全书》作者的博士论文(1997、2001),司马朝军关于《四库全书总目》的两部著作(2004、2005)等,但盖氏出色的解释框架仍可启发当今学界对清代政治和思想进行多元化理解。通过此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深受乃师史华慈和师兄孔飞力的影响。
2010年,盖博坚出版专著《清代督抚及其行省》,体现出他对清代行政管理、政治精英和地方社会的深刻了解,反映出欧美学者关注“中央-地方”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最近,他又提出“新清史后的清史”(a post New Qing Qing History)的理念,提出要注重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当然,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中国学者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萧公权在探索地方社会和士绅上为国际学界提供了经典研究。但这启发我们在考察古代中国的任何问题时,都应注重权力网络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掩卷沉思之余,笔者认为,结合此书,我们还应进一步挖掘和反思两个问题。
第一,清修《四库全书》所体现的学者和政府的互动关系,在清修《明史》或其他官书的活动中是否也有体现?应该看到,清修《明史》的历程很漫长,从顺治绵延到乾隆,所关涉的问题也更多样和复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盖博坚的分析模式对清修《明史》反映的清代前期的政府与学者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从而理解十八世纪清修《四库全书》之前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盖博坚的观点提出质疑或补正?因为清修《明史》代表着清代已经确定了对自身合法性进行历史书写的权威解释,清廷自然不会允许再有独立于官方史学之外的另外解释,因此乾隆时期的文网日密也就水到渠成。而且,在修《四库全书》时,乾隆命阿桂先后修《清朝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又修《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和“清三通”,我们应注意到《四库全书》不是孤立的,它也是网中之网,和这些书共同指向的乾隆的满汉治理构想和十八世纪的时代诉求。
第二,回到作者一开头所言盖博坚提出的“知识分子之问”:清代中国存在一群反对国家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吗?全书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不断强调十八世纪最杰出的学者都自愿甚至热情地参与了《四库全书》项目,说明作者明显持怀疑态度。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肯定要从学理上批判性地理解这一观点。一方面,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与现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差异的,阎步克曾考察士大夫从儒到吏的演变过程,但士大夫仍有傲视政统的道统谱系、精神气质和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构建、走向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紧密相连,但它们的构建是否或能否在中国传统基础和现有条件上取得突破和超越?如果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存在一些认同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看待十八世纪的思想遗产呢?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