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旺读《伽达默尔传》︱哲学与生产它的哲学家

今天的人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翻开一本哲学家的传记?在一些有着不寻常性格或经历的哲学家那里,人们可能想从中读到一些奇闻轶事或八卦,以作为日常谈资,或给讲授哲学时的枯燥增加一点佐料。有的人可能想从传奇哲学家的人生历程中寻找某种典范人格,或获得某种感召自己的力量。又或者有人仅仅出于好奇,想知道孕育那些伟大思想的哲学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但如果人们都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读大部分哲学家的传记,那他们可能会大失所望,因为以此来看大部分传记都是乏味的。除了少数像马克思这样非正统书斋式的哲学家,大概不会有传记电影会选择哲学家作为传主,他们那惊心动魄的历险主要封闭在思想着的大脑里。在格朗丹为《伽达默尔传》所写的引言中,一开头就提到了海德格尔关于亚里士多德生平的著名评论:“关于哲学家个人,我们想要知道的仅限于他在某个时候出生,他劳作,然后他死去。”海德格尔的看法是颇具代表性的,它容易让人想到钱锺书有名的“母鸡论”:“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果你关心哲学家的思想,那么你应该去读哲学家的著作,何必去了解哲学家是怎样的人呢;如果你想从作为个体的哲学家那里学到什么,那你常常会发现不如去找其他更好的替代者,例如政治军事领域的英雄人物;如果你仅仅好奇是怎样的人物孕育了这种思想,那你可能很难逃脱钱锺书的讥讽。
有一种较弱的辩护,体现在许多不那么典型的传记作品中,他们自称为哲学家的“评传”或“学述”。人们读他们是为了帮助理解他的哲学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思想,你必须了解思想家的生平、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他是为了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才做出了这样的思考。更强的论断会说:你只有了解哲学家面临怎样的问题,想解决怎样的问题,你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你只有试着去理解哲学家这个有血有肉的人,你才能懂得他真正“想说”什么,才能理解他那些抽象而普遍的思考背后的真实意图。依此看法,哲学家和哲学就不是如钱锺书所说像鸡和鸡蛋那样可分离的。为了给自己从事的工作辩护,《伽达默尔传》作者格朗丹立刻对海德格尔的观点提出谨慎的异议:“一种思想的出现难道不是对那个时代之焦虑的一种回应吗?这种思想难道不是内在于每个特定时代下接受这样或那样教育的个体的经历之中吗?哲学的任务难道不是去思考生活本身,去理解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是如何在它们的时代中紧密交织的吗?”
不过,相比这种谨慎的异议,格朗丹随后引用的法国哲学家斯蓬维尔的话——它听起来有些武断和激进——可能更有益于两种立场之间的争辩。他说:“实际上没有什么哲学,只有哲学家。”这就是说,在哲学(蛋)和生产它的哲学家(鸡)之间,不仅有是否可分离的问题,还有优先性的问题:一个哲学家是因为他思考了哲学,所以才是哲学家呢,还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所以他所思考的东西才被称为哲学?这听起来像是柏拉图关于抽象的美和美的事物、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的现代翻版。倘若这样理解的话,结论就会是:只要我们不再赞同柏拉图式理念的优先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总是哲学家优先于哲学,哲学不过是对个体哲学家之生命和所思所想的一种抽象,一种事后的建构。

于是,哲学家的传记在此意义上就具有了更特别的价值,这种价值甚至隐隐地凌驾于一切哲学经典著作之上:一切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传记或学述;而一本好的哲学家传记,也总是哲学思想的呈现,而且是他更源初、更深不可测的呈现。按照德里达的看法,人们只有把握了哲学思想的传记特征,才能真正地进入这种思想。一本好的哲学传记,或对哲学思想的好的解读,应该无止境地向那作为自身性、专名、独一无二个体的哲学家还原,而不只是从中读出某种普遍的思想。这就如同人们去了解一个所爱的人,不应把他的品质、特征、话语、思想当做他的化身(这些东西别人也会有),而是在他和他所拥有或给出的东西之间不断往返,以寻找通达他本人、他的名字的道路。本雅明在《单行道》中说:“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其实,与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是在这种专名的意义上,德里达在《论生死》的研讨班中说:“传记在今天应该被重估,也正被彻底重估。今天,一个哲学家的传记不再能够作为经验的偶然被考量,也即将他的名字和签名放在提供给单纯内在哲学阅读的系统之外,借此人们可以在你们知道的装饰性和传统的风格下书写哲学家的生活,也不能够作为心理传记被考量,这个心理传记根据(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的)经验的机制来说明系统的起源。一般的传记,尤其是哲学家们的传记的新疑难需要调用不止一种新资源,而其中至少包括哲学家的专名和签名的新问题的资源。无论是(结构或非结构的)哲学体系的内在主义解读,还是哲学的(外部)经验—遗传学的解读,都绝不能如此探问这一在作品和生命、体系和体系之主体之间的动态边界。”
于是,哲学家的传记就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与哲学思想的解读一起构成了保持张力的两个端点,召唤我们不断往返,探索两者之间的动态边界。我们应该不断地从哲学家出发去理解哲学,又从哲学出发去理解哲学家,并且最终总是返回到哲学家本人那里:对哲学家的思想的正确解读,永远不是从中读出了某种可表述的观念,而是从中读出了深渊。
带着这种方式去看待哲学传记,那么我们可以说,格朗丹先生是伽达默尔传记的几乎难以替代的作者人选:一方面,他是当今解释学思想界为数不多的权威,对解释学,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有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本人与伽达默尔有深入交往,有着长时间共享的生命经验,这种生命经验是理解哲学家个体的卓越条件。这么说当然不是要回过头来依仗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义解释道路,这是很早伽达默尔就反对的,同时也是格朗丹本人所反对的。而是说,理解是两个个体之间生命经验的交锋,只有达到相似的生命经验高度的人,才能够展开真正的对话。

在格朗丹先生的笔下,这部长达五百页的传记所呈现的伽达默尔的思想道路/经验和生命道路/经验,正有着典型的相互呼应、相互阐释的循环关系。一方面,伽达默尔的思想总是谦逊而灵活地寻求倾听和理解,总是更愿意假设他人比自己更正确,总是抱着“理解的善良意志”去展开对话,并且相信在这种对话辩证法的展开中,我们能收获更丰富的生命经验。这种经历痛苦和否定而无限展开着的对生存的理解,就是解释学所追求的目标。为此,他总是反对科学理性的片面性和有限性,总是呼吁在解释学的精神下走向对话和团结。另一方面,伽达默尔本人的生命历程也有着相似的形象。他曾用自己年轻时学骑自行车的经验来描述自己选择的生命道路和思想道路:“我有一个孤独的童年,他们给了我一辆自行车让我支配,我只能独自学习骑车。在我的花园里有一座小山丘,我从上面往下骑。在失败几次以后,我有了一个重大的经验:只要我紧紧地攥住车把,我就总是摔倒。但当我放松时,它就会自己向前。直到今天,这个例子让我们明白了政治家也明白的事情以及构成其使命的东西:如果他想要能够领导和实现其目标的话,他必须创造平衡的局面。”在伽达默尔寻求职业前途时,在他面对纳粹的强大压力时,包括在他后来担任莱比锡大学校长期间,他的行为和选择总是尽可能地在不同力量、不同原则之间寻求平衡,如同他的解释学总是寻求在不同立场之间找到平衡。这种权衡取舍,伽达默尔将之阐释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
这种“实践智慧”和无原则的圆滑权变怎么区分呢?我们可能会有些遗憾地发现,在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伽达默尔从来都不是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甚至我们会发现,若单从道德上来评价,伽达默尔可以说是十分平庸的人物。他曾为了获得教职而向纳粹势力做某种圆滑的妥协,在可能的危险面前他总是缺乏抗争的勇气,甚至在私生活上,他对爱人也屡有懦弱背叛之举:和他的老师一样,他在有家室的情况下爱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学生。而在对方落入纳粹虎口时,他却没有试图营救,而是尽可能地切割关系以免引火上身。
如果我们联系前面谈的生命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不意味着我们在自相矛盾。一个伟大的思想不是意味着哲学家要有一个伟大的道德人格,至少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中是这样。对于中国思想来说,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思想一开始寻求的就是生命和道德的学问,而不是纯粹的探求真理。但在西方思想界,我们见过了太多太多的反例。雅斯贝尔斯曾经感叹过,他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伟大的海德格尔思想,会诞生于道德人格如此平庸的人物身上。但问题在于,这种“道德”的评价对于哲学家的生命而言可能并不是十分关键的衡量尺度。甚至我们会说,一个“伟大”的人格可能不必是一个崇高的“道德人格”。在这里,是否足够强有力、足够富有艺术性、足够独创和典范,可能才是更好的标准。我们这里并不是要走向尼采的立场,把道德的尺度看做是平庸而颓废的尺度。但我们应该承认,伟大的思想家有权力重新思考和界定道德的尺度,而不能仅仅被固有的道德尺度所评判。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像评鉴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去评鉴哲学家们:有充满缺陷的英雄,有富有魅力的恶棍,也有标准但却平庸的好人。我们可能不认同某些哲学家的一些做法,但却不得不钦佩他们强有力的生命力和独创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指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要创建一种堪称伟大的思想,必须要常人无可匹敌的心理能量的力度和持久度。
按照这种尺度,读完《伽达默尔传》的读者,也许会多少有些失望。因为客观而言,伽达默尔不是西方哲学史上那种第一流的天才。他不像尼采那样有强悍地冲破一切藩篱的彻底性,也不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有直指根底的迷人的偏执力量,甚至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开始曾认为他完全缺乏哲学的天赋,只是个平庸的学生,很长时间没搞明白什么是哲学。在生活和行为上,伽达默尔也基本没有摆脱学院教授的既定轨道。但可能恰恰是这一点,是《伽达默尔传》最让我受启发的地方:他的思想和生命都带有一种平凡的伟大、不典范的典范,因而昭示了一条“可学而至”的思想道路和生命道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读者而言,这可能更具有借鉴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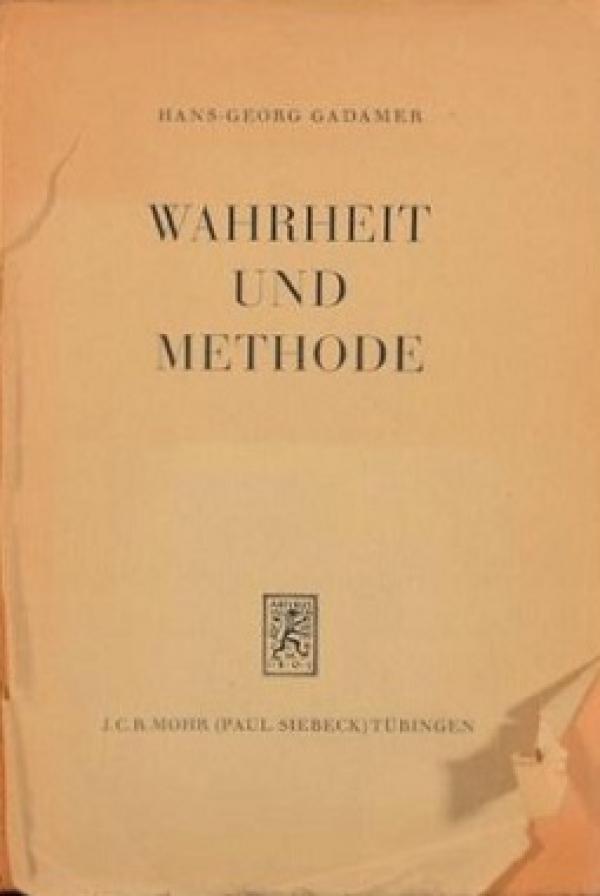
从生命道路上说,伽达默尔直到三十八岁才获得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正式教职——莱比锡大学的编外教授职位,他很长时间内成果发表都可以说乏善可陈,直到六十岁时,才撰写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并且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才逐渐收获缓慢的成功。从思想道路上说,他的解释学强调人文主义根基的浸润,强调长期积累、缓慢训练而养成的良好分寸感和趣味,强调静水流深的视域融合的解释学经验,这对于所有人文学科来说都是十分适用的,是这些学科的“反对方法的方法”。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天才式的洞见当然很重要,但长期积累所形成的视域更加可靠。对于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这可能都是唯一一条通向伟大的道路。坊间传言,王季思先生有半开玩笑的“治学秘诀”:“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从伽达默尔的角度看,可以有另一层意思:人文主义的传统中,重要的思想从来都离不开时间的缓慢积累。
今年是伽达默尔诞辰的一百二十周年,从以上角度看,我们今天翻开《伽达默尔传》,纪念这位百岁老人,无疑会是富有教益的,无论人们是想从中得到对解释学思想的更深理解,还是想从哲学家本人那里获得启发。解释学告诉我们,一切无非是存在论的解释学经验,活生生的生命经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让我们去听听这位富有智慧的老人的经验吧。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5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