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赵敦华:回到中世纪历史看到底什么是“人文主义”
中文的“文艺复兴”译自西文的Renascence(复兴),其实并无“文艺”之意,“文艺复兴”的中译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似乎这场复兴只局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如莎士比亚、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塞万提斯、拉伯雷等人的作品。但实际上,复兴时期是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复兴自13世纪开始,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神学相结合,把经院哲学推向了理性的高峰。人们由此看到了希腊哲学的魅力,但又缺乏全面了解希腊文化的途径。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关闭了它的高等学府。一批学者携带古希腊罗马典籍流亡意大利,流亡的希腊学者带来的是西方人渴望已久的文化宝藏,促成了文艺、语言学、科学、哲学和神学的繁荣。文化上出现了新旧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学与神学、古代哲学与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和复兴的其他古希腊哲学派别、个人主义与权威主义、批判精神与教条主义、理性与信仰、经验科学和自然哲学、科学与伪科学相互撞击与混淆,表现出从中世纪到近代文化过渡的特征。
“人文主义”兴起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指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科大致相当古罗马学校讲授的课程,以古典拉丁文为主,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与道德哲学。与中世纪“七艺”相比,人文学科省略了“四艺”与逻辑,增加了诗学、历史与道德哲学,它的培养目标是个人的表达能力和文化修养。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除少数几所意大利大学之外,仍从事以逻辑为基础的经院哲学与神学的教育。两类不同的教育是造成人文主义者与经院学者的思想和风格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人们常把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当作罗马教会的对立面,其实两者既有对立的方面,也有调和的方面。人文主义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而是用宗教的名义,把人的卓越上升到上帝般的崇高位置。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的题材大都取自《圣经》,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摩西》《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等,都是教堂的装潢。教皇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利奥十世等人都十分欣赏并赞助人文主义者创作古典艺术。天主教内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提出过宗教改革主张,但丁在《神曲》中谴责僧侣的腐败,把在世的教皇尼古拉三世打下地狱。爱拉斯谟宣扬的返回福音书和保罗神学的改革主张风靡一时。虽然罗马教会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教廷和教士阶层在思想上墨守成规,在生活上日益世俗化,沉溺于物质和艺术享受,大肆搜刮财富,发行欺骗信众的“赎罪券”。当不可能在罗马教会内部进行改革时,外部的改革便势在必行了。

人的尊严、自由和德性
第一位自称人文主义者的彼特拉克说他是第一个论述人类尊严的人,他说,其他人放弃了这一主题是因为论述人类悲惨更容易。他针对的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论人类悲惨的条件》中强调人是值得怜悯的悲惨动物。在此之后,人文主义以“人的尊严”“人的崇高”为题,而传统主义者则以“人的悲惨”为题,针锋相对地陈述各自观点。传统主义者囿于人对上帝的服从,把人说成是匍匐在上帝脚下的微不足道的生物,过着不能自主的悲惨生活,等待上帝拯救。人文主义者一般都不否认人与上帝的联系,但利用这一联系论证人与上帝相似、高踞万物、自主自由的尊严。比如,托麦达(Anselm Turmeda, 1352—1432?)在《驴的论辩》的寓言中设想人与驴争论谁更优越的问题。人最后找出的证据说服了驴:上帝肉身化的形象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德国的人文主义者阿格里帕(Agrippa, 1486—1535)说,人体的构造是一个小宇宙,他不但包含着组成地上的四种元素,还包含组成宇宙的第五种精神性的元素,人类的构造是天界与地界的缩影,人体的站立姿势使人不像其他动物只能盯着地面,他可以仰望苍天,因此能以上帝的精神世界为自己的归宿。
斐微斯(Juan Luis Vives, 1492—1540)在《人的寓言》中把世界比喻为造物主为人准备的一座舞台,人是可以扮演从最低等的植物到最高级的神灵的演员。造物主从人的本性中除去了固定的本质,人的行为决定了他的存在。他的实体包含着其他本质,具有高于物质和动物世界的能力,也高于自身的道德约束力以及高于公共生活的政治权力。人的最高价值是自由,即选择和造就他自己地位的力量,这是天神赋予人的礼物,人运用自由最后变成最高天神,达到了神的儿子与神一体的最高境界。通过这一方式,斐微斯在“三位一体”的神学信仰中注入了人文主义的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要从古代的人性论、德性论和幸福观中找到基督教的拯救。彼特拉克在《论自己与他人的无知》中说,“拯救却没有足够的认识”,要认识上帝,“这是真正的和最高的哲学”。彼特拉克说,他之所以推崇柏拉图、西塞罗、塞涅卡,因为他们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基督教。他认为柏拉图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最接近于上帝;他从塞涅卡那里了解到:“除了灵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对于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伟大的。”即使如此,他认为古代哲学不能代替基督宗教,当他“在思考和谈及最高真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灵魂拯救时,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瓦拉在《论真正的善》的对话中呈现出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和基督教三种伦理观的交锋。他总结说,斯多亚主义者为德性而德性,忘记了德性和上帝的联系,他们所谓的德性是虚假的,实际上是与最高的善相违背的恶。伊壁鸠鲁主义者为快乐而追求德性,正确地看到德性的实用目的,但他们否认灵魂不朽和来世报应,认为幸福只是现世可以获得的快乐。基督徒为了来世幸福而追求美德,天国的快乐才是真正的永恒的善;然而,现世快乐是心向来世所获得的正当体验。没有快乐,就没有希望和期待,则一事无成,恭顺而又毫无乐趣地侍奉上帝的人一无是处,因为上帝喜欢快乐的仆人。他是以宗教和信仰的名义反对经院哲学,反对神学与哲学结盟,指出哲学不应是神学的姐妹或庇护人,经院哲学对于宗教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它曾造成众多异端。
艺术家阿尔伯蒂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其他部分。他说,上帝创造人是为了让他的杰作被人所欣赏。人在自然界中的崇高地位在于自然赋予人的卓越本性,这些德性包括“理智、可教性、记忆和理性,这些神圣性质使人能进行研究,辨识、认识要避免的和可敬的东西,以使他以最好的方式保存自己。除了无价的可企羡的伟大礼物之外,上帝还给人的精神和心灵另外一种能力,这就是沉思。为了限制贪婪与无度,上帝给人谦和与荣誉的欲望。另外,上帝在人心之中建立了把人类联结在社会之中的坚固纽带,这就是正义、平等、自由和爱心”。
人文主义者借用人与上帝的关系论证人的崇高地位,他们并未完全脱离中世纪思想的前提。但另一方面,他们借用古代伦理学思想,肯定在中世纪被压抑或遗忘的幸福和价值。除了新近引进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的道德哲学,更多宣扬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世俗方面,强调健康、幸运、富有和物质利益是外在的实际存在的善,认为没有这些外在的善,内在的善也不会实现。人文主义者称颂的幸福是内在与外在的善、灵魂与肉体快乐的协调。
人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
人文主义者把批判矛头指向经院哲学,但更激进者进一步提出了用更符合人性的温和、开明政治代替宗教专制的主张。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是英国政治家,1529年起任大法官,因拒绝承认英王亨利八世有权领导教会而被处死。莫尔是人文主义者,他把一些希腊文的传记、诗歌、政治与宗教著作译为英文。他的代表作《乌托邦》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端。
莫尔的政治蓝图以道德理性为基础,他以人文主义的高尚的德性标准否认财产的道德价值。虽然他得出了其他人文主义者没有说出的废除私有制的结论,但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仍然是人文主义者的政治道德化的主张,这一主张直接承袭了基督教政治的传统,因此有人称莫尔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伸,正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表达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理想,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aivelli, 1469—1517)试图按照罗马人政治学说的标准塑造新型统治者。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律师家庭,自幼接受人文学科教育,青年时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1512年美第奇家族攫取政权后离开公职,因被怀疑参与反美第奇活动而遭软禁。在此期间,撰写《君主论》献给美第奇。获释后于1513—1519年写成《论李维的前十书》等著作。1527年共和国重新建立之后失去公职。

《君主论》鼓吹绝对君权,《论李维的前十书》论证共和制的必要性,两者看起来相互矛盾,其实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在当时的政治学著作中,君主制和共和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制度。《君主论》是献给君主的进谏,制定供统治者阅读的行动准则,特别注重统治者的品质和能力,而《论李维的前十书》是向大众发表的著作,主要论述各阶层应遵循的政治制度。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列举历史上和现实中成功君主的事迹,得到正反两面经验,当君主“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越来越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反之,“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他称赞当今的西班牙国王阿拉冈的费尔迪南多是“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因为他的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马基雅维利为君主制订的准则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非凡才智的声誉。”君主只要能够“征服并且保持这个国家”,“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
关于人民是群氓,马基雅维利用性恶论作了说明:“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面对这样的臣民,君主有理由不受道德的约束,他不可能避免残忍的名声,他的安全更多地在于被人畏惧,而不在于被人热爱,最有成就的君主都是不重信用的,如此等等,这些品质都是恶,但非如此便不能统治,这可以说是以恶治恶。
传统公认的正义、自由、宽厚、信仰、虔诚等美德,在马基雅维利眼里没有自身的价值,不是君主必须践履的原则,对君主行为没有道德约束力。他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与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如果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身毁灭。”
马基雅维利还教导君主:“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另一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属于人类特有的,而第二种方法是属于野兽的。”既然人类都是“冒牌货”的群氓,君主要以“半人半兽的怪物为师”。在运用野兽的方法时“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君主的艺术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当狐狸,什么时候当狮子,特别是要“深知这样做狐狸”,那就是,“君主必须深知这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人们是那样地单纯,并且那样地受着当前的需要所支配,因此要进行欺骗的人总可以找到某些上当受骗的人们”。
《君主论》赤裸裸地鼓吹武力征服、欺骗、作恶,即使在黑暗时代也难以成功,更不要说在民渐开、法制成熟的中世纪晚期了,把马基雅维利看作第一个近代政治哲学家是荒谬的。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有现实主义因素的话,那可以在《论李维》中看到。马基雅维利用肯定的态度谈论人性。他说:
从天性上说,人即使有能力获得一切,也有这样的欲望,可是命运却让他们所得无几。这会使人的头脑中不断产生不满,对已有的东西产生厌恶。
无论是对不安于现状的追求还是对一切限制的憎恨,都是人类的自由天性。以历史变化的眼光看待人性,马基雅维利赞扬古代人自由的德行。他说:
了解古代王国的人都知道,由于风俗的差异,它们的善恶有多有少,可是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唯一的不同是,上天先是把德行放在亚述,又放在米底,然后放在波斯,最后是意大利和罗马。虽然在罗马帝国之后,再没有出现一个把世界的德行集于一身的帝国,然而德行却被分散于众多的民族,让他们过着有德行的生活。
马基雅维利唯独不把基督教道德列入德行。他说:
我们的信仰不同于古人。我们的信仰,指明了真理和真理之道,使我们不看重现世的荣耀,而异教徒却对它极为推崇,把它视为至善……除了现世荣耀等身者,例如军队的将帅和共和国的君主,古代的信仰从不美化其他人。我们的信仰所推崇的,却是卑恭好思之徒,而不是实干家,它把谦卑矜持、沉思冥想之人视为圣贤……这种教养,这些荒谬的解释,使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
自由”(libertas)在古罗马共和国的维护者西塞罗、萨路斯特(Sallust)和李维(Levi)等人著作中的主要含义指免受外族奴役以及公民的利益互不冲突。马基雅维利憧憬古罗马共和国的光荣,看到罗马的伟大在于共和制度。他说:
精明的人创立共和国,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自由构筑一道屏障,自由生活方式存续之短长,端赖此屏障之优劣。
罗马共和制建立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制度,“由于三种统治形态各得其所,此后共和国的国体更加稳固”,“在这一混合体制下,它创建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后来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根源是平民和元老院的内讧,演变为皇帝专制的帝国。马基雅维利一反《君主论》中关于君贵民轻的议论,证明人民“并不比君主更加忘恩负义。说到做事的精明和持之有恒,我以为人民比君主更精明、更稳健、判断力更出色。人民的声音能比作上帝的声音”。
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人都在传统意义上肯定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而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共和制度得到政治自由的思想,并把各派力量的均衡作为政治自由的保障。
必须承认,近代政治哲学对自由的理解更接近马基雅维利。但不能因此夸大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现代性,他在否认和忽视基督教信仰的条件下谈罗马共和制度是不现实的,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否应算作自欺之人,因为我在自己这些文字中,也对古罗马时代大加赞美,谴责我们的时代。”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是超前的空想,那么马基雅维利憧憬的古罗马就是复古的妄想。

中世纪晚期失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教会由于自身腐败和神学的分裂而失去大一统的权威。教会内部的改革派要求用宗教会议的集体领导代替教皇个人独裁。1409年比萨主教会议宣布:“教皇也是人,因此,他也会犯罪,犯错误”;“教皇必须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主教会议……否则主教会议有权废黜他”。宗教会议运动在1417年召开的康斯坦茨会议上达到高潮。但是,教皇否认会议决议,发表禁止主教会议上提出反对教皇的公告。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在英国和约翰·胡斯(John Huss)在波希米亚发动的反对腐败和教皇独裁的群众运动遭到镇压,胡斯甚至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天主教内部要求制度改革的呼声被扑灭之后,人文主义者运用古代思想资源发出了攻击经院哲学的思想改革呼声。德西代·爱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是天主教内部这一改革思潮的代表。他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天主教徒家庭,少年时代在天主教会内有革新精神的共同生活兄弟会中受教育。1487年成为奥古斯丁会教士,1492年被任命为神父,后来在巴黎、牛津、卢汶等地学习,先后在剑桥、卢汶、巴塞尔和弗莱堡大学任教。

爱拉斯谟的《基督教士兵手册》是为一个担心“陷入宗教迷信”和“信仰犹太教那样的畏的宗教;而不是爱的宗教”的士兵而写的;爱拉斯谟说明了基督教的本质有两条:一是以《圣经》的知识为武器与生活中的罪恶作无休止的斗争,二是关注内心对上帝和邻居的爱,而不是外在的崇拜活动。为了获得《圣经》的知识,必须热忱地研究上帝的道,熟悉保罗的教导。他认为异教徒,如柏拉图主义者、斯多亚派“通常是优秀的道德教师”。而古代思想的主要注释者是早期教父如奥立金、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爱拉斯谟明确反对经院学者和僧侣,说他们纠缠《圣经》文字而忘了精神,依赖邓·司各脱却不读《圣经》原著,在学术上沉溺于文字而不关注精神实质,与在行动上装作虔诚却不关心他人的人同样不正当。他斥责那些伪君子:“你的兄弟需要帮助;这时你却喃喃地向上帝作祷告,装作看不见你的兄弟的需要。”他还说:
你一夜输尽千金时,一些贫穷的女孩为了生活需要出卖肉体,失去了灵魂。你说,“这与我有何相关?我只想与我相关的事”。你能不能看到,像你这样想的基督徒还能算作人吗?
爱拉斯谟在《圣经》希腊文拉丁文对照本的前言中自称他的思想是把学问与心灵融合一体的“基督的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这是两个与经院哲学相对立的概念。他说:
在这种哲学中,心灵的意向比三段式推理更为真实,生活不仅仅是争论;激励比解说更加可取;转变是比理智思索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有学问的,但一切人都能成为基督徒,一切人都能是虔诚者,我斗胆说,一切人都能成为神学家。
爱拉斯谟的理想是用“基督的哲学”改造神学,按保罗的主张改造教会,更重要的是除去人性中虚浮矫揉的一面,恢复简单、质朴的自然本性。福音书的素朴信仰胜过繁琐的说教和仪式。他在《谈话集》中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海难事故之中,船上的人惊慌失措,乞求圣徒保佑,许诺报答的誓言。只有一个母亲保持平静和尊严,怀抱着孩子,默默地祈祷,最后只有她得救。他相信符合自然本性的基督教信仰与一切圣贤发现的真理是相通的,反对宗教狂热和专制主义,主张通过教育而不用强制手段改变人的不良生活。他赞赏苏格拉底娓娓动人的劝导,更推崇他视死如归的气概;他的名言“圣苏格拉底为我们祈祷”是一个基督徒对异教徒道德的最高评价。
爱拉斯谟宣扬的返回福音书的改革主张和新教改革纲领有一致之处,却不是罗马教廷的主导思想。爱拉斯谟温和的人文主义与路德激进的信仰主义差距甚大。我们将看到,这一差别酿成了他们之间的激烈论战。人文主义者的这些改革主张既没有被罗马教廷所采纳,还遭到新教改革派的反对,但它们对宗教改革运动的进程以及后世的启蒙精神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古典学和《圣经》考察
早期人文主义者一般不关心自然研究,彼特拉克的一段话有代表性。他说,自然之物“即使是真实的,对幸福生活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了解动物、鱼类和蛇类的本性,却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的起源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后期一些人文主义者热心于自然哲学,但过于思辨和奇巧,落后于同时代新兴的自然科学。但不能说,人文主义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可以说,他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或艺术创作具有严谨探索和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现在的古典学主要讨论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文学(philology),基本不触及宗教信仰问题。这门学科在诞生时却是一门专门针对中世纪“学问”(doctrine)的精细的艺术(art)。关于古典学的科学性,19世纪的尼采深有体会。他评价说,语文学训练是一种长期养成的科学习惯,文科中学的任务是“教你严格的思考,谨慎的判断以及前后一致的推断”,“只有当正确阅读的艺术,即语文学,得到最新的发展的时候,所有科学才能赢得连续性和恒久性”。
古典学创始人都有批判志趣和改革主张。瓦拉用文字考证与解释学的方法,首先证明8世纪以来一直作为教皇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的历史文件《君士坦丁馈赠》是伪件。
古典学公认的创建者爱拉斯谟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希腊文拉丁文对照的《新约全本》(Novum Testamentum omne)。原来他只想用当时流利的拉丁文重新翻译《圣经》,但后来发现替代中世纪流行的通俗(Vulgate,武甘大)拉丁文《圣经》的最佳途径是用希腊文《圣经》勘定后者的错误。他的工作奠定了他作为古典学创始人的地位。爱拉斯谟新编和新译的《新约》和《康普顿斯〈圣经〉》全本都得到教皇利奥十世的批准,爱拉斯谟并把他的新编本献给教皇。始料未及的是,宗教改革中流行的《圣经》新译本却成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激烈冲突的根源,故有“爱拉斯谟下蛋,路德孵鸡”之说。但这不是爱拉斯谟的本意。
《圣经》批评有一个从“低阶批评”(lower criticism)到“高阶批评”(higher criticism)的过程,但两者密不可分。文字考证必然导致对《圣经》意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约翰短句”(Comma Johanneum)。和合本及大多数现代版本《圣经》的《新约·约翰一书》5:6—8记作:“这藉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但中世纪流传的通俗本5:7—8却有这样的短句:“天上记着的有三样:父,道和圣灵,这三样是一。在地上作见证的也是三样。”(英王钦定本记作:“For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record in heaven,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Ghost: and these three are one. And there are three that bear witness in earth, the Spirit, and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and these three agree in one.”)这段话被认作三位一体的明显证据。但爱拉斯谟发现当时所有希腊文《新约》中没有中间这一段,因而在新本的第一、第二版排除了这一段,但第三版以后的版本以一个新近的希腊文本为根据恢复了这个短句。现在发现,这个短句不见于早期的希腊文版本和最早的拉丁通俗本,很多人相信,有短句的那个希腊版本很可能是1520年的产物,短句是依据5世纪流行的拉丁通俗本页边的一个注释倒译过来的。罗马教会于1927年承认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释经问题。
在宗教改革之中,《圣经》低阶批评走向高阶批评。“低阶批评”是对《圣经》文字的勘定、版本的比较和文本的翻译。新教翻译和使用的《圣经》首先引起了与天主教的版本之争,新教使用的版本只承认《旧约》39卷为正典,而把拉丁通俗本《旧约》46卷中另外7卷和《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中的附录和一首赞歌当作外经。罗马教廷在宗教改革进程中首先阐明关于《圣经》正典和教廷传经的教义。1546年4月,第四次特伦托主教会议颁布关于《圣经》正典的敕令,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凡不接受正典的全部之书包含在“老的武甘大本之中,以及主观故意蔑视此后传统者”,“让他被诅咒”(即革除教籍)。这个规定以武甘大本作为标准,确定正典的卷目,以及“此后传统”即天主教会传经传统的权威。而新教不但否认教皇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威,而且不承认罗马教廷传经传统的权威。加尔文后来在《基督教要义》中更明确地说:“认为评判《圣经》的大权是在于教会,因此确定《圣经》的内容也以教会的旨意,这乃是非常错误的观念。”17世纪近代政治哲学奠基者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在他们的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解释《圣经》,他们一方面借助低阶批评的语文学考证,另一方面受当时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影响,从而把《圣经》解释转化为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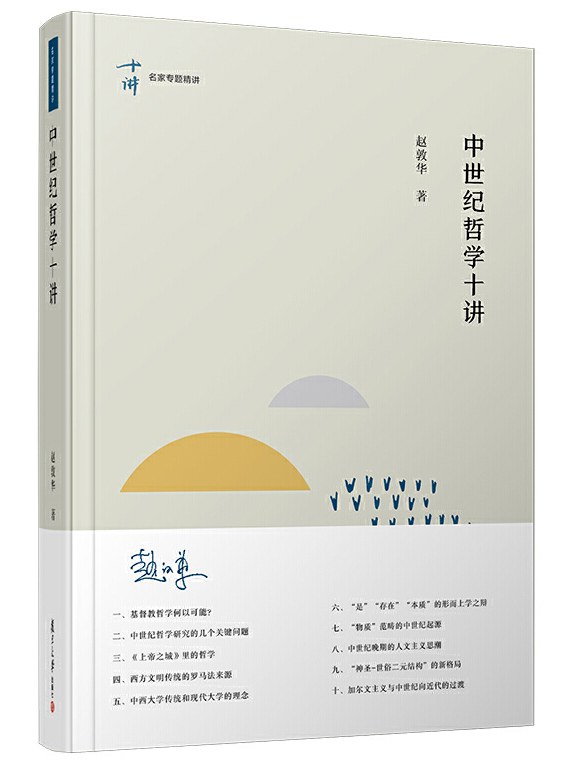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